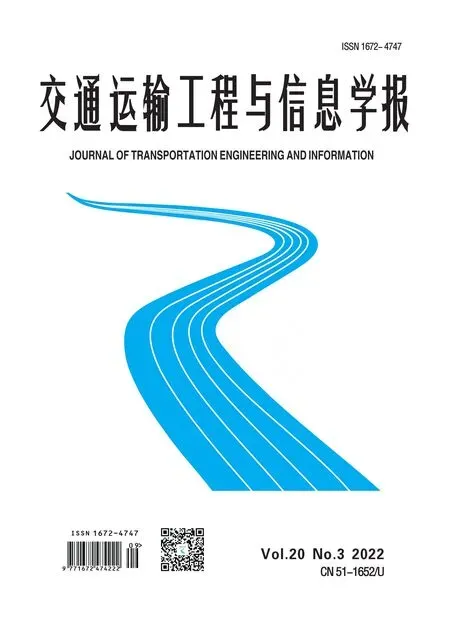考慮排隊長度的信號交叉口生態駕駛軌跡優化
黃意然,宋國華,彭 飛,黃健暢,張澤禹
(北京交通大學,交通運輸學院,北京 100044)
0 引 言
信號交叉口是交通路網的關鍵節點[1],其交通擁堵和機動車排放是城市交通環境改善的重要環節[2]。由于前方未知的信號配時和排隊信息,接近交叉口處的駕駛員往往難以確定何時加速或減速,產生過多的啟停行為和激進的加減速[3],且由于信號配時影響,交叉口處排隊等待通行的車輛不斷累積會造成交通擁堵,增加車輛怠速時間,這些行為導致了額外的能耗和排放[4]。不同于已有研究[5]直接優化交叉口信號配時可能會犧牲低等級道路的通行能力,基于V2I(Vehicle-to-Infrastructure)技術的生態駕駛(Eco-driving)策略可以改變駕駛員的不良駕駛行為,避免急加速、急減速或者長時間怠速等[6],從而優化車輛軌跡,有效改善以上問題。目前百度導航軟件在部分城市最新上線了“紅綠燈倒計時”功能[7],通過顯示剩余變燈秒數避免駕駛員的緊急剎車行為,該設計為考慮信號的交叉口生態駕駛軌跡優化提供了強有力的現實支撐。同時,研究到達信號交叉口的車輛及時跟上前方車隊并快速通過交叉口,可以預防交叉口排隊溢出,提高路網通行效率。因此,考慮排隊長度的生態駕駛軌跡優化對于緩解信號交叉口擁堵和減少能耗與排放,進而構建城市低碳交通具有重要意義。
目前,信號交叉口生態駕駛策略研究[8-13]大多基于V2I 技術提前獲取信號相位和配時(Signal Phase and Timing,SPaT)信息,在構建不同信號相位的場景下為車輛提供通過交叉口的生態駕駛軌跡,以減少能耗和排放,并利用數值仿真評價了生態駕駛策略的效果。除數值仿真外,已有研究還通過仿真模擬器或車內交互設備實驗,評價生態駕駛建議對改善駕駛員行為的效果,這些建議包括不同相位下的加減速選擇推薦[14],通過交叉口的推薦速度和釋放加速踏板[10,15]等。上述研究都基于理想的交通條件下優化單個車輛的駕駛軌跡,即忽略了車輛之間的相互作用和限制,為考慮實際交叉口排隊的駕駛環境,更多學者在上述研究基礎上基于前方排隊信息提出生態駕駛策略。這些研究主要分為兩類:(1)通過機器學習和最優控制理論等智能算法求解生態駕駛軌跡優化模型,生成速度建議曲線,比如利用Q-learning[16-17]和策略梯度[17]的強化學習算法、動態規劃算法(Dynamic Programming,DP)[18]、模型預測控制算法(Model Predictive Control,MPC)[19]、非線性內點法[20]、偽譜法(正交配置法)[21]、龐特里亞金最小值[22]等,不同程度上減少了能耗和排放。(2)設置更為簡單明了的駕駛車速建議,通過制定一定行駛規則引導后車采用生態駕駛行為的方式到達信號交叉口,一方面基于完全網聯環境下考慮排隊延誤時間[23]改善已有生態到達算法[9];另一方面設置減速通過信號交叉口的規則[24-25]或目標車輛固定初始速度的仿真情景構建目標車輛的速度曲線[26-29],都有效地實現了排隊情景下的信號交叉口生態駕駛。
針對單車的生態駕駛軌跡優化研究無法響應實際信號交叉口處存在的排隊現象,所以更多研究通過考慮排隊信息的影響來優化目標車輛到達交叉口的軌跡,以完善實際信號交叉口場景刻畫。但是,這些研究還存在一定不足:(1)采用機器學習和最優控制理論等智能算法,實時計算效率不高。面臨不斷變化的交通流狀態可能存在需要更長時間提前訓練模型(如強化學習)、計算量大而效率低(如DP 算法)、數據不穩定(如內點法、偽譜法)和結果依賴于初值猜測(如龐特里亞金最小值)等缺點,降低了生態駕駛軌跡優化模型這一即時策略的實時應用性。(2)駕駛建議操作復雜,人工駕駛車輛難以實現。據美國聯邦高速公路管理局的調查研究[30],未來道路交通將長期處于人工駕駛車輛(Human-driven Vehicle,HV)和網聯自動駕駛車輛(Connected and Automated Vehicle,CAV)并存的混合交通流狀態,而基于魯棒性低的算法(如MPC)或者完全網聯環境下的生態駕駛策略會降低人工駕駛車輛駕駛員的可操作性,近期的現實意義較低。(3)車輛到達信號交叉口的場景設置和仿真情景還有待完善。已有研究設置了簡明的駕駛規則,但是缺乏考慮不同信號相位和排隊長度的情景,難以反映前后車輛速度、間距等場景特征的變化情況對目標車輛排放的影響,此外,較多研究設定車輛減速通過交叉口的規則可能會犧牲交叉口通行能力。
因此,本文構建考慮不同排隊長度的信號交叉口場景,嘗試為到達交叉口的車輛提供簡單易于操作且具有一定駕駛員操作容錯性的“單次踏板”生態駕駛行為。擬將行為分類識別為不同模式以適應場景特征的變化,并構建相應的數學模型,通過數值仿真并結合基于比功率分布的交通排放模型測算目標車輛CO2排放,進而評價模型生態效果。
1 信號交叉口場景構建
本文考慮排隊長度構建的單車道信號交叉口場景如圖1所示。此時,由若干輛普通車組成的車隊(藍色車輛)正在或準備排隊離開交叉口,車隊尾車(前車)后方有一輛可以接收V2I通信的車輛(后車,紅色車輛)正靠近交叉口。軌跡優化的目標車輛為后車,范圍為后車從駛入交叉口上游至到達交叉口的過程,主要影響參數為前后車初始速度和初始間距,當初始間距中包含其他車輛時,在獲取后車前方最近一輛車的信息下,仍可以簡化為以上場景。基于V2I 技術后車可以獲取交叉口信號配時和排隊信息并接受駕駛建議,其中基于激光雷達、雙目攝像機等車載傳感器設備可以獲取前車速度、位置等信息,不考慮換道行為和其他交叉口的影響,忽略坡度對車輛影響,所有車型一致。

圖1 信號交叉口場景Fig.1 Signal intersection scene
根據信號配時和排隊信息,該交叉口場景分為兩類:
(1)綠燈場景:當前信號為綠燈,后車逐漸靠近交叉口而前方車隊正在離開交叉口。為實現生態駕駛,該場景的理想狀態為在剩余綠燈時間內交叉口上游排隊可以完全消散,且后車以更加生態的駕駛行為行駛到達交叉口。
(2)紅燈場景:當前信號為紅燈且即將結束,后車逐漸靠近交叉口而前方車隊正在上游等待且準備離開交叉口;當信號轉為綠燈時,車隊開始啟動并離開交叉口,情況與綠燈場景一致。為實現生態駕駛,該場景的理想狀態為在紅燈時間內后車以更加生態的駕駛行為行駛且不受車隊狀態影響。
2 生態駕駛行為模型構建
2.1 “單次踏板”生態駕駛行為
與推薦速度的駕駛建議相比,駕駛員更容易服從簡單地松開踏板的駕駛建議[31],而當駕駛員直接松開踏板進行車輛滑行時,可以利用車輛自身阻力進行緩慢減速,減少車輛駕駛軌跡波動[32],增加了駕駛安全性,而且降低了油耗和排放[32-34]。因此本文利用車輛滑行,提出了“單次踏板”的生態駕駛行為,該行為旨在減少后車踩加速踏板或制動踏板的次數來降低速度曲線的反復波動,且使后車盡快跟上前方車隊通過交叉口,以緩解交叉口擁堵。該生態行為的基本原則具體如下:
(1)僅踩過一次踏板,后車就可以加入前方車隊,然后一起通過交叉口;
(2)在踩下踏板達到一定速度后,后車釋放踏板開始滑行,直至加入前方車隊;
(3)后車需要在紅燈結束后加入前方車隊,并在綠燈結束前到達交叉口。
基于圖1 中不同的場景參數(前車初始速度、后車初始速度、兩車初始間距),將后車的駕駛行為識別為三種模式:(1)加速-滑行:先加速再滑行;(2)減速-滑行:先減速再滑行;(3)勻速-滑行:保持勻速再滑行。根據基本原則,“單次踏板”生態駕駛行為控制流程如圖2所示,首先獲取信號配時、排隊信息和后車信息進行交叉口場景判別;然后對后車行為分類識別為加速-滑行、減速-滑行和勻速-滑行三類模式,提出生態駕駛軌跡的優化算法;最終后車按照識別的模式實施生態駕駛行為以執行優化算法。

圖2“單次踏板”生態駕駛行為控制流程圖Fig.2 Flow chart of“single pedal”eco-driving behavior
2.2 生態駕駛行為建模
根據行為控制流程將圖1 的場景分為三個階段:(1)初始階段;(2)滑行階段;(3)加入車隊階段,如圖3 所示,并對各階段進行數學建模。表1為模型所用各參數說明。

表1 相關參數說明Tab.1 Parameter description

圖3 生態駕駛行為模型構建分階段示意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eco-driving behavior model
2.2.1 初始階段
初始時刻t=0,前車以初始速度vA0跟隨車隊,后車以初始速度vB0進入交叉口上游,前后車初始間距為d0。獲取當前信號配時和排隊信息將生態駕駛行為分類識別為加速-滑行、減速-滑行和勻速-滑行三種模式,駕駛情況分別為加速、減速和勻速,然后為后車提供相應的在[amin,amax]范圍內的初始階段加速度aB0。當t=ta-τB時,后車得到“釋放踏板”的駕駛建議,并將在τB后做出反應。
2.2.2 滑行階段
當t=ta時,根據生態駕駛行為的第二條基本原則,后車釋放加速或制動踏板然后開始滑行,此時后車速度應小于最大速度,假定最大速度即為期望速度vm。駕駛員在滑行時完全松開踏板,車輛引擎供油被切斷以緩慢減速,由于規定禁止空擋滑行,本文指的是帶擋滑行。不考慮道路坡度,移動中的后車的總牽引力為[35]:

式中:FB是總牽引力(N);A是輪胎和附件負載的滾動阻力以及來自剎車片和車輪軸承的阻力(N);B為動摩擦系數(N·s/m);C為空氣阻力阻滯系數(N·s2/m2);M為車輛實際質量(kg);δ為質量修正參數,取常數1.04[35]。
當自動擋車輛帶擋滑行時發動機的牽引力接近于零,效果與空擋滑行相近。為簡化處理,假定當后車滑行時牽引力F為零,得到滑行時車輛加速度和速度的關系:

當t=tj-τB時,后車得到“加入車隊”的駕駛建議,并將在τB后做出反應。
2.2.3 加入車隊階段
當t=tj時,后車正好加入車隊。根據生態駕駛行為的第三條基本原則,后車應在紅燈結束后且到達交叉口前加入車隊,即tj應大于剩余紅燈時間tr,后車位移xB小于交叉口上游長度du。此時前車和后車的位移分別為:

考慮到Newell 模型[36]參數易于標定,計算效率高,且能夠很好地反映車輛油耗和排放[37]等優點,本文采用Newell 模型描述車輛之間的跟馳行為。根據Newell模型中車頭間距和速度的線性關系[36]得到此時位移差Δd應滿足:

當t=te時,后車到達交叉口,根據生態駕駛行為的第三條基本原則,整個過程的行程時間te應小于剩余綠燈時間tg。
根據數學模型,加速-滑行、減速-滑行和勻速-滑行模式的軌跡示意如圖4 所示,藍色虛線表示前車軌跡,紅色實線表示后車軌跡。

圖4 加速-滑行、減速-滑行和勻速-滑行模式的軌跡示意Fig.4 Trajectory diagrams of accelerate-coast,decelerate-coast and keep-coast
3 仿真實驗及生態效果評價
3.1 模型參數標定
本文基于數值仿真評價“單次踏板”行為的生態效果,以剩余綠燈時間tg為60 s和交叉口上游長度du為300 m 的場景為例,設置不同的場景參數:(1)前車初始速度為vA0;(2)后車初始速度為vB0;(3)初始間距為d0,同時在區間[amin,amax]內以0.02 m/s2為間隔劃分初始階段的加速度aB0,進而刻畫不同情景下的前后車時空軌跡。基于采集的北京市823輛輕型客車共800萬條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逐秒軌跡數據,構建了加速度-速度特征庫,擬合得到的最大加速度-速度關系作為后車最大加速度amax的取值。同時提取出700 個交叉口軌跡數據并擬合出一條典型排隊通過交叉口的軌跡作為前車仿真軌跡。最小加速度amin[12]為-3 m/s2,期望速度vm為60 km/h。反應時間τB為1 s,最小安全距離δB為7.26 m[38]。車型為Ford Explorer,滑 行 模 型 參 數 取 值[35]:A=181.4 N,B=2.42 N·s/m,C=0.62 N·s2/m2,M=2 190.85 kg。仿真實驗步長Δt為0.1 s以保證更精確的軌跡刻畫和排放測算,假定當后車加入車隊時前后車速度差Δv無限逼近于0.5 m/s。
選取基于比功率(specific power,VSP)分布的交通排放模型測算CO2。在不考慮道路坡度且后車為輕型車的條件下,基于加速度和速度可以得到后車VSP的計算公式[39]:

根據Frey 等[39]的VSP 聚類方法,本文根據實際數據情況以1kW/t 為間隔將VSP 聚類在區間[-20 W/t,20 W/t]上[40]。CO2排放量等于該VSPBin區間中的平均排放率乘以排放時間,總CO2排放量為每個VSP Bin區間的CO2排放量加和:

式中:ECO2為后車CO2的總排放量(g);p為VSP Bin 區間的總數;Erj是CO2在VSP Bin 區間j中的平均排放率(g/s),由實際道路輕型車排放率數據采集處理得到,如表3 所示。VSP Bin 區間大于0時,隨著區間升高CO2平均排放率呈上升趨勢。

表3 各VSP Bin區間的CO2平均排放率Tab.3 Average CO2 emission rates of VSP Bins
3.2 最優駕駛計劃
基于數值仿真結果得到在前后車初始速度和初始間距的場景參數變化情景下,后車在初始階段采用不同加速度時的CO2排放,本文定義后車CO2排放最低的加速度方案對應的行駛軌跡為最優駕駛計劃。三類模式的最優駕駛計劃的CO2排放與場景特征的關系如圖5 至圖7 所示,各模式下不適用的信號交叉口場景未在圖中列出。

圖5 加速-滑行模式下最優駕駛計劃的CO2排放與場景特征的關系Fig.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2 emissions and scen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ptimal driving plan in accelerate-coast

圖7 勻速-滑行模式下最優駕駛計劃的CO2排放與場景特征的關系Fig.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2 emissions and scen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ptimal driving plan in keep-coast
(1)初始間距及前車初始速度固定時,后車初始速度越低,最優駕駛計劃的CO2排放越高。較低初始速度意味著后車需要更高的加速度或者更長的加速時間以盡快加入前方車隊,以上行為會導致更高的比功率區間和CO2排放。
(2)前后車初始速度固定時,不同模式下初始間距與最優駕駛計劃的CO2排放關系存在差異。對于加速-滑行和勻速-滑行模式,初始間距與最優駕駛計劃的CO2排放呈負相關,在這兩類模式下后車可以更快松開踏板進入滑行階段,增加滑行時間以減少CO2排放;而對于減速-滑行模式,隨著初始間距增加,最優駕駛計劃的CO2排放先降低后增加,當初始間距較大時,后車減速較為緩慢以保證可以及時且安全加入前方車隊,增加了制動時間和CO2排放。
(3)在相同的場景初始條件下,加速-滑行模式的最優駕駛計劃帶來的CO2排放最低。與減速-滑行和勻速-滑行模式相比,采用加速-滑行模式后車可以分別平均減少16.4%和9.02%的CO2排放。這是因為采用加速-滑行模式時,后車在初始階段會提速以便更快進入CO2排放較低的滑行階段。
3.3 駕駛員操作容錯性分析
實際駕駛中,駕駛員難以完全遵從駕駛建議的加速度,因此設置研究可接受加速度區間為[aB0-0.5,aB0+0.5]m/s2以分析場景參數對最優駕駛計劃的駕駛員操作容錯性的影響。面向CO2排放值定義駕駛員操作容錯性ω為可接受加速度區間內最高CO2排放高于最優駕駛計劃的CO2排放的比例,如下式所示:

式中:Emax為可接受加速度區間內的最高CO2排放;Emin為最優駕駛計劃的CO2排放。ω越低,說明可接受加速度區間內的各加速度方案與最優駕駛計劃的CO2排放相差越小,駕駛員操作容錯性越高,即駕駛員更容易遵循該駕駛行為以達到生態駕駛。實際應用時,可限定ω范圍以確保一定的駕駛員操作容錯性。
選取前車初始速度0 km/h 和后車初始速度20 km/h 的加速-滑行模式,前車初始速度0 km/h和后車初始速度40 km/h 的減速-滑行模式,以更細粒度2 m為間隔劃分初始間距,得到兩類模式下初始階段加速度、初始間距和CO2排放的關系如圖8(a)和圖9(a)所示。初始間距固定時,CO2排放與初始階段加速度呈正相關;初始階段加速度固定時,CO2排放與初始間距呈負相關。

圖8 加速-滑行模式Fig.8 Accelerate-coast
在圖8(a)和圖9(a)情景下,圖8(b)和圖9(b)反映了初始間距為60 m 時CO2排放和初始階段加速度的關系。計算得到圖8(b)中最優駕駛計劃對應的初始階段加速度為0.25 m/s2,CO2排放為35.76 g,結合加速度可行解得到可接受加速度區間為[0.23 m/s2,0.75 m/s2],該區間內CO2排放最高為38.36 g,根據公式(11)得到該情景下的駕駛員容錯性為7.27%。同時得到不同初始間距下的駕駛員操作容錯性變化情況(見圖10),均不高于17%,說明最優駕駛計劃具有一定的駕駛員操作容錯性。整體上減速-滑行模式的駕駛員操作容錯性稍低于加速-滑行模式,加速-滑行和減速-滑行模式的駕駛員操作容錯性平均值分別為9.96%和13.36%;初始間距較低時,加速-滑行和減速-滑行模式分別保持在最高和最低水平,隨著初始間距增加最后處于平均值附近浮動。

圖9 減速-滑行模式Fig.9 Decelerate-coast

圖10 不同初始間距下的駕駛員操作容錯性變化情況Fig.10 Fault tolerance of the driver's operation under different initial spacing
3.4 模型生態效果評價
為評價最優駕駛計劃的生態效果,本文模擬了常規駕駛計劃的駕駛軌跡,即在駕駛員不知道前方信號和排隊信息情況下的一般駕駛軌跡:當與前車間距較大時,駕駛員會以舒適加速度逐漸加速到期望速度,加速度隨速度增加而減小;當與前車間距不足時,駕駛員難以預估準確間距進而產生反復的加減速,導致波動的速度曲線。基于加速度-速度特征庫(3.1 節),研究通過蒙特卡洛(Monte Carlo)方法隨機抽取當前速度對應的加速度,形成常規駕駛計劃軌跡,并計算軌跡逐秒CO2排放數據構建排放清單,重復實驗50 次取均值再與最優駕駛計劃進行對比。
圖11 和圖12 分別為圖8(b)和圖9(b)的情景下采用兩種計劃時前車與后車的軌跡時空圖,采用最優駕駛計劃時后車的駕駛軌跡明顯比常規駕駛計劃平滑,且后車可以更快跟上前方車隊。本文以后車從駛入交叉口上游至到達交叉口這一過程的行程時間和CO2排放為指標評價最優駕駛計劃的生態效果,不同間距下評價指標對比情況如表4所示。與常規駕駛計劃相比,在加速-滑行和減速-滑行模式下后車分別可以減少平均3.9%和2.3%的行程時間,以及平均24.2%和39.0%的CO2排放。除減速-滑行模式的行程時間外,隨著初始間距增加,最優駕駛計劃的優化效果更加明顯。因此,“單次踏板”生態駕駛行為的最優駕駛計劃在不增加行程時間的前提下,可以有效減少CO2排放,實現生態駕駛。

表4 最優駕駛計劃生態效果評價Tab.4 Ecological effect evaluation of optimal driving plan

圖11 加速-滑行模式下最優駕駛計劃的駕駛軌跡優化效果Fig.11 Driving trajectory optimization effect of optimal driving plan in accelerate-coast

圖12 減速-滑行模式下最優駕駛計劃的駕駛軌跡優化效果Fig.12 Driving trajectory optimization effect of optimal driving plan in decelerate-coast
4 結 語
本文研究了考慮排隊長度的信號交叉口生態駕駛軌跡優化方法以減少機動車排放,構建了不同的信號交叉口場景,提出了“單次踏板”生態駕駛行為。然后根據場景特征將行為分類識別為加速-滑行、減速-滑行和勻速-滑行三類模式,在考慮駕駛員操作容錯性下得到異質性最優駕駛計劃,基于數值仿真得到以下結論:
(1)與常規駕駛計劃相比,最優駕駛計劃能夠改善車輛到達交叉口的駕駛行為,優化駕駛軌跡,減少超過2%的行程時間和20%的CO2排放,隨著前后車初始間距增加,最優駕駛計劃的優化效果更加明顯,尤其是當場景特征相同時,車輛采用加速-滑行模式帶來的CO2排放最低。
(2)最優駕駛計劃具有一定的駕駛員操作容錯性。研究設置可接受加速度區間計算得到不同間距下最優駕駛計劃的駕駛員操作容錯性均不高于17%。整體上,加速-滑行模式的駕駛員操作容錯性高于減速-滑行模式;初始間距較低時,加速-滑行和減速-滑行模式的駕駛員操作容錯性分別處于較低和較高水平,隨著初始間距增加,駕駛員操作容錯性逐漸收斂至平均值上下浮動。
(3)交叉口場景特征會影響最優駕駛計劃的CO2排放。初始間距和前車初始速度固定時,后車初始速度與最優駕駛計劃的CO2排放呈負相關;前后車初始速度固定時,加速-滑行和勻速-滑行模式下最優駕駛計劃的CO2排放與初始間距呈負相關,而減速-滑行模式下最優駕駛計劃的CO2排放隨初始間距增大先減少后增加。
隨著V2I技術的推廣應用,生態駕駛行為可以應用于手機導航軟件或交互設備中以優化到達信號交叉口車輛駕駛軌跡,減少交叉口擁堵和CO2排放,同時通過設置可接受加速度區間,可以達到一定范圍的駕駛員操作容錯性。在未來研究中,需要考慮換道行為、多個信號交叉口以及區域路網對該生態駕駛行為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