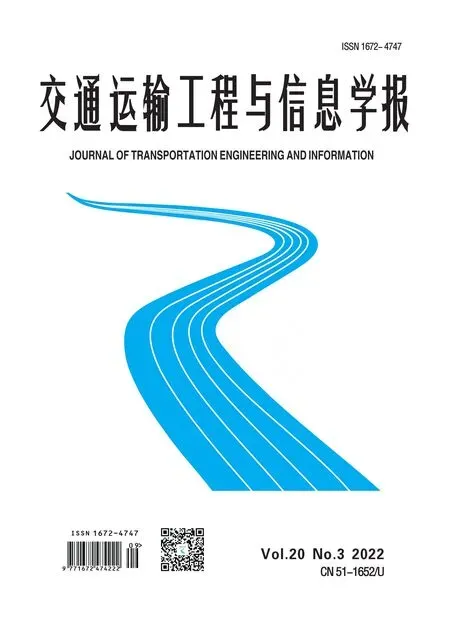策略性交通出行選擇行為研究評述:實驗經濟學方法的應用
齊 航,于躍洋,王光超,賈 寧,凌 帥,賀正冰
(1.湖北經濟學院,財經高等研究院,武漢 430205;2.天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部,天津 300100;3.華中師范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武漢 430079;4.北京工業大學,城市交通學院,北京 100020)
0 引 言
由于城市交通系統的動態性、復雜性和出行者的不確定性等特點,盡可能真實地刻畫出行者選擇行為規律是國內外城市交通管理研究領域的熱點與難點問題[1-2]。受實驗經濟學與行為經濟學發展的影響,目前交通出行選擇行為研究出現了明顯的學科交叉的趨勢[3-4]。
一方面,隨著行為心理學成果的日益豐富,以“前景理論”、“學習理論”等為代表的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飛速發展[5],交通行為研究者借鑒行為經濟學的最新理論成果提出越來越多的基于“有限理性”的路徑選擇模型[6-10]、網絡均衡模型[11-12]和動態交通路徑調整模型[13-15]。另一方面,隨著實驗室實驗(Laboratory Experiment)方法日漸成熟,以Selten、Rapoport 教授團隊等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者針對交通網絡上的路徑選擇、出發時間選擇等策略性交互行為開展了廣泛的實驗室實驗[14-15]。出行選擇行為實驗研究日漸發展成為交通管理與經濟學交叉的熱點問題之一[3]。
按照國外學者Rapoport 教授的主張①這種分類與文獻[3]的分類方法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可以根據不確定性來源的不同而將現有出行選擇行為實驗研究劃分為兩類[16]。第一類實驗目前以交通學者為主,數量較多,關注的是環境(或外生)不確定性(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這類實驗往往假設道路的旅行時間服從給定的隨機分布,用來刻畫道路通行能力由于交通事故、惡劣天氣、道路維修等原因而產生的隨機變化。這類實驗本質上是基于一個底層假設——城市交通網絡中的出行者數量足夠多,以至于每個個體出行者對路網擁擠水平、成本分布造成的邊際影響微乎其微、可忽略不計。在這種假定下,個體選擇某條路徑所體驗到的出行成本是某個給定隨機分布的一次具體實現值,個體之間不存在直接的交互和影響[17-19]。這類實驗的參照理論往往是個體決策領域(Individual Decision-making)中的期望效用理論。以這類實驗結果為啟發,研究者提出了基于前景理論的路徑選擇模型等理論[20]。
第二類實驗目前以經濟學者和行為運營學者為主,數量相對較少,關注的是策略(或內生)不確定性(Strategic Uncertainty)[20]。這類實驗往往考慮了個體選擇的正外部性(如公共交通或共享交通)或負外部性(道路的擁擠效應),即假設道路的旅行時間是由共同選擇的總人數決定的[21-22],以此來刻畫交通需求的內在波動性引起的不確定性。在這種假定下,個體收益不僅與自身決策相關,也與其他人的選擇相關,分散自治的個體通過共同對路網成本分布產生的影響而發生交互作用。這類實驗通常將群體在網絡結構上的路徑選擇問題描述為N人非合作的博弈(N-person Non-cooperative Game),屬于交互群體決策(Interactive Group Decision-making)領域,通常旨在檢驗均衡理論對網絡流量分布和出行者行為的解釋力等。還有極少量實驗研究,以簡化的形式同時考慮上述兩種不確定性[16]。
第二類實驗研究相比于第一類而言,研究數量較少,并且以國外學者為主。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國內交通學界在該方向上最早的國際期刊發表記錄是2016 年[21]。近年來,國內學者黃海軍、姜銳、馬壽峰、王文旭、肖鋒等及其團隊先后產出了一些交通選擇行為的實驗研究成果,然而該方向尚在起步階段,目前的成果較為零散,缺乏橫向比較和系統梳理。
本文重點關注第二類策略不確定下的交通出行選擇行為實驗是基于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出行者策略性選擇行為在實踐生活中十分常見。例如,為了躲避擁堵,通勤者可能采取“錯峰出行”策略或有意避開主干道,選擇支路、小道等策略[23];又如,當通過交通電臺或其他渠道得知某條道路非常暢通時,部分司機可能預測這條道路會因為信息發布而引來大量流量從而很快變得擁堵,因此選擇規避該條道路;再如,人們會先考慮周圍居民的潛在選擇從而決定是否加入“拼車”或“定制公交”等方式以共同分擔出行成本。由于或正或負的外部性的存在,人們對于其他出行者會如何決策的預期和判斷,將會影響其進行是否出行、目的地選擇、路徑選擇、出發時間選擇、出行方式選擇等各個維度的決策。另一方面,實驗室實驗方法可以通過恰當地控制一些干擾因素、提升研究結果的內部有效性,非常適合于研究策略不確定條件下的交通出行選擇行為。
因此,本文重點關注第二類策略不確定下的交通出行選擇行為實驗,旨在通過推介和評述將新興的實驗室實驗方法應用于策略性交通出行選擇行為的研究,增進交通科學領域專家學者對實驗室實驗方法的了解和認識,激發更多交通行為研究者科學嚴謹地、創造性地運用實驗室實驗方法開展研究,促進更多學科交叉成果涌現。同時,對現有出行選擇行為實驗發展的總結與反思,不僅對于交通管理領域發展有益,或對于行為經濟學所影響的其他交叉研究方向(如行為運營、行為公共管理等)也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上述諸多方面共同構成了本文的研究動機和學術貢獻。
1 實驗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適用性探討
1.1 策略性交通出行選擇行為實驗基本流程
實驗室實驗方法已經發展成為檢驗行為理論、發現行為規律的一種科學研究范式并逐漸獲得廣泛認可。以實驗室實驗為主要方法的實驗經濟學走入經濟學主流,并促進了很多學科交叉研究方向的形成(如行為運營、行為金融等)。實驗室實驗方法是指對于除感興趣的操縱變量(自變量)和觀測變量(因變量)之外的環境變量和干擾變量加以控制,征召自愿參加的被試者進入特定的實驗室場所,并將其隨機分配到不同實驗條件(Condition)或實驗處理(Treatment)中去,通過按照實驗說明中的規則進行決策而獲得與實驗中表現正向相關的金錢報酬,從而獲取行為數據用于檢驗現有的理論預測或理論假設[24-25]。
為了更清晰地展示策略不確定條件下交通選擇行為實驗的實施過程,本文借鑒孫曉燕[25]等人的文獻繪制交通選擇行為實驗典型流程圖如圖1所示。

圖1 策略或內生不確定條件下的交通出行選擇行為實驗典型流程Fig.1 Flow chart of strategic travel choice laboratory experiments
1.2 實驗經濟學應用于交通行為研究的方法論基礎
在交通路徑選擇行為實證研究中,傳統的數據采集方法主要包括實地觀測法和實證調查方法(RP 調查、SP 調查);新興的數據采集方法還包括實地/田野實驗(Field Experiment)、虛擬現實實驗(Virtual Reality Experiment)①實地實驗/田野實驗是介于實驗室實驗和實地觀測方法之間的實驗方法,區別于完全基于現實交通場景所自然產生數據的實證觀測方法。虛擬現實實驗,通常是指在駕駛儀仿真器上進行的,或利用虛擬現實設備進行的實驗活動,是介于實驗室實驗和實地實驗之間的實驗方法。。然而,針對交通網絡上的策略交互行為的研究,以上方法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對于路徑選擇行為的實地觀測需要在真實交通路網上開展,具有實施成本高、干擾因素多、操作難度大等困難。其次,實證調查方法和虛擬現實實驗更加適合研究個體心理和決策行為,難以在調查或實驗過程中為參與者提供其他參與者決策等信息的反饋。再次,一方面是因為開展實地實驗需要當地政府部門支持,難度大、經濟開銷大、操作性較低;另一方面,實地實驗可能會受到除了參與者之外的其他利益相關群體的制約,所形成的公眾輿論等會反過來影響參與者的態度和行為,因此實地實驗應用在策略性交互行為研究方面仍然進展緩慢。
與上述數據采集方法相比,實驗室實驗方法具有實施成本低、實驗條件可控、可復制性強,能夠獲得高度的內部有效性(Internal Validity)的優點。盡管現有實驗中所設計的路網與現實世界還有很大的差距,正如Smith[13]指出,基于引致價值理論(Induced Value Theory)恰當設計的實驗不僅能較好地模擬實際路徑選擇場景中的關鍵條件(不確定性來源、擁擠效應、網絡拓撲結構等),而且能夠有針對性地檢驗相關理論及假設。任何科學研究方法均很難同時具備高度的內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②內部有效性或者內部效度是指能夠正確地將某個觀測現象或結果歸因到某一種特定的被研究因素上去,而能夠最大程度地避免錯誤地歸因到其他的干擾因素或控制變量上面去。外部有效性是指基于有限的樣本中得出的研究結論推廣到更為一般的總體中去而仍然能夠成立。。上述不同的研究范式在保證內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方面各有所長,研究者需要根據自己研究目的側重點的不同而選擇適合的研究方法(如圖2 所示)。而實驗經濟學方法是現有實證類方法中內部有效性最強的研究手段,可以作為實地調查和實證觀測等各類實證研究的起點[3,24]。

圖2 四種實驗或實證研究方法的內外部有效性比較示意圖Fig.2 Types of experiments in relation 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validity③圖片來源于文獻[3]中圖3。
1.3 實驗經濟學發展路徑對交通行為研究的啟示
近四五十年來,實驗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的快速發展,為實證研究復雜的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決策行為提供了便利。目前,已經有三代學者對實驗經濟學或行為經濟學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24]。第一代行為經濟學家是指活躍在20 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一批學者,他們通過在實驗室實驗中的觀察,指出了傳統/古典經濟理論體系所無法解釋的異象,如阿萊悖論、損失規避、錨定效應等;在接下來的20 世紀末到21 世紀初的階段,第二代行為經濟學家開始針對上述心理現象構建具有更加真實行為心理基礎的一般化的理論模型,如以不平等厭惡為基礎的合作模型,k層次學習模型等;而在最近,在第二代研究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第三代學者探索將這些成果運用到相關的實踐領域中去,用于預測或引導人們的選擇行為,如助推設計等[26]。
回顧實驗經濟學與行為經濟學學科領域迅速發展的歷程,交通行為和交通管理研究者至少得到兩個方面的啟示[27]:
第一,行為經濟學的理論與實驗室實驗的方法,交替地互相作用,使得對方更趨完善,形成了這門學科向前發展的強大動力(如圖2 的上半部分)。一方面,理論對人們的決策行為形成預測,指導實驗設計應當收集哪些數據,并為行為分析提供基準參照。另一方面,實驗中發現的現有理論不能解釋的“異象”(Anomalies)或規律可以啟發研究者提出新的理論,通過不斷地使用理論解釋新“異象”的方式,相關理論也便日臻完善。

圖3 實驗經濟學領域與交通行為科研領域研究范式對照示意圖Fig.3 The schematic drawing of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methodology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and transport behavior research
第二,實驗室實驗可以作為各類實證研究的起點,在嚴格控制各種干擾因素的條件下檢驗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研究者可以在反復檢驗該實驗現象或因果關系穩健性的基礎上,逐步將實驗室實驗擴展到現場實驗,甚至是指導實踐的應用研究中去[3]。
本文將根據策略性交互行為類別的不同分為路徑選擇、出行方式選擇及出發時間選擇這三類分別進行綜述。
2 路徑選擇的行為實驗
路徑選擇是目前交通選擇行為實驗研究最為關注的一類決策行為,下面將依據研究目標或側重點的不同,從信息影響的評估、網絡均衡及動態演化理論的檢驗以及Braess 悖論的驗證三個方面分別進行綜述。
2.1 評估信息發布對選擇行為的影響
發布行前信息或實時信息是一種重要的交通需求管理手段(Travel Demand Management,TDM),其目的是引導和改變出行者路徑選擇行為,從而達到避免交通擁堵、提高系統效率的目的。交通研究者往往預期先進旅行者系統(Advanced Traffic Information System,ATIS)能夠通過減少出行者面對的不確定性從而減緩交通擁堵,然而,目前實驗室實驗研究尚未得到一致的結果。Ben-Elia 和Shiftan[20]將實驗研究交通信息的種類分為兩類,行前信息(Pre-trip Information)和實時或在途信息(Real-time or en-route Information)。
探究提供行前信息對于人們路徑選擇行為影響的實驗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92 年,Iida[28]等人設計了單一OD 兩條平行路徑的簡單路網,將參與者隨機分配到部分信息和完全信息兩個實驗處理中。部分信息處理中,參與者只能了解已選路徑的成本情況,而在完全信息的處理中,參與者能夠得知所有路徑的成本信息。結果發現,平均來說,路徑流量分布非常接近于均衡預測,然而個體選擇隨著時間卻始終沒有穩定下來。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德國博弈論學者Selten[17]等人再次印證了均衡對于群體層面網絡流量分布的解釋力。這一研究發表在博弈論與實驗經濟學國際頂尖期刊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上,激勵了更多經濟學者和運營管理學者關注交通網絡上的策略性交互行為。該文首次從微觀角度提出了兩類個體對于信息的響應模式:“直接響應型”參與者——以較大的概率選擇歷史上收益更好的路徑和“反向響應型”參與者——由于預判到大多數人是“直接響應型”而避免選擇或離開上一輪收益更好的路徑。Qi[22]等人借鑒了心理學中“序列依存性”的概念,利用條件概率構建了表征出行者對交通信息的響應模式的理論,并將實驗中的參與者聚類為四類:直接響應型、反向響應型、高度風險規避型、維持現狀型。Meneguzzer[29]發現“反向響應型”往往比“直接響應型”收益更高。
實時在途信息對路徑選擇行為的影響是實驗研究關注較多的另一個話題。Mak[30]等人采用了一個由12 條路段和8 條互相各有重疊的路徑組成的“復雜”路網,實施了實時在途信息和行前信息兩個實驗處理。結果顯示,參與者在兩個不同的實驗處理下所表現出的學習行為并沒有顯著的差異,只是在實時信息的情景下人們表現出更多的慣性行為。Klein 和Ben-Elia[31]結合了學習理論探討信息的影響;Adler[32]研究了實時信息和歷史經驗的聯合作用;Liu[33]等人研究了實時信息準確度對于路徑選擇的影響;Ben-Elia[34]等人發現實時信息能夠通過降低旅行時間不確定性而促進學習,從而促進出行者做出最優選擇;Yu 和Gao[35]通過實驗發現,短期內慣性對個體決策的預測能力較強,而長期來看學習行為對個體決策的預測能力較強。
2.2 檢驗經典網絡均衡與動態演化理論
策略不確定性條件下的路徑選擇問題通常被描述為N人非合作博弈模型,因此這類實驗的研究目的往往是檢驗網絡均衡的預測能力或解釋力。Lindsey[36]等人首先闡述了在現實交通環境中,路徑的擁堵效應與通行能力隨機驟降可能會同時發生的情況,在此假設基礎上,提出了考慮行前信息影響的網絡均衡模型。Rapoport[16]等人設計了與該理論的假設相對應的實驗,通過實施不同通行能力情景的實驗,驗證并支持了理論模型所預測的“信息悖論”現象,即當所有路徑通行能力波動出現強相關性時,提供行前信息反而使得系統總旅行時間上升。這一對研究是理論指導實驗、實驗反過來驗證和促進理論的優秀研究范例。Dixit 和Denant-Boemont[37]設計了能夠區分純策略納什均衡、混合策略納什均衡和隨機用戶均衡這三種均衡理論的三類實驗。這是設計實驗檢驗和區分幾種競爭性理論預測能力優劣的典型研究。
Rapoport[38]等人考慮具有正外部性的交通網絡和具有異質成本結構的參與者,提出了一類關于共享出行的社會困境博弈模型。這類社會困境具有以下特征:任何人的參與行為會對其他所有參與者帶來正的外部性;當所有人都自愿參與該集體項目時,社會總福利達到最大化。然而,如果一些代表性決策者發現退出項目是一種占優策略,那么這一集體項目的潛在好處將會降低,從而導致更多的成員選擇退出。這種可能迭代發生的非激勵效應(或稱“雪崩效應”)將會使得社會總福利飽受損失。論文開展了實驗室實驗,對社會困境模型進行檢驗,實驗結果證實了“少數人破壞整體”確實可能在現實人群中發生并對社會總福利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
與傳統均衡理論中出行者“完全理性”的假設不同,在現實生活中,出行者對于道路擁擠程度規律認知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可能是通過不斷調整選擇、獲得反饋、總結經驗并更新知識而形成的。因此,交通研究者已經提出了眾多的Day-today 網絡流量動態演化模型。為了檢驗不同的基于路徑的Day-to-day 理論模型對觀測行為的解釋力,Yu 和Gao[35]基于微信社交平臺組織并實施了包括三條路徑路網的虛擬現場實驗,運用統計方法檢驗了路徑流量和路徑之間成本差對于路徑之間換路率的非線性影響,該研究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理性行為調整過程(Rational Behavior Adjustment Process)的理論框架。Wang[39]等人令參與者先后在單OD 二條平行路徑到五條平行路徑的不同網絡結構上進行路徑選擇實驗,從而檢驗幾種經典的Day-to-day模型,并與Yu和Gao[35]等人的結論進行了對比分析。Song[15]等人利用已經發表的多源的實驗數據,對比檢驗了強化學習、信念學習、經驗加權學習模型,以及基于馬爾科夫的適應性學習模型對實驗中人們行為調整的預測效果。Ye[40]等人組織了實時信息條件下的實驗,比較并發現了基于擇路準則的學習模型的預測效果要優于以往研究中常用的基于路徑的學習模型,并且短期內出行者更多表現為慣性,而長期中學習行為的解釋力更強。在Qi[22]等人發現的慣性與響應強度異質性兩個行為規律的啟發下,Qi[41]等人分別提出了一類確定型和一類隨機型Day-to-day模型,經檢驗兩類模型均能夠較好地重現實驗結果。這三個工作是實驗研究啟發理論建模的一類嘗試。
2.3 提供關于Braess悖論的經驗證據
以上兩類實驗均是假設出行者同一個網絡拓撲結構上進行路徑選擇或調整,而當允許網絡拓撲結構發生變化時(如新增道路或封閉現有道路),人們的路徑選擇調整在某些條件下可能會引起Braess悖論[42]。它是指在一定條件下,為網絡新增路段反而導致系統效率降低,或刪除路段反而能夠提升系統效率的一類反直覺的現象。實驗室實驗方法的引入,幫助研究者確認了這類悖論在真實人群中發生的可能性。Rapoport[43]等人對于使用嚴格控制的實驗室實驗方法證實Braess 悖論的存在進行了開創性的工作。該研究實施了“新增道路”和“封閉道路”兩種處理下的實驗,實驗結果推翻了“Braess 悖論的影響微乎其微,并且會隨著人們出行經驗的積累而減弱”的原假設。受此啟發,更多的實驗研究對實驗環境控制變量的各個方面進行了變化和嘗試(如不同的需求水平[44]、路網拓撲結構[45]、信息發布策略[46]、流量組織形式[47]等),不斷地證實了納什均衡理論的預測能力,驗證了“Braess 悖論現象確實會在真實人群中發生”這一結論的穩健性。
3 出行方式與出發時間選擇的行為實驗
路徑選擇、出行方式選擇和出發時間選擇均是假定出行者在策略不確定條件下受到他人決策影響的決策行為,然而也存在差異。關于路徑選擇決策,個體出行者的備選方案(即可選路徑)是給定需求的起訖點對后,由特定的網絡拓撲結構而生成的,一般是離散的、具體的;出行者群體選擇的結果是需求或流量在空間維度上的分布。關于出發時間決策,個體出行者的備選方案(即可選時間點)不依賴于特定的網絡拓撲結構,可能是離散的或連續的,因此備選方案集合的規模一般更為龐大;出行者群體選擇的結果是需求或流量在時間維度上的分布。針對出行方式決策,個體出行者的備選方案(即可行的出行方式)也不依賴于網絡結構,而且往往是離散的、抽象的,備選方案集合規模一般較為有限,因此出行方式選擇中行為規律的一般性較強,更容易遷移應用到其他類似離散選擇問題中,例如Rapoport[38]等人探討了人們選擇是否加入成本分攤的公共出行方式的實驗現象和結論,對于解釋人們是否選擇參與醫療互助金計劃等其他領域的離散選擇問題也具有啟發意義。
3.1 出行方式選擇的行為實驗
除了與路徑選擇決策相關的Braess 悖論之外,交通中另一種常見的悖論Downs-Tomas(DT)悖論則是與出行方式選擇決策相關的。它是指在一定條件下,改善道路通行能力可能會吸引原來選擇公共交通方式的人群轉向使用私家車自駕出行,從而使得擴容后的道路再次變得擁擠,整個系統效率降低的現象。Denant-Boèmont 和Hammische[48]的研究是目前已知的最早采用實驗室實驗方法驗證了DT 悖論存在的研究。實驗分為兩個階段,首先由一位扮演公共交通運營者的參與者選擇公共交通的服務水平,其次給定服務水平不變,其他參與者扮演出行者在公共交通出行和私家車出行之間進行重復選擇。Dechenaux[49]等人進一步檢驗了結論的穩健性。
隨著共享交通的發展普及,“拼車”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出行選擇,一些實驗研究率先開始關注這類成本分攤的共享出行(Cost-sharing or Ridesharing)行為。區別于路徑選擇行為實驗,出行方式選擇行為實驗中的個體的出行方式選擇不完全是具有負外部性的特征,還可能具有正外部性,即選擇的總人數越多,人均成本越低。實驗設計中最常見的、也是代表正外部性最簡潔的成本分攤函數形式是m/f,其中m是給定常數,代表該出行方式的總成本,f為選擇該方式出行的總人數。在Liu[50]等人的實驗中,參與者要在固定成本的私家車、均攤成本但總成本較低的拼車(Carpool)以及均攤成本且總成本較高的班車(Shuttle)這三種出行方式之間進行重復選擇,結果發現,人們很快能夠找到均衡方案。受此啟發,Rapoport[38]等人將對稱參與者假設一般化為非對稱參與者,構造了非對稱/完全異質的私人成本,參與者需要在固定成本且異質的私人出行方式和均攤成本的公共出行方式之間進行重復選擇。實驗結果同樣驗證了納什均衡對觀測行為非常強的解釋力。
在具有多重均衡的交通系統中,人們由于缺乏協調而使得群體無法達到帕累托效率的均衡條件。針對人們在公共交通(正外部性)和私家車(負外部性)兩種出行方式之間的選擇問題,Han[51]等人設計了行為實驗來探究潛在影響協調行為的因素,結果發現:(1)信息反饋不僅能夠促進帕累托效率均衡的達到,并且能夠幫助個體行為的穩定;(2)收斂到非效率均衡的歷史經歷會影響人們的初始選擇偏好甚至群體實現的均衡選擇;(3)非有效均衡與有效均衡之間的壁壘越高,這種轉換越難,而有效均衡的吸引值越強,它在均衡選擇中越容易被選擇。
Zhang[52]等人則創造性地研究了自動駕駛出行和自駕常規車輛出行之間的選擇行為。實驗設定在自動駕駛與普通汽車混合行駛的道路上,自動駕駛車輛比例的增加將減少道路擁堵,但使用自動駕駛車輛的出行成本始終高于使用普通汽車。實驗結果表明,使用補貼措施消除出行成本的貨幣不公平,能夠有效提高自動駕駛出行的使用,緩解交通擁堵,提高社會效益。論文在結合馬爾科夫自適應學習模型和離散選擇模型的基礎上,構建了能夠描述出行選擇行為的仿真模型。結果表明,出行者的感知出行公平會顯著影響出行選擇行為;出行信息會顯著增加感知出行不公平,然而在提供出行補貼的條件下,出行信息會顯著減弱感知出行不公平,從而提高社會總福利。
3.2 出發時間選擇的行為實驗
出發時間選擇的行為實驗通常設置在交通瓶頸問題(Bottleneck Problem)的背景下。Daniel[53]等人在一個Y 型的上下游均存在瓶頸的交通網絡上進行實驗室實驗,結果發現:(1)實驗中觀測到的出行者群體的出發時間選擇分布大致符合混合策略均衡的預測,證實了Nash 均衡對于數據的解釋力;(2)與理論預測一致的是,在上游瓶頸通行能力改善的處理中,經由該瓶頸的出行者行為和成本沒有受到顯著影響,然而具有其他起訖點出行需求的人們卻不得不選擇更早的時間出發,從而增加了整個出行者群體的總成本。可見,在這一出發時間的策略交互博弈中,某條道路通行能力改善后,整個系統效率下降的Braess 悖論現象再次發生;(3)簡單的強化學習模型便可以解釋實驗中人們表現出的“神奇”默契協調現象。
受此啟發,Sun[54]等人也實施了基于瓶頸路段的出發時間選擇的實驗室實驗,發現了無論實驗設置的參數尺度如何變化,宏觀層面上出行者群體選擇分布均接近于用戶均衡理論的預測,并且交通信息對于群體行為和個體行為產生的影響是不同的。實驗也同樣發現了人們的適應性學習的過程,使用強化學習和Fermi學習模型均能夠較好地重現宏觀層面的實驗結果。Sun[55]等人的實驗發現,瓶頸路段通行能力減少時,群體達到用戶均衡穩態需要更長的時間,并且提供信息對無論是群體行為還是個體行為均沒有顯著影響。Liu[33]等人的實驗發現參與者很可能追求的是出行成本預算的最小化而非出行成本本身。Yang[56]等人通過實驗檢驗了“錯時上班”(Staggered Work Hours)機制對于出發時間選擇行為的影響。
3.3 同時考慮兩種策略性出行選擇決策的行為實驗
Mak[57]等人首次同時考慮了擁擠效應(負外部性)和共享出行(正外部性)的路網,并同時考察出行者的方式選擇與路徑選擇兩個決策維度。實驗采取的是被試間-被試內混合設計的方案,對于網絡拓撲結構的變化采用被試內設計,即同一組被試者依次參加基礎路網與擴展路網(或先擴展路網后基礎路網)的實驗;對于多個參與者的決策是同時進行還是序貫進行,采用的是被試間設計,即不同組被試者被要求同時決策,或是依次決策(參與者能夠在觀測到已經做出決策的部分參與者結果的條件下進行決策)。在這類具有正外部性的網絡上,Braess 悖論一旦發生,它的系統效率損失程度是更加巨大的。實驗發現,Braess悖論現象穩定出現,即使是決策可見度更高的序貫決策條件下,也沒有顯著地緩解Braess 悖論發生所導致的系統效率的巨大損失。劉天亮[58]等人通過實驗方法研究了朋友圈的交通信息交互對于出發時間和路徑選擇行為的影響。
此外,還有一些研究關注出行者“是否出行”的決策行為,運用實驗室實驗方法證實了在考慮彈性需求條件下仍然可能出現交通悖論現象[59-60],由于篇幅關系本文不再詳述。
4 討 論
當前最新探討實驗經濟學方法應用于交通出行選擇行為研究的綜述文章是出自Dixit[3]等人和孫曉燕[25]等人。因此,本文梳理了近五年(2018—2022 年)最新發表的策略性交通出行選擇行為實驗研究論文共15 篇。這些論文發表的期刊包括:行為運營頂尖期刊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行為經濟頂尖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交通管理頂尖期刊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B/C/F以及權威期刊Transportmetrica、Travel Behaviour and Society 等,其中國內學者主導的論文比例達到40%。這一現象說明,交通科學領域的國際期刊正在越來越接受實驗室實驗研究范式,并且國內學者的貢獻度越來越大,也取得了一定的話語權。本文從實驗設計中的控制變量、操縱變量(自變量)、觀測變量(因變量)三個方面,將最近五年該方向的研究發展趨勢概括為三點:
(1)對實驗環境中控制變量的設定更為豐富,還出現了少量在真實路網上進行的實地實驗[26-27]。實驗控制變量包括路網結構和路徑成本函數設定、出行者特征假設等。與早期實驗中路徑線性成本函數設定不同,Ye[40]等人和Meneguzzer[29]采用了非線性成本函數來刻畫路徑旅行時間;與大多數實驗的參與者“同質化”假設不同,Rapoport[38]等人和Yang[56]等人分別考察了具有異質成本函數的參與者和“錯時工作”的參與者;與大多數實驗假定擁擠道路不同,Han[51]等人和Zhang[52]等人考慮了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同時存在的決策情景。
(2)探究ATIS 或交通需求管理政策(TDM)影響的實驗研究熱度不減。這類研究是策略性出行選擇行為實驗研究中開始最早、數量最多的分支。與過去實驗將ATIS 提供給出行者的信息的“量”作為操縱變量不同(分為完全信息或部分信息的不同處理),Liu[33]等人將ATIS 的市場滲透率(能夠獲取完全信息的出行者比例)作為操縱變量開展實驗[45]。與大多數實驗考慮用戶均衡型信息發布策略不同,Klein 和Ben-Elia[31]通過引入獎懲機制來提升出行者對于以系統最優為準則發布的誘導信息的服從率。Mak[60]等人假設出行者是序貫決策而非同時決策的,操縱變量是在該出行者之前已經做出選擇的其他出行者的決策是否可見。
(3)實驗觀測的重心從路徑選擇決策逐漸擴展到出行方式選擇和出發時間選擇等策略性出行行為。隨著實驗室實驗方法日漸為交通學者所接受和采納,學者們將這種新范式應用于本質相通、研究較少的出行方式選擇[38,48-52]和出發時間選擇[53-57]上,促成了更多學科交叉成果的出現。
5 展 望
近年來,實驗經濟學方法論的飛速發展和普及,為實證研究復雜的個體決策與交互決策行為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工具。實驗室實驗方法以其成本低、可控性強、可復制性強、便于得到高度內部有效性結論的優點,成為研究策略不確定條件下交通選擇行為的一種可行的新工具、新方法,可以作為實證觀測和實地調查方法的有力補充。在交通行為研究中運用實驗室實驗的方法日益得到研究者的重視,也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然而,這類交叉研究尚處在相對初級的階段,目前的成果根據研究目標的不同較為零散,缺乏橫向比較和系統梳理。本文認為未來策略性出行選擇的行為實驗研究應關注(但不限于)以下幾個方面:
(1)改變實驗控制,以檢驗實驗結論的穩健性。未來的實驗設計可以在考慮參與者的計算和理解能力的前提下,嘗試更加多樣化的實驗環境,例如采用非線性的路徑成本函數、設定不同路徑互相重疊的網絡結構、招募真實司機參與實驗等。
(2)放松實驗假設、逐步開展(準)實地實驗,以提升實驗結論的外部效度。在理性認識實驗室實驗方法局限性的基礎上,注重實驗室方法與其他實證類方法的互補,考慮將實驗行為數據和多源大數據相融合[61],遵循“發現異象-構建理論-應用實踐”的發展路徑,運用實驗室實驗方法得到內部有效的結論后,繼續放松實驗假設,創造條件在真實路網上進行實驗或實證觀測,以逐漸探討研究結論的外部有效性,并對交通管理政策影響進行評估。
(3)考察組合決策,以回歸交通出行選擇的本質。策略性交通出行選擇行為包含是否出行、目的地選擇、方式選擇、出發時間選擇、路徑選擇等多重維度。出行者往往同時做出若干類決策,或者完成“一攬子”出行決策。因此,未來實驗研究應從個體行為視角出發,通過巧妙設計、逐步開展組合決策的研究。例如,在瓶頸問題中考察出發時間與出行方式的組合決策[62],在自動駕駛與人工駕駛混合條件下考察出行方式與路徑選擇組合決策[63]等。
(4)注重實驗現象與理論模型之間的“對話”,以增強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之間的互相促進。交通出行選擇行為建模和實驗雖然各自取得了豐富成果,然而仍相對孤立地發展,未來研究應當充分重視以理論模型來指導實驗設計,并且不局限于檢驗均衡的預測效果、獲得顯著的處理效應,以及使用簡單的學習模型大略擬合實驗數據,而應注重以實驗現象啟發微觀個體和宏觀網絡方面的理論建模,使得理論研究與實驗研究能夠互相促進、共同發展。
(5)評估政策干預或“助推”的效果,以促成理論和實證成果指導交通管理實踐。未來研究可以開展更多類型的交通需求管理政策對行為的影響研究,一方面,評估政策干預或政策“助推”的效果,另一方面,通過了解個體響應行為的規律,啟發和改善相關管理政策的設計和實施,從而實現改善交通擁堵、減少環境污染、提升社會總福利等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