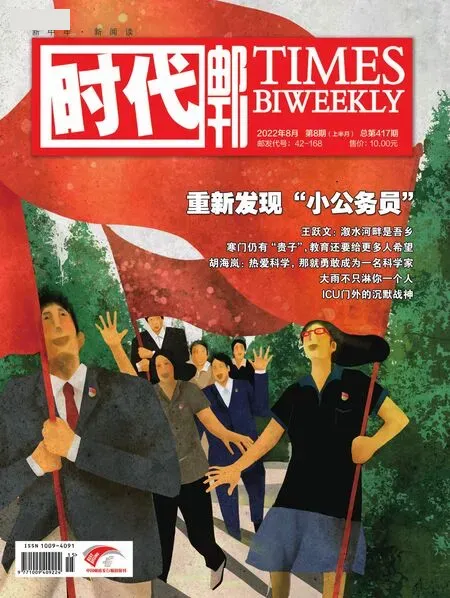“棒棒”時代轟隆遠去
● 楊雪

在街頭接活兒謀生的人,成為都市搬運的重要力量,他們被叫作“棒棒”。數(shù)據(jù)統(tǒng)計,隨著城市化進程,“棒棒”的人數(shù)在20年的時間里,一直在逐年下降。
在媒體表述中,冉光輝是被視作重慶“棒棒”精神符號的男人,2010年,這個一手扛著貨,一手牽兒子的山城“棒棒”,被攝影師許康平拍下,隨后在網(wǎng)絡上傳播,轟動一時,有人說他“肩上扛著家庭,手里牽著未來”。
扛著家庭的冉光輝,今年52歲了。他有危機感,這危機感來自歲月累積,來自整個“棒棒”時代如嘉陵江水一般的轟隆遠去。
當了一天外賣“步兵”
暑天來臨,冉光輝還嫌天不夠熱。他喜歡夏天,哪怕悶熱也行,扛箱子的時候不穿上衣,流汗流得痛快,還不用反反復復穿衣脫衣,“干活方便”。他沒穿外套,單穿一件加了薄絨的圓領長袖衫,匆匆忙忙趕往大正商場。
許多外賣員和他擦身而過,冉光輝目不斜視,對這些和自己有短暫交集的“同行”不瞥一眼。2021年的“雙十二”落幕,“棒棒”生意開始進入淡季,在別人的建議下,他嘗試去送外賣,他本來想著這活兒不會比當“棒棒”更辛苦,但是當自己真正跑一下,他發(fā)現(xiàn)不是那么回事。
雖然東西不重,但在地形復雜的重慶,每一個陌生訂單的具體位置,冉光輝都要琢磨很久。他長年在朝天門活動,超過這個地界,幾乎就超出了他的認知范圍。“爬上爬下,有些地方?jīng)]有電梯,很累。我又不會騎車,只能做‘步兵’,送貨全靠腿。”只跑了兩個訂單,冉光輝就放棄了,“一單4.5元,加起來9元,還要被平臺扣3元。這個錢不好掙。”
山城多梯坎,大正商場的運貨廣場在三樓而不是一樓。每天早上八九點,商家們陸陸續(xù)續(xù)拉開卷簾門營業(yè)。作為大正商場生意最好的“棒棒”,冉光輝的業(yè)務集中在四樓和五樓,內(nèi)衣、內(nèi)褲、襪子和睡衣,小的鋪子八九平方米,大的鋪子能占小半層樓。今天有沒有貨要發(fā)、有多少、什么時候發(fā)、發(fā)什么快遞,冉光輝上上下下溜一圈,心里就能有點譜,大概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在他頭腦中漸漸展開,剩下的工作就是按照節(jié)奏取貨和發(fā)貨。
對針織品市場的“棒棒”來說,一年也要分淡旺季。夏天算淡季,因為衣服輕薄,箱子數(shù)量就減少,重量也輕;到了冬天,一個箱子塞不下多少厚衣服,一張訂單要多發(fā)幾個箱子,冉光輝就能多賺一點錢,但這樣的箱子很重,他記得自己背過最重的一單,一箱東西超過了400斤。
冉光輝雖然是這個市場生意最好的“棒棒”,但他這幾年越發(fā)覺得生意艱難。“10年前的大正商場和現(xiàn)在沒法比。那時候一個鋪子一天發(fā)七八件甚至十多件貨出去,現(xiàn)在,有些鋪子兩三天發(fā)一件。”有的鋪子在這里一開10多年,也有些做著做著就撐不下去了,大浪淘沙黯然撤離。
(1)實現(xiàn)了新能源汽車電池和智能空調(diào)的集成化管理,通過對電池能源損失的熱量進行二次利用,在確保汽車電池正常工作的基礎上,將電池耗能過程中所產(chǎn)生的熱量進行充分利用,有效降低智能空調(diào)在工作時的能耗。
扛活兒的時候,冉光輝穿梭在四通八達的商場中,常常一扭頭就不見了。
冉光輝的扁擔放在商場里一個下水管背后,從頭到尾都沒有派上過用場。這是一根俗稱“硬頭黃”的南竹,顯然曾經(jīng)用過很多年,磨得油光锃亮。但現(xiàn)在它蒙著一層薄薄的灰,大部分的時間里,站在粗壯的白色塑膠水管背后。這里還塞著其他幾根棒棒,顏色各不相同,淺黃、灰綠,粗細差不多,長約一米,站著的時候,“棒棒”們倚靠著這些老伙計歇一口氣。大正商場里這幾根藏著的棒棒,看起來都已經(jīng)很久沒人用了。
扛出一套房
當那些棒棒不再被使用,“棒棒”們也在逐漸消失。
如果要追溯“棒棒”的歷史,可以前推到明末清初。資料顯示,當時,重慶出現(xiàn)“王爺會”“土地會”等神會組織,各分地盤,其頭目管理一個片區(qū)的人力運輸。隨著水運業(yè)發(fā)展,本來流動分散的碼頭腳夫逐漸聚攏,清朝光緒年間,重慶地區(qū)出現(xiàn)了“九門八碼頭”力幫,力幫隨后租下碼頭經(jīng)營權(quán),控制各個碼頭的搬運裝卸。新中國成立后,原屬幫會組織的裝卸工人大多轉(zhuǎn)入搬運裝卸公司,直到1982年以前,重慶都以“限制單干、打擊投機、取締野力”為方針。
和很多人印象中模糊的行幫性質(zhì)碼頭腳夫不一樣,現(xiàn)在的“棒棒”,事實上是從20世紀80年代才誕生的“新事物”。1983年,重慶為搞活經(jīng)濟開始允許“農(nóng)民進城搞運輸”。真正意義上的現(xiàn)代“山城棒棒軍”由此出現(xiàn)。鼎盛時期,重慶有數(shù)十萬名“棒棒”在山城上下來回穿梭,但隨著城市化進程,“山城棒棒軍”的人數(shù)在20年的時間里,一直在逐年下降。
冉光輝沒讀過什么書。從上世紀80年代零零散散做“棒棒”算起,入行已經(jīng)二三十年。
他記得當時的行情,從碼頭挑一擔東西上大街,大概兩三元。他跑得勤快,什么活兒都搶著接,從不挑三揀四,這也是“棒棒”們最講究的行規(guī)——不挑輕重,有活兒就要上,誰要是挑挑揀揀,會被別人看不起。
靠著踏實肯干,也因為“明星光環(huán)”無形中為他做了背書,經(jīng)營十幾年,冉光輝現(xiàn)在在大正商場有10多個固定客戶。對“棒棒”們來說,有沒有固定客戶很重要。就這么5元、10元地掙,冉光輝硬生生在重慶解放碑掙出一套房子。“60平方米,不大,買得早也不算貴,2016年的時候7000多元一平方米,40多萬元。”40萬元,以扛一包200斤左右的貨收入10元來計算,他扛了4萬包貨。買房以后,冉光輝感覺終于給了妻兒“一個家”。
冉光輝對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但對這個身份并不太認同。他始終覺得,做“棒棒”是賣力氣、上不得臺面的工作。但他不知道的是,“棒棒”早已成為重慶的一張名片,體現(xiàn)的是當?shù)厝说某钥嗄蛣凇⑶趧谧粤ⅰ?/p>
作為行業(yè)明星,冉光輝覺得這份工作不會再有年輕人加入。“現(xiàn)在的孩子都讀過書,能找到體面工作誰愿意來吃這種苦?去工地打點雜工,工資按天算,都比當‘棒棒’穩(wěn)定。”
但其實也有新人加入,比如23歲的付家林。“進廠打工要求太多。每當辭職總會損失工資。”當“棒棒”是做完一單立刻收一單的錢,這讓付家林覺得安心。
付家林清楚記得自己入行一年多以來干過最累的一單。那活兒是搬運地鐵里用的機器。根據(jù)機器上的銘牌,這塊鐵疙瘩重量達到了700公斤……休息了15分鐘,10名“棒棒”齊上陣。“嘿咗!”“嘿咗!”“嘿咗!”“嘿咗!”上一級臺階,喊一聲號子,男人們所有的力氣踩在腳下、扛在肩上,不銹鋼的棒棒被壓出明顯的弧度。還差最后一坡,就能抬上地面,另一名領頭人已力不從心,付家林頂了上去,他第一次感受到前排的壓力,16級臺階,走到第12級臺階時,眾人的號子不知道什么時候已經(jīng)變成了“雄起”。棒棒將付家林壓彎了腰,從肩膀滑到了脖子。他用盡全身力氣,撐完最后4級臺階。
“棒棒已經(jīng)消失”
聚集在一起的午夜“棒棒軍”,在黎明前的晨光里散去。他們幾乎都有幾種身份:在工地打工的、還在校讀書的、做平面設計的自由職業(yè)者……“棒棒”的工作不足以養(yǎng)活他們以及家人,在他們的選擇中,“棒棒”大多是用時間和力氣增加一部分收入的次要選擇。這個“次要選擇”自己能做多久?付家林沒仔細想過這個問題,但作為老前輩,冉光輝早已嗅到冬天的味道,除了嘗試著跑了一天的外賣,他還試過直播賣臍橙。也拍小視頻,“明星棒棒”的光環(huán)給他帶來流量和關注,現(xiàn)在,他的視頻賬號粉絲超過10萬人,和粉絲合拍、賣家鄉(xiāng)的臍橙、扛貨時順手來個自拍……
“有公司找過我,說要簽約合作,沒有意思。”他看過一些合同,覺得當主播和進廠似乎沒有太大不同,錢不能現(xiàn)結(jié)、直播時間有規(guī)定,連收入都是按分成,“我還要被他們管到。”錢要手手清、時間要自由,十幾年前選擇“棒棒”的理由,現(xiàn)在依然適用。
冉光輝也知道自己在逐漸老去,雖然豪情壯志“還要再干十年”,但他的腰椎已經(jīng)出過問題,手指也明顯變形,他擔心自己隨時有倒下的一天。
在冉光輝嘗試轉(zhuǎn)型的同時,許多“棒棒”也在尋找更多的可能性。“轉(zhuǎn)行送外賣的、上工地的、進廠的、去開滴滴貨運的。”10多年前給冉光輝拍下照片的攝影師許康平始終關注著這個群體,在他看來,“‘棒棒’已經(jīng)消失了。”
現(xiàn)在,在重慶的街頭,仍能看到或坐或立的“棒棒”們,但數(shù)量已大不如前。許康平說,西北民族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幾名學生近年來做過一次重慶“棒棒”生存現(xiàn)狀調(diào)查,最后的結(jié)論是“目前數(shù)量已不足2000人,且以老年人居多。”
這和他最開始用照片記錄這個群體的擔憂相符。隨著城市建設,朝天門碼頭在過去數(shù)年里的改造中,階梯已經(jīng)大幅減少。從大正商場往朝天門物流站這一條路被修成坡道,沒有電動車的人,拉著推車也能走,雖然費點力,但總比肩挑手扛輕松不少。
運輸工具的變化,讓“棒棒”們成為更廣泛意義上的搬運工。他們用肩膀扛活兒,攢夠一車就用推車送到樓下,再輾轉(zhuǎn)換成帶了電機的大推車,人坐在前面,車把手一扭,毫不費力。
還有一些變化超出許康平的預料,譬如電商和物流的發(fā)展擠壓著“棒棒”的生存空間。除此之外,諸如快遞、閃送等,也在頂替一部分“棒棒”的工作,貨運平臺的出現(xiàn)也讓一些年輕且更能自我學習的“棒棒”轉(zhuǎn)向做貨運司機等工作。
“或者可以說,‘棒棒’已經(jīng)消失了。對于曾經(jīng)數(shù)十萬人的這個群體而言,個體的存余不影響‘消失’這個判斷。”許康平有些惆悵,他想,新出生的孩子們,恐怕不會再有“棒棒”這個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