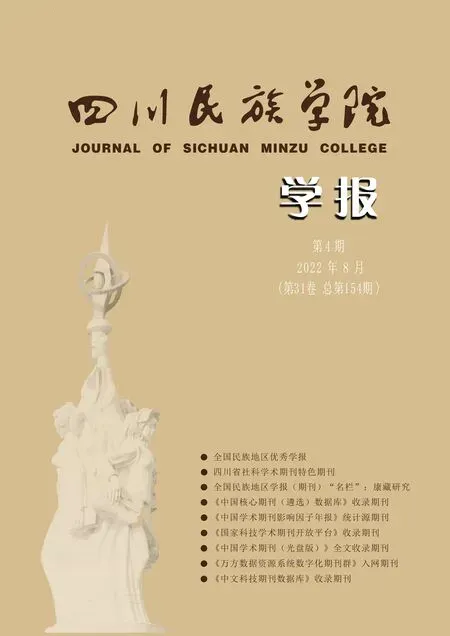吐蕃印章演化及文化特性初探
程忠紅 吾金昂加
(西藏大學,西藏 拉薩 850000)
印章的使用是人類社會進入經濟、文化、宗教、藝術秩序化文明的一個重要標志,在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中都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且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均有應用。那么,印章起源于何時?印章起源于什么樣的背景與條件下?印章的雛形又有什么樣的功能特征?中西方對于這一系列問題的認知與界定可謂是相差甚遠,這種差異性的認識也直接影響了印章的定義、功能以及文化外延等多種問題的研判。可見,印章起源這一追根溯源的問題始終是造成諸多問題存在巨大差異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中外印章研究的重要內容。
藏文入印后,吐蕃時期的用印記載和印章實物成為探討西藏印章起源的重要內容。關于吐蕃印章的材質與使用在傳統藏族文獻中有零星記載,近現代的發掘與研究學成果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第一,文獻史料的發掘與研究。20世紀40年代,根敦群培在《白史》一書中首次臨摹了敦煌藏文寫卷P.T.1083號卷的“大將軍敕令之印”(《白史》中寫作:倫崇即及拉桑西桐蓋印發出)和P.T.1085“亨迦宮敕令之印”[1]18-19;第二,金石史料的發掘與研究。20世紀80年代,王堯在《吐蕃金石錄》一書中,翻譯了吐蕃赤松德贊時期諧拉康甲、乙二碑的用印和其他用印[2]116+127;第三,考古文物史料的發掘與研究。20世紀初,斯坦因(Aurel Stein)在新疆和田、米蘭吐蕃戍堡遺址采集、盜掘出土吐蕃時期印章4枚并公布在《西域考古圖記》[3]《古代和田——中國新疆考古發掘的詳細報告》[4]二書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藏隊、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在2016年第11期《考古》中發表了《西藏朗縣列山墓地的調查與發掘》,首次公布了出土于西藏朗縣列山墓的一枚吐蕃時期骨質塔鈕印[5]62,以及2018年“血渭一號墓”出土了一枚“甥阿夏王之印”,系赤德祖贊時期吐蕃賜給墀邦公主之子莫賀吐渾可汗的官印[6];第四,專題及綜合研究。20世紀80年代初至今,我國史學界、翻譯界、收藏界、文博界等多學科的學者涉獵了吐蕃時期印章的研究,可謂是成果豐碩,但這些研究都繞過了吐蕃印章的溯源問題,或“述而不作”不下結論,或介紹西藏古代印章則從出土或傳世的吐蕃時期印章說起。
李帥在2018年第2期《文物》學刊上發表的《吐蕃印章初探》與2019年第2期《中國藏學》學刊上發表的《論印章在吐蕃社會的使用》二文,系統地梳理并研究了吐蕃時期印章的類型、性質、特點、官私印的使用以及吐蕃印章的淵源等問題,這對研究吐蕃時期的印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李帥認為,“吐蕃印章的淵源至少受到了漢地和西方印章文化的雙重影響。”[7]這一觀點是通過唐與吐蕃時期印章實物在形制、尺寸、陽刻、分類、使用五個方面分析后的結果,學術視野開闊,十分難得。但該文對藏文入印之前的吐蕃印章以及吐蕃印章出現的時間上限問題并沒有論及,也沒有追溯吐蕃印章的起源點。如果以“貞觀八年(634),其贊普棄宗弄贊(松贊干布)始遣使朝貢”[8]為時間節點,吐蕃時期及以后的印章,其文化性與豐富性確實是在多元一體下多民族文化相互交流、交融、交匯的結果。尤其是元、明、清及民國時期,歷代中央對西藏地方實施了系統性冊封,這對元以后西藏官、私印的體系建設、風格特點的形成、甚至是演變規律均具有導向性。那么,藏文入印之前的吐蕃印章呢?包括吐蕃政權初期(633-650年)、部落聯盟時期甚至更早時期的吐蕃印是什么情況呢?第一,如《根敦群培文集精要》載:“囊日倫贊時代蘇毗小邦首領森波杰已有璽印”[9],旦增南達在《藏族古代史瑣議》(藏文)印影本一書中輯錄了李迷夏的王璽之印,并將象雄文的璽印內容釋讀后轉寫為:“Kha tshan pa Shang Lig Shi ra tsa(統御世界之王)”[10],根敦群培的《白史》和敦煌藏文寫卷P.T.1288《吐蕃贊普傳記》中亦記載了象雄王妃贊蒙賽瑪噶的用印。這些用印是否又受漢地影響呢?第二,斯坦因(Aurel Stein)所得的新疆和田、米蘭吐蕃戍堡遺址采集或出土的吐蕃印章,為8世紀中后期甚至是9世紀初期的遺物。據王堯、陳踐等學者研究,在吐蕃占領西域各地時“吐蕃占領區的常駐軍政官吏多來自吐蕃本土各部落的基層官員,吐蕃簡牘文字也似出于下級軍官和吏員之手。”[11]同時楊公衛(尼瑪扎西)在分析西域契約時又指出,“與漢文契約相比古藏文契約則更具有官方特點,它的見證人多由數位官員擔任。”[12]并且,擔任契約見證人的吐蕃占領區官員多數使用圓形印。由此可見,吐蕃時期印章是方是圓并不能作為官私印劃分的主要依據。斯坦因(Aurel Stein)在西域所得的吐蕃印章,或許是吐蕃占領米蘭時期的基層藏族官吏印章,也或許是具有官、私并用性質的印章。這也說明,吐蕃占領西域時,其印章的使用范圍已深入基層,職官設置與職官印更是十分完備。
一、中外印章起源研究啟示
(一)起源諸說
西方學者將最早的印章起源追溯到距今7000多年的敘利亞和安納托利亞,盡管這一時期的印章還不具備戳記載體的復制功能,尚處于印章雛形期,但多數西方學者通過對印章紋飾多樣性的研究,認為此時的印章因具有一定的標識個人身份的功能,即是最早的印章。顯然,標識功能是西方學者追溯印章起源點的依據。我國中原地區印章的起源之說主要有以下五種:
1.神話起源說,即中國古璽起源于上古時代的“黃龍送璽”[13]110“鳳凰送璽”[13]141等天授神話。
2.外來起源說,即認為中國古璽源于古巴比倫地區蘇美爾人的陶圓筒印章[14]。
3.巴蜀起源說,即中國古代璽印最早起源于巴蜀古印[15]。
4.殷墟起源說,即中國最早的璽印為安陽出土的三件銅璽[16]12。
5.陶拍、陶戳起源說,即印章起源于新時期時代的陶拍、陶戳[16]]12。
隨著考古的推進,早期印章實物和相似物被不斷發現,這也推動了學界對印章起源問題的認識與再探討。尤其是新石器時代的陶拍、陶戳、陶質印模(主要是用于陶器紋飾的拍打工具)等引起了印界學者的廣泛關注,因陶印模與印章的初始功能相似,許明農認為陶拍就是“陶工所用的戳印”[16]12。對此,鐘雅倫、李學勤等學者也提出了“土陶印模、陶拍與印章起源或古璽有聯系”[17]。“擦擦”印模與吐蕃印章的關系就如同中原陶印模與印章的關系一樣,其初始功能極為相似,并且“擦擦”印模與吐蕃印章之間還表現出形制特點、鈐蓋方式、文化內涵等諸多的相似性。因此,本文認為,復制與戳記不僅是印章的初始功能,還是印章的溯源點。集中考釋“擦擦”印模與吐蕃印章的文化共性便成為吐蕃印章溯源問題的關鍵。
(二)功用諸說
印章的功能是一個發展與演變的過程。大英博物館出版的《7000yearsofseals》一文,將印章的功能解釋為“證實(憑信)或保證”[18]。我國中原地區印章的功用經歷了陶業制作的“印用”、商貿往來的“信用”、政治典禮的“權用”與書畫鑒賞、雕版印刷的“泛用”等多個階段,印章的使用范圍也同樣經歷了從私印到官私印并用的發展過程。
藏文入印后,吐蕃印章不僅私人用印普遍,官印更是被廣泛用于頒布誥敕、發布文告、制定法典、護持盟誓、征收財稅、驛遞文書、簽訂官契等多個領域中。吐蕃時期的印章也因制作目的、使用范圍、官私屬性、形制特點、鈐蓋載體、文化內涵不同而具有復制、示信、標識、象征、封物、護佑等諸多功能。其中,護佑功能是吐蕃印章最明顯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這種護佑心理是通過特有的印章鈕式和圖文內容來承載寄托的。通常,吐蕃時期的佛教印會使用佛塔、蓮花、造像、吉語、咒語以及帶翼獅子等內容作為圖、文、鈕入印,承載佛教護佑;苯教印則通過雍仲符號、大鵬鳥等具有苯教代表性的符號入印護法;吐蕃時期的世俗百官印頗受佛、苯宗教文化的影響,因此印面多以圖文并茂形式呈現,印文以職官名、衙署名為主,圖紋或鈕式中會置入出世神獸、入世瑞獸、吉語或吉祥符號等內容作為護佑政權的象征;相對于官印或宗教印而言,吐蕃時期的私印護佑形式較為靈活,可根據不同的宗教文化信仰和個人喜好選擇。元以后,歷代中央頒賜給西藏地方的宗教名號印、世俗爵號印其形制依然充滿了不同含義的護佑色彩。至今,西藏仍有不少人認為佩戴印章或塔形印模具有護佑平安、辟邪納福的功能,也許正是吐蕃印章“護佑功能”的傳承與演化。
(三)名稱諸說
“印”在中外多種語言詞匯中均有動詞與名詞的兼作之意,動詞的“印”指復制印記,凡印之屬皆從印。按也[19]。名詞的“印”指具有復制印記的具體物件名稱。如“印”在英文中作seal,拉丁文中作sigillum,巴列維語中作muhr,古埃及則曾用象形文字符號來代表印章[20],又如蒙文中作:Tamgha,漢文中作璽、璽節、印、章、印章、印信、記、寶、關防、圖、圖章、圖書等,具有各種異稱。
在藏文詞匯中有關“印章”的名稱和寫法多種多樣,但每個名稱的詞性和使用具有因時而異的背景與含義。例如:
1.Phyag rgya,即印章。
2.Phyag tham,即印章。
3.Sug rgya,即印章的敬語,亦指手印。是在藏文中是手的敬語,rgya即印章。以上三個詞為同義詞,均有“印章”之意,同時也有“手印”的意思。
4.Dam phrug,即小印章,一般指尺寸較小的印章(私印)或關防印。
5.Thel tse,即印章,是口語化的一種印章稱謂。
6.Bka′rtags,即蓋印,具有“加蓋”和“鈐印”的意思。
7.‘Dra brko,即仿造、仿制、復制印。
8.Dam,即印章。根據使用者身份不同又可分為多種名稱,如Srid dam,即攝政使用的印章,Bka′dam,即噶廈使用的印章。
前三個藏文印章名詞,在敦煌文獻和吐蕃碑文中出現較多,是吐蕃時期常見的寫法。(1)此觀點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了西藏自治區檔案館道煒·才讓加研究員、布達拉宮管理處索南航旦研究員、西藏大學文學院羅布教授及索南次旦博士等人的指導與幫助,在此一并致謝。關防印始見元代,所以Dam phrug應是薩迦時期出現的藏文名詞,第八個名詞Dam及結合使用者身份衍生出的Srid dam、Bka′dam等詞,應為清代甘丹頗章時期的名詞與寫法。從藏文詞匯中有關“印章”的名稱與寫法可以看出,西藏印章的發展有可能經歷了宗教印、政教印、政治印、專用印等幾個階段,同時也說明西藏印章的起源深受宗教文化影響。
二、吐蕃印章脫胎于“擦擦”印模的可能性分析
“擦擦”本是梵文中的一個擬聲詞譯音,源于模具制作小型泥塑佛像或佛塔時,因擠壓或按捺所發出的擬聲,后成為西藏地區用于供奉或裝藏而制作小型泥塑佛像或佛塔作品的專用名詞。
“擦擦”印模主要有覆缽式和平面式兩種,前者為脫模制作,后者為捺印制作。覆缽式“擦擦”印模是一種內部陰刻圖像或文字的深凹形脫模模具,脫制時需要將印泥在模具內充滿并多次擠壓,脫制出的佛像是一尊多面像或多尊連體像,佛塔成像“擦擦”則是立體高浮雕制作。平面式“擦擦”印模,印面一般為單面,制作時直接將印面按捺在印泥上,印出的平面佛像、佛塔或經文等內容的“擦擦”具有淺浮雕感。杜齊(G·Tucci)認為,“擦擦”本身具有“真相”或“復制”的意思[21]。可見,功德信仰是制作“擦擦”的主要目的,但復制是“擦擦”印模類似于印章的主要功能。
(一)覆缽式“擦擦”印模的傳入與使用
據《賢者喜宴》《布頓佛教史》《西藏王統記》《漢藏史集》《西藏王統記》《雅隆尊者教法史》等多部藏文古籍記載,4-5世紀吐蕃贊普拉脫脫日年贊時期,佛教“擦擦”印模等一批佛教寶物始傳我國西藏。有文記載說是五種,五種說包括除兩部經卷、寶塔、彌札手印和“觀音咒塔印模”。有文記載說是六種,包括三部經卷、寶塔、彌札手印和“觀音咒塔印模”。據《西藏王統記》記載,“觀音咒塔印模”即“十一面如意寶觀音菩薩的陀羅尼咒印模觀音像”[22]。由此可見,此時傳入西藏的“擦擦”印模,在形式上是十一面的覆缽式,內容上是一種初傳的觀音法相,時間上應是西藏地區出現最早的印模記載。
有關這些佛教寶物的來源到底是天降還是人為,《尼泊爾教法史》解釋說:“是由印度班智達羅灑措和藏族翻譯師黎特司帶到西藏的,因為當時贊普此指拉脫脫日年贊不懂梵文,所以班智達和譯師將經典和法像等物留在宮中。”[23]《尼泊爾教法史》的解釋至少有兩方面的合理性。一是早期佛教傳播者在語言、文字受限的異域傳教,攜帶這種小型的佛教膜拜物以直觀的方式進行傳播是行之有效的;二是這批天降之物之所以被稱為“年波桑哇”,意為“威嚴神秘”或意譯“玄秘神物”,是因為西藏人不能解釋它的來源和目的,但又覺得珍貴。這也說明當時的西藏人不懂梵文。“年波桑哇”的天降之說,顯然是早期佛教傳播者迫于苯教的崇天心理以及苯教在吐蕃地區根深蒂固的影響暫時無法被動搖的附會之說。關于這些寶物的下落,《漢藏史籍》載:“這些奇異之物,就安放在宮殿頂上,用供神的飲料和藍色玉石等供養。”[24]東嘎·洛桑赤列在《東噶藏學大詞典》中解釋:“這些圣物后來8公元世紀,赤松德贊時期修建桑耶祖拉康大殿外左側的白塔時作為藏裝在佛塔里了。”[25]可見,“擦擦”模具(也有可能用此印模已經制作了“擦擦”)與其他寶物作為佛塔裝藏早在8世紀時吐蕃就有的習俗。
(二)平面式“擦擦”的出現
覆缽式印模傳入西藏的時間為公元4-5世紀,平面式印模何時傳入并使用,文獻中沒有明確記載。多數學者認為,“擦擦”始于公元10-11世紀西藏后宏期阿底峽大師的傳入,并在西藏西部阿里地區托林寺作為佛塔裝藏物和供奉物被大量制作。因此,“年波桑哇”印模的傳入,并沒有得到史學家們的認可,且阿里托林寺及其附近所收集到的“擦擦”及印模一直被學界認為是西藏最早的“擦擦”和印模。
隨著考古發掘工作的不斷深入,青海省考古研究所對都蘭縣熱水鄉吐蕃墓地進行考古調查與發掘時,從墓地的塔基中清理出了大量“擦擦”。根據塔基上堆積的地層和塔的建造材料、構造分析,青海考古研究所所長許新國研究員認為,出土“擦擦”是吐蕃墓葬同時期的遺跡、遺物,且出土的佛塔、佛教造像“擦擦”目前所知至少有5種,均以黃色泥土制成,除一種覆缽式塔為脫模法制作,其余都是在泥片上按印制成[26]。張建林教授根據“擦擦”實物觀察,分析了吐蕃時期墓葬“擦擦”的兩種制法,其中一種便是按印制成的平面“擦擦”。另外,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仝濤研究員認為,“考肖圖遺址內出土的“擦擦”,首次將其年代提早到8—9世紀,代表著最早出現的“擦擦”類型。”[27]同時期考古發掘出土的“擦擦”,還有青海省烏蘭縣大南灣遺址中發現的泥質“擦擦”亦屬于吐蕃時期遺存。多地考古發掘出土的吐蕃時期“擦擦”,足以改觀學界對“擦擦”起源的再認識。
可見,平面式“擦擦”模具早在公元8世紀時已有使用(見圖7、圖8)。平面“擦擦”的制作就是按印所成,這與斯坦因(Aurel Stein)在新疆米蘭地區盜掘的早期藏文淺浮雕封泥印的使用如出一轍,僅有的區別就是印面的具體內容與復制后的具體功用。
三、“擦擦”印模與印章的文化共性
“擦擦”印模自傳入西藏以來,在鈕制造型、印面圖像、鈐蓋載體、使用范圍等方面均發生了歷史性流變,在一定程度上為印章的產生奠定了技術支撐與使用基礎。這一演變從“擦擦”印模與早期印章之間所呈現出的諸多文化共性中可以看出。
(一)鈕制造型
佛塔作為象征佛陀真身與精神的建筑物,早在前吐蕃拉脫脫日年時期已與“擦擦”印模一起傳入西藏。吐蕃時期的佛塔不僅用于塔的修建、“擦擦”制作,同時也作為印章鈕制使用。
目前,可見的單件佛塔題材“擦擦”,在西藏、青海、甘肅等地均有發現。如8-9世紀吐蕃時期青海烏蘭縣大南灣遺址、青海都蘭考肖圖遺址出土的塔形“擦擦”,11-13世紀西藏托林寺遺址出土的塔形“擦擦”,11-13世紀甘肅武威、黑水城等西夏遺址出土的塔形“擦擦”。直至清代,單件塔形“擦擦”依然是“擦擦”制作的主題類型之一。
截至目前,國內外可見的吐蕃時期印章實物有8枚,其中4枚是角質印章,1枚是合金材質印章(鈕殘),1枚是鼻鈕銀質印章,另外2枚則是塔形鈕骨質印章。

圖1 考肖圖遺址出土的吐蕃時期塔形“擦擦”(2)圖片來源:仝濤.絲綢之路上的疑似吐蕃佛塔基址——青海都蘭考肖圖遺址性質芻議[J].中山大學學報,2017(2):106.圖2 托林寺出土的13-14世紀塔形“擦擦”(3)圖片來源:廣東省博物館,西藏博物館.雪域瑰寶[M].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12:57.

圖3 烈山墓出土的吐蕃時期骨質塔形印章(4)圖片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藏隊,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西藏朗縣列山墓地的調查與發掘[J].考古,2016(11):62.圖4 新疆和田采集的吐蕃時期塔形印章(5)圖片來源:李帥.吐蕃印章初探[J].文物,2018(2):69.
20世紀初期,斯坦因(Aurel Stein)在新疆米蘭吐蕃戍堡遺址盜掘出土的4枚角質印章,基本保留了動物角的原型,通體呈帶有一點弧度的直鈕形狀。距印面約五分之二處鉆有橫向穿孔,應是作為佩戴時的穿繩孔,與“擦擦”印模鈕部的穿孔一樣。西藏印章上的綬帶最早見于元中央所賜西藏地方秩品較高的官印,但西藏傳統的私用印章、寺院印基本上是用各種皮繩系掛,也許吐蕃時期的骨質印、角質印是用皮繩系掛的。
據陳慶英、鄒習成在《吐蕃王朝飛馬使印章考釋》一文介紹,飛馬使印章為合金材質。因鈕部殘斷,無法得知吐蕃金屬印的鈕部形狀。以上7枚吐蕃印中,骨質、角質印為圓形、橢圓形,印面直徑從1.7到1.4厘米不等。合金質印章為方形,邊長2.0×2.0厘米,厚度0.3厘米[28]37。無論是骨質、角質還是合金印均刻有邊框,印文均為凹刻的陰文。考古發現的第8枚吐蕃印是“血渭一號墓”出土的駱駝紋與藏文合璧的銀質印章,印面呈陽刻,方形,鈕制為鼻形,有穿孔,圖文之間出現分欄設計。駝鈕印是中原王朝對邊疆少數民族首領冊封印章的常見鈕制,吐蕃王朝對于聯姻外戚“阿夏王”也給予了駱駝題材的圖形印章,但并沒有將駱駝直接作為鈕制,而是將駱駝作為印文中的圖像使用,這也說明吐蕃古代印章在汲取中原印章文化特點的同時也保留了自身傳統制印的特色。
從以上8枚吐蕃時期實物印章的形制上看,吐蕃印鈕出現了由塔形、角型向中原地區流行的鼻形轉變,材質由角質、骨質等天然材料到金屬質地材料轉變,形狀從圓形(或橢圓形)邊框、方形邊框到分欄設置的轉變,印文由陰文到陽文的轉變。
(二)圖像題材
圖像作為早于文字的一種文化現象,是人類長期的、主要的思想感情表達方式。圖像印章又稱肖形印,四大文明及五大原生語言地區均有發現。“安陽三璽”除了其中一枚是“亞”字印,另外兩枚也是圖像印,甚至有些學者質疑它是不是印章。顯然,圖像印雖然不是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政治意義中的印章,但它具有印章標識的性質與復制的功能。“安陽三璽”圖像是商周時期青銅器物上含有一定思想與文化的示意性圖形,它是印章,且是印章內容上的第一個發展階段。圖文合璧印章則是在文字“表音突破”認識下的文化漸變,應用于印面上的各種靈獸動植物圖像與意識形態下的政治權威相輔相成,是統治者為了進一步加強印章權信執行力的手段,是印章內容發展上的第二個階段。吐蕃印章因受傳統“擦擦”模具制作的影響與文字普及的限制,主要內容也是圖文合璧形式。
圖5是烏蘭縣大南灣遺址出土的吐蕃時期陶制“擦擦”,圖像內容是佛教中的蓮花化生圖(6)日本學者吉村憐先生認為,蓮花是佛、菩薩和天人們的母胎,生出了化生像之后,就成為他們的臺座,輕輕地托著他們的身體,那是一種堅固而巨大的花。藏傳佛教也講,蓮花生大師即從蓮花中化生而來。,嚴格講,此圖像是化生時空動態圖像中的其中一副,用該圖像制作“擦擦”,是佛教信徒出于對眾佛、菩薩化生而出的圣潔之意的敬仰表達。圖6是一枚佛教印,印面圖像也鐫刻著蓮花化生圖,印面中部增加了藏傳佛教中常見的喜旋紋。就“擦擦”與佛教印之間的印面圖像分析看,均屬于蓮花化生題材。
吐蕃時期的印文主要有新疆、敦煌等地出土的吐蕃古藏文文獻卷子上鈐蓋印文、新疆米蘭發現的封泥印文、諧拉康石碑碑文中提到的封以誓文的“雍仲紋印”[2]116等。
通過“擦擦”印面圖像與吐蕃印章實物、文獻記載、鈐蓋印文等幾方面的圖像內容量化分析發現,吐蕃印章的圖像內容,主要由佛教、苯教中常見的各種奇異靈獸、植物及部落圖騰、族徽、家徽代表符號等組成,文字內容則由驛站名、職官名、人名、部落名、族名、工匠名、吉語、咒語,以及文字系統化后出現的宗教禱告詞等組成。從圖文合璧的內容上劃分,主要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苯教文化印,包括作為苯教象征最突出題材的“瓊鳥紋”和“雍仲紋”,以及帶雙翅的“飛狗”“飛馬”“飛獅”“飛鴿”和半人半獸圖形等內容。第二種是佛教文化印,包括佛教象征符號的蓮花紋、獅子紋、祥云紋等。第三種是圖騰文化印,包括氏族圖騰和家族圖騰,如苯教《亡靈書》記所載:木不黨氏族的圖騰是白獅,賽瓊扎氏族的圖騰是綠龍,秦贊卓(東)氏族的圖騰是白螺色大鵬鳥,穆查嘎氏族的圖騰是白色禿鷲鳥[29]。
隨著多種文化的不斷深化與融合,吐蕃印章的圖像內容還表現出從“神獸”動物到“世間”動物的運用特點。尤其是吐蕃后期敦煌文獻中所鈐蓋印文,驛站、宮廷部門所發出的帶有雙翅的馬、狗、獅、白鴿、異化鷹等圖是神靈異獸向世間動物過渡的性質,體現了從苯教代表性符號向佛教代表性符號傾斜的特點,以及佛苯宗教符號相融合的特點。這也說明,吐蕃印章內容與社會文化、政治制度背景有著密切的關聯。

圖5 烏蘭縣大南灣遺址出土的吐蕃時期陶制“擦擦”(7)圖片來源: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烏蘭縣大南灣遺址試掘簡報[J].考古,2002(12):55. 圖6 佛教印(8)圖片來源:雕版收藏家湯紹波博士供圖。

圖7 烏蘭縣大南灣遺址出土的吐蕃時期“擦擦”經文(拓本)(9)圖片來源: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烏蘭縣大南灣遺址試掘簡報[J].考古,2002(12):54. 圖8 古格時期的平面式梵文“擦擦”經(10)圖片來源:西藏博物館藏品。
(三)鈐蓋載體
吐蕃時期印模的使用不僅是制作“擦擦”,在敦煌出土的藏文卷子《印沙佛文》P·2255V中記載了赤祖德贊親臨主持“印沙”法事活動。“印沙”活動中所使用的工具之一便是各種形式與內容的印模。譚蟬雪先生在《印沙·脫佛·脫塔》一文說:“印佛作法是釋教修行建福的方式之一,以木刻或銅鑄之佛和塔形象印于紙上、凈沙上或虛中……紙本絹畫屬于印佛作法。”[30]由此可見,印沙法事活動中所使用的模具材質有木質的也有銅質的,印制的媒介可以是在凈沙上、紙張上、絹畫上,甚至上虛空中,不拘一格,但模具的鐫刻深凹程度是有區別的,印在凈沙中的印模應是鐫刻印紋較深的一種模具,用于脫佛、脫塔的制作,類似于覆缽式的“擦擦”模具;印在紙本、絹畫上的印模應是鐫刻印文較淺的一種模具,用于印佛、印塔、印經咒等,類似于平面式印模或印章形式。佛教中非常強調造像功德,無論是“擦擦”制作還是“印沙”法事活動,覆缽式的“脫”制和平面式的“印”制,都是吐蕃時期常見的兩種制作方式。
鄭也夫在《雕版印刷的起源》一文中,論述了紙張的出現代替了封泥的使用,印章的鈐蓋媒介也從封泥逐漸變成紙張,這種變遷直接導致了印文篆刻從陰文向陽文的轉變,即在蓋印對象從封泥向紙張的變遷中,發生了陰文向陽文的轉化[31]。新疆米蘭吐蕃戍堡遺址發現的封泥印文,就類似于圖文凹刻較深的“擦擦”印模。可見,無論是“擦擦”印模還是吐蕃印章,其鈐蓋載體都經歷了從泥印到紙絹印的發展過程。
同時期,在佛經典籍中也開始出現大量的佛像、佛塔、經咒內容的扉畫和插畫,這與西藏“風馬旗”中的紙質、絹質佛像、經咒單頁印刷以及雕版畫的印刷等都類似于印章的捺印使用。捺印就是指將鐫刻好的圖像印模按印在泥、紙、絹等材質上,復制出同樣的圖像,用于信仰或做記號。謝生保、謝靜《敦煌版畫對雕版印刷業的影響》一文中提到,捺印的千佛、菩薩像可能是佛經扉頁畫的源頭,也是中國木刻版畫的開始。鄭如斯、肖東發先生在《中國書史》中也說:“這種模印的小佛像,標志著由印章至雕版的過渡形態,也可以認為是版畫的起源。”[32]他們已把佛像印模看作是肖形印的一種,一語道出了佛教印模向印章乃至雕版的演變與過渡。
另外,國家圖書館藏 BD14711 南齊寫經卷,背面印有一組圖文并茂的捺印佛像,這也說明佛教印的內容經歷了從圖像到經文、圖像合璧再到純文字版式的發展歷程。同樣,“擦擦”印模和印章也經歷了從圖到圖文合璧再到純文字的發展與變遷,吐蕃印章正是在“擦擦”模具捺印與復制的基礎上,逐漸從形制到內容脫胎演變而成。
(四)使用范圍
西藏印章的起源離不開“擦擦”印模的出現與使用,尤其是早期的宗教印,其圖像寓意與“擦擦”制作幾近相同。藏文創世后,西藏印章(官、私印)所體現出的宗教內容逐漸弱化、淡化,甚至完全脫離。因此,可以說西藏印章從文化特性方面經歷了早期宗教文化時期、政教文化時期、政教文化印章分離時期三個階段。
吐蕃印章的使用范圍非常廣泛,并不局限于紙絹類的公文,還應用于封泥、石碑等多種載體上,使用范圍主要有以下5種情況。
1.作為契約文書封泥使用
20世紀初期,斯坦因(Aurel Stein)在米蘭吐蕃城堡遺址、麻扎塔格遺址、尼雅遺址等地盜掘出大量公元8-9世紀吐蕃時期的藏文簡牘和其他遺物,在啟封和未啟封的簡牘上均有發現藏文封泥印記。封泥的印面有圓形、方形、橢圓形等多種樣式,部分封泥還留有印臺和印文兩截不同層次的痕跡,與青海烏蘭縣大南灣遺址、都蘭考肖圖遺址出土的塔形“擦擦”類似,且封泥周邊也有拓印時翻出的泥漿。由此可見,吐蕃時期的封泥印已有印臺而且印文陰刻較深,這說明吐蕃時期封泥印的鐫刻和鈐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早期“擦擦”模具制作的影響。雖然西藏本地暫未發現吐蕃時期的封泥遺物,但在新疆各地所發現的這批吐蕃官方簡牘封泥卻完全可以彌補對吐蕃時期封泥使用的認識。
2.作為寄存封物使用
松贊干布在位時期,通過政治聯姻方式對周邊諸部兼并攻取,南征北戰不斷擴大吐蕃疆域,他的同胞妹塞瑪伽爾嫁給香雄王黎彌賈為妃,贊普曾派補金贊芒瓊探望塞瑪伽爾,臨別前塞瑪伽爾說:“可將此物,獻上贊普。”因以一件蓋有印信之物,交于芒瓊[1]51。贊普啟封視之,乃是三十余塊上等松耳石也。贊普尋思再言曰:此似說:吾等若敢進攻黎彌賈,可佩此松耳石。如不敢攻者,如同婦女,當戴巾幗也。于是王臣皆急作準備,遂將黎彌賈國政摧毀[1]52。文中,并沒有具體描述賽馬加爾使用的印章具體是什么形制和內容,但根據文中描述可知,公元7世紀時吐蕃印章具有封存信物之用。
3.作為護持盟誓使用
盟誓,是西藏苯教文化中常見的一種心理制約方式,吐蕃時期所立盟誓碑一般建立在贊普與大臣之間、大臣與大臣之間,通常具有將盟誓內容昭告天下的示信特性。赤德松贊在位時期(798-815年)所立的兩座諧拉康碑(甲碑和乙碑),石碑通體鐫刻了赤松德贊授予娘·定埃增的盟書誓文。諧拉康碑(甲)碑文載:“盟書誓文,明白勒諸石上,四周封以大印而覆蓋之。”[2]116諧拉康碑(乙)碑文亦載:“將誓文勒諸石上,四周蓋印護持。”[2]127(甲)碑又載:“王兄牟茹贊普與王(太)戚族,諸小邦、平章政事社稷大論以下、諸大尚論均使其參與盟誓,誓文封以雍仲之印。”[2]116(甲)碑文還記載了,詔敕盟書正副本三本,蓋印加封后的收藏方式以及置放在盟誓文龕內的副本開啟程序和要求。從碑文記載可知,印章用于盟誓中有三處,一是在石刻四周蓋印護持(在諧拉康兩座石碑中未見印文,但同時期的工布第穆石碑(見圖9)基座上陽刻著一排雍仲符號,也許正是加蓋印章永固護持的象征),二是盟書誓文以雍仲之印加封,三是盟書誓文開啟后蓋印加封。另外,在云南迪慶藏族自治州德欽縣發掘的“法王皇帝圣旨碑”殘碑上也發現一枚鐫刻:“圣稱四川左布政之印”九個篆文的漢文大印印跡。[33]北京一處的藏文石塔塔基上也有鐫刻印文的記載。法王圣旨碑和塔基上鐫刻印文應是源于吐蕃時期盟誓碑上蓋印護持習俗。

圖9 工布第穆石碑(11)圖片來源:夏格旺堆.工布雍仲增刻碑調查[J].西藏民族大學學報,2020(6):123-129.
4.作為鈐蓋公文使用
吐蕃印章用于鈐蓋公文,在敦煌吐蕃藏文卷子上有大量的印跡可見。吐蕃時期已設有派專人護送信使和加蓋印章的專門機構。飛馬或(飛狗)圖案之印是發自軍鎮,而飛鳥圖案是發自王廷內府。[28]38告牒中使用的印章有帶翅蹲獅子印章(陽文)、展翅鳥圖像印文、藏文(陽文)印文,戒律卷子上鈐蓋的牛或馬圖像與藏文(陽文),官吏呈請狀中的人物圖像和藏文,在印上角有臃腫符號(陽文),會盟告牒上的展翅飛鳥圖像和藏文(陽文),新疆米蘭出土的人騎飛馬圖像和藏文,契約文書或甘結中一般官員或百姓則使用印祥云紋、花朵紋或雍仲紋印章。可見,印面圖形是區別于發文機關級別與公文緊急程度的重要標志。
5.作為辟邪祈福使用
自古以來,吐蕃印章無論是印鈕、印臺、印面等外在的圖像設計,還是內在的隱喻、寓意,所呈現的文化特點始終難以脫離宗教文化的影響。尤其是苯教、佛教中的吉祥符號,要么雕刻成印鈕,要么鐫刻在印面,均具有祈福、禳禍、護持等含義。所以,西藏印章不僅具有政教公文鈐蓋的實用性,還可以作為辟邪祈福用于裝飾和佩戴,也有在新生兒舌面上加蓋印章的習俗,用以祈禱新生兒安康。
四、結語
印章起源關系到印章使用時間的上限問題,中外學界對這一問題的追溯可謂是眾說紛紜。縱觀諸說,顯然不論什么樣的稱謂、什么樣的鈕制、什么樣的圖文內容,什么樣的形制,只要它具有捺印、戳印或翻印出印文(含圖、文或圖文并茂的印跡)的復制功能,它就是印章雛形。把吐蕃印章的起源與“擦擦”印模聯系起來加以分析,是不無道理的,因為“擦擦”印模和印章之間不僅關系密切,而且具有諸多文化共性。通過吐蕃時期可見印章實物特有的佛塔造型鈕制、浮雕式封泥印跡的鈐蓋以及所呈現出的苯教、佛教文化內容等元素,與覆缽式“擦擦”印模的塔形、平面式“擦擦”捺印的復制方式、“擦擦”實物印面內容的對比分析可知,印模和印章始終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尤其是吐蕃宗教印基本沒有脫離“擦擦”印模的形制母體,足以說明吐蕃印章發展有著從宗教到政教轉化的趨勢,直至吐蕃中后期,吐蕃印章在本土文化的滋養下發生了質的蛻變,由原來的宗教主題內容逐漸延伸至軍政、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并漸成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