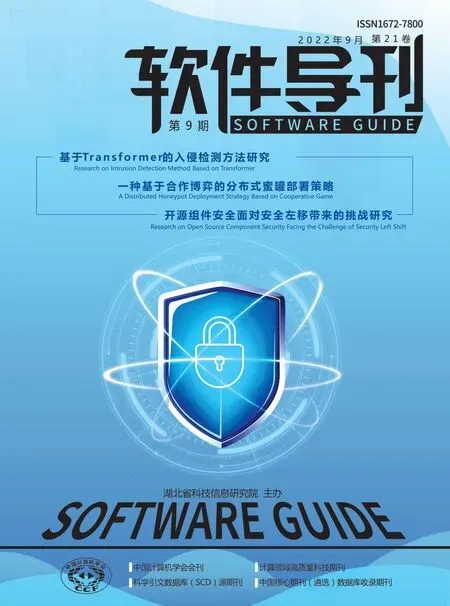基于RBT的計算機編程自適應教學策略研究
孫 進,陸 音,朱云霞
(南京郵電大學物聯網學院,江蘇南京 210003)
0 引言
社會各行各業都需要大量的智能信息系統,如電子商務網上商城、飯店酒店管理系統、交通管理控制系統、軍隊指揮信息系統等,這些都離不開編程設計與實現[1]。由于我國教育體制方面的原因,國內的學生一般需要到大學一年級以后才開始學習計算機編程課程。C 語言是一門面向過程的計算機編程語言,其設計目標是提供一種能以簡易方式編譯、處理低級存儲器,僅產生少量機器碼以及不需要任何運行環境支持便能運行的編程語言[2]。
國內很多高校在多個學院都開設了計算機編程的主干必修課程。C 程序設計課程是計算機編程中具有入門性和引導性的基礎性課程,其最根本目的是使學生接觸并了解計算機編程概念,以便在后續學習和工作中將計算機編程思想融入到自己的專業中[3]。
布魯姆分類學是美國教育心理學家本杰明·布魯姆于1956 年提出的分類法,其對教學者的教學目標進行分類,以便更有效地達成各個目標。布魯姆分類學的最終目標是鼓勵教學者達到3 個領域的教學目標,以構建完整的教育目標體系[4-5]。很多學者將布魯姆分類學應用于各種課程和教學模式中,如李征驥等[6]探索了布魯姆教學目標分類理論在人工智能導論課程教學中的應用;靳英輝等[7]對布魯姆目標教學法應用于留學生循證醫學全英文教學的實踐效果進行了研究;齊燦等[8]對布魯姆教育目標分類理論視閾下的混合式大學英語課程思政進行了研究;陳妍如等[9]從力學課程基本教學目標出發,以線上線下混合教學模式為載體進行布魯姆目標分類法實踐。但以上研究并未解決學生在學習領域知識時,對于學習活動數量、種類和復雜性方面的適應性問題。
本文的創新之處在于將智能技術與學習理論相結合,以便在計算機編程課程中為學生提供適應性學習活動。進一步來說,為更好地評估學生對課程的學習效果,采用基于規則的決策模型和改進的布魯姆分類(Revised Bloom Taxonomy,RBT)中的模糊權重,以便根據學生的知識水平以及活動的類型、數量和復雜性向學生提供自適應學習活動。
1 基于RBT的學習活動
本文涉及的領域知識為計算機科學課程本科階段的編程語言C,相關知識由8 章組成,包含基于RBT 的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該分類法提供了一個框架,可根據學生的認知技能將學習成果分為6 個級別,根據復雜程度逐漸深入,即:
(1)L1(記憶)。學習目標:學生應該能夠定義、描述、識別、了解、概述、回憶和識別事實;學習活動:標記圖書、抽認卡、閱讀材料、記憶活動、觀看演示文稿和視頻。
(2)L2(理解)。學習目標:學生應該能夠解釋、概括、解釋和重寫事實或案例;學習活動:創建類比、小組討論、記筆記、講故事、用光板畫圖表和流程圖。
(3)L3(應用)。學習目標:學生應該能夠應用、構造、演示、發現、修改和使用事實;學習活動:構造概念圖、分析解決問題的案例、通過簡答題學習、演示、小組工作、練習和計算。
(4)L4(分析)。學習目標:學生應該能夠分析、比較、區分、識別、說明、概述、關聯和分離事實;學習活動:分析魚缸、辯論、測試、研究案例、采用圖表進行對比、小組調查、問卷調查。
(5)L5(評價)。學習目標:學生應該能夠評價、比較、批評、解釋和證明事實;學習活動:調查、評論論文、寫博客、列表優缺點。
(6)L6(創造)。學習目標:學生應該能夠分類、合并、組合、生成、組織、重構和重寫事實;學習活動:創建新模型、撰寫論文、研究項目、開發與描述新的解決方案或計劃、集思廣益。
RBT 可用于為學習者選擇最合適的學習活動,因此可系統使用RBT 來推斷每個學生的經驗、能力和知識水平,以便提供給學生適合其水平的學習活動。
2 使用標準化的模糊權重調整學習活動
向學生提供適應性學習活動需要考慮其知識水平,然而,確定一個學生的知識水平并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而且充滿了不確定性。特別是,得分為8.8/10 的學生不能確定為優秀或非常好,兩種狀態都有一定程度的真實性。在這種情況下,模糊邏輯可成為解決方案[10]。在此方法中,指定了7 個模糊權重來表示學生學習編程語言C 的知識水平,即新生(N)、初學者(B)、中級(I)、良好(G)、很好(VG)、高級(A)、專家(E),其中新手(N)的模糊權重隸屬函數如下:

其余6 個模糊權重隸屬函數與上式類似,這里不再一一贅述。式中,x是學生分數,同時圖1 描述了模糊權重方案。

Fig.1 Schemes of fuzzy weights圖1 模糊權重方案
每個模糊權重由梯形隸屬函數表示,這些函數由4 個邊界值(a1、a2、a3和a4)描述:隸屬度在a1與a2之間從0 增加到1,在a2與a3之間以1 的度數變平,然后在a3與a4之間從1 減小到0。選擇梯形隸屬函數是因為在每個知識水平類別中都有一個區間(a2與a3之間),學生的分數完全屬于該類別。
綜上所述,7 個模糊權重用于描述學生在所教領域(編程語言C)的當前知識水平。上述隸屬函數用于定義這些模糊權重的值,范圍為0~1。當知識水平的值等于1 時,意味著學生已掌握了該領域知識,并且對知識是完全熟悉的。因此,每個劃分的模糊集中的總值描述了一個領域學習單元的知識水平,并且等于1。因此,μN(x) +μB(x) +μI(x) +μG(x) +μVG(x) +μA(x) +μE(x)=1。
模糊權重及其隸屬函數的閾值由15 名公立大學計算機編程領域的教師確定。更具體地說,要求教師以描述性的方式定義學習者在整個學習過程中的知識水平,并描述不同知識水平學習者的差異。教師教授編程語言的經驗超過12年,可以準確描述學生的知識水平。
3 自適應輔導決策
本節介紹基于7 種模糊權重應用的規則,以便針對學生的知識水平提供自適應輔導。在教學策略上,每一章都是通過學習活動來教授的,因此這些規則有助于系統決定每個RBT 級別學習活動的數量和復雜性,且這些活動必須交付給每個學生。這些規則是由上述15 位計算機編程教師制定的,特別地,其被賦予13 個派生類別的隸屬函數,并被問及獲取每個案例領域知識所需的每個RBT 級別學習項目的數量和難度,然后考慮其答案的平均值來形成規則。
整套規則如表1 所示,其描述了每個模糊權重實例的學習活動數量和復雜程度。RBT -Li(i=1,2,3,4,5,6)是RBT 的第i 級,cj(j=1,2,3,4,5,)是復雜度j從1(非常容易)到5(非常難)的學習活動。規則形成的推理為:學生成績的提高表明學生獲得知識,并進入更高階的認知技能階段。因此,隨著學生取得更好成績,RBT 水平越高,批量學習活動越少。例如,新手學生需要研究RBT 初始水平(如記憶或理解)和低復雜性的問題,而專家級的學生則需要處理更復雜的問題。該主張基于15 位經驗豐富的教師的意見以及RBT 模型,該模型指出,高階認知技能的獲得以較低層次的知識為前提。
例如,根據這些規則,如果一個學生被歸類到第3 個模糊集中,即其被定性為中級[等級:5.2/10,μN(5.2)=0,μB(5.2)=0,μI(5.2)=0.8,μG(5.2)=0.2,μVG(5.2)=0,μA(5.2)=0,μE(5.2)=0],所提供的學習活動將是:①1 個復雜度為5的RBT-L1學習活動;②2個RBT-L2學習活動:1 個復雜度為4,1 個復雜度為5;③1 個復雜度為3 的RBTL3 學習活動;④2 個RBT-L4 學習活動:1 個復雜度為3,1個復雜度為4;⑤2 個RBT-L5 學習活動:1 個復雜度為2,1個復雜度為3;⑥2 個RBT-L6 學習活動:1 個復雜度為1,1個復雜度為2。
4 評價結果及討論
教育軟件評價對于評估系統的有效性和學生的認可程度非常重要。因此,其被視為開發周期的核心階段。為進行定性評估,本文對系統進行了以下兩方面評估:①使用t 檢驗對教學策略的適應性、學習活動類型和數量進行評估;②學習成果評估。
4.1 參與人員
在南京一所公立大學C 編程本科課程的輔導期間,本文對該系統進行了評估,為期一個學期,150 名二年級本科生與該課程的3 位導師參與了評估過程。將所有人員分為3 組,每組人數相等,即50 名學生。為保證定性評價,分組時注重考慮學生特點。每組人員特征如下:第一組——平均年齡:19.3,性別:23 個女性,27 個男性;第二組——平均年齡:19.2,性別:22 個女性,28 個男性;第三組——平均年齡:19.3,性別:23 個女性,27 個男性。3 組共同特征如下:①城市學生與農村學生比例相等;②都學習過計算機高級知識;③所有學生第一年都成功通過了相同數量的課程;④所有學生都參加了C 編程課程并希望取得高分。

Table 1 Adaptive-assisted decision rules表1 適應性輔助決策規則
在整個學期中,實驗組(第1 組)學生都使用該系統進行學習,通過自適應學習活動實現領域知識的個性化,而對照組學生使用具有相同用戶界面的傳統版本的系統進行學習。第2 組使用的系統版本提供了具有特定學習活動的學習材料,所有學生都相同,并且不是基于RBT 設計的,而第3 組使用的系統版本提供了理論格式的學習材料,也沒有適應學生的需要。3 位導師參與了該實驗,每組1位,幫助學生使用這些系統。
4.2 教學策略評價
為評估學生對領域知識適應的滿意度,本文采用統計假設檢驗(t 檢驗)將所提出的系統與傳統版本的系統進行比較。傳統的系統通過固定的學習活動傳遞領域知識,其中第2 組沒有采用適應性學習活動及任何學習理論,所以本文使用第2 組的數據進行對比。該實驗可揭示通過基于RBT 設計的適應性學習活動進行的輔導是多么成功。在學期末課程結束后,要求兩組學生根據李克特量表回答以下問題,并從“非常”(10)到“完全不”(0)進行打分:
Q1:學習活動是否與你的知識水平相對應?
Q2:活動數量是否適合有效學習?
Q3:活動的復雜程度是否有助于你的學習?
t 檢驗分析結果如表2 所示。由此可推斷出針對上述問題,兩個實驗的平均值之間存在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本文提出的系統在基于學生知識水平的學習活動的準確性以及活動數量和復雜性方面超越了傳統版本,這些結果是意料之中的,因為本文提出的系統結合了領域知識的智能機制,使學習活動可適應學生需求。通過提供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環境,進一步提高了知識獲取與學習效率。

Table 2 Analyzing the results of the t-test表2 t檢驗分析結果
4.3 學習成果評價
本節通過比較使用本文系統與兩個傳統版本系統的學習成果來評估輔導質量。為評估學習成果的改善情況,采用前測—后測非等效組設計。其中,對3 組的所有學生進行了相同的預測試,以評估其以前在該領域的學習情況。在整個學期中,實驗組(第1 組)的學生使用本文的系統進行學習,而對照組(第2、3 組)的學生使用兩個傳統版本的系統進行學習。每章結束時,所有學生都接受了相同測試。由于后測分數被認為是其最終分數,因此采用章節測試的平均值。
采用配對t 檢驗來比較每組前測與后測分數之間的差異。在第1 組中,前測平均值為5.58/10,后測平均值為8.06/10,其均值差為2.48,表明t1=-28.555 和P1=3.37 ×10-32<0.05 有顯著改善。對于第2、3 組,前測與后測均值分 別 為5.62-7.02 和5.34-6.8,t2=-16.333,P2=1.84 ×10-21<0.05,t3=-17.834 和P3=4.55 × 10-23<0.05 均 有顯著改善。為識別本文系統與傳統版本系統之間的差異,使用單向方差分析統計模型,該模型是測試以上3 個組以探索其之間在假設方面是否存在顯著差異最合適的方法。本文對學生的最終成績進行了方差分析檢驗,零假設表明實驗組與對照組之間的學習成果沒有差異。因為F=13.221 >F臨界值=3.058,方差分析檢驗的結果表明零假設不成立,表明3 組的平均值并不完全相等。為了確定哪個組不同,采用最小顯著性差異(LSD)檢驗,得到LSD=0.46。將第1、2 組(diff1,2=1.04)和第1、3 組(diff1,3=1.26)平均值之間的差異與LSD 值進行比較,因為兩個差異值都大于最小顯著性差異值(diff1,2>0.46 和diff1,3>0.46),所以報告了一個顯著結果。因此,本文提出的系統在提高學習效果方面優于傳統版本。第1 組與第2 組之間的統計顯著性差異顯示了本文采用學習活動的適應性及學習活動設計效率,第1 組與第3 組之間的統計顯著性差異也驗證了本文采用教學策略的有效性。
5 結語
本文根據RBT 學習理論,通過為學生提供適應性學習活動,提出一種新穎的教學策略。其是通過采用基于模糊權重的決策來實現的,該決策根據學生在領域概念中的分數來定義學生的知識水平并推斷出學習材料。結果是每個學生都根據其知識水平來接受學習活動,而其在學習活動的數量、類型和復雜性方面都具有適應性。系統評估結果是非常樂觀的,顯示學生滿意度較高,而且獲得了更好的學習結果。學生對這種新穎的教學策略的評分高于8.2/10,表明基于其知識水平所提供學習活動的數量和復雜性是合適的。此外,前測與后測評估顯示學生成績得到了顯著提高,證實了該學習方法的適用性。最后,將該系統與兩種傳統版本的系統進行比較,結果表明,該系統在提高學習效果、適應性、RBT 使用效率以及教學策略的有效性方面都優于傳統版本的系統。本研究的重點是以學生的知識水平作為其適應性的主要決定因素,從而為學生提供適當的學習活動。未來將結合其他學生特征的模糊權重,如情緒狀態、錯誤類型等,以期增強系統適應能力,進一步提升學習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