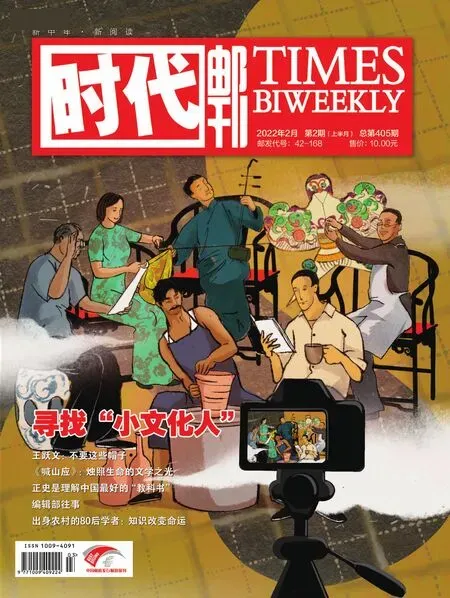神秘ICU:潰敗的孤獨與重建的希望
● 劉少明
對于普通人來說,ICU神秘、不可觸碰,但作為重癥病人求生的“最后一道防線”,ICU被寄予了最大的希冀。從收治、搶救、穩定病情,再到離開,生死線上的掙扎與救援,讓醫護人員與病人及其家屬結成“同盟軍”,最終形成如親似友一般的連結。

ICU里,什么是容易被忽視但又至關重要的?在心肺復蘇、機械通氣、腎臟替代治療等現代化治療手段之外,營養治療、心理關懷……那些于細微之處展現出來的關愛,也是幫助病人活下來、好起來的關鍵要素,也亟待被人們看見和理解。
孤獨與暴瘦
“這是普通人難以想象的感覺,一邊嘴巴饞,一邊肚子脹。”回憶起在ICU的日子里,暴瘦、無法進食的同時卻沒有饑餓感的狀態,老單斟酌了半天用詞,最終說了這樣一句話。
因高血脂引發胰腺炎的老單先后兩次住進了ICU。先是因為胰腺炎發作緊急入ICU,一待就是十二三天。不能進食,只能輸液,150多斤重的老單暴瘦,約30斤的體重迅速“消失”。雖然沒有饑餓感,但長期臥床導致腸道功能受影響,老單時不時會有腹脹的感覺。
在長期臥床的重癥病人中,你很難找到“胖子”。不論之前體形如何,在與病魔的斗爭中,他們大多經歷了營養供應不上或者吸收不足的階段,由此暴瘦。ICU的床逐漸顯得寬大,插在身上的管子就像繩子一樣,將他們瘦弱的身軀綁在床上。“不能動,只能抬頭盯著天花板,一秒一秒地挨過去。”老單說。
老單還經歷過一次轉院,入院后,保守治療的他一直高熱不退,最后由專家拍板緊急安排了手術。手術后,虛弱的老單直接被送進了ICU,再次縮進“最后一道防線”內。
單間,窗簾拉起,監護室形成獨立隔絕的空間。再次入住ICU,20多天的漫長時光里,老單的意識一直很清醒,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沒有手機,沒有電視。老單回憶說:“假如意識模糊也就好了,但我一直是很清醒的,就很難受。”
在當時,老單每天最快樂的時間有兩個,一個是被推出房間去做CT的時候,他感覺“就像被釋放一樣,外面什么都是很新鮮的”。還有一個就是和家人見面。等待家人的到來是他唯一能夠紓解情緒的方式。根據規定,ICU的探視時間在下午4:00—5:00。假如當天兒子來探視,老單從早上10點就開始頻繁地看鐘表,“11點了,12點了,下午1點了,2點了,3點了,3點半了,還有半個小時兒子就進來了……”
但即便非常渴望并珍視這1個小時的探視時間,老單在兒子來的時候,還是常常跟他說,“你別來了,多麻煩”。老單說,“人不能太自私,兒子也是要工作的”。最終,“孤獨”成為他在ICU的時光里濃重的底色。
關懷,于細微之處
“我們醫生其實有兩種價值,一種是治療價值,病人的治療需要你;還有一種是心理價值,體現在對病人以及家屬的安慰和陪伴上。”ICU里的醫護人員越來越多地關注到病人的心理與情感,常州市武進人民醫院的ICU醫生陳丹就是其中之一。因為始終秉承“兩種價值”這一理念,陳丹能夠非常敏銳地覺察出病人的訴求,有時候,甚至只需看上一眼。
2019年秋,一對80多歲的老夫妻因為呼吸衰竭同時進入常州市武進人民醫院ICU。武進人民醫院的ICU是一個個單間,相鄰房間用大塊玻璃隔斷,窗簾沒有拉起來時,隔壁的情況一目了然。
老爺子當時已經呼吸急促,口唇紺青,說不出話,但仍努力掙扎著側身,目光鎖定在隔壁單間的老伴身上。老太太病情輕一些,戴著無創面罩,在呼吸機的支持下,缺氧很快得到緩解,生命體征也還平穩。她的目光同樣看向了老爺子。
陳丹對老爺子說:“現在情況比較危險,要給你做氣管插管了,不要緊張,可能會有些難受。”老爺子有些抗拒,搖搖頭,突然激動了起來,艱難地抬起手,指了指隔壁,又將目光投向陳丹。
有10多年ICU經驗的陳丹,瞬間就明白了老爺子的意思:他想和老伴說話。情況危急,陳丹給老爺子戴上無創呼吸機,又拿來寫字板,把筆塞到老爺子手里,對他說:“老爺子,你有什么話寫下來,我會拿給你老伴看的,不能再耽誤時間了。”
老爺子顫巍巍地寫下了歪歪扭扭的5個字:“欠情,快活點!”前2個字是對過往表達歉意,后3個字是對老伴的未來寄予希望。盡管傾力救治,還是沒有出現奇跡。而那塊最后關頭遞上的寫字板上的5個字,就成為老爺子留給老太太的最后一句話。
“口渴、疼痛、想見親人……”陳丹那塊重癥監護室里的寫字板,不斷傳達著無法言語的重癥病人的心聲,成為他們表達的一個窗口。“治療之外,心理上的關懷對于病人其實也是非常重要的。”從業16年的陳丹,曾經遇到過病人因為過于恐懼,在出了ICU之后經常做噩夢,情緒的崩潰直接導致病情惡化,最終再次回到ICU。
因此,在武進人民醫院,對于收治的病人,有條件就給予單間,一方面是保證搶救場面不出現在其他病人面前,另一方面也避免人來人往打擾到病人休息,盡可能地改善病人的睡眠。同時,醫生每天笑臉相迎、言語安慰,緩解病人及家屬的緊張情緒。“陪伴病人一起度過艱難的時光,給他鼓勵與信心。”
老單的“孤獨感”,在ICU里并不少見。而ICU醫生們也都明白,與家人的溝通,是病人消解“孤獨”的最佳方式。因此,在疫情來臨,家屬無法進入ICU探視后,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重癥醫學科醫生張蕾第一時間主張視頻探視。由醫生帶著手機到病床前,與病人家屬進行連線,“清醒的病人可能聊的時間長一點,沒有清醒的,也讓家屬看一看病人的情況。”
10多年的重癥臨床經驗告訴她,家屬密切了解病人的情況,不僅能夠給到病人安慰,還能減緩醫生的壓力。“很多家屬不理解,‘為什么昨天還好好的,今天病情突然就惡化了?’”張蕾提到,“家屬見不到病人,唯一的信息來源就是醫生,家屬會因為病人病情的起伏而焦慮,這種時候,醫生會面臨更大的壓力。”所以她始終堅持,病人與家屬、醫生與家屬都需要盡可能保持溝通,“互相理解并支持,才會有美滿的結局”。
張蕾和同事也越來越注重對于病人的人文關懷,醫護人員除定期開家屬溝通會之外,每天還會給病人做早期的康復治療,或者是播放音樂舒緩病人的心情,在手套上給病人畫個笑臉……“盡可能地讓病人處于一種比較舒適的狀態。”
“病人跟醫生實際上是朋友和親人的關系。”張蕾表示,“因為重癥病人的病情隨時都在變化,所以醫生一定要守在床邊,嚴謹敏銳地觀察。無論過程有多么復雜或者艱難,在ICU里大家的目標是很純粹的,就是希望病人可以好起來。”張蕾的目標,也是眾多重癥醫護人員的心中所想。
“如履薄冰地往前走”
重癥病人的病情每天都在變化,醫護人員往往需要根據病人最新的情況來定制個性化方案。在強調綜合救治的重癥醫學科,全方位的評估和治療要求醫生對病人的身體狀況有細節性的把握。在這些細節中,營養供給也是需要傾注心血的關鍵一步。
80歲的馮老爺子就受益于精細化的營養治療。2019年11月,馮老爺子因為“食管破裂、多器官功能衰竭”進入ICU,病情十分危重。醫生不得不反復告知病情及預后,讓家屬做好思想準備。
入院前期,因為食管破裂、意識不清醒,馮老爺子不能直接進食,張蕾和同事針對馮老爺子不同時期的不同狀態,制定了非常完整細致的個性化營養方案。早期沒有辦法放置胃管,就通過靜脈打營養針,注入脂肪乳、氨基酸這類人體必需營養。
“能經正常的消化道(食管、胃、腸等)吸收營養是最好的。”因此,隨著病情穩定下來,馮老爺子做了手術,術中醫生放置了一個空腸營養管來解決他后續的營養問題。“給了他一個生命管線,讓他慢慢從腸外營養過渡到腸內營養。”
有了空腸營養管之后,營養方案還是需要細化。馮老爺子最先接受的是滋養型腸內營養劑,短肽類,是預先消化好的,不會增加腸道負擔。馮老爺子的進食方式也在根據病情不斷調整,從最初的靜脈注射,到經空腸管輸入營養液,最后是經口進一些流食,慢慢過渡到正常的飲食。
“基本上我們每天都會評估病人的營養耐受狀態。謹小慎微、如履薄冰地往前走。重癥醫學科內,病人的情況瞬息萬變,可能上一分鐘情況還可以,下一分鐘就不行了。”
馮老爺子年齡大,病情又復雜,中間起起伏伏,經歷了幾次很危險的時刻。除營養問題之外,馮老爺子的意識狀態、多重耐藥、血流動力學的評估,重重考驗擺在醫生們的面前,他們每走一步,都是慎之又慎。
在歷經138天的“生死難關”之后,馮老爺子終于痊愈出院。后來,馮老爺子的家人告訴張蕾,在出院那天,他們扔掉了原本寫好的追悼詞,轉而為醫生們寫了一封感謝信。
更好的生活
在ICU里,最緊迫的是時間,最漫長的也是時間。
張蕾陪伴馮老爺子在昏迷與清醒間和病魔斗爭了138天,最終馮老爺子以穩定的狀態順利出院;陳丹上班時隨身帶著紙筆,讓病人能夠第一時間寫出自己想說的話;熬過漫長恢復期的老單每次去復診,都要看看自己的醫護朋友們。
重癥治療的意義與情感支持不斷地蛻變與沉淀。陳丹說:“病人離開ICU并不是最終的目標,未來更好的生活才是。”
一天清晨,張蕾打開手機,看到馮老爺子的女兒發來的視頻。視頻里的老人正跳著廣場舞,精神矍鑠,絲毫不見病痛的困擾。“即使離開了醫院,他也愿意和你分享自己的生活。”張蕾覺得,這是身為重癥醫生最幸福的時刻。
重癥室的日常里,不僅需要科學、包容,也含有對個體的支持。全面的關懷才能最終驅散病痛,讓孤獨潰敗,支撐病人和家屬去迎接一個全新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