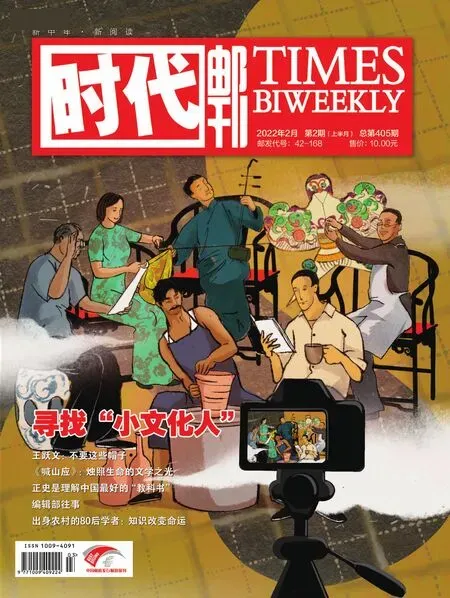出身農村的80后學者:知識改變命運
● 呂德文

畢業于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研究生班的黃國平,1987年出生在四川南充一個小山坳里。他家境貧窮,12歲時,母親離開了家,17歲時,父親遭遇車禍去世。2017年,他在自己的博士論文致謝部分中寫道:“在煤油燈下寫作業或者讀書都是晚上最開心的事。如果下雨,保留節目就是用竹筍殼塞瓦縫防漏雨。高中之前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夜里抓黃鱔、周末釣魚、養小豬崽和出租水牛……”

▲ 肖清和

▲ 黃國平
他還寫道:“這一路,信念很簡單,把書念下去,然后走出去,不枉活一世。”
現在,他就職于某互聯網公司人工智能實驗室。
1980年出生于安徽潛山一個小山村的肖清和,同樣家境貧寒。8歲那年,他的爺爺病逝,家中無一分錢積蓄,多虧一位醫生資助了20元,才最終辦了喪事。小升初考試時,他考了全鄉第二名,卻因為交不起學費而失學,只能邊放牛邊找書看。第二年春天,在母親的努力下,他終于重返學校。1999年,他考上了北京大學。
2009年,他在博士論文后記中寫道:“母親不止一次和我說過,她不能死,她要忍,她要堅持,因為她要讓我上學,她要讓她的兩個孩子好好活著。”
現在,他是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同時還是上海大學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副主任。
像黃國平、肖清和這樣的人并不少,他們都是80后,出身農村,幼時家庭極端貧困,在他人的幫助下才得以繼續上學,通過努力最終取得了較高學歷或較好的工作機會,擺脫了貧困。
他們的奮斗歷程,是“知識改變命運”的過程,也應和著我國改革開放后經濟騰飛、教育發展的進程。從更深層次來看,他們在某些方面已成為我國知識界的獨特存在,并將為我國的發展貢獻更多力量。
折射社會變遷
今日,出身農村的80后學者是一個數量龐大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的心靈體驗,很大程度上折射了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社會變遷。
自古以來,出身底層的知識分子都是少數,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后,廣大的普通群眾才獲得了平等的教育機會,進而開啟了真正意義上的精英流動。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共產黨便在革命隊伍和邊區開展了識字運動,為中國革命儲備了人才。新中國成立后,掃盲運動在全國各地蓬勃開展,完整的公立教育體系也逐步建立起來了,連最普通的底層民眾也有機會接受文化教育甚至高等教育。
改革開放后,“知識改變命運”幾乎成了中國農村最具影響力的時代口號之一。高考制度的恢復,為來自各階層的人提供了更為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義務教育的全面普及,則使得絕大多數農民子弟接受了基礎教育。優秀的農民子弟也有機會獲得相對優質的教育資源,繼而考上大學,甚至是比較好的大學。尤其是,20世紀末中國高校開啟了大規模的擴招,這客觀上為農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創造了更多機會。
可見,“知識改變命運”是制度實踐的結果。
家庭合力奮斗
80后出生之時,還處于計劃生育政策實施的初期,他們所在的家庭也多是多子女家庭。在當時的經濟社會條件下,普通家庭供一個孩子讀書,尤其是完成義務教育之后繼續供其上高中、大學,的確是一項重大家庭決策。
絕大多數農民家庭對子女的投資是理性的,父母如果認為家中子女聰明好學,有較大的希望考上大學,一般都會積極支持其完成學業,很多農民甚至“砸鍋賣鐵也要供孩子上學”。很多極貧家庭,也的確因為供孩子上學而負債累累,生活更加艱辛。
彼時,村莊的社會結構比較完整,鄉土社會的倫理文化也比較有活力。鄉土社會既有溫情脈脈的一面,也有冷酷無情的一面,很多80后農家子弟都體驗過鄉土社會的人情冷暖。極貧家庭在農村常常受到排斥,事實上,讓子女“有出息”,最終在當地揚眉吐氣,是很多農村父母培養子女的根本動力之一。很多農家子弟,將通過個人奮斗擺脫家庭困境視為自己的人生責任。
當然,農家子弟如果足夠優秀和爭氣,往往也會獲得更多善意。每一個通過考學走出困境的80后農家子弟,都或多或少得到過親朋好友甚至是無關人士的無私幫助。
流動的中國
某種意義上,80后很可能是具有完整鄉土生活體驗的最后一代人,他們完整體驗了鄉村社會的人情世故。他們的人生經驗里,對中國社會的底層架構并不陌生。“知識改變命運”之所以有力量,是鄉土社會的傳統和現代教育體系相互碰撞的結果。
相比之下,90后農家子弟的農村生活經驗則未必完整。20世紀90年代后,流動人口數量快速增長,很多90后農家子弟都當過“留守兒童”,他們很難真正觸碰鄉土社會的文化沖擊了。
在90后的成長經歷中,農村教育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教育市場化對公立教育體系有巨大沖擊力,城鄉差距也越來越大。一些90后農家子弟,甚至需要“離土離鄉”到城市接受比較好的教育。
可以說,80后為家庭、家族和家鄉而努力奮斗,而家庭、家族和家鄉也為其成功而感到榮耀的體驗,90后就會越來越難理解了。
獨特的存在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群體,接受國家正規學術訓練的80后農家子弟很可能是一個獨特的存在。
在學術界,知青一代是顯著的存在。他們在改革開放初期進入學界,很多人是各學術單位的奠基者。由于有上山下鄉的經歷,他們亦有底層生活經驗,對中國社會的底層架構有深切認識。這些人生經驗對他們的學術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
作為知青一代的學生輩,60后和70后的代際特征并不明顯。但80后學者,卻是一個特征鮮明的知識分子代際群體。尤其是來自農村的80后學者,很可能在塑造新一代知識分子群體的某些特征。
首先,80后學者得到了專業訓練。受益于上兩代學者的努力,80后在接受高等教育時,學科體系已經比較完整,專業也比較齊全了。他們所接受的大學教育,可以說已經是專業教育了。而且,很多新的專業教育,是順應現代社會發展而開設的。這一代學者一般都在專業領域從事學術工作,有著專業的視角和堅持。
其次,他們深受學術體制的規訓。以績效考核為中心的學術管理體制建立起來,成為80后學者立身學術界的制度基礎,這使得一部分學者有強烈的職業危機感,從而偏離了傳統知識分子的身份想象。
同時,他們成長于社會巨變時代。他們的人生經歷同樣豐富,也具有內在張力,同樣會對他們的學術思想造成巨大沖擊。換言之,就學術創新而言,80后學者在經驗、專業訓練,乃至學術資源的支持上,都具有良好的條件。
致敬一個時代
客觀來說,80后學者還不算是成熟的一代知識分子群體。
知識分子是一個為國家和民族思考的群體。從學者到知識分子之間,還有一道需要跨越的鴻溝,即超越自我,讓學術工作從為個人安身的職業轉化為為生民立命的志業。80后學者成長于改革開放時期,親身丈量了時代變革的深度和廣度。這個時代是如此偉大,它在中國歷史上真正做到了精英的更替。作為這一歷史進程的當事人,80后學者有更好的條件來回饋這個時代。而一旦將時代經驗融入學術工作,再結合實踐,具有時代烙印、呼應大眾需要的學術,必定會產生。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這些80后學者在博士論文后記中回顧自己的人生經歷,不僅僅是為了感謝某些人,更是為了致敬一個時代。每一個個體的經歷,也許是特殊的,但他們最終實現了人生逆襲,卻是一系列制度實踐的結果。隱藏在中國社會內部的基因,需要我們去理解和挖掘。
我們同樣不能忘記,在80后學者的同行人中,實現人生逆襲的,畢竟是少數。而且,很多80后學者的人生逆襲,恰恰是建立在親人做出犧牲的基礎上的。他們是時代的幸運兒,也有責任為民族思考,盡力為大眾追求美好生活創造更好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