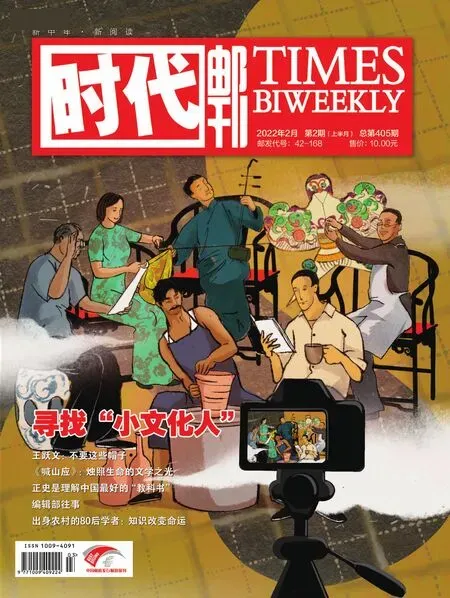鳳凰琴:一篇小說,一群人,一個村
● 喻珮
“一排舊房子前面,一面國旗在山風里飄得很厲害,舊房子里傳出一陣讀書聲……”這是小說《鳳凰琴》中關于鄉村小學的經典場景。1992年,作家劉醒龍發表敘寫鄉村教師命運的中篇小說《鳳凰琴》。對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相當數量的中國鄉村教師而言,這部作品曾讓他們“抱頭痛哭”,卻又是不忍擱下的枕邊讀物。

《鳳凰琴》及其續篇《天行者》,被認為是一部完整展現20世紀后半葉中國鄉村教師命運與中國鄉村教育史的文學作品。《鳳凰琴》的發表對當時全國200萬民辦教師轉正工作起到了推動作用。
而今,在《鳳凰琴》發表29年后,湖北誕生了一個“鳳凰琴村”。
故土上誕生“鳳凰琴村”
2021年11月,在鄉村振興的建設高潮中,湖北團風縣上巴河鎮張家寨和螺螄港兩個行政村正式合并為鳳凰琴村。
張家寨村,是劉醒龍的故鄉。鳳凰琴村,這個與他的文學作品同名的村名,是兩村合并之后,由當地的村干部、村民代表投票選出的新村名。
為什么想到以一部文學作品來命名新的村子?第一個提出這個想法的是上巴河鎮政府二級主任科員范秋軒。盡管是20世紀90年代初的事情,范秋軒對當時鄉村教師人手一冊《鳳凰琴》的畫面仍記憶猶新。“我當時去一些村里的學校,每到一所學校,都能看見老師的抽屜里有一本《鳳凰琴》。”
2020年底討論合村并組后更名的問題,范秋軒率先提議改為“鳳凰琴村”,“這部作品有影響力,我把‘鳳凰琴村’的來歷講給村民聽,他們也很贊同,希望借助文化知名度,把家鄉建設得更好。”
劉醒龍出生在湖北的江邊小城黃州,1歲多的時候,便因父母工作調動去了100公里之外的英山縣。再次回到故鄉時,他已30多歲,那次,他同父親正在小山上走著,找尋長輩的墓地。突然不遠處有人喊父親的小名,那人指了指另一處山頭,用鄉音告訴父親,墓地在那邊。
“那一年,父親在芭茅草叢生的田野上,找到一處荒蕪土丘,驚天動地地跪下去,沖著深深的土地大聲呼喚自己的母親……”正如劉醒龍所寫,“鄉土看似有根,實在是一種漂泊。這樣的漂泊者對于故鄉的夢想與懷念,是普通人難以想象的。”
正是這次尋根之旅,讓劉醒龍和故土在精神上有了更深的連接。此后,劉醒龍每年清明節都去張家寨村祭祖掃墓。
61歲的劉愛國是新組建的鳳凰琴村的黨總支書記,也是之前張家寨村的老支書。“新村名經過了村民投票,村里直接參與投票的有200多戶。”劉愛國給劉醒龍打電話,告訴他新的“鳳凰琴村”掛牌了。電話那頭的劉醒龍有許多難以名狀的感動。
“隨著鄉村的進步發展,不再是用簡單的村、寨這類原始的文化符號來給一地留下標記,而是用某一種文化熱點,或是有更廣泛意義的文化符號作為家鄉的標志,說明村民在文化品位方面有了更高追求,我為這樣的鄉村深感欣慰。”劉醒龍說。
有界嶺的地方就有“界嶺小學”
劉醒龍的中篇小說《鳳凰琴》首發于1992年,開篇便用班主任激勵張英才的口頭禪“死在城市的下水道里,也勝過活在界嶺的清泉邊”,凸顯了“界嶺”這一端與那一端的巨大反差。
回憶創作的初衷,劉醒龍說,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民辦教師非常普遍,幾乎每個村辦一所小學。他的高中同學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當民辦教師。最終,他將這些相熟的人、事、物,熟悉的鄉村生活面貌,勾勒成小說中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形象。

▲ 鳳凰琴村總支書劉愛國(左三)、鳳凰琴村駐村干部陳慧仟野(左四)與村民合影
劉醒龍寫作《鳳凰琴》時,全國還有200萬民辦教師。《鳳凰琴》的發表及影視改編,讓民辦教師群體受到關注,對民辦教師轉正工作起到了推動作用。
許多讀者都從《鳳凰琴》和《天行者》中找到自己啟蒙小學的影子。劉醒龍曾說,界嶺小學的原型地是黃岡市英山縣的父子嶺小學,在當地被稱為小界嶺。小界嶺以北之水匯入巴河,小界嶺以南之水流入浠水。凡山嶺分水之處,總有地名被慣稱為界嶺。百川千山,界嶺無數。正因為有如此多的界嶺,界嶺小學之名也擁有了普遍意義,更能凸顯出其文學典型。
界嶺小學可以視為所有艱苦地區的鄉村學校,以及堅守在鄉村教師崗位上的中國最基層知識分子的集合。它坐落在每座渴望知識的山脊上。
回憶往事,劉醒龍動情地說,“1983年5月,晚開的杜鵑花開放時,也是我由英山縣閥門廠借調到縣文化館的第二個月,和一位副館長到當時的父子嶺鄉,推動建立全縣第一座鄉級文化站。每天忙完工作后,我就往四周的山野信步走一走。那天傍晚,第一次爬上鄉政府左側的山崗,忽然發現半山腰的幾間土坯房前,豎著一面國旗,旗桿是用兩根松樹桿捆扎而成,那面國旗因掛得太久,幾乎見不到鮮紅的顏色,我知道那肯定就是當地的小學。自此以后,一連七八天,我每天傍晚都要到那道山崗上,那面國旗在晚風中飄蕩,在一面蔥綠的群山之間格外顯眼。”
1992年1月,已經調到黃州工作的劉醒龍在動筆創作時,眼前浮現出那面在父子嶺小學和莽莽大別山上飄蕩的國旗。于是,《鳳凰琴》應運而生。
村里的種子
大別山麓,巴水河畔,湖北團風縣十力學校書聲瑯瑯。該校是2009年3月將團風縣十力中學和上巴河小學合并而成,是團風縣第一所九年一貫制學校。從大山里走出去,又回到自己成長的起點任教,十力中學校長孫進回憶起自己的啟蒙老師依然感慨萬千。
“小時候在村小學上學時,老師們的生活非常艱苦,家里有農田,還要長期奉獻于教育。這些最初對于知識的渴望,對于教師這個職業的認識一直激勵著我,讓我不忘走上三尺講臺的光榮與職責。”孫進說。
學校有一棟四層的教學樓,配有實驗室、儀器室、體育器材室、圖書室等,每間教室的黑板中間還配有一個多媒體屏幕,此外還有標準化的食堂,以及塑膠跑道。學校老師介紹,放學后孩子們乘坐校車返回,有的回鄰村,有的回鎮上,家長們到指定地點接送。
2000年以后,隨著中國城鎮化建設不斷推進,農村人口大量轉移,農村子女隨遷進城,農村師資及學齡人口隨之逐年減少,全國各地村級小學也逐步退出歷史舞臺。張家寨小學(又名新興小學)于2002年因生源持續減少而停辦,教師合并到標云崗小學。
在《鳳凰琴》成為現象級文學作品的17年后,劉醒龍推出續寫的長篇小說《天行者》,并憑借該作斬獲茅盾文學獎。從中篇小說《鳳凰琴》到長篇小說《天行者》,他將20世紀后半葉中國鄉村啟蒙教育遙遠而模糊的概念,轉化為一幅鮮明的全景式圖像。
“中篇表達是一段情懷,長篇一定是對命運有所感悟,才能寫得出來。”劉醒龍說,長篇小說不是寫故事,是書寫一段命運、一個時代。帶著生活閱歷和對人生的體察,慢慢走入歷史,才會看得更加清晰。
劉醒龍認為,一群看似卑微渺小,看似普通的平凡人,往往具有很大的象征意義,迸發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在看似做不出任何驚天偉業的地方,怎么實現人生的價值,這是時代交付的命題。
“我是從鄉村走出來的人,有責任、有義務把記憶留下來,把一些小小的變化所包含的內核告訴世人。”劉醒龍說,任何變動總會帶來一些連鎖反應,比如改村名這件事也許就是一個契機,撬動鄉村發展的契機。
站在原張家寨村委會門口,劉愛國指著對面一處寬敞的大舞臺說,劉醒龍十分關心家鄉建設,村里這塊“鄉村大舞臺”上的對聯正是他所作所書,“古今妙戲從無獨唱,山水豪情當有對飲”,短短兩句話,彰顯出這個小村落的文化格調。
“如今村集體在銀行有了存款,村民的生活越來越好。”劉愛國自豪地說。
駐村干部陳慧仟野大半年以來一直籌劃著全鎮行政村布局調整的問題,合并、取名這樣的一件件大事拆分成無數件小事,填滿了他近期的工作和生活。
“各種聲音都有,也有反對的聲音,不同意合并的、不同意取新名的,最忙的時候一天接50個電話,還要集中座談,個別交流。”投票前一晚,陳慧仟野還在螺螄港村一位老支書的家里談心,最后一刻才終于做通了工作,讓對方破除了心中的憂慮。最終,同意合村并組的得票率高達98.7%。
“尊重歷史,尊重民意,尊重未來。”這是陳慧仟野對于取名“鳳凰琴村”的看法。在他心里,劉醒龍更像是“村里的種子”,希望借勢提升劉醒龍故鄉的知名度,大力推動鄉村振興。
“鳳凰本就是天生的一對,兩個村合在一起,寓意吉祥、美好。”村里的老人黃新元這樣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