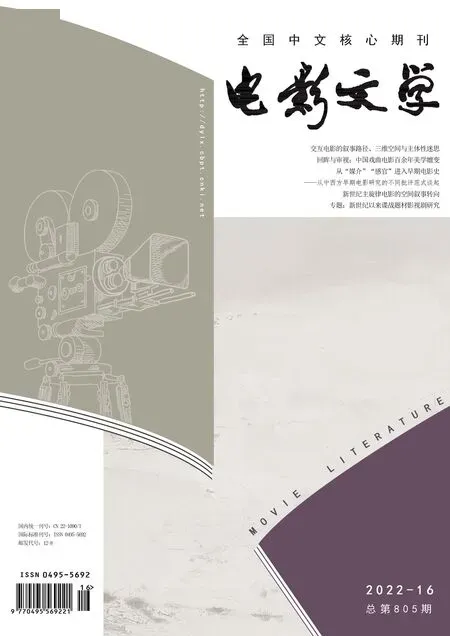新世紀主旋律電影的空間敘事轉向
徐明亮 杜 安
(貴州師范大學傳媒學院,貴州 貴陽 550000)
在敘事作品中,“空間也屬于一種敘事元素”,運用或借助空間進行敘事的手法被稱為“空間敘事”,故事內人物生活與活動的場所被稱為“敘事空間”。在電影這一敘事藝術中,“空間敘事”也被“講故事的人”廣為使用。“電影是照相術的產物”,其如實再現物質現實的能力使得“人們容易產生錯覺,以為外部現實世界就是銀幕上所呈現的世界那樣”。電影通過視聽語言的運用,對現實物質空間進行呈現和表征,能夠改變人們對現實世界的認知想象。
主旋律電影是“貫徹中國當代主流意識形態并以塑造英雄人物形象(或正面人物形象)為主要導向的影片”,是能夠正確反映我們的時代精神和我們社會的本質,能夠在社會上產生積極向上的思想引導的作品。筆者發現自21世紀以來,仍舊“以傳輸國家意識形態話語為創作導向,以表現國家主義、民族主義、英雄主義、時代精神為價值內核”的主旋律電影的空間敘事策略發生了轉向,具體表現為:敘事空間從“沉重”空間轉向“輕逸”空間、從歷史空間轉向現代空間、從本土空間轉向異域空間、從單一空間轉向多元空間、從真實空間轉向“擬象”空間。在本文中,筆者希望通過對新世紀主旋律電影空間敘事轉向圖景的勾勒,以及對主旋律電影發生空間敘事轉向的原因、意義和價值的探析,讓主旋律電影制作者認識到主旋律電影界發生空間敘事轉向這一藝術思潮的具體表現和原因,以期為主旋律電影制作者在今后的影片創作實踐中講好中國故事提供空間敘事層面上的借鑒。
一、從“沉重”空間轉向“輕逸”空間
巴什拉在《空間的詩學》中提出,空間不單單是物質性的物理場所,它同時也是“充斥著人們的記憶和想象”、“承載著想象或虛構價值”的精神空間,是人類意識的居所,是人們的內心回憶和空間形象相互交織、融合的共同體。從敘事空間“所承載的想象或虛構價值”的輕重的維度來觀照,在20世紀,主旋律電影的敘事空間是“沉重”的,是積淀著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凝結著時代精神和革命文化內涵、表征著意識形態的宏大場所,是愛德華·索亞所謂的被人們賦予時代精神和社會文化內涵的“第三空間”,其中浸潤和棲居著人們的歷史想象、國家記憶,兼具物理性、精神性和社會性。這類空間通常表現為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和社會意義的歷史性事件的發生場所。例如,《長征》的故事空間設定在湘江、赤水河、大渡河、甘肅會寧等“紅色”場所,全景展現出長征的全過程,表現出共產黨人信仰堅定、不畏艱險的偉大胸襟;《孔繁森》的敘事場所選定在“世界屋脊的屋脊”——阿里,講述了孔繁森同志在西藏阿里地區工作期間,為百姓排憂解難,為西藏經濟發展和文化繁榮做出偉大貢獻的故事,展現出一位共產黨員的責任與擔當,體現出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與使命。依托于“沉重”空間進行空間敘事,主旋律電影復現出中國人民奮發圖強、流血犧牲的悲壯歷程,傳承了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表現出敘事者對先輩們英雄品德和英雄行為的認同,有利于喚起觀眾對國家和社會的集體記憶,維系人們的國家信仰和文化認同,也使得主旋律電影獲得了一種崇高的、史詩般的美學品格。
而21世紀以來,主旋律影片開辟出一種新的空間敘事手法,電影藝術家們開始將影片的故事空間設定在“輕逸”空間。這類空間并不是人民群眾的家國意識、社會記憶、民族想象的居所,而是“無名”的地方場所,是不為世人所熟知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空間。例如,《我和我的家鄉》就由“北漂一族”的生活市井、貴州黔南阿福村苗寨、浙江千島湖望溪村、陜西毛烏素沙漠、東北鄉村等不背負中華民族同胞的國家想象、歷史想象的敘事空間串聯而成,影片真情勾勒出社會主義新時期新農人怡然自得、和諧完滿的新畫像,展現出新時代中國脫貧攻堅的勝利圖景。
在筆者看來,21世紀的主旋律電影通過“輕逸”空間的敘事設定,實現了“小敘事”的敘述實踐,向觀眾述說出地方化、個人化的故事,使得主旋律電影獲得一種微小化、輕盈的美感,避免了依托于“沉重”空間而進行的“宏大敘事”帶給觀眾的說教感、沉重感、嚴肅感,讓觀眾能夠以一種輕松的心態觀影,并使得觀眾可以從個體的微觀視角更具體地洞悉和體認到影片傳達的宏大概念,彌補了以往主旋律電影“不接地氣”的不足。例如,《我和我的家鄉》依托于“無名”空間進行“輕逸”空間敘事,依次向觀眾講述了發生在熱心市民張北京、農村發明家黃大寶、支教老師老范、治沙英雄喬樹林、基層村干部馬亮等個體身上的家鄉故事,觀眾能夠從發生于他們身上的故事中更切近地透視到中國的“山鄉巨變”,更細微地體認到中國醫療、科技、教育、生態、民生事業的進步,從而會更加堅定自己的國家信仰認同。
二、從歷史空間轉向現代空間
巴赫金認為,藝術中表現的事物是一個“藝術時空體”,“時間的標志展現在空間里,而空間則要通過時間來理解和衡量”,換言之,藝術中的空間不僅是三維立體的物象,其更具有第四維——時間的屬性。從敘事空間所處的時間坐標的視角來品鑒,在20世紀,主旋律影片的敘事空間多為歷史空間,具體體現為保留、存儲、展示歷史文化和凝固人們的歷史記憶的地方場所、歷史上的政治事件發生的場所、英雄模范人物生活的地域、革命戰爭發生的地區,講述的故事皆旨在歌頌黨的正確領導、前輩先烈的英雄精神。例如《秋收起義》將敘事空間設定在1927年湘贛邊界的革命老區,藝術地再現了“秋收起義”的全過程;《上甘嶺》將故事空間限定在抗美援朝時期的“上甘嶺戰役”戰場,講述了上甘嶺戰役中,中國志愿軍堅守陣地、與敵人浴血奮戰的故事。通過將敘述視角限定在歷史空間之中,主旋律電影再現出波瀾壯闊的中國人民浴血奮斗的悲壯史,建構起國家和民族的歷史敘述,有利于喚醒觀眾的歷史記憶,增強觀眾對國家和民族的歷史認同。
21世紀以來,主旋律電影創新出一種“現代日常敘事”的敘事模式,不同于以往“聚焦歷史、歌頌英模”的主旋律電影敘事程式,新世紀的主旋律電影不再將敘事空間限制在距今較為久遠的“紅色”歷史空間,而是將敘事視點移焦于新世紀的現代日常空間,講述了在新世紀日常生活當中各行各業普通人的不平凡的故事,凸顯出中國當下時代的時代風貌。例如,《中國醫生》將敘事空間設定在武漢金銀潭醫院,講述了中國各地“白衣逆行者”不顧自身安危守護國人生命安全的動人故事,詮釋出“中國醫生”醫者仁心、大愛無疆的高貴品質,側面展現出中國速度和中國力量;《中國機長》將故事空間設置在川航3U8633航班,講述了飛機途中遇險,終于化險為夷的故事,謳歌了“中國機長”敬畏生命、敬畏責任的職業精神,折射出中國航天的安全;《緊急救援》的故事空間在山林、火海、海上等救援現場,影片講述了中國海上搜救中心救援隊員執行海上救援任務的故事,展現出中國救撈人勇于擔當的一面,凸顯出中國救援精神和國際人道主義精神。
詹姆斯·凱瑞在《作為文化的傳播》中提出,“傳播是一種通過對符號系統的建構來生產、維系、修正和轉變現實的符號過程”。在筆者看來,主旋律電影的傳播,也是一種通過電影藝術的“符號系統以創造和傳遞關于現實的知識的符號過程”。在21世紀,通過運用現代空間敘事策略,主旋律電影講述出當下時代的中國好故事,展現出現代中國堅持人民生命至上的理念、國力強大、不畏困難等諸多現實,建構起觀眾的現代國家想象,使得觀眾堅定自己的國家身份認同,維系了現代中華民族這一“想象的共同體”。例如,《中國醫生》講述的是發生在中國普通人身上的中國故事,就會讓觀眾認識到中國醫務人員的英勇與無私,想象到現代中國醫療衛生系統的力量和速度,進而觀眾會對國家治理產生信心和自豪感,對現代中國的國家信仰會得以堅定。
21世紀的主旋律電影通過現代空間敘事,在建構觀眾的現代想象的同時,也旨在表現出現代人的情感結構,以期喚起現代觀眾的情感共鳴,使得觀眾獲得情緒浸入式的觀影體驗。雷蒙·威廉斯認為,情感結構是生活于特定時代的人們的“一種特殊的生活感覺,一種無須表達的特殊的共同經驗”,生活于不同時代、不同空間的人們,其產生的情感結構是有差異的、獨一無二的、具有時代個性的。這種感覺或經驗不是脫離特定歷史與社會條件的,而是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內具有穩固而明確的共通性,是處于某一個時代人所能察覺到的共同文化意識。他同時認為,文學和電影是記錄感覺結構的物質載體。“人們只有真正身處那個時代才能切身經驗、感受那一時代人們的感覺結構,而后人由于受到其所處時代利益關系和價值體系的影響,其在閱讀文學和電影時,是無法真正觸及那一時代人們的感覺結構的”。所以,21世紀主旋律電影通過運用現代空間進行敘事,講述出生活于現代社會空間中現代人的生活故事,反映和折射出現代人的感覺結構,表現出現代人的生活經驗和實踐意識。而現代觀眾由于和21世紀主旋律電影中的角色共處于同一歷史時期的社會之中,其感覺結構具有共通性,更能理解影片角色的心理、生活感覺和社會體驗,更易與影片人物產生情感共振。例如,不同于20世紀主旋律電影表現的是中國革命、改革、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先輩們的感覺結構,在《我和我的家鄉》中,電影里五個故事皆把目光投向現代家鄉,《北京好人》展現出中國鄉村醫療的發展成就,《天上掉下個UFO》刻畫出農民發明家用科技助力鄉村振興的智慧與浪漫,《最后一課》歌頌了為鄉村教育奉獻青春的鄉村教師,《回鄉之路》讓觀眾對身邊的“治沙英雄”們心生敬佩,《神筆馬亮》讓觀眾為基層村干部獻身農村建設的“大愛”精神而動容。影片記錄了脫貧攻堅時期中國人民共同的生活經驗、精神風貌、社會實踐,折射出“詩意地棲居”于中國鄉土的現代農民積極奮進、熱愛家鄉、理性科學、富有智識的感覺結構,這種感覺結構更易被“同時代的人”——與影片角色生活于相同時代環境、對脫貧攻堅有共同社會經驗和時代記憶的新時代的觀眾——所把握,影片人物信仰國家的認同心理和參與新農村建設的時代經驗也更易被現時代的觀眾所理解。觀眾能夠對影片人物的社會心理和生活經驗感同身受,對影片人物產生共情,更有利于新主旋律影片的主旨、內涵和意蘊被觀眾接受和理解。
阿爾都塞曾指出,“意識形態是個人同周圍現實環境的‘想象性關系’的再現,它是一套隱蔽的觀念體系,人們往往根據這種觀念體系來感知和想象世界,在意識形態的鏡像中識別、想象自我的形象和文化身份”。大眾傳媒就是一種“意識形態機器”——一種國家進行社會控制的非暴力性手段,目的在于傳輸、宣揚國家的意識形態以潛移默化地教化公眾,將無社會特征的個體(自然人)“詢喚”(塑造、社會化)為具有社會屬性的主體(社會人)。筆者以為,21世紀主旋律電影通過現代空間敘事,其目的也在于通過意識形態的傳輸,將公眾塑造為具有自我“民族—國家”身份認同的主體。例如,《緊急救援》通過講述中國救撈人執行救援任務的敘述實踐,傳遞出的意識形態——現代中國“民族—國家”(在影片中,救援隊是“民族—國家”力量的延伸,隱喻著“民族—國家”)是愛護子民的“家長”,就會促發、引導觀眾聯想起自己和周圍現實環境(國家)的關系。當觀眾看到影片中和自己同樣膚色、說著同一種語言、生活于同一個國家領土范圍內、受同一個國家力量保護的人們的故事時,觀眾也會想象出和確認自己在社會中的身份歸屬“位置”和社會角色——我也是現代中國的一員、現代中華民族的同胞。當觀眾對這種意識形態內化和認可之后,21世紀主旋律電影就實現了其“詢喚”個體的目的——“召喚”出對自我社會身份產生認同的現代中國的“民族—國家”主體,維系了新世紀中國“民族—國家”主體的國家信仰與民族認同。
傳播效果理論“模仿理論”認為,電視、電影等大眾傳媒表現了人的行為方式,這種表現能作為行為“榜樣”讓受眾模仿。筆者認為,21世紀主旋律電影對現代空間敘事策略的運用,其目的也在于通過電影媒體去再現和放大現代社會各行各業中“平凡英雄”不平凡的精神和實踐,引導觀眾進行模仿和學習,以形塑出更多現代社會的“行業英雄”,有利于實現傳播協調社會、重構現實秩序的目的。例如,《烈火英雄》以“大連7·16油爆火災”為原型,講述了沿海油罐區發生火災,消防隊伍不畏艱險、團結一致、奮勇抵抗,以自我生命為屏障,堅決捍衛國家及人民財產安全的故事。影片真切表現出消防員勇往直前、不畏犧牲的精神,真實描摹出“最美逆行者”在危險面前流露出的英雄主義姿態,就有利于使得現實生活中的消防員受到銀幕上消防英雄們舍生取義、堅毅頑強的精神信念的感染,以其為行為“榜樣”,并模仿其報效國家、奉獻社會、英勇無畏的實踐行為。相應地,現代社會中,將會有更多的“烈火英雄”被培養和塑造出來。
三、從本土空間轉向異域空間
電影“事件發生于空間當中”,而事件是人為制造的,由于人的行動能力和行動場域有限,相應地,事件的發生現場——敘事空間——也是有地理范圍邊界的。從敘事空間所位于的地理坐標的層面來比較,在21世紀以前,主旋律電影的敘事空間大多是在本土空間,主要講述的是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革命戰爭故事、改革人物故事、時代模范故事。例如,《開天辟地》選取的敘事空間是北京和上海,再現出毛澤東、李大釗等革命志士創建中國共產黨的艱辛歷程;《焦裕祿》呈現出的敘事空間是河南省蘭考縣,將焦裕祿在蘭考工作期間帶領全縣干部群眾治理風沙、水澇、鹽堿“三害”的故事向觀眾娓娓道來。主旋律影片通過本土空間敘事,引導觀眾回顧中國歷史瞬間,能夠使得觀眾銘記過去,認識到國家的偉大與崇高,受到先輩們高尚精神的感召,堅定自己的國家信仰。
及至21世紀,主旋律電影沒有因循過去將敘事空間局限于中國本土空間的陳規,而是做出了將敘事場所延伸至異域空間的突破。例如,《戰狼2》中,故事發生在非洲國家,上演了一出中國士兵拯救境外遇險同胞和難民、捍衛世界和平的好戲,成功塑造出了新一代中國軍人的英雄形象;《紅海行動》將敘事空間鎖定在北非,講述了中國海軍蛟龍突擊隊執行撤僑任務,并成功摧毀恐怖分子販賣核戰原材料陰謀的故事,體現了中國海軍強烈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精神。
在《東方學》中,薩義德指出,西方世界為了實施對異己力量的文化霸權——統治、重建、管轄文化“他者”——而“發明”出東方主義話語。在這種話語實踐的“框架”下,地理位置相異于西方世界的部分歐亞國家被“東方化”成和西方世界對立的“東方世界”,中國也被命名、界定為“遠東”的范疇,被“生產”“想象”、塑造為落后、邪惡、帶有威脅性的“他者”,被主觀賦予破敗、野蠻等否定性負面價值。21世紀的主旋律電影通過異域空間敘事,全景描摹出中國力量與“他者”勢力的對抗沖突情境,形象地反映出國力強盛、愛護生命、胸懷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當代中國形象,有利于洗刷西方世界“東方化”出的負面的、扭曲的中國形象與偏見。例如,在《戰狼2》中,當非洲國家發生叛亂時,中國海軍派出軍艦執行撤僑行動,彰顯出愛護人民生命、現代化軍事力量強大的國家形象;以冷鋒為代表的中國軍人不僅拯救自己國家同胞脫離戰亂的險境,同時也拯救華資工廠中的眾多外籍員工于水火,隱喻出博愛善良、心系世界人民安危的中國風貌。
四、從單一空間轉向多元空間
在馬爾丹看來,電影的敘事空間具有構造性。他認為,電影在處理空間時,通過將許多空間段落進行并列、聯結,可以創造一個綜合的整體空間。在庫里肖夫的“創造地理實驗”中,我們也可以認識到電影中敘事空間的組織性與構造性,即電影中完整的敘事空間是通過對各個鏡頭中再現的局部的場景空間進行“裝配”而構成的。觀眾利用其“完形心理”機制可以在心理意識深處建構起一個完整的敘事空間,獲得對敘事空間的“完形”感知。換言之,觀眾在觀影時,會自發性地啟動一種將事物進行想象性的拼貼、聯系起來的心理機制,在這種心理機制的作用下,“觀眾會有意識地對自己從電影畫面中經驗到的場景空間進行組織、拼接、縫合,建立起各個場景空間之間的聯系”,從而在腦海中生成、形構出一個抽象的完整、立體、宏觀的敘事空間。從觀眾腦海中想象出的敘事空間的表現樣態這一角度來體味,在20世紀,人們在觀看每部主旋律電影之余,在腦海中構想出的敘事空間只有一個,影片講述的故事也只有一個。例如改編自巴金小說《團圓》的影片《英雄兒女》,描寫了以王成、王芳為代表的“英雄兒女”在朝鮮戰場上流血奮斗的故事,表現出“最可愛的人”舍生忘死、堅強勇毅的無畏精神。影片中支撐敘事情節開展的諸多空間如朝鮮戰場、志愿軍指揮部、文工團表演舞臺等,都是具備情節上的聯系性的,各個敘事空間隨著故事人物的行動、情節的發展而展開,共同服務于統一的敘事主題:講述震撼人心的英雄兒女故事,描摹英勇無畏的英雄兒女形象。
21世紀以來,在主旋律電影譜系中,一種“主題—并置”敘事模式的電影創作類型蔚然成風,這種電影類型類似于“故事集”,一個電影文本由多個主旨相同的故事以并置的結構形式組合而成,各個故事之間沒有敘事學意義上的時間、空間和因果邏輯聯系,而是自足自在的。人們在觀影過后,在腦海中對主旋律電影會產生一種多個敘事空間并置、彼此割裂的印象。例如影片《我和我的祖國》就在共同的“展現人們的愛國情懷”的主題統攝下,并置式地敘述了七個時間、空間上毫無“敘事性聯系”的故事:《前夜》復現出開國大典前夜,電動旗桿設計師為保障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上空順利飄揚,不舍晝夜、攻克難題的過程;《相遇》將鏡頭聚焦于研制原子彈的科研人員舍棄小我的奉獻精神;《奪冠》通過再現上海石庫門弄堂內,人們觀看中國女排奧運會奪冠的故事,折射出人們強烈的國家認同感;《回歸》歌頌了在香港回歸時,中國外交官、儀仗隊軍人、香港警察、鐘表師傅等人堅決捍衛國家主權的意識;《北京你好》以喜劇化的風格為人們演繹出一出人們爭奪北京奧運會門票的好戲,凸顯出人們的民族自豪感;《白晝流星》描摹出草原少年對國家航天技術的敬畏之心;《護航》雕刻出閱兵式中預備飛行員“靜穆的偉大”……影片通過不同時空故事的拼貼、構成,彰顯出不同時代中華兒女對祖國無法割舍的情感和濃烈的愛。
在《想象的共同體——民族意識的起源與散步》中,安德森指出,傳播科技是個體在心理意識深處召喚、想象出“民族”意象——“想象的共同體”——媒介,在社會中扮演著黏合劑的角色,能夠聯結起個體和族群同胞,促進個體“想象”自身和所屬民族群體的關聯,有利于增加民族的向心力。例如,行動能力有限的讀者個體通過對以報紙和小說為例的印刷媒介文本的閱讀,能夠想象和意識到自己是某一民族的一員,感覺到遠方同胞的存在,產生“我”和遠方同胞同屬于一個民族國家的意識,進而民族的團結和族群凝聚力會得以延續與加強。筆者以為,21世紀主旋律電影(也屬于傳播技術)采用“多元空間”敘事策略的目的也是為了以電影為媒介,給觀眾創造出一個“想象民族國家的群眾儀式”,在觀眾腦海中召喚出他們之間互相聯結的意象——想象的民族共同體,促進民族同胞們的凝聚力,筑牢人們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21世紀主旋律電影譜系中,敘事人通過“多元空間”的選擇、組織和并置,勾勒出跨地域、多地區的敘事設想,一方面有助于不同地域的受眾通過觀看被銀幕“賦魅”的發生于自身所在地區的故事,都能夠和自身所屬于的地方社區產生情感勾連,獲得和確認一種“我”屬于這個民族、地區、文化、地方語言領域的歸屬感,堅定自己的身份認同、地域文化認同。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隔絕于不同空間的觀眾通過觀看電影中上演的各個地區的人物生活故事,想象到自己和“他們”——生活于別的地區的中華兒女——的關聯,認識到自己和“他們”都共同屬于中華民族,有利于喚起觀眾的民族身份自覺,促進各個空間地區的人們心連心,實現對觀眾民族身份的認同構建,觀眾對民族的信仰和情感依附會得以維系。例如,生活于冀中、西部戈壁、上海等地區的觀眾通過觀看《我和我的父輩》中發生于各自所在地區的故事,就會產生“我”屬于這個地區的歸屬感,觀眾對各自所屬的地域文化的認同感也會得以加強;同時,各個地域的觀眾也會意識到自己和別的地域的同胞之間所存在的地理聯系——都生活在中國國家領土范圍內、身份聯系——都屬于中華民族共同體,觀眾的民族群體意識會得以凝聚,民族的向心力和團結意識會得到增強。
五、從真實空間轉向“擬象”空間
引用語言學的觀點,電影銀幕上顯現的空間形象作為一種影像言語,作為“一種完美的空間能指”,其也是有空間所指的。從敘事空間能指的空間所指這一維度去分析,在20世紀,主旋律電影中的空間形象是“現實主義的”、源于生活的,是通過對現實物理空間的“機械復制”而生成的,其空間所指是一種在現實世界中有對應物的真實空間。例如,在《開國大典》中,天安門廣場、西柏坡等場景畫面都是實景拍攝的,無不令觀眾感覺真實;在《劉胡蘭》中,劉胡蘭“生于斯,長于斯,參加革命于斯”的云周西村的空間造型,皆是現實空間的銀幕“復原”,也是不令觀眾產生“間離”之感的。
在21世紀,由于新的電影工業系統技術邏輯的賦能,主旋律電影在空間造型時,不再依賴現實生活中物理空間的再現進行視覺空間的表征,而是利用電影工業系統的功能技術支撐,仿造出模擬現實的“擬象”空間,這種“擬象”空間是一種“超真實”的、在現實生活中沒有任何真實空間所指與之對應的空間影像。例如,《攀登者》改編自1975年的真實事件,講述的是中國攀登隊成功登頂“雪山”珠穆朗瑪峰并完成高度測量,奪回珠穆朗瑪峰實際高度的國際標準定奪權的故事。影片拍攝場地并不是在珠穆朗瑪峰,而是取景于天津和青海崗什卡雪山,電影銀幕上呈現的狂風呼嘯、暴雪肆虐的“珠穆朗瑪峰”就是一種利用新型電影拍攝技術和特效技術制作合成出的模擬珠峰的“擬象”空間,是一種奇觀化的、“仿真”的“景觀”。
首先,21世紀的主旋律電影通過“擬象”空間敘事,能夠使得電影藝術創作者突破現實條件的束縛,實現理想的藝術形式的傳達,促進觀眾認同電影的敘事邏輯和價值內核,使得電影“叫好”。例如,在《攀登者》中,創作者可能囿于自然天氣條件、拍攝周期、制作資金等原因,無法真實再現出珠峰、雪崩、風暴等物質現實。但是通過技術特效“擬仿”出珠峰、雪崩的“擬象”,導演解決了再現的難題,完成了理想的電影視效的呈現,有利于導演的意識和藝術理念的傳達。珠峰等“擬象”空間能夠作為一種“劇戲容積”——生成戲劇性事件的情境,強化攀登者和自然環境的戲劇沖突,渲染出攀登的緊張、危險,推動敘事情節的進程,能夠有力地彰顯和突出中國攀登者熱愛祖國、不畏艱險、百折不撓的攀登精神。
其次,“擬象”空間敘事也有利于打造出奇觀化的銀幕景觀,帶給觀眾新奇、沖擊、轟動的“驚顫”審美體驗,順應了當下視覺文化時代“奇觀電影正在取代敘事電影成為電影的主導形態”的創作潮流,能夠吸引觀眾觀影,使得電影“叫座”。例如,《攀登者》中的珠峰、雪崩、風暴等“擬象”奇觀,《中國機長》中營造的飛機失控、抖動、顛簸等“擬象”場面,以及《烈火英雄》中利用特效技術“擬仿”出的火災“擬象”,無不帶給觀眾新奇、刺激、震撼的奇觀化視覺體驗。
結 語
在21世紀,主旋律電影創新出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使得主旋律電影“茁壯成長”。主旋律電影敘事者通過創新性的空間元素的選擇、再現和構造,建構出“陌生化”的敘事空間,營造出別開生面的戲劇情境,敘述了不落窠臼的故事,表現出獨出心裁的故事內涵,有利于改變人們腦海中對主旋律電影產生的刻板印象,魘足新世紀觀眾變異的、追求新奇的審美心理,讓觀眾在享受視聽盛宴的同時,潛移默化地受到國家意識形態話語的洗禮、社會主流思想精神的感召,國家信仰和文化認同得以維系。
但是筆者以為,主旋律電影在創新空間敘事策略的同時,也不應該忽視影片故事中的人物塑造和情節安排,因為人物和情節同樣是構成故事所需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在人物塑造層面,羅伯特·麥基認為敘事作品要塑造出有“弧光”的人物形象。換言之,他認為“最優秀的故事作品也注重人物真實內心的展現和真實性格的揭露,注重人物的本性發展軌跡或變化的表現”。在情節組織層面,什克洛夫斯基認為“藝術的手法是增加人們感受事物的難度和時延的復雜化形式的手法”,他提倡敘事人要“敘述出情節波折的故事,以滿足觀眾體驗和領悟藝術自身的目的”。因此,筆者期望在今后的主旋律電影世界里,“敘事人”在借鑒和創新主旋律電影空間敘事表達方式的同時,也不忘在人物塑造和情節設置層面展現出更多的想象力,塑造出有“弧光”的人物,編構出具有波折的情節,繼續雕刻主旋律電影新面孔,努力使主旋律電影的“藝術形式與通行的、正常的、現有的藝術規范相背離,以造成‘差別化’的藝術審美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