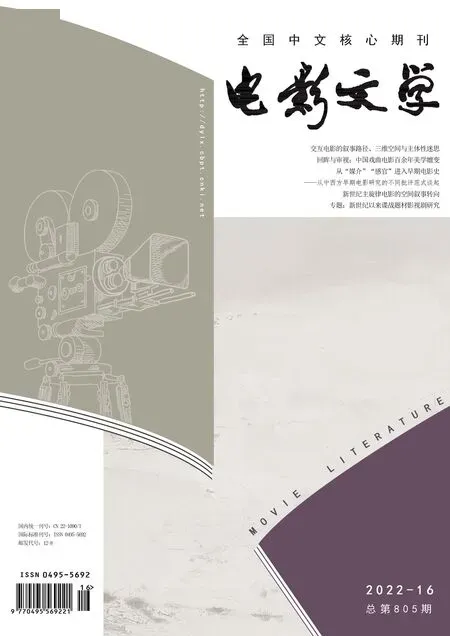交互電影的敘事路徑、三維空間與主體性迷思
李興國 劉奕鑫
(1.河北傳媒學院影視藝術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00;2.河北傳媒學院研究生院,河北 石家莊 050000)
媒介理論家保羅·萊文森在他的著作《數字麥克盧漢——信息化數字指南》中提出“因特網及其體現、證明和促進的數字時代,是一個大寫的補償性媒介”,誠然,我們已然進入一個復合型媒介的時代。交互電影作為影視藝術與游戲產業創新融合的產物,近些年頗受學者們的青睞,與之相關的研究成果也日益增多,其研究視野多聚焦于影游融合、敘事特征、脈絡溯源、影像本質等相關議題。本文將立足于新媒體時代背景,運用數字媒體學者列夫·馬諾維奇提出的新媒體語言相關理論對交互電影中的敘事和空間展開詳盡的分析,進而立足于人類的主體性,思忖交互電影于人類的賦能與解構。
一、交互電影的敘事路徑
數字時代的“先知”麥克盧漢提出“一種媒介是另一種媒介的內容”,交互電影作為影視藝術和數字游戲的融合,一方面將影視藝術的電影理論、視聽語言語法等作為工具箱引入其中:另一方面將數字游戲數值化、自動化、模塊化、多變化的索引性信息處理特征融入其間,形成循環與線性并存的伸縮式敘事路徑,為用戶帶來別具一格的審美體驗。
(一)神話行動元模型
交互電影中,用戶擺脫了傳統影像消費中旁觀者的角色,以編碼者的姿態入場,以任務為驅動,輔以界面提示的操作引導,通過操縱交互電影中的數字化身,游走于分布式的劇情支線,最終完成任務,獲得獎勵。在這個過程中,神話行動元模型賦予交互電影穩固的線性故事主干。
語言學家格雷馬斯在其著作《結構語義學》中以自己總結的兩對行動元——主體/客體、發送者/接受者為基礎,融合普若普在《俄國民間童話的形態學》中提出的31個“功能”和蘇里奧在《二十萬個戲劇情節》中提出的六個“戲劇功能”,最終梳導出三對行動元范疇,即主體/客體、發送者/接受者、輔助者/反對者,這為支線繁多的交互電影架構了穩定的核心主干敘事路徑。以《隱形守護者》為例,肖途(主體)在戰亂頻繁、民族危亡的時代環境(發送者)熏陶下,渴望民族獨立、國家統一(客體),在恩師方老的引導下成為一名在敵區潛伏的共產黨員。肖途的主要任務是在日軍、國統軍和上海地方勢力之間周旋運作,以獲取有價值的情報信息,在此過程中以武藤志雄和李峰為代表的反對者們對肖途的潛伏工作屢屢迫害,同時肖途也受到以莊曉曼、陸望舒為代表的輔助者的幫扶。肖途即用戶的數字化身隨著劇情的推進將經歷數次選擇,其結局大致可分為兩個方向:初心如磐,為國家和民族的獨立復興奮戰到底,最終犧牲自我或苦盡甘來/被敵對勢力所蠱惑走上歧途、身亡。換言之,肖途在與敵人步步驚心的斗智斗勇中艱難潛伏。雖然交互電影劇情紛繁、支線龐雜,但是宏觀梳理便會發覺其核心主干敘事路徑與傳統影視作品無異,兩者皆依托于格雷馬斯的神話行動元模型(見圖1)。需要注意的是,交互電影不僅是影視藝術的敘事學發揮著作用,游戲的算法規則亦隱藏其中。

圖1 《隱形守護者》之神話行動元模型
(二)核心與從屬
交互電影中,用戶以任務為驅動、選項為路徑,實現與NPC之間的差異化互動。用戶不同節點的差異化抉擇使NPC與用戶化身之間的好感度產生波動,進而觸發不同的情節走向,但是“隨著游戲的進展,玩家會逐漸了解這個游戲世界中建立的運行規則,進而了解到最隱藏的邏輯——簡而言之,就是它的算法”。《隱性守護者》中,如果肖途沒有在日本駐滬領事武藤志雄面前累積6分好感度,便無法開啟下一章。《底特律:成為人類》康納支線中,如果康納在與漢克的搭檔過程中沒有累積一定值的好感度,康納會被漢克槍殺,后期亦不會出現覺醒的分選項。根據交互電影的玩法設置,用戶經歷“失敗”或“死亡”結局后可讀檔重來,即用戶在算力驅動的索引性劇情循環中尋找通往下一章節的出路,在線性敘事與循環敘事并行的伸縮性敘事路徑中探索前行。值得一提的是,交互電影創作者為用戶提供可視的樹狀劇情結構圖,用戶可以在場景或者游戲結束時查看自己的游戲劇情進度,圖譜清晰地顯示出用戶選擇了哪些劇情支線、錯過了哪些劇情支線,刺激用戶沉浸式多維探索這個虛擬世界。
敘事學家西摩·查特曼指出敘事事件不僅有其聯結邏輯,而且還有其等級邏輯,進而提出主要事件—核心與次要事件—從屬,“核心事件是結構上的節點或樞紐,是促使行為進入一條或兩條(甚至更多)路徑的分叉點,從屬事件可以被去除而不會擾亂故事情節,功能是填充、說明、完足核心”,其關系圖見圖2。

圖2 西摩·查特曼核心與從屬的關系圖
這是影視藝術線性敘事結構的經典圖譜,諸核心事件連接構成有且只有一條完善的敘事邏輯主線,橫貫敘事路徑始末,主導事件的走向,從屬事件或預敘或回溯核心事件,交互電影則與此不同。交互電影汲取了數字游戲可伸縮的分布式信息分布模式,借力其模塊化、自動化的信息處理特征,打破了封閉單向的線性敘事,它將用戶的所有選項視為同等效力。依托背后的算法邏輯,用戶的每一次選擇都是一次數據的累積,累積的結果導致“及時分叉或延時分叉”,系統將自動匹配與之相對應的模塊內容。用戶自動匹配到的故事模塊可以引用西摩·查特曼的核心事件與從屬事件來進行劃分,若用戶各節點選項的數值累積導向了從屬事件,用戶將來到相應結局,繼而進入自動循環——重啟本章節。若用戶既往選項的數值累積引向了核心事件,則打破循環,進入線性敘事。綜述之,基于數字游戲伸縮性的信息分布特征,用戶通過控制化身進入半開放的自動化敘事界面,交互電影中的敘事路徑將由經典的封閉性線性圖譜(圖2)轉化為線性與循環并存的伸縮式敘事框架(見圖3)。圖3中虛線表示死亡或通關失敗,從屬事件觸發死亡或通關失敗則自動跳轉循環選項。

圖3
須知,僅有引擎驅動的數據模塊無法完成交互電影的文本建構,這僅僅是數字游戲處理海量信息的附屬特征。交互電影作為影像文本,邏輯清晰的敘事閉環是其創作根基。正如自亞里士多德以來人們秉持的傳統敘事觀點,敘事順序不是簡單的線性的,而是因果關系的。其因果關系可能是公開的,即準確的;也可能是隱蔽的,即暗示的,引申至交互電影中,敘事結構可以是線性的,也可以是循環的,它們都是用戶依托劇情線索數次選擇后的敘事結果。伸縮式的半開放敘事結構是交互電影中用戶索引性因果敘事關系的呈現路徑。
二、交互電影的三維空間
隨著技術的迭代升級,交互電影也不斷發展,由真人實景的現場類比拍攝轉化為真人表演與建模渲染的數字合成,由在情節關鍵處穿插選項轉化為用戶實時操縱化身自由行動。交互電影一方面重塑了用戶與內容的交互模式,改變了用戶影像信息的消費習慣;另一方面改變了內容與用戶打造“共謀”關系的路徑,用戶從局外人的“看”或“凝視”轉化為局內人的“游目”。換言之,隨著技術的演進,交互電影中用戶的內容消費呈現空間化趨勢,進一步拓展了影視美學和數字游戲的空間維度。
自15世紀起,透視法依托繪畫開始了對人類視覺消費的漫長詢喚,繪畫藝術堅守著透視法的創作規則,為觀眾在二維平面上提供最佳的視點體驗,立體事物被當作平面圖式看待,20世紀誕生的二維影視藝術自然而然地沿襲了這一傳統。回顧人類影像消費的歷史,正如列夫·馬諾維奇所言:“阿爾伯蒂的窗口、丟勒的透視儀器、暗箱、攝影和電影,所有這些基于屏幕的設備都要求觀看主體保持不動。”從電影、電視、PC互聯網到移動互聯網,雖然用戶與屏幕之間的距離不斷縮短,但用戶一直處于被靜止的狀態,被動地接受屏幕內經由蒙太奇暴力閹割后的透視畫面,直到交互電影的出現打破了這一現狀。
如上文所言,隨著技術、硬件的升級,交互電影也迎來自己的革新。當下交互電影一般分為兩種,一種是真人演繹的實景類比拍攝,如《黑鏡:潘達斯奈基》《隱形守護者》,另一種是對真人的表演進行數字捕捉。身體動作捕捉有兩種類型,第一是動作捕捉,第二是技術捕捉即點對點捕捉(此技術也是用戶可以通過交互界面精準控制角色行為的關鍵),在此基礎上建模合成影像,如《底特律:成為人類》《暴雨》。前者依托影視藝術的場景構圖、景深設計、場面調度、攝影機運動等視聽規范,為固定不動的幕前用戶提供最佳透視點,用戶使用過程表現為觀看動態視頻,到了情節關鍵節點處,在系統提供的多項選擇中進行選擇抉擇,這是交互電影對用戶與屏幕交互的積極探索,也是交互界面的初級形態。后者借用數字技術仿造攝影機的光影大大擴展了空間的表現力,實景難以拍攝的畫面都可以在此得以實現。同時基于點對點捕捉技術,用戶可以控制化身根據自己的視點需求展開自由的探索,這是用戶與屏幕交互的升級,在此過程中,打破了蒙太奇對用戶視點的桎梏。經典好萊塢電影基于用戶固定不變的位置,運用場面調度、景深設計、攝影機運動等多手段來講述故事,為屏幕前的觀眾選擇最佳視角,以提升觀眾的審美體驗。交互電影則推翻了最佳視角,將視點選擇權給予受眾,用戶以自己的視點自由探索,空間得以釋放出更加多元的信息,讓用戶沉浸式地體驗第二人生,以《底特律:成為人類》康納支線為例,康納一出場便是協助人類警察與劫持人類女孩兒的仿生人談判,談判前用戶需要操縱康納在受害者房間內自由尋找線索,以增加對劫持人類女孩兒事件始末的了解,此處線索的多寡會直接影響談判的成功率。
綜上可以得出,傳統影像是通過對鏡頭前事物的類比復制、時間延遲呈現在觀眾面前,其視點設置類似于一扇固定的窗口,觀眾通過這扇窗欣賞創作者構建的虛擬世界。數字化的交互電影通過真人表演與數字合成渲染相結合的方式,打破了蒙太奇構建的最佳視點,拓展了影像空間,玩家通過交互界面進入虛擬世界,根據自己的興趣點操縱化身對影像空間展開多維探索。換言之,傳統影像依托西方透視法為觀眾在二維屏幕內搭建觀賞虛擬世界的最佳視點,以提升觀眾的沉浸式體驗,數字合成的交互電影以中國欣賞長卷山水畫的“游目法”見長,交互電影借力數字技術向用戶讓渡視點選擇權,于三維空間自由探索的同時增強了用戶的臨場體驗感。
交互影像生產范式的轉化,放大了用戶個體化情感在影像中的索引性效果,用戶可以通過心理的投入,在時間空間的雙重缺席中獲得在場的滿足。不過,當用戶沉浸于虛擬空間提供的歡愉之余,我們不禁沉思交互電影通過伸縮式敘事與數字化身為用戶提供強臨場感審美體驗的同時,是否會給人類的身體與社會空間的體驗關系帶來反向規訓?
三、主體性迷思
依托于線性與循環并存的伸縮性敘事模式,借力于數字捕捉與渲染合成的三維空間,用戶一別往昔沙發土豆的被動承受者角色,化身超人在虛擬世界多重探索、實現“游牧式”的生產快感。與此同時,我們應當注意交互電影營造的強臨場感體驗可能會造成用戶“異己性”的缺失,日益形成麻木的“自戀型人格”。
(一)“云”上狂歡的“游牧主體”
傳統的影視文本可看作封閉的“讀者式文本”,用戶傾向于將文本的意義作為既成的意義來接受,在影像消費中用戶通過自身的割裂來實現滿足,即用戶的身體留在封閉的原地,通過“凝視”完成主體對影像世界和攝影機視角的雙重認同,進而擺脫肉身的限制,在時間、空間雙重缺席中實現在場窺視的滿足感。
隨著技術的迭代演進,在類比性日益讓位于序列性的交互電影中,文本的性質亦發生了轉變,從讀者式文本更多地轉向生產者式文本,后者出自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一書,“它并未要求讀者從文本中創造意義,也不將文本本身的構建法則強加于讀者身上,同時自身已經包含了與它自己偏好相悖的聲音”。用戶在交互電影中依托交互界面及其背后的數據算法系統設置獲得了身體的延伸,用戶不僅可以通過自己的視野拓展多元空間,還在與算法的實時反饋下操縱故事情節的發展轉向,消解了機械復制時代藝術“萬物皆同”的感覺,再現了本雅明筆下古典藝術的“靈光”。
尼爾森·古德曼在對藝術進行分析時,將藝術分為真跡藝術和多階段藝術,前者是獨一無二的、不可復制的,具有本雅明所言的古典藝術的“靈光”。此處暫且拋開藝術真跡在印刷技術出現前所特有的權威性和崇拜價值,從結構主義視域來對真跡藝術進行解讀可發現其包含雙重語義,一方面藝術文本的物理結構是獨特的別具一格的存在;另一方面藝術品中包含了創造者充沛的情感意蘊。交互電影中用戶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玩家,用戶依據自身的審美趣味和價值取向選擇游戲路徑,與文本背后的創作者共同編碼,創造具有特定意蘊的文本內容。在虛擬世界抒寫迤邐篇章的用戶獲得躲避式和生產式的雙重快感。
首先是躲避式的生產快感。根據歐文·戈夫曼的擬劇理論,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傾向于通過控制自己的言行,尤其是他人認為難以控制的那方面來完成自身形象的塑造,且要注意在不同“觀眾”面前進行區隔管理,以維持自身在不同觀眾群體面前的獨立形象。在交互電影中“表演”的用戶有天然的隔離優勢,虛擬世界的用戶化身具有匿名性,表演失敗后也可以毫無負擔地重新來過。與此同時,在虛擬世界中用戶可以逃避傳統意識形態和社會倫理的詢喚,無所顧忌地進行心理活動外化和客體化的表演,在虛擬世界獲得躲避式的快感。如在《隱形守護者》中,用戶通過數字化身——肖途進入風雨飄搖的近代史,角色身附共產地下黨員“胡蜂”、日本駐滬領事武藤志雄得力助手——亞輝通訊社記者、上海興榮幫成員及其后期解鎖的國統軍長官等多重身份,小心翼翼地游走于多方勢力之間。在這個虛擬世界,用戶得以暫時摒棄現實世界的諸多不快,釋放內心壓抑的情感,并隨著游戲中敘事的走向或悲或喜或哭或笑,情感得以凈化的同時獲得躲避式的快感。
其次是生產式快感。用戶在系統提供的多重選項中自由抉擇,通過其背后數據的層層累積構建出一張獨特而又完整的龐大信息網,依托系統算法的索引性規則,用戶的數據將直接自動轉化為下一層級的情節內容,繼而,用戶得以從符號學的意義上對現實社會中的霸權進行抵抗,以獲得有別于封閉文本的生產式快感。以《底特律:成為人類》中卡拉支線為例,卡拉帶著愛麗絲逃離陶德家后無處可去,隨著夜幕的降臨下起了小雨,卡拉亟須為二人找到一處可以過夜的地方,這時卡拉可以:(1)打碎車窗,在廢棄的車內過夜;(2)去商店偷一把剪刀,把鐵網剪開,在爛尾樓過夜;(3)偷商店的錢,去賓館過夜。綜觀三項選擇都是對傳統社會規范不同程度的冒犯和中傷,在這里體現了費氏筆下“游牧式的主體性”,仿生人在人類宰制性體制所提供的資源和商品中,根據當下的需要,偷偷獵取、拼接,創造自己的“文化”,同時亦是用戶通過虛擬世界的文化碎片體驗來實現內心情緒的宣泄。
交互電影中的用戶需要在沉浸式體驗和理性化思辨間反復跳躍,這是布萊希特所倡導的“陌生化理論”的良好踐行。陌生化理論就表演方法而言,要求角色與表演者保持一定的距離,表演者應當駕馭角色。在游戲影像中,用戶操控化身游走在虛擬時空,一方面沉浸式扮演系統為化身訂制的人設屬性,與化身在多元的敘事路徑中共歷風雨;另一方面,用戶需要隨時保持理性,實時推敲文本背后隱藏的邏輯,對創作者的內容設置及其映射的現實世界展開重重深思。但是隨著用戶于交互電影中投入時間和情感的遞增,用戶與化身之間的界限趨于消弭,用戶的數字化身越發向用戶的數字孿生靠攏,固定NPC越發向用戶的朋友角色靠攏,這可能會形成用戶“異己性”的缺失,即喪失換位思考的能力,日益淪落為麻木的自戀型人格。
(二)那喀索斯的自戀型人格
在交互電影中,用戶通過鼠標、鍵盤操控化身(角色)的言行,推進劇情線的發展,在此過程中,用戶與化身在身體和思想兩個維度上共存。隨著時間投入的遞增,用戶與化身的契合度越發提高,同時用戶不得不面對與之隨行的潛在危機,即如果用戶未能成功挑戰映射世界中的自己,奪回身體與意識的主導權,用戶將被桎梏于冰冷的鏡像,受制于自戀型人格,最終消失在無盡的虛空。
首先是身體層面的共存。雖然交互電影中用戶操縱的角色外在形象是系統或默認或官方提供的諸多皮膚之一,但隨著劇情支線的推進,尤其交互電影中多是以第一人稱內視角展開敘述,用戶須實時留意NPC的臺詞、動作、道具等實時表現,為自身的決策提供邏輯支撐,保障化身即用戶自身的生命。隨著用戶于交互電影中投入時間和情感的與日俱增,用戶與化身之間的心理距離越發縮短,身負用戶精神寄托的角色將變成獨一無二的專屬化身,向用戶于虛擬世界中的數字孿生靠攏,屆時沉溺于交互電影的用戶將會變成麻木的那喀索斯,“考起詞源,那喀索斯與‘麻木’同出一源。少年那喀索斯誤將自己的水中倒影當成另一個人。他在水中的延伸使他麻木,直到他成了自己延伸(即復寫)的私服機制(servomechanism)”。這對操縱交互電影的我們敲響了警鐘,交互電影通過交互界面的設置讓用戶的身體和思想實現延伸,可是延伸也是另一維度的暴力截除。用戶在虛擬世界對角色實行操縱時需要按照系統指定進行一系列QTE操作,QTE操作的結果會對敘事內容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以《暴雨》中史考特支線為例,史考特尋找到羅倫房間后敲門,當羅倫第一次開門時,如果用戶操作速度不夠快,史考特便進不了門,需要等羅倫拒絕關門后再次敲門。《底特律:成為人類》中康納和漢克追捕對人類造成傷害的卡拉和愛麗絲,在此過程中經過一條車流密集的道路,如果用戶QTE操作不暢,康納會被路過的車輛撞死。在交互電影中用戶和化身打破了屏幕壁壘,實現了身體層面的共存,當下我們需要意識到,用戶通過交互界面操縱化身時已然被技術反向操縱。
其次是意識層面的共存。交互電影中主角是用戶的化身,固定NPC是格雷馬斯理論中功能明確的行動元,最終構架出結構嚴謹的敘事模式。臨場感沉浸式體驗讓用戶深度代入角色,與固定NPC產生真摯的情感,但如果用戶沉溺于虛擬世界的化身與NPC之間的交往,則易缺失在現實世界社會化過程中形成的“異己性”特征,即換位思考的能力,“精神分析學家海因茨·科胡特(HeinzKohut)描述了‘異己性’的障礙,他將這種脆弱的人格特質稱為自戀人格——這類人格的特點并非孤芳自賞,而是自我意識缺損”。現實社會中,無論是兒童還是成人都需要不斷社會化以適應迅速發展的社會,其中一個重要的途徑是根據他者對自己的反應形成自我認識,來調整自身使其符合社會規范,即庫里的鏡中我。基于交互電影中數值化引擎驅動敘事模塊的前行路徑,交互電影中的用戶很容易依據自身審美特性篩選與自身需求相契合的客體——NPC,進而收獲“完美”的社交關系。由此,用戶自身將變成一個封閉的系統。同時,交互電影營造的虛擬世界中角色都須遵守特定的規則,才能跳出自動化的循環,推進情節走向,用戶的思維也將在這個過程中逐漸變得機械化。正如雪梨·特克爾就人類和計算機的關系展開廣泛調研時得出的結論“當面對不同程度的‘智能’機器時,人們傾向于以對待人類的方式與其相處……計算機的運算模式影響了他們思考的方式”,虛擬世界中用戶與角色們的意識逐漸趨同,交互電影背后的意識形態隱而不彰地匿身其中。
正如福柯通過對身體與權力關系的系列研究,提出歷史將在人的身體上留下痕跡這一結論,當代人類身上亦打下技術的烙印。在“嗅覺、味覺,還有觸覺等幾乎已經完全被視覺所吞噬并吸收”的年代,交互電影部分釋放了人類的肢體,也為人類的主體性埋下了隱患。
結 語
新媒體時代,游戲不斷向聲畫兩大元素敘事的影視藝術靠攏,影視藝術也不斷向釋放用戶能動性的游戲靠攏,交互電影是影視藝術與游戲產業適應網生代用戶信息消費習慣的里程碑式產物。交互電影依托于數字游戲可伸縮的分布式信息處理模式重塑了影像藝術的線性敘事模型,構建了獨特的半開放式敘事路徑,賦予用戶更多的選擇空間,助力用戶的心理活動得以客體化表現出來。與此同時,隨著科技的更迭演化,影像藝術制作過程中數字合成的空間序列日益取代復制類比的時間序列,交互電影重塑了屏幕與用戶之間的關系,用戶由“凝視”固定二維畫面的觀眾轉化為“游目”于動態三維空間的“游牧主體”,享受著躲避與生產的雙重快感,但正如上文所言,媒介于人類而言,既是延伸又是截除,用戶在掌控化身的同時亦面臨被化身背后的算法所掌控的危機。
交互電影是技術迭代的產物,相信隨著5G、云計算、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底層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交互電影也將迎來自身的升級重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