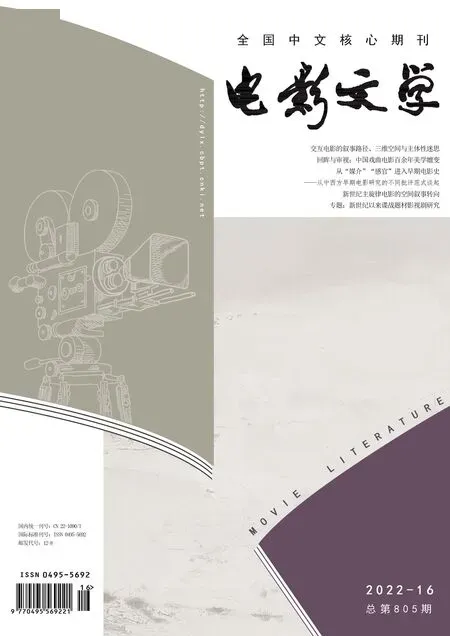承繼、融合與超越:新世紀國產諜戰片的美學表達
白麗娜
(湖北文理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湖北 襄陽 441000)
誕生于20世紀50年代的諜戰片是冷戰思維模式下的直接產物,是研究兩大陣營對峙時期的重要文本。進入后冷戰時期以來,諜戰電影卻并未因冷戰的結束而消亡,反而在科技元素和炫目特技的包裹下變得更為矚目,007系列成為最具代表性的反叛表達。相較于國外諜戰片的蓬勃發展,國產諜戰片產量較少,然而伴隨著《風聲》等一系列影片的出現,新世紀國產諜戰片在兼具主流意識和大眾文化產品雙重屬性的前提下完成了對美學風格的自我書寫。
一、承繼:抗爭與死亡的崇高之美
國產諜戰片作為反特片的延續,從類型模式上可以稱之為古典模式,因為它的審美形態是在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中產生的某一類型審美意象的“大風格”,尤其是擅于在宏大主題之下展現崇高與優美。在西方美學史中,優美與崇高是兩種公認的重要審美范疇。朗吉努斯在《論崇高》一書中認為:“崇高的風格是一顆偉大心靈的回聲,‘崇高’應具有莊嚴偉大的思想和慷慨激昂的熱情。”而康德則認為崇高能讓自身發現另一種類抵抗的能力,在康德看來,崇高來源于主體采取的斗爭行為,進一步明確了審美主體如何完成崇高感的構建。在中國傳統美學中,與崇高語義接近的詞有風骨、遒勁、健美、雄渾、豪放等。王國維提煉出壯美以區分西方美學意義上的崇高。崇高美的審美特征往往體現在以下幾點:(1)崇高美是一種壯麗之美,不僅指自然之雄渾壯麗,更意指偉大超然的精神、強大的反抗力量;(2)崇高美的生成機制是痛感到快感的間接轉化;(3)當崇高與某種價值系統聯動時,便有了崇高的道德意義,或者指認精神人格的不斷超越。
(一)諜戰片中崇高美的來源
新世紀國產諜戰片的整體美學傾向是表現這種古典主義審美范疇的崇高美。首先,崇高對象與敘事主體形成一種對立關系,崇高對象不僅指自然,更是各種邪惡、黑暗的勢力,在數量、強度、信息掌握度等方面掌握絕對優勢,通過這種“力的強大”“量的巨大”,引發主體和觀眾對強大力量的恐懼,從而產生對主體的崇敬之感。如同柏克所言:“凡能以某種方式適宜于引起苦痛或危險觀念的事物……就是崇高的一個來源。”如電影《懸崖之上》,開篇便是執行“烏特拉”行動的四人小組被隊內成員出賣,敵暗我明的艱難處境,使得主體的行動舉步維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魄力和完成任務的艱險,引發了受眾對主體行動的崇敬之感。電影《東風雨》中,一方面由于上線的死亡,主人公安明的身份受到組織的懷疑;另一方面藤木使用反間計,將一份裝著假名單的膠卷以成海岸的名義流出,局面錯綜復雜,主人公處在危機重重之中,最終歡顏采用死間的方式去核實信息的真偽,主體在絕境中的行為選擇極大地激發了受眾的欽佩之情。《密戰》中我方情報系統被搗毀,林翔臨危受命,來到危機四伏的上海,首先要解決的困境是收集材料,組裝出一臺發報機。艱難的組裝之路與敵方傾巢而出的探測儀在畫面上形成強烈的對比,進一步烘托出敘事主體的弱小。
諜戰片的崇高美首先便展現在這種強烈的對比之中,敵眾我寡的懸殊力量、敵暗我明的迷局之惑、敵強我弱的艱難困境,這種矛盾對立的行動元構成了格雷馬斯符號矩陣理論中的X(主體)和反X(主體對立面)。在明確的激勵事件的推動下,主人公會自發構建欲望目標,故事因而產生巨大的動能,反X構成了主人公實現目標的最大障礙。崇高感在某種程度上便來源于X與反X之間的強大對比,反X越強大,X行動的阻力越大,人物的崇高感便越突出。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的諜戰片如《羊城暗哨》,通常刻畫的是“國共對峙”的政治環境,這種二元對立的政治環境設置要求創作者指認價值立場,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導向性。而隨著歷史話語和時代語境的變化,新世紀國產諜戰片所營造的政治環境則是多元復雜的,個體處于一個錯綜復雜、險象環生的政治環境中,創作從二元對立轉變為多元博弈,善惡二元結構被解構,如《風聲》《東風雨》《蘭心大劇院》中多元勢力博弈的多角度、交叉式立場。在這樣的環境中,個體的對立面變成了群體,每個勢力都有可能對個體完成任務構成阻滯,從而讓個體的行動懸疑叢生。如電影《東風雨》的政治環境設置中包括共產黨(安明、郝碧柔)、國民黨(歡顏)、日軍(藤木芳雄)、日籍布爾什維克(中西正弘、成海岸)等不同的政治勢力,《蘭心大劇院》中設置了盟軍、軍統、汪偽政府等不同政治勢力,在懸疑色彩的包裹下,每一方的身份都是迷幻的,這讓個體陷于迷局之中,難分敵我,在與各方力量的斡旋中,進一步肯定了個體的價值立場。
(二)諜戰片中崇高美的展現
新世紀國產諜戰片的崇高美在敘事層面往往被賦予了英雄主義的悲壯意味。一方面繼承了“十七年”反特片塑造英雄人物的傳統,但在塑造人物時更側重于群像式的書寫:凸顯集體英雄。另一方面,更注重勾勒英雄人物的復雜性,體現了英雄人物從“神性”到“人性”的轉變與回歸。
1.暴力美學突出崇高
一方面,個體在與恐怖的客體進行斗爭的過程中,往往表現出堅韌的意志力和頑強的抗爭力,特別是新世紀國產諜戰片通過“刑訊逼供”的極致情境,考驗著主體的意志與人性,表達著暴力奇觀,宣泄著視覺消費的快感。《懸崖之上》對張憲臣的電刑,《東風雨》對歡顏的車裂刑,《風聲》對吳志國采用的針刑、對顧曉夢采用的繩刑,這些動刑拷問的招數駭人聽聞,非常人所能忍受。在《誰是臥底之王牌》中,敵人企圖從五名女性口中得知“王牌”的真相,五名女性要逐一接受刑訊逼供,相比觸目驚心、血肉模糊的行刑場景,等待行刑時的恐懼心理和精神焦慮更加刺激著觀眾的神經。逐一刑訊的過程,宣泄著身體暴力的奇觀,形成了暴力的集中展示。以暴力“景觀”刺激受眾的感官,營造暴力的商業觀賞性,在極致的痛苦中驗證英雄人物的信仰,暗合著消費邏輯下受眾呼吁信仰的文化心理。更重要的是在一種儀式化的呈現中考驗人性,是出賣情報、茍且偷生還是堅持真理?從主體心理來看,崇高是以痛苦為基礎的,它涉及人的“自我保存”的欲念。當主人公舍棄自我保護的欲念,守節守義、寧死不屈時,人物的身份得到指認,身體受難承載信仰之光,新世紀國產諜戰片便在如布迪厄所說的“場域”中,以市場(視覺消費)為紐帶,在政治、文化、美學等不同場域找到了身體暴力的合法性,英雄人物的崇高美透過這種“獻身倫理”而體現出來。
2.死亡美學驗證崇高
除了這種獻身倫理,死亡美學也在新世紀國產諜戰片中承載著重要功能:突出英雄人物使命的崇高。傳統諜戰片中主要通過英雄個體力量喚起觀眾對意識形態的認同和回歸,以小見大地弘揚革命信仰和時代精神。新世紀國產諜戰片中的英雄人物則往往是一群人,是集體英雄的形象,他們時刻處于死亡威脅之中,但諜戰片的崇高感并不來源于主體自身的死亡,更多是依靠同志、戰友的死亡來突出,如《秋喜》中夏惠民逼迫晏海清殺死戰友以證清白時,晏海清矛盾而痛苦,戰友則暗示其開槍;《懸崖之上》中張憲臣選擇犧牲自己讓周乙擺脫嫌疑;《東風雨》中歡顏替換了咖啡代替安明實行“死間”。這種死亡方式的選擇,一方面刻畫出英雄人物的“人性”,這種“人性”的表達在敘事中主要通過友情、親情、愛情的情感描寫來完成,在生與死的抉擇中進一步強化這種情感的戲劇張力,渲染出主人公無助、掙扎、矛盾的“人性”,也體現出舍生取義,交付生命保護戰友而犧牲的悲壯之美。
另一方面,延續生命只為完成任務,他們把任務看得高于個人生命,在權力意志的指引下,主人公確信自己的政治選擇是合法的、正確的,那么其使命便被指認是光榮的、崇高的。正如康德所言,“對于自然界的崇高的感覺就是對于自己本身的使命的崇敬”。在集體英雄和悲壯犧牲的情感旋渦中,新世紀國產諜戰片找到了其價值確認的置換手段,那就是使命的崇高。在肯定使命崇高的前提下,權力意志轉化為生存意志,當主人公面臨戰友、親人、愛人的死亡,一種強烈的生存意志產生,促使主人公完成了超我的轉化,個體早已不懼生死,但必須生存下去才能創造活動,完成使命,實現精神人格的超越。通過超越,個體得以獲得其價值意義,集體生命也得到了另一種延展。諜戰片中的崇高,“所引起的是一種間接的愉快,先是一瞬間的生命力的阻滯,而立刻繼之以生命力更加強烈的噴射”。
在諜戰片中,主體崇高感來自將其由對客體的恐懼而產生的痛感轉化為由肯定主體尊嚴而產生的快感。英國經驗主義美學家柏克在他的文章《論崇高與美兩種觀念的根源》中指出,美與崇高在性質上十分不同,美以快感為基礎,崇高則以痛感為基礎。身體暴力書寫著極致的痛感,集體英雄與死亡美學肯定著主體的價值尊嚴,個體轉變為崇高的主體,在抗爭的過程中崇高美就誕生了。
(三)諜戰片中崇高對象的形式
康德認為,崇高可以在一個無形式的對象上看到,即崇高對象無規律、無形式。諜戰片由于表現的是隱秘戰線上的斗爭,這種特殊的題材類型決定了審美主體身份的模糊性。也就是說,諜戰片中的英雄形象本身可能與美的審美對象截然不同,但諜戰題材電影的崇高感恰恰卻能從此罅隙中生成。如電影《密戰》中的人物梁棟在目睹青梅竹馬的蘭芳被侮辱時選擇明哲保身,他不屬于“優美”的審美范疇。但在后續與大貓、岑子默等人的接觸中,他逐漸找到了人生的價值,并選擇與其并肩戰斗。可見,崇高可以在一個“無形式”的對象上看到。梁棟的轉變外因看似是對蘭芳的舊情,內因則是被英雄人物的信仰所召喚。當“無形式”的對象被感化、被召喚,他們在思想和力量上獲得成長,將對個人愛情和前途命運的追求轉化為利他的心理,并自覺地內化為個體為實現信仰而做出的抗爭行為和選擇,英雄人物信仰的崇高便得到驗證。在影片《聽風者》中,同樣有這樣的敘事表述。何兵是個街頭小混混,當他被帶到701實行偵聽任務時,仍向組織提出了一系列利己的過分要求,這說明何兵并沒有完成其身份的確認,仍游離在701政治秩序之外。當張學寧犧牲后,何兵決絕地戳瞎自己的雙眼,只為讓自己重新獲得靈敏的聽力。這里的敘事從何兵對張學寧的愛情敘事轉變為革命敘事,何兵自主、自覺地完成了自我身份的指認,如同俄狄浦斯刺瞎雙目般完成“救贖”(張學寧因何兵偵聽錯誤而死),頗具儀式意味,通過主體自我的超越,一種從容且悲壯的崇高美得以詮釋。
二、融合:消費視域下的通俗美學
學者胡克認為:“時代雖然變化,但是諜戰片的本質并沒有發生任何的變化,那就是政治性與娛樂性的完美結合,變化的是不同的政治性與不同的娛樂要求,需要更多地適應社會心理和主流觀眾的欣賞口味。”新世紀國產諜戰片將突出宏大革命敘事的政治意識形態的話語表述功能逐步退去,在消費驅動下進行類型重構與符號重塑,用通俗化的大眾美學來迎合市場規律。
(一)類型融合
“十七年”反特片成功塑造出驚險樣式,而隨著新世紀歷史話語的變遷,諜戰片的意識形態功能逐漸弱化,在迎合大眾文化品位和審美情趣時,有意識地向通俗美學靠攏,使得新世紀國產諜戰片成為經典商業片的類型代表。作為一種類型,諜戰片的類型表征首先體現在敘事上,敘事圍繞著“獲取情報”而集中展開,營救任務、送出情報、甄別身份、發布困境、暗殺計劃等為諜戰片中常見的敘事模式。在此敘事動力的牽引下,幾方勢力蠢蠢欲動,最終通過主人公的抗爭活動,完成了對理想信仰、奉獻精神、人性等具有通俗性、普世性的價值觀念的傳達,代替了傳統諜戰片宏大的革命意識形態敘事,體現了現代觀眾的審美要求。
在創作類型上,體現了不同電影類型的融合,以增強影片的娛樂性,從而迎合受眾的審美趣味。在新世紀國產諜戰片中,愛情、動作成為常見的類型元素,被融合進諜戰敘事當中,并開始嘗試喜劇元素的融入。《聽風者》中張學寧與老鬼之間的情愫無法宣之于口,老鬼只能在張學寧犧牲后獨自悲慟哭泣。《東風雨》中當安明與歡顏漫步在下雨的街頭,清冷的畫面,特寫鏡頭下濺起的雨滴,愛情的美好讓大眾暫時忘卻了隱秘戰線的殘酷,實現了影片敘事節奏的短暫延宕,達到了抒情的意味。《密戰》中林翔與賀蘭芳原本是為完成任務而假扮的夫妻,在生活與工作中最終假戲真做。這個敘事橋段被影視作品反復生產,但觀眾仍樂此不疲地想要“窺探”二人的感情是如何遞進的,突出“志同道合”的愛情表述。
此外,動作元素在新世紀國產諜戰片中也多有表現,跟蹤、追逐、打斗、槍戰,這些激烈的場面,帶給受眾強烈的視覺刺激。在緊張的氣氛中,跟蹤與追逐的戲份展開,鏡頭跟隨著人物穿梭在不同的環境空間,喧囂的鬧市、幽靜的弄堂、林立的舊式筒子樓,展現了濃郁的舊式城市空間,節奏緊湊而明快。在《密戰》中,還加入打斗的戲份,人物身手矯健、武功高強,構建著英雄崇拜的虛構想象,打斗場景重在表現動作的飄逸流暢,體現出暴力的形式美感。
除此之外,由于復雜嚴峻的人物處境和正統的價值規范,諜戰片中很少融入喜劇元素。但由于歷史語境的流變,新世紀國產諜戰片采用通俗美學的敘事策略,開始嘗試融入喜劇的元素。當然,喜劇元素的融入方式還需要進一步探討,當下主要通過人物的外部動作和語言來進行展示,如《密戰》中大貓在對賀蘭芳進行訓練時,特意模仿闊太太們的語言動作,用夸張的動作神態博人一笑;再如,影片結尾皮埃爾架著飛機準備起飛時的豪言壯語與未能如愿的啞口無言形成強烈對比。這些夸張、搞笑的外部動作增強著影片的娛樂性,正是新世紀國產諜戰片主動貼近觀眾的注解。
(二)構建符號景觀
克里斯蒂安·麥茨認為電影語言區別于一般語言,因為電影有自己的一系列符號系統。讓·鮑德里亞指出,在消費社會中,消費過程本身具有豐富內涵,這使得人在消費時更加關注商品所蘊含的符號意義。新世紀國產諜戰片在靠近消費邏輯和通俗美學的同時,本身體現出類型符號的趨同性。在電影中,場景的設計、人物的服裝、空間的處理,色彩、聲音的運用,形成了符號景觀。
新世紀國產諜戰片的符號系統中,首先值得討論的是人物的服裝。在影片中,主人公大多身著長款深色大衣和戴手套、頭戴禮帽,看似偽裝在熙攘的人流中,但由于電影類型符號景觀的呈現,受眾可以一眼就對其進行識別,這就構成了溫別爾托·艾柯在《電影符碼的分節》中所說的識別符碼。偽裝也是一種暴露,從而說明諜戰片中的人物其實始終處于危險之中。正如前文所述,新世紀國產諜戰片多表現多元的政治勢力,讓主人公處于敵我難辨的困頓狀態,在視聽表達上常“以顏色設喻”,在宴會等場景中畫面顏色五彩斑斕,光線明暗交替,從而表達出敵我難辨的迷離之感。在刻畫主體時,則往往區分熱鬧場景中的彩色,畫面多以冷色(藍色)、暗色為主,用以暗喻危險的存在。除此之外,槍聲、汽車剎車聲等聲音元素也是諜戰片的一種符號,標志著諜戰片的類型。但是,在通過符號景觀確認諜戰片類型定位的同時,也要注意符號一旦成為景觀,便可能會消解價值傳遞的深度,并讓受眾產生視聽上的審美疲勞。
三、超越:謎題敘事中的極簡主義美學
新世紀以來,國產諜戰片以一種亞/準電影類型出現在觀眾視野中,它在文本母題設置上延續了反特片的主題屬性,但在敘事模式上卻呈現出謎題敘事的特點。所謂的“謎題敘事”主要是指謎題電影(Puzzle Films)中呈現出的敘事方法,是構成謎題電影的骨架,它注重設置邏輯間隙、通過信息缺失、利用反直覺以及編織復雜化的文本,在電影中設置“匙眼裝置”,使電影呈現出“謎題導向”,讓原本簡單的敘事變得錯綜復雜。在諜戰片中具體表現為多方力量圍繞“情報”這一匙眼裝置展開智力博弈,《東風雨》《羅曼蒂克消亡史》《蘭心大劇院》等影片就是典型代表,通過多線交叉的敘事讓觀眾在觀看的過程中被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所纏繞,從而抵消過于簡單的臉譜化人物矛盾沖突,進而增加影片的觀賞度。謎題敘事作為現代電影的重要表征,是類型電影敘事鏈條日益成熟的重要表現。不過需要指出的是,諜戰片盡管在謎題設置上大費周章,甚至有些故布疑陣,但它卻與謎題電影大相徑庭,其結局的必然性導致它所構建的謎題敘事始終是以鏤空的形式包裹在反特影片的模型之外。換言之,新世紀國產諜戰片在敘事模型上是對《冰山上的來客》《羊城暗哨》《地下尖兵》等經典影片敘事結構的迭代升級,而這也直接影響了諜戰片在謎題敘事中內滲出極簡主義的美學風格。
勃興于20世紀60年代的極簡主義,來自繪畫、雕塑、建筑等藝術領域,它奉行“少即是多”的藝術法則,追求藝術上的簡約性。這種“簡約而不簡單”的藝術形式表現在電影中內化為內容和形式的極簡。具體來講,內容的極簡主要表現為影片的主題,而形式的極簡主要表現在場景設計和畫面元素中。作為為數不多的能夠與“國際同步”的類型影片,諜戰片在主題表現上始終遵循主流意識形態的詢喚。從《風聲》到《蘭心大劇院》,盡管敘事變得越來越錯綜復雜,但主題卻始終明晰,甚至有些單調,即情報得以傳遞、正義戰勝邪惡。略有不同的是,部分影片因為受到其他類型電影的影響,將愛情、動作、驚悚等子題融入片中,例如,《東風雨》中融入的“愛情”子題為影片涂抹一層柔情氣息,而《智取威虎山》中融入的“動作”子題則讓影片的陽剛氣息更為濃烈。從表象系統來看,新世紀國產諜戰片在主題展現上逐漸模糊歷史與想象之間的界限,如《色,戒》當中的易先生就有歷史原型。然而無論影片表象如何,它在深層的表意系統中始終在回答“我是誰”的核心問題。
相較于內容的極簡,諜戰片在形式上的極簡要更為寬泛,它集中表現在電影的構成元素當中,尤以場景設計為核心。《風聲》作為敲響新世紀諜戰片的頭號影片,在敘事模式上已然呈現出謎題敘事的先兆,只是缺乏懸而未決的結局,在“找出間諜”的游戲法則下推進故事,然而從敘事場景來看,整部影片卻采用了極簡的場景,聚焦于“裘莊”這一固定場景(因而一些研究者認為《風聲》采用的是“密室逃脫/殺人”的游戲模式)。極簡的場景讓電影回歸戲劇舞臺,“三一律”的運用讓戲劇性沖突更為密集,影片的節奏也因此變得更為緊湊;與此同時,極簡場景所營造出來的恐怖氛圍也暫時遮蔽了劇情當中存在的邏輯漏洞。《智取威虎山》作為紅色革命的經典樣本,在徐克改編的影片中,威虎山也是以極簡場景的形式存在,尤其是眾匪寇會聚的“百雞宴”大廳,所有重要的戲份都是在這一場景中發生、完成。除去極簡的場景,在《風聲》《聽風者》《東風雨》《秋喜》《智取威虎山》《蘭心大劇院》《懸崖之上》等影片中,“風、雨、雪”等自然元素成為影片表意系統的重要符號。自然元素一方面可以預示人物內在的情緒,另一方面亦可預示緊張的格局關系,《東風雨》中的“雨”是不該相戀的兩人愛情的見證,但更重要的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暗示,是大戰即將來臨的秘密代碼。《懸崖之上》飄落的雪花既是對革命戰士嚴酷、冰冷的考驗亦是對“烏特拉”行動背后日軍殘暴行徑的控訴,它使得影片形成了冷冽的詩意美。《聽風者》中對“風”的傾聽既是對天賦異稟者的展現,更重要的是對從“自我”向“超我”邁進的革命者的塑造。在《蘭心大劇院》中,瓢潑的大雨配合喪失色彩的黑白色調既是對那段艱難歲月的真實展現,亦是對復雜的國際局勢的闡述。
新世紀國產諜戰片在消費主義的影響下,縫合通俗美學的敘事策略,傳達出崇高之美。手持攝像與黑白影像結合的《蘭心大劇院》,數字技術運用下的《懸崖之上》,讓新世紀國產諜戰片多了一些大膽的藝術表達和革新的技術實踐,使諜戰片依托其特殊的題材,在商業類型化敘事的基礎上,成為新主流電影中一種特色鮮明的電影類型。在新時代語境中,諜戰片理應實現大眾文化與主流意識的完美融合,深度詮釋核心價值和中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