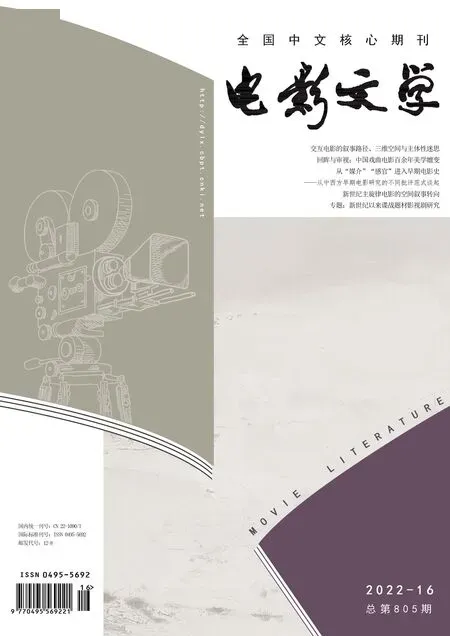現實題材劇中工人話語解讀與意蘊表達
秦麗婷
(吉林藝術學院藝術研究院,吉林 長春 130021)
電視劇作為主導當代大眾文化消費的一種藝術形態,對中國美學實踐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現實題材一直是國產電視劇的創作主流,其以普通人的生存為審美關照的對象,建構真實生活空間,對當下社會進行鏡像投射,探尋現實生活與現實主義藝術之間的平衡。現實題材劇中對工人群體的塑造受到社會發展進程、地緣文化觀念、社會意識、工人社會地位變化等影響,每個時代呈現出不同的創作特色。
回顧歷史,1919年我國工人階級首次以獨立的社會團體和政治組織展開五四運動,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結合,工人群體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耀眼新星”。隨著中國工業化發展的推進,工人階級的地位逐漸提高,產業工人、知識分子、基層管理干部等都被劃分為工人群體,工人階級隊伍不斷壯大,當之無愧地成長為我國最具先鋒性和先進性的社會力量。數字化時代進程的加快,媒介融合成為主流,互聯網技術的勃興促使工人群體的社會屬性升級,逐漸塑造成為“新時代工人”,創造出新的工人文化實踐運動,體現出社會主義思潮中工人階級獨特的藝術魅力。從2018年的《大江大河》到2019年的《奔騰年代》再到今年的《人世間》,以工人形象為敘事主體的現實題材劇受到追捧和好評,這類題材以審視的目光觸及工人的真實生存境遇,通過反映他們的現代性困境,進一步對人性進行思考和探賾;同時,隨著對工業題材和工人形象的關注度上升,不少電視劇也存在口碑“撲街”的現象,產生“過于套路”“愛情砝碼多”“人物不接地氣”等問題,如何避免這些問題,創作出更多有口皆碑的影視作品成為我們亟待思考和解決的命題。
一、工業范式形塑:作為話語表達的陣地
1949年以來,我國非常注重工業發展,工業化進程的加快也助推中國向工業強國邁進。文藝作為時代的反映和產物,文藝創作須與時代同頻共振。
(一)第一階段:政治宣揚與英雄母題
工業題材與主流意識形態緊密相關,早在1942年毛澤東同志就提出工農兵是文藝的主人,為工農兵服務是文藝創作的主要職責。因此,工農兵成為主要創作對象,工業生產線成為反映時代的主要敘事環境。20世紀五六十年代,政治運動影響了文藝事業的發展,文藝工作者的創作激情日益高漲,工業題材的類型實踐推向高潮。其中工業電影起步較早,《橋》《特快列車》《他們在成長》等影片的涌現,成為反映黨和國家促進民族身份認同與歌頌新生活的同一性追求以及進行政治宣傳的重要工具。工業電影對共產主義感召下集體主義意識的著重渲染,為實現社會主義而奮斗的去個人化英雄塑造,展現工人階級在革命斗爭中掌握政權的光輝形象,對社會主義精神和無產階級思想的宣揚,為工業題材電視劇創作提供導向,建立起基本的類型范式和敘事母題。1980年,首部工業題材電視單本劇《喬廠長上任記》在中央電視臺錄制,這得益于中央廣播事業局提出的“大辦電視劇”的號召,推動了電視劇藝術生產,也為文學改編成影視劇提供了模式范本,對中國電視劇的復興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二)第二階段:微觀敘事與紀實探索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電視劇創作類型變得多樣化,大眾的生活習慣和審美旨趣發生改變。工業題材劇也獲得了新的發展,從最初的政治傳聲筒轉向對個體價值的關注,聚焦宏觀背景與微觀個人之間的生存關系。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及一系列工業體制改革措施出臺,為工業題材影視劇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底色。《赤橙黃綠青藍紫》《內應力》《改革者》等劇先后播出,具有濃郁的工業氣息和時代氣息。同時“改革”題材創作中對變革中的人的精神意志的投注蓋過了對政治或經濟層面的單一敘述,如《鐵人》(1990)對原型王進喜身上所代表的時代價值“再現”和“模仿”,歌頌我國石油工人的光榮形象,具有獨特的紀實主義藝術魅力。21世紀初,現實題材劇從混沌逐漸走向自覺,初步顯現出對本體意識的挖掘,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文學改編體量大,占工業題材創作主體。文學傳遞著人道主義的價值,建構起普世性和社會性的文化場域,對電視劇藝術有著深入的影響。文學與影視劇的耦合,一元到多元的過渡,不論是從思想上還是從形式上,都體現出獨特的審美表達。諸多工業劇都是基于文學小說的架構,書寫了工業體制內人的生存百態,對中國工業改革的現實歷史進行深切回望。《禍起蕭墻》(1982)在主題表現上繼承原作“傷痕文學”的范式,針砭時弊,昭示改革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必然趨勢。
二是對紀實性電視劇的探索。電視劇的文學場是塑造工業文本和厘清時代脈絡的重要工具。2003年9月,中國工會將進城務工人員首次寫入大會報告,將其定義為工人階級隊伍的新成員。“民工荒”“工人討薪”等現象成為社會熱點,受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受到社會思潮的影響,導演管虎創作電視劇《生存之民工》(2003),以紀實性的影調來展現農民工在城市如螻蟻般的艱難困境。
三是產業經濟升級,引發“民工劇熱”。最早反映農村人外出打工現象的《外來妹》(1991)講述主人公趙小云走出大山,通過打工成長為玩具廠廠長的故事。“她的‘成功’不僅傳達出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完成了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呼應,而且以影像的方式緩解了社會轉型過程中群體的社會焦慮,以電視劇替代性的想象滿足人們的欲望需求。”《吳福的故事》(1994)則是借農民吳福的目光環視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邁進的歷史震蕩。《民工》(2005)以家庭為敘事單位,通過父子兩代人的打工遭遇來展現農民工的艱辛和苦楚,真實反映外來務工人員的生存境況。從“外來妹”到“農民工”,現實題材劇對工人階級的稱呼發生著變化,也預示著中國從農業大國向工業大國的轉變,“城鎮化”“現代化”逐漸成為發展主流。
(三)第三階段:政策扶持與多元融合
2005年以來,我國逐漸注重通過現代媒介技術傳播文化,電視劇發展迎來新的階段,電視劇的市場活力也得到釋放。同時,《關于推薦優秀現實題材電視劇的通知》的下發也表示著國家對現實題材影視劇創作的大力扶持。2009年,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文化產業振興計劃》,明確影視劇將成為重點文化產業之一,要滿足多種媒體和終端對影視內容的需求。現實題材電視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同時也面臨市場挑戰。
當前,我國現實題材電視劇創作多元化,文化體制的改革,市場占比和收視率成為判斷電視劇成功與否的主要環節,促使大部分電視劇以滿足廣大受眾收視喜好和觀賞興趣為前提進行生產。在此基礎上,不少工業題材劇取得佳績,如《大工匠》(2007)播出后反響熱烈,收視率高達6.8%,大幅刷新工業題材劇的最高收視率。2008年,以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為背景的《漂亮的事》在央視和沈陽影視頻道播出,平均收視率達1.78%。《中國志愿者》《春草》等劇聚焦農民工身上的優秀品質,塑造出充滿青春和朝氣的鮮活形象。由此可見,工業題材創作初顯較可觀的類型特征,找尋到貼合受眾審美旨趣的創作思路。瑕不掩瑜,在肯定工業劇的同時也可以看到,當前工業題材創作仍存在受眾群偏倚和商業化侵襲的漏洞。由于工業劇創作大多取材于東北老工業基地,受眾對象多集中于東北地區人民以及其他地區的老一輩,無法做到目標受眾全民化,流失了大批觀眾群。且當下工業題材劇創作存在過分追求收視市場,在劇情設計上刻意淡化工業元素,摻雜了諸多偶像劇式的成分,不利于工業題材范式的探索和實踐。
二、工人圖譜敘寫:作為影像修辭的文本
主角人物的選擇和塑造是影視劇創作的重中之重,其扮演著情節走勢和價值表達的關鍵角色。“敘事并不是一個靜態的故事,也不是一個孤立的行動,而是某人出于某種想法和目的在某個場合對某人講述某個故事。”近年來,工業題材創作大幅增加,對工人形象的刻畫愈加立體,從多角度、多側面打破受眾對工人群體的固有印象。工業題材劇在一定程度上綜合了工人群體有關家庭、工作等各種現實議題,以展現工人的日常生活來吸引人們對工人以及工業改革的關注,通過影視劇這一大眾媒介來引發受眾的思考和認同,同時幫助工人群體甚至弱勢群體來建立生活自信和自我覺醒意識。
(一)“家文化”建置下的工人群像
在中華民族悠久歷史文化傳承中,儒家文化傳統強調的“血親人倫”深深烙印在國民心中,“家”成為人們最難以割舍的倫理情感,以家庭為單位的藝術創作也最能引起受眾的共鳴。家庭,是人們與社會聯結的起點,是人們進行社會生產和交往關系的紐帶,承載著民族文化傳承和展現社會變遷的意義。《蒼茫》(1996)將一家大型鋼鐵企業從建設之初到改革開放以來近40余年的變遷與五個家庭的悲歡離合緊密聯系在一起,表現了方國棟、蔡大興等職工的奮斗史詩。該劇分上下兩部,上部講述歷史洪流中五個家庭、兩代人不同時期的變化與糾纏,下部以改革開放時期工人、企業家、領導干部等對鋼鐵企業變革做出的突出貢獻來展現崇高的工匠精神。《父輩的旗幟》(2008)則講述“光榮大院”里三個撫平鋼鐵工廠勞模家庭間的愛恨糾葛。鐘浩從不理解勞模父親鐘守城一生執著“光榮”二字到父親被人陷害病逝后幫助父親洗刷冤屈,最終理解父親的追求,并傳承父親“光榮”的旗幟。
現實題材劇《人世間》(2022)講述一個家庭里三代人半個世紀的滄桑巨變,用編年史的形式譜寫20世紀60年代工人家庭隨著時代的變化所經歷的觀念轉變和人物之間的情感糾葛以及生存境遇,客觀還原時代原貌。學者張廣智曾將歷史與藝術創作相結合的方式稱之為“影視史學”,即以影視的方式傳達歷史以及我們對歷史的見解,偏重于敘述歷史以及后文字時代的歷史形態認識理解歷史。《人世間》摒棄了“傷痕文學”的苦難范式,以周姓一家人的崢嶸歲月來觸及最冷冽而又溫暖的百態人間。劇作在敘事結構上以點帶線、以線帶面,通過兩條主線來推動情節的發展:一條是以周家人的情感聯結為主線,生動詮釋當下最真摯的夫妻情、父子情以及兄弟情;一條是以“光子片”里成長的秉昆、德寶、趕超等“六小君子”為主線,刻畫時代洪流中的人情冷暖。“儒家思想中最為講究的人的倫理,即由自己角度出發,去思考和自己在社會中存在關聯的一群人所產生的關系和之間的關聯性。”影像化的家庭具象不僅是簡單化的傳統情感聚合,工業敘事特有的工友情也可以視作一種特殊的家庭關系被提及。以家為內核的現實敘事所鋪陳的歷史溝壑與賦予的精神實質幫助受眾對工業題材和工人群體建立起情感的連接,使更多的人能夠從“純理性生物”轉化為“共情生物”,通過與劇中人物的情感交響產生對倫理道德和人生哲理的思辨,進而將這種家族情懷的價值認可推及對國家意識的主體認同。
(二)工人塑刻的性別觀念突圍
在電視劇的發展歷程中,工業敘事往往被刻板化地認作是男性題材劇,如《劉山子的喜怒哀樂》(1986)、《大潮汐》(1994)、《黑臉漢子》(1996)等劇,通過男性為敘事視角塑造采煤工人、國有企業員工、筑路工人等多個工種形象。哲學家恩熙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曾在他的著作《人論——人類文化哲學導引》里將人視作一種“符號的動物”,替代其為一種“理性的動物”。在工業題材劇高產的20世紀八九十年代里女性只能作為“附屬品”而存在,盡管出現了零星以女性工人為主角的電視劇,如《外來妹》(1991)里進城打工的“外來妹”們、《京九情》(1995)里女工程師肖晶等,但他們在劇中都受到情感的牽絆,還停留在片面化、單一化的個性塑造,依附男性的敘事機理未完全打破。進入21世紀,性別平等觀念提升,女性獨立自主意識愈加強烈,快消時代激發以女性為主體的消費矩陣,催生“得女性觀眾得天下”的市場環境,影視劇開始進入“她時代”。《黑金地的女人》(2008)以“礦嫂”黨素珍等人為原型展現煤礦工人的妻子在建設礦山時期所做出的貢獻,圍繞女性的家庭、情感以及個人價值等多方面敘事。《漂亮的事》(2008)里身為工程師的沈晗在國企改革面臨困境時,主動帶領其他女工程師一同克服難關,彰顯女性本色。《女工》(2009)則以浦小提的半生為主線,講述她從下崗工人到家政公司員工再到自己成立家政公司當老板的社會角色轉變。
如果說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工業敘事對女性的塑形是一種試驗,那么21世紀初對女性形象刻畫則更加鮮活,探索女性的更多側面。英國作家愛德華·摩根·福斯特(E.M.Forster)將人物分為扁平人物和圓形人物兩種,扁平人物易于識別和記憶,圓形人物則立體和新穎。“一個圓形人物必能在令人信服的嘗試下給人以新奇之感。圓形人物絕不刻板枯燥,他在字里行間流露出活潑的生命。”因此,創作者們開始有意規避單一化和臉譜化的形象,注重關注人物心理變化和內心世界,對女性話語構建也逐漸轉向人的精神探尋。《大江大河》(2018)里的姐姐宋運萍,因家庭出身受盡白眼,婚后還被婆婆刁難,但她勤勞勇敢,顧全大局,能夠在弟弟和丈夫面臨麻煩時常常提點,也正因為她的美好,當她不幸去世時才更叫人惋惜。《奔騰年代》(2019)里的金燦爛從軍隊轉業,主動來到機車廠上班,她永不言敗、不驕不躁的精神氣圈粉無數,展現著電力機車研發變革中的女性力量。《火紅年華》(2021)里大學生秦曉丹畢業后繼承父親遺志,在大三線建設中盡顯巾幗不讓須眉的青春風采。女性議題的話題性和互動性幫助工業題材劇裂變成多個敘事維度和營銷角度,極具社會意義和傳播價值,《大江大河》《奔騰年代》等劇的熱播,可以窺見并非只有大女主、女性群像的劇種能奪得女性觀眾青睞,只有真正擺脫性別框架束縛,在精神上展現自信和獨立的女性形象才能被觀眾深記。
(三)工人群體的階層意識轉化
工業題材不僅在敘事主體及角度上有所創新,在敘事環境和社會角色身份上也存在變化。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強調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工人階級是我國的領導階級,是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代表,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力軍。”早在1925年,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曾指出,工人階級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是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1949年后,知識分子也被列入工人階級。隨著產業結構升級,社會平等觀念的深入,階級意識弱化,促進社會發展和時代振興。
任何符號都有意義。“符號是攜帶意義的感知,意義必須用符號才能表達,符號的用途是表達意義。”新業態產生的社會符號落實到文藝創作里主要呈現于工人不同社會層級的性格塑造和人物刻畫上。“善惡對立是敘事倫理取向中的一種可能,對立情況大致可分為兩種——對立沖突型、非對立沖突型。”綜合分析,20世紀80年代的知識分子形象多站在產業工人的對立面,過于頌揚技術工人的英雄行為和革命精神,對其他人物刻畫趨于邊緣化,以迎合傳統二元對立的敘事結構;而新時代的工業題材創作,不僅規避了非黑即白的敘事套路,而且增加了諸多產業工種,人物設計也更加合理化。《大江大河》以宋運輝、雷東寶和楊巡為典型人物來講述改革開放時期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浮沉。《共和國血脈》(2019)以石油開發為主線,演繹石油工人們相繼開發諸多地方油田的奮斗故事。《人世間》則以一個家庭的變奏曲觸及產業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領導干部等多個職業領域,人物性格塑造生動立體。大兒子周秉義工作認真踏實,備受贊譽卻極少時間能夠陪伴家人;喬春燕處事精明、斤斤計較但開朗豁達、助人為樂;曲秀貞身為書記原則性強、實事求是,看似難以接近,實則可愛善良;“反派”駱士賓行為不檢、處心積慮,卻心思通透、有遠大抱負。羅伯特·麥基對人物的成長軌跡定義為“人物弧光”,《人世間》里的每一個人都極具煙火氣,無論他們最終走向是變好還是變壞,都是社會人情冷暖的現實燭照。
通過《人世間》主要人物角色和職業背景統計(見表1)中也可以發現,新時代的工業敘事刻意減少了對工業歷史鉤沉的宏大敘事,轉而觸及工人群體的心路歷程走向和個人價值實現。以平民化的視角觀照工業振興和時代變革,用“微觀視角”嵌入“宏觀視角”的敘事方式傳遞人文價值和情感認同。

表1 《人世間》主要人物角色和職業背景統計
三、工廠意象建構:作為生存空間的外化
在工業題材創作中,工廠成為與工人群體相伴而成的影像符號,在一定程度上聚合工人生產與生活,成為個體回憶與時代記憶的紐帶。在中國傳統美學中,藝術意象常被作為載體幫助主體建立起對人生的審美認識。早期劉勰注重“意象”的審美體驗作用,將審美重點轉向內在之美的體驗。之后朱光潛、宗白華將審美意象具象化,建立起主體在審美意象的體驗中獲取感受。隨著人們對藝術意象的認識逐漸明晰,創作者們開始通過自身的審美情感投注到塑造的主體中,形成特定的符號。“藝術意象凝聚的人生境界是藝術在人生層次上的升華……藝術意象的質量高低取決于藝術意象中凝聚的人生境界。”工廠審美意象的建構依托工業屬性,是工業題材創作必不可少的意象載體。工業題材影視劇創作初期,受到社會語境的影響,工廠常被作為工人階級屬性、國家意識形態的外化;新時期,后工業時代來臨,科技化產業振興與現代性文化語境雙重交響,承載著歷史與回憶的工廠不再依附于工人階級話語而存在,成為人們精神世界和現代經濟發展的表征。
在當前現實題材創作中,工廠的藝術意象主要以兩種形態出現,通過對工廠這一敘事空間的表述來構筑創作者的審美世界,進而傳達更深層次的價值內涵和時代意義。第一種表現形態是對歷史與個體記憶的重現與再造。工廠因其具有的工業屬性,意象空間的建立不僅是個體體驗的窗口,也具有群體性的意義屬性。“空間永遠不是一種單純的框架,也不是一種真實的描述性環境,而是一種特殊的戲劇容積。”既往對工廠的刻板印象里會概念化地認為是專屬于工人生產的封閉式空間,如《車間主任》以20世紀90年代的哈爾濱工廠車間為影像空間,灰暗的機械廠房、清一色的藍色工服和黃色安全帽,工人們日復一日地重復著生產零件和機械制造的流水線作業,段啟明、張一平等車間干部立志要為工人做事,劉義山等工人充滿激情地工作,也有程全等工人想要下海經商,脫去工人外衣。《大江大河》中宋運輝的前半生都是在國有企業度過的,從金州化工廠技術員到東海化工廠廠長,工廠作為一種空間記憶屬性將他的情感關系匯聚,與黃師傅的師徒情、與尋建祥和虞山卿等人的工友情、與程開顏的愛情等以及成家后宋運輝居住的工人大院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載著他的個體記憶。與電影強調工廠封閉化概念不同,電視劇的工廠意象空間更貼近于日常化敘事,是工人生存空間的外化,是其集體生活的折射以及師徒關系、工友關系、家庭關系等社會關系網群的集合。
工廠意象空間的第二種形態是現代經濟的功能性意義建置。后工業文化語境中,消費經濟、數字經濟等被廣泛提及,物質不再僅僅是社會符號的一種再現,而是社會實踐生產和文化意義調配的結合。工廠的物質屬性不能作為社會生產、城市化發展的簡單論調,而是科技化、現代文明以及人文價值的多重指涉。中國藝術文化傳統中“入世精神”和“詩化風格”呈現出社會現實和人生價值的關照,成為新時代融合個體生命與社會實踐的新形式。電視劇《人世間》中軍工廠出身的工人槍械專家杜德海堅決反對賣廠,甚至不惜身綁炸藥包來威脅;劇集最后原醬油廠、木材廠等工廠已高樓林立,“光子片”面臨拆遷改造,諸多住戶大鬧政府。植根于新的工業文化土壤,“舊家園”的崩塌不僅代表著個體“懷舊詩”式的記憶流逝,也是現代文明進步、產業經濟發展的寓言。“任何‘理解的共同根基’都不可能從‘沉默無聲’中油然而生,而只能在某種既存指意行為的共同實踐中生成——在這種實踐中,物質體被置于特定的處所,并被指派特定的意義。”從冷峻的筆調到溫情的時代詩,在工人獲取主體意識以及大眾產生情感共鳴的同時,工廠作為意象空間符號開始延展到鐵路、航天等多個產業領域,更深層次地體現對時代意義和人文價值的思考。
四、工業共同體表達與精神面相
現實題材的工人群像摹寫建置在宏大背景下,人物圖景隨著國家意識形態的變化發生轉向,宏大背景與個體命運互視,承緒集體記憶與個體感悟的“交響”,保持對主導文化意義的認同。在工業范式的形態構成上,作為現實題材的一部分,工業類型依托主旋律,承擔主流價值傳導的政治使命,同時要兼容人類情感的共通和凝聚。張世英在《哲學原理》中提到要將“現在的視域”與“過去的視域”結合為一看問題。以“過去的視域”來看,工業題材劇高產于改革的陣痛期而稀缺于發展的現階段,產業工人的真實生存境遇、工人階級銳意進取的奮斗精神以及工業文明發展的現代化進程不應該游離于大眾視野,尤其是在主旋律題材創作受政府扶持和市場關懷的當下。以“現在的視域”來看,大數據等媒介生態系統革新,從盲流到農民工再到工匠進而衍生數字勞工,工人從“影像符號”引申到“媒介符號”,媒介對工人群像進行二次書寫,對工人的定義愈加寬泛,工人主體地位的提高需要我們樹立起保護意識和他者思維,規避媒介消費語境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現今的工業題材創作出現了工業思維模式化、劇情設計程式化、人物形象刻板化等問題。因此,《大江大河》《人世間》等劇的熱播為工業范式提供鏡鑒意義,幫助創作者從橫向比較中找到定位,爭取早日搭建起屬于中國工業題材和工人話語體系的成熟路徑。
總體而言,新時期以來的工業題材電視劇創作以歷史為原點,以人民為坐標,融合以工人家庭、工友關系和工廠空間的血緣共同體及地緣共同體觀念,還有意打破社會與個人相對立的關系,形塑個人、社會與國家同頻共振、共融共生的家國共同體表達,關照現實與關注個體的價值立意催生觀眾的共情,使得觀眾主體性意識與電視劇雙向聯結,延續工業故事與工匠精神的主體認同,回應家國同構的共同體召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