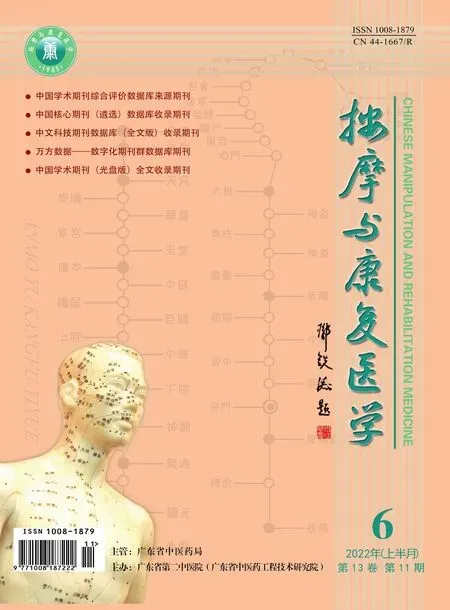“治痿獨取陽明”指導下康復鍛煉配合針刺、電針改善腦卒中患者足下垂的臨床研究
顏玲玲,陳媛,王欣宇,吳佳,王馨瑤,芮曉東,陳麒陽,劉康
(溧陽市人民醫院,江蘇常州 213300)
腦卒中(Stroke)是指由腦血管性病因引起的中樞神經系統急性、局灶性損害導致的神經功能缺損,具體包括腦梗死、顱內出血和蛛網膜下腔出血,具有死亡率高、致殘率高、復發率高的特點[1]。據統計每年全世界約有170萬人罹患腦卒中,其中一半的腦卒中患者發生死亡,約占全年死亡人口的11%左右,而70%~80%的存活者遺留不同程度的肢體殘障,直接影響其生活質量[2]。偏癱步態是腦卒中者后期下肢功能失常的主要表現,一般表現為擺動期足下垂、內翻、髖關節外展外旋的劃圈步態[3]。其中足下垂不僅是導致患者下肢運動功能障礙的最重要因素,也是促使中風患者跌倒、外傷等二次損傷的關鍵誘因,主要與小腿前外側背伸肌群神經失能有關[4]。因此,早期改善小腿前外側背伸肌群神經反射,持續治療足下垂是恢復腦卒中偏癱患者下肢功能的關鍵。
腦卒中后遺癥期所出現的偏癱步態屬于中醫學的“半身不遂,萎癥等諸癥”范疇,在治療方法上建議采用中醫治療。“治痿獨取陽明”是傳統針灸治療肌肉萎縮、運動功能障礙的精髓[5]。筆者所在科室長期以此為選穴針刺的原則,從恢復下肢脛腓神經反射角度指導治療腦卒中后遺癥期患者患肢足下垂,效果顯著,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6年10月~2020年11月在溧陽市人民醫院康復醫學科診斷為腦卒中后遺癥期并足下垂的382例患者,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分為針灸組和對照組各191例,其具體資料見表1。兩組患者性別、年齡、病程、偏癱側、卒中類型、Brunnstrom分期等一般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表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f,±s)

表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f,±s)
注:組間比較,P>0.05
?
1.2 診斷標準 參照2006年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神經科專業委員會制定的《腦梗死和腦出血中西醫結合診斷標準(試行)》[6]中腦卒中的診斷標準,并經顱腦CT或MRI確定,主要包括以下3點:①卒中診斷的確立,具體診斷包括腦出血或腦梗死性卒中;②存在患側足下垂畸形,即患側足背伸困難或在足不離地的情況下患足僅可輕度背伸;③足下垂由腦卒中誘發,兩者存在直接相關。
1.3 納入與排除標準
1.3.1 納入標準①病情穩定,無嚴重并發癥或感染類疾病,可以配合進行康復治療;②年齡≥40歲,且病程≥6個月;③腦卒中后遺癥期,Brunnstrom分期Ⅱ~IⅤ期;④患者及家屬簽署書面知情同意書;⑤醫院倫理委員會備案同意。
1.3.2 排除標準①既往患側肢體殘疾或功能活動不良;②不能耐受針灸、電針治療或無法按照醫囑完成臨床試驗;③采用了針灸、電針治療以外的其他療法;④伴有凝血障礙、出血傾向或嚴重心腦血管疾病等不宜納入的疾病。
1.3.3 脫落和終止標準①治療期間二次中風,發生嚴重心腦血管疾病或感染類疾病;②未按照醫囑完成治療及隨訪;③治療期間采用了除醫囑之外的治療,可能影響結果客觀性者。
1.4 治療方法
1.4.1 對照組 采用康復訓練矯正患側足下垂,具體方式包括:脛前肌力量訓練,患者平臥,術者坐位被動屈伸、內外翻患者踝關節10min;患者坐位,屈膝90°,足跟著地,足掌盡量背伸、而后擊地,連續5min;患者立位、健側負重,患肢主動背伸、跖屈、內翻、外翻5min。步態分解練習時患肢腳盡可能邁前,全腳掌著地。小腿三頭肌解痙訓練時,患者取臥位,術者一手固定患足踝關節上方,另一手向下牽拉跟骨,前臂對抗足掌、被動背伸踝關節,維持15s,每天兩組,每組10min;可下床活動患者站楔形板,借助于自身體重前傾牽拉小腿后肌群,每次20min,楔形板的坡度根據攣縮程度調節。以上鍛煉每天2次,上午、下午各1次,連續治療8周。
1.4.2 觀察組 在經過以上治療后,即選擇患側陽明經穴合谷、曲池、伏兔、足三里、上巨虛、下巨虛、豐隆、解溪、內庭、陽陵泉進行針刺治療,具體操作包括:患者處于平臥位,局部皮膚常規消毒,選用0.25mm×40mm華佗牌一次性無菌毫針直刺入穴15~30mm,順時針捻轉15~20s,重插輕提10次,留針30min。足三里、陽陵泉為一組穴位電極(G6805-B型電針儀),足三里為刺激電極、陽陵泉為參考電極,采用連續脈沖波,根據患者耐受程度,強度選擇為患者達到感覺閾及痛閾之間4/5刺激強度,頻率2Hz,時間20min。每天1次,每周治療5~6次,連續治療8周。
1.5 觀察指標
1.5.1 下肢神經肌電活動應用日本光電MEB-9200K肌電誘發儀檢測,安靜室內、保持皮膚濕潤、皮溫28~30℃,室溫18~25℃的適宜狀態下,患者平臥伸膝,充分暴露檢查部位,地線位于記錄電極與刺激電極之間,檢測腓總神經及脛神經的運動傳導和感覺神經傳導,刺激強度按照引出最大波幅后,重復3次,取3次平均值。具體檢測指標及正常標準包括[9]:①運動神經末端潛伏期(distal motor latency,DML):脛神經DML正常為≤5.8ms,腓總神經正常為≤5.0ms;②運動神經傳導速度(motor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MCⅤ):正常為≥40 m/s,<40m/s為傳導速度減慢;③感覺神經傳導速度(sensory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SCⅤ)≥40m/s,<40m/s為傳導速度減慢;④感覺神經電位(sensory nerve action potential,SNAP)正常為≥6.0μⅤ。
1.5.2 下肢功能 采用Fugl-Meyer運動量表下肢部分評分[8],其包括協調與速度、平衡能力、關節活動度及關節疼痛等方面,總分為34分,分數越高恢復越好。
1.5.3 運動功能治療前后對兩組患者進行Brunnstrom分期評定[10],分期越高表示運動功能越好。Ⅱ期:極少的隨意運動,但不引起關節運動;Ⅲ期:在坐位或立位時可以屈曲髖、膝關節;Ⅳ期:坐位屈膝>90°;Ⅴ期:健側站立位時,患側可屈膝伸髖,伸髖下踝可背伸;Ⅵ期:協調運動基本正常。
1.6 統計方法 采用SPSS 19.0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以均值加減標準差(±s)表示,兩組間均值比較采用兩獨立樣本t/t′檢驗,治療前后比較采用配對t檢驗。無序計數資料以頻數(f)、構成比(P)表示,采用χ2檢驗。兩樣本等級資料比較,采用Ridit分析,由DPS 7.05進行數據處理。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試驗完成情況 治療期間對照組5例發生二次中風,2例因其他內科疾病轉外院,得184例;觀察組7例發生二次中風,1例因其他內科疾病轉外院,得183例。經過正態性檢驗,數據符合正態分布。
2.2 神經肌電活動
2.2.1 運動神經治療前,兩組患者脛、腓總神經DML、MCⅤ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與治療前相比,治療后兩組脛、腓總神經DML、MCⅤ均顯著改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與對照組比較,觀察組脛、腓總神經DML更短,MCⅤ更快(P<0.01、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脛、腓總神經運動神經肌電活動情況比較(±s)

表2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脛、腓總神經運動神經肌電活動情況比較(±s)
注:與治療前比較,①P<0.05;與對照組比較,②P<0.05,⑵P<0.01
?
2.2.2 感覺神經治療前,兩組患者脛、腓總神經SCⅤ、SNAP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與治療前相比,治療后兩組脛、腓總神經SCⅤ、SNAP均顯著改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與對照組比較,觀察組脛、腓總神經SCⅤ顯著更快,SNAP顯著更高(P<0.01),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脛、腓總神經感覺神經肌電活動情況比較(±s)

表3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脛、腓總神經感覺神經肌電活動情況比較(±s)
注:與治療前比較,①P<0.05;與對照組比較,⑵P<0.01
?
2.3 下肢功能 治療前,兩組患者Fugl-Meyer運動量表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與治療前相比,治療后兩組Fugl-Meyer運動量表評分均升高,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與對照組比較,觀察組Fugl-Meyer運動量表評分較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Fugl-Meyer運動量表評分比較(±s)

表4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Fugl-Meyer運動量表評分比較(±s)
注:與治療前比較,①P<0.05;與對照組比較,②P<0.05
?
2.4 運動功能 治療后,兩組患者Brunnstrom分期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觀察組優于對照組,見表5。

表5 兩組患者治療后Brunnstrom分期比較(?,ˉR)
3 討論
腦卒中是因腦血栓或腦血管破裂等各種病理因素導致的腦血管性病變[11],多見于中老年人,其復發率、致殘率和死亡率高,嚴重威脅著國民的生命健康[12]。根據其發病進程,主要分為急性期、恢復期和后遺癥期。后遺癥期是腦卒中繼急性期和恢復期之后遺留不同后遺癥的時期,主要以半側肢體偏癱、行走功能障礙為主,改善患者足下垂癥狀是臨床重要的康復治療內容,對患者的后期生活質量極為重要[13]。腦卒中后,中樞神經支配紊亂,踝關節周圍的肌肉組織和韌帶組織等不能夠被正常的神經支配,受重力作用出現跖屈、內翻,導致腦卒中后足下垂[14]。
康復鍛煉貫穿于腦卒中的始終,康復鍛煉的最終目的是讓其回歸家庭、回歸社會、盡量讓其軀體和心理能夠自主康復。腦卒中后遺癥期患者患側肌張力增高,可能是中樞受損,小腿三頭肌牽拉反射作用增強增加了肌肉的僵硬度和踝關節周圍肌肉韌帶結構發生變化的結果[15]。此時踝關節正常活動受限,無法按照原來的運動方式運動,導致步行不穩,容易跌倒。康復鍛煉主要以被動+主動屈伸踝關節及步態分解練習為主,目的在于緩解肌肉、韌帶僵硬和粘連。長期進行強化的主動運動可以充分發揮患者的主動參與意識,提高腦卒中患者對患肢的掌控能力[16];而被動屈伸鍛煉則有利于恢復患者本體感覺和前庭功能,促進功能恢復。Khattab S等[17]認為長期(≥5月)康復鍛煉能夠顯著改善腦卒中患者的下肢功能,但從遠期來看單純康復鍛煉效果有限。中樞神經細胞作為永久細胞,損傷之后往往難以修復和完全替代,因此腦卒中的康復時間跨度較長,而康復難度相對較高,單一的康復鍛煉無論是患者依從性還是起效時間均較差[18]。另外也有研究發現[19],隨著腦卒中病程發展和患側肌萎縮程度的增加,同樣強度康復鍛煉誘發的患者疼痛和康復不耐受顯著增加,形成了康復鍛煉-不耐受-康復鍛煉強度降低的惡性循環,嚴重影響了康復效果。因此,臨床中將康復鍛煉和針刺等傳統療法結合治療腦卒中后遺癥期肢體殘障。
腦卒中導致的偏癱、足下垂在中醫學屬于“痿證”范疇,早在《內經》時期已對其病因、病機及治法進行了詳盡論述。《素問·痿論》云:“治痿者獨取陽明,何也?岐伯曰:陽明者,五藏六府之海,主潤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也……故陽明虛則宗筋縱,帶脈不引,故足痿不用也。”陽明屬胃,為氣血津液生化之地,生化乏源,則津液不足,無以滋養,故而宗筋不利;又陽明多氣多血,亦感熱邪,故而清陽明之熱,治在四肢。痿證一病,正氣虧虛為本,外感六淫為標,痰、瘀為病理產物,氣血逆亂而引起腦脈痹阻,四肢不養故足痿[5]。由此,或病虛,或病實,治皆歸陽明,即“治痿獨取陽明”。
臨床報道,針刺對該病的足下垂癥狀有較好療效[11,20]。本研究在“治痿獨取陽明”理論指導下,取合谷、曲池、伏兔、足三里、上巨虛、下巨虛、豐隆、解溪、內庭穴位。合谷為陽明經原穴,主疼痛,半身不遂;曲池,陽明經合穴,主治風痹邪氣,半身不遂;伏兔屬足陽明胃經穴,主風勞痹逆,攣縮;足三里為足陽明經合穴,針刺足三里可激發陽明經氣,濡養筋肉,往往與陽陵泉配對使用,具有固本培元、通絡止痛的功效。陽陵泉為八會穴之筋會,又是足少陽膽經之合穴、下合穴,是治療半身不遂的主穴之一。現代醫學認為,針刺陽陵泉可以增強中風偏癱患者患肢感覺反饋和促進其運動信號輸出,改善下肢功能[21]。上、下巨虛分別為陽明大小腸之下合穴,治療風濕痹,手足不仁,腳脛酸痛屈難伸;豐隆為陽明胃之絡穴,主腿膝酸,屈伸難;解溪是足陽明胃經穴,主治下肢痿痹、足下垂;內庭為足陽明經滎穴,治療四肢厥逆,手足冷。諸穴配伍共奏補脾和胃、補益氣血、疏通經絡、除痹祛風之效,如《素問》言“補其滎而通其俞,調其虛實,和其逆順,筋脈骨肉,各以其時受月,則病已矣”。現代醫學認為針刺改善腦卒中足下垂的機制包括:①調節受損周圍神經功能,恢復肌細胞固有疏松性,促進細胞內新陳代謝,減緩肌蛋白因神經支配后的變性[22];②調節腦血流量,改善腦組織氧代謝;③通過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抑制脂質氧化從而減輕腦缺血再灌注損傷;④促進本體感覺恢復和誘發相應的腦電活動等[23]。除了常規針刺治療,在本研究中采用電針刺激足三里、陽陵泉這組穴位增加刺激強度。與手針相比,電針通過電流形成的捻轉幅度和速度均較高,因此刺激強度大[24]。電針治療神經系統損傷具有優勢,具有促進受損神經軸突再生、減少神經膠質瘢痕形成、抑制氧化代謝產物累積、增加神經營養因子分泌等多種生物學作用[25]。現代醫學認為,運動終板、神經突觸集中區域可能是中醫學經絡穴位發揮療效的物質基礎,刺激相應肌肉、肌腱軟組織的運動終板和神經突觸可以顯著改善對應解剖部位的運動功能障礙[26-27]。足三里、陽陵泉均位于小腿外側,兩穴處均有控制小腿前外側背伸肌群的腓神經及其屬支走行,因此在針刺足三里、陽陵泉的同時加用電流刺激發揮針刺和電針以上療效的疊加效應可能是觀察組獲得更好療效的重要原因。
本研究結果顯示:經針刺治療后,觀察組脛神經、腓總神經運動神經末端潛伏期、運動神經傳導速度顯著改善,同時脛神經、腓總神經感覺神經傳導速度、感覺神經電位亦改善顯著;此外,在Fugl-Meyer運動量表評分中,觀察組顯著區別于對照組,肯定了針刺陽明經治療腦卒中后遺癥期足下垂的臨床療效。在“治痿獨取陽明”指導下電針、針灸合康復鍛煉可以顯著改善腦卒中足下垂患者的肌肉活動和運動功能,為臨床治療該類疾病提供了可參考的建議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