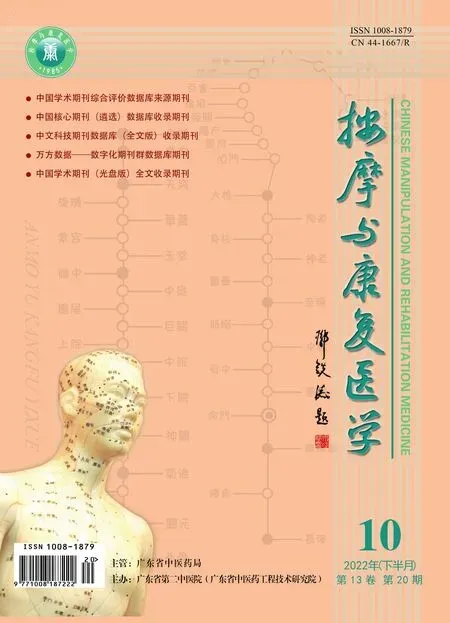綜合康復訓練治療巨腦回畸形兒童復雜功能障礙1例及文獻回顧
彭穗英,王曉蘭,周曉明,馮蓓蓓,王偉銘,劉恩桐
(1.中山大學附屬第六醫院,廣東廣州 510655;2.廣州醫科大學附屬腦科醫院,廣東廣州 510370;3.深圳恒生醫院,廣東廣州 518115)
巨腦回畸形是一種由胚胎發育期神經元分化移行異常引起大腦皮質構成障礙的先天性疾病[1],該病患兒常在運動、語言及認知方面表現出不同程度的發育遲滯[2]。目前研究認為引起神經元移行異常的原因主要為基因遺傳及突變,已發現的常見異常位點包括常染色體17p13.3 處的LIS1 基因及性染色體Xq22.3-q23 處的DCX 基因[3]。近親結婚為巨腦回畸形患者家族史的一個顯著特點[4],也有研究指出產前使用止痛劑、抗生素、甲狀腺素、麻黃堿等藥物及妊娠早期陰道出血、頻繁上呼吸道及泌尿系感染、低血壓、X 光接觸史等均有可能增加巨腦回畸形發病的風險[2]。由于巨腦回畸形發病率較低,目前對該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病因及發病機制探索方面[5-6],而對有助于提高患者生存質量的康復治療鮮見報道。我科對1名巨腦回患兒進行了綜合康復治療并取得滿意效果,現將有關資料加以總結。
1 臨床資料
呂某,女性,2 歲10 月,因“言語、行走不能2年余”入院。患兒出生7個月會抬頭,12個月時在兩手支持下能坐,20 個月在家屬扶助下站立1~2s,至今仍不能行走;患兒喜坐,可俯爬,爬行模式為腹部著地的匍匐爬行。18 個月會發“媽”。患兒母親孕期身體健康,否認感冒、服藥及毒物接觸史。患兒在孕43 周出生、產程順利,出生時阿普加評分正常,出生體重2.9kg,身長不詳。出生后母乳喂養,患兒8個月起逐漸添加各類輔食,現飲食結構已同成人。患兒無抽搐發作史。父母體健,無傳染病及毒物接觸史,無家族性遺傳疾病,父母非近親結婚,非單親家庭。神經系統查體:神志清楚,哭聲響亮,僅可發“ba”、“ma”等單音節;注意力不集中,檢查欠配合;脊柱生理彎曲存在,運動無受限,四肢肌張力正常,雙上肢肌力5 級,雙下肢肌力4+級,雙側膝關節過伸畸形,左膝關節PROM 5°~130°,右膝關節PROM 5°~125°。近端肌力,遠端肌力不配合檢查。腱反射正常,病理反射未引出;拼鑲嵌板、搭積木、畫線、認圖形等項目模仿操作差。在當地醫院頭顱磁共振檢查提示:雙側大腦皮質彌漫性增厚,腦溝變淺,腦回減少,符合巨腦回畸形[7],見圖1。

圖1 患兒頭顱磁共振圖像(T1、T2及T2-Flair像)
2 治療方法
2.1 評估方法
2.1.1 吞咽言語能力(1)攝食吞咽功能檢查:流質食物,飲水量30mL 時有口角流出,無嗆咳。小兒喂食軟食物,避免硬的固體食物,需進食特殊類型食物。(2)Frenchay 構音障礙評定:反射——流涎D級;構音器官——下頜靜止狀態下D級,唇靜止狀態下D 級,舌、軟腭等不配合檢查;構音檢查——發聲,語音不配合檢查。
2.1.2 語言能力s-s語言發育遲緩評價法[8]評價言語能力。
2.1.3 神經發育檢查Gesell 嬰幼兒發育量表[9]評估整體神經發育評估。
2.1.4 運動能力 采用粗大運動能力測定(GMFM-88)量表[10]評估運動能力。
2.1.5 功能診斷 吞咽障礙、構音障礙、精神發育遲滯。
2.2 治療經過 采用綜合康復訓練治療,包括運動與作業康復訓練、吞咽、言語治療、藥物治療、中醫針刺,連續治療6周。
2.2.1 運動與作業康復訓練(1)依據神經發育療法[11-12],利用Bobath 球進行骨盆帶的前后傾控制,限制異常運動和姿勢,提供正確的感覺輸入,每天1次,每次30min。(2)墊上活動及高椅坐位訓練上肢手功能[13],包括不同高度取接物品、堆積木游戲等,每天1次,每次20min。(3)坐站轉移,扶持站立訓練,平衡杠內扶持及手推車步行訓練,每天1次,每次20min。(4)運用數字OT 評估與訓練系統(型號FlexTable,FT201,中國出產,廣州市章和電氣設備有限公司),該平臺使用多點觸控技術,提供融合視覺、聽覺、觸覺等多感官的上肢運動控制互動訓練,患兒在扶站狀態下進行每天30min的認知訓練。
2.2.2 吞咽、言語治療(1)吞咽治療:神經肌肉電刺激,多感官刺激;(2)語言訓練:①事物基礎概念、語言等認知訓練、實物及彩圖、重復練習;②手勢語訓練、事物及狀況的手勢模仿[14];③自言自語、自我對話;④溝通行為誘發,溝通情景、游戲訓練法。
2.2.3 藥物治療 采用促智藥物奧拉西坦口服,每日兩次,每次0.8g[15]。
2.2.4 中醫針刺 取穴于頭部——州圓,上肢——靈骨、大白,下肢——失音,每天1 次,每次留針30min。
3 治療效果
3.1 運動能力 治療后患兒坐位平衡好,在較強外力推動下仍能保持平衡。自主翻身動作迅速、流暢,爬行模式為四點跪位爬行,可獨自從坐位站起,獨自站立可持續20~30s,扶持站立可持續3min。雙下肢肌力上升到5 級,下肢體佩戴支具后可糾正膝關節過伸現象,在牽手或扶墻情況下行走約8m。訓練前GMFM 粗大運動量表得分為臥位及翻身84.31%、坐位68.33%、爬行與跪位47.62%、站立7.70%,行走跑步及跳躍0.00%;訓練后相應得分為臥位及翻身98.04%、坐位90.00%、爬行與跪位71.43%、站立25.64%,行走跑步及跳躍22.20%,見表1。

表1 綜合康復治療前后GMFM得分比較
3.2 吞咽、語言能力 訓練后患兒語言及手勢語提示可理解部分事物名稱,她可清楚發“媽媽、爸爸、汪汪、要”等1~2 音節詞語,自發無意義音節增多;能用點頭,搖頭及指物等手勢語表達需要。訓練前語言發育s-s 法為符號形式-指示內容的關系處于階段2-1 事物功能性操作、2-2 事物的匹配和2-3事物的選擇均未能通過。基礎性過程檢查處于1歲前年齡水平,交流態度一般。Frenchay 構音障礙評定:構音器官檢查分級,流涎D 級,下頜靜止狀態D 級,唇靜止狀態D 級。訓練后s-s 法發育階段上升至3-1 手勢符號階段(符號形式-指示內容的關系的階段分5 階段,第1 階段-對事物,事態理解困難;第2階段-事物的基礎概念;第3階段-事物的符號;第4 階段-詞句,主要句子成分;第5 階段-詞句,語法規則),基礎性過程(操作性課題)上升至1 歲5 個月部分年齡水平;交流態度好。其他檢查:Frenchay 構音障礙評定,流涎分級從D 級上升到C 級,唇分級從D 級上升B 級,下頜分級從D 級上升B 級(Frenchay 評分:分ABCDE 五級,A 級指正常,B級以下異常)聽力檢查正常。
3.3 認知能力 訓練前患兒注意力不集中,拼鑲嵌板、搭積木、畫線、認圖形等項目模仿操作差,訓練后患兒注意力可保持30s 至1min,拼鑲嵌板、搭積木、畫線基本能模仿完成,能識記圓形,三角形。訓練前Gesell 神經發育商數(DQ)為適應行為20.13、大運動行為17.73、精細運動23.33、語言行為23.33、個人社交行為18.96;訓練后相應發育商數為適應行為35.86、大運動行為32.94、精細運動45.16、語言行為27.45、個人社交行為36.54,見表2。

表2 綜合康復治療前后Gesell發育商數比較
4 討論
巨腦回畸形是一種胚胎發育期神經元分化移行異常引起大腦皮質構成障礙的先天性疾病[1]。胚胎期,神經元在化學信號引導下由腦室周圍向外逐漸遷移并形成大腦皮質。正常分化的皮質應包含6 層細胞結構,而巨腦回畸形患者神經元遷移不完全,往往僅包含4 層細胞結構,在大體病理上則表現為腦回減少、腦溝變淺,大腦皮質呈“光滑”狀[3]。巨腦回畸形患兒常表現出運動、語言及認知發育遲滯,對患兒的生活造成巨大影響[2],與我科對患兒在運動、語言、認知方面的評估結果一致,均表現出極重度發育遲滯(Gesell評分DQ<25),其中大運動中的站立、行走、跑步跳躍能力及語言能力缺失尤為突出(GMFM 對應得分為7.70%、0.00%)。而由于巨腦回畸形發病率較低且重型患兒難以生活至成年[16],臨床對該病康復治療方案及療效的觀察尚無統一標準,希望本病例總結能對該方面有所補充,為該病臨床研究提供更多證據。
人類的神經網絡在一生中均處于動態變化之中,通過學習與訓練,神經元之間可以建立新的、更廣泛的連接通路[17]。而神經元等由神經干細胞分化而成,有研究表明運動、行為學訓練可以促進移植的神經干細胞遷移、分化,并提高移植細胞在腦梗死大鼠腦內的存活率,促進神經功能障礙的康復,對神經行為學改善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18-19]。另一項研究表明,使用運動再學習療法訓練(主要為增加運動控制能力)對腦缺血損傷猴的神經功能障礙改善顯著,能夠促進腦血流量增加,一定程度下促進神經再生,而且對其意識形態、自我控制能力、平衡能力等癥狀體征改善明顯[20]。我科對患兒采取的對癥強化訓練,制定了包含運動、語言及認知訓練在內的綜合康復訓練方案,與上述運動訓練目的方法類似。其結果顯示患兒的運動能力提高明顯,且其運動功能恢復相較于相似殘障程度的腦癱患兒恢復快;流涎癥狀明顯改善,認知能力有一定程度改善,非語言表達能力明顯進步,而語言功能改善不明顯。患兒運動能力的改變與前述研究的結果類似,因此推測其可能是由于巨腦回畸形這個疾病主要是神經細胞遷移異常,神經元細胞仍具有較強的再發育及再分化能力,而腦性癱瘓則多為神經元缺血死亡所致,因此在短期使用對癥的強化運動訓練后可使患兒一定程度下增加神經元細胞的增殖分化,增加腦血容量,改善其自我控制、平衡能力等。該推測可借助腦功能磁共振成像及彌散張量成像技術加以驗證[21],并需要長時間的病例對照觀察,這將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而對于其語言、認知能力的改變,可能與控制該種能力的神經通路的復雜性相關。運動的神經通路構成較為簡單,容易通過訓練改善通路連接。而語言神經通路構成較為復雜,短期訓練難以明顯改善通路連接。而且語言為人類特有的抽象高級神經功能,其學習難度很大,故需要更為漫長的訓練過程。
近年來,人們發現經絡與微循環存在著密切的關系,經絡是中醫理論的精髓,微循環的結構與經絡循行存在相似之處,微循環的血流灌注量能夠反映經絡的循經感傳現象[22]。針刺療法可通過多環節、多途徑、多層次調節機體微循環狀態,且有著效果持久、調節全身、不良反應小等優點。在生理狀態下,針灸可調整機體達到最佳的微循環生理狀態;病理狀態下,針灸可有效改善微循環障礙,使機體趨于平衡狀態。大量動物實驗表明,針刺可通過調節腦缺血區的灌注及腦微血管自律運動,改善腦部的微循環狀態。李麗等[23]研究發現,頭排針治療前后,腦梗死患者頸動脈的血流速度及血流量均有顯著升高,認為頭排針治療能在短期內增加頸動脈血流量,提高為腦循環供給的總能量,改善微循環指標,但頸動脈系統總能效率(振蕩總能與總能量的比率)在治療后無顯著變化。同時,這種良性調節作用會體現在不同腧穴上。
本研究也給患兒使用了促智藥物奧拉西坦,并進行了促進神經發育針刺治療。奧拉西坦作為臨床上常用的促智藥物之一,其對于血管源性癡呆、腦性癱瘓均有較好的治療效果[24]。其作用機制為激活腺苷酸激酶和作用門冬氨酸受體,升高大腦皮質和海馬部分乙酰膽堿轉運,提高膽堿攝取親和力和促進大腦對葡萄糖、氧氣的代謝,從而保護和修復神經元,改善記憶、思維和學習能力[25]。尚有研究證實,奧拉西坦能夠促進大腦皮層聯絡纖維束重塑,從而實現功能恢復[26]。同時,該藥毒副作用小,適用于兒童[25]。此病在中醫學上屬于腦病范疇,針灸在治療腦病及修復神經上具有確切的療效。董氏奇穴針法在治療和調神腦病上具有明顯的優勢,因此采用董氏奇穴針刺州圓、靈骨、大白、失音。州圓位于頭頂,主治神經失靈,具有醒腦開竅的功效;靈骨和大白相配,主治肺脾;失音主喉,開眼通竅。因幼兒肺脾本嬌弱,通過針刺靈骨、大白促進患兒的肺脾功能的恢復,同時針刺州圓、失音促進腦神經的修復和發育。
除對患兒進行了積極康復治療外,也密切觀察患兒的日常生活行為,以期發現患兒是否在某方面有特別表現,如能加以培養則有利于患兒日后參與社會生活。在治療過程中,患兒對顏色搭配顯示出特長,能很好地選擇自己的衣物(通過表情及簡單詞語表達對服裝的喜惡),故建議家長培養患兒的相關藝術特長,例如繪畫。此外,在對患兒的整個訓練過程中,強調運用正向激勵法。當患兒正確完成某項指令或較以前取得進步時,將給予微笑、擁抱、輕撫,并以維生素糖果作為獎勵;同時特別注意防止患兒發生碰撞、跌倒,以避免其對訓練過程產生恐懼,這對于確保患兒配合治療具有重要意義。在長期的臨床經驗中,發現患兒的治療時期會影響療效。在兒童發育早期(3 歲前)進行干預將明顯降低語言障礙的短期和長期的不良影響,但該病例尚未對此進行長期觀察記錄分析;并且由于本病的特殊性、罕見性、治療周期與倫理問題,本研究未能避免患兒的生長發育對綜合康復療法療效評估的影響。
雖然目前除了本研究所采用的綜合康復治療方法之外,尚有許多新興治療技術如神經干細胞移植、基因沉默及過表達等被用于巨腦回畸形的動物模型研究中[27-28],但由于以上技術的復雜性和效果的不確定性,尚未被正式用于臨床治療中。而本研究的綜合康復療法的療效為此病的臨床治療提供了一個良好的選擇。因此,積極康復治療在一段時期內仍將是改善巨腦回患者各方面能力的首選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