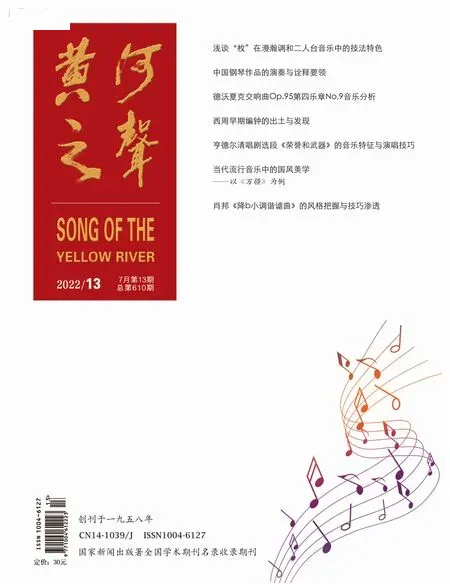西周早期編鐘的出土與發(fā)現(xiàn)
毛 悅
自20世紀(jì)50年代以來,在陜西、山西、河南等地,陸續(xù)出土了少量編鐘,這些編鐘均出自墓葬,且為科學(xué)發(fā)掘品。與此同時(shí),其他一些地區(qū)雖也有編鐘出土,但多為單件品或是私人收藏,以及明器編鐘等情況[1]。它們或是伴隨一些如水土流失、泥石流等自然現(xiàn)象出現(xiàn),亦或是無目的性掘獲等,使得這類編鐘成為偶然發(fā)掘品。由于這些編鐘多非科學(xué)考古所得,因此它們具有隨意性、偶然性和盲目性,從而缺乏嚴(yán)謹(jǐn)?shù)目茖W(xué)性,因此這些樂器均不作為本文探討的對(duì)象。本文所要論述的編鐘時(shí)代包括西周早期至中期,橫跨成—康—昭—穆—恭五個(gè)時(shí)期。
一、陜西地區(qū)
西周時(shí)期,周族主要居住于陜西中部以及甘肅東部地區(qū),在數(shù)代先輩的努力下,周族經(jīng)過后稷封邰(今陜西武功)、公劉遷豳(今陜西旬邑)、太王居岐(今陜西岐山縣)、文王治豐多次遷都后,最終由武王將王朝建都于鎬京(今西安市長(zhǎng)安區(qū))[2],直至周平王東遷之前一直盤踞在此。西周在政治上實(shí)施分封制,很多諸侯國(guó)在陜西周邊建立政權(quán),文化上不但以周文化為主,同時(shí)又結(jié)合了當(dāng)?shù)赝林幕纬闪烁鞯氐奶厣@使得周文化不但得到了繼承同時(shí)也得到了發(fā)展。陜西作為周文化的中心,同時(shí)在晚商文化的影響之下,使得這一地區(qū)出土的西周樂器既偶有晚商特征,也具有鮮明的西周早期特征。出土編鐘主要包括:
(一)陜西寶雞竹園溝七號(hào)伯格BZM7
(二)陜西寶雞茹家莊伯旨BRM1乙室
1974年,在寶雞市茹家莊BRM1乙室出土甬鐘三件(BRM1乙:28、29、30)。該墓葬位于陜西省寶雞市茹家莊,當(dāng)時(shí)共發(fā)掘了BRM1、BRM2兩座墓葬,以及馬坑、車馬坑[5],其中BRM1已出土編鐘三件一套。
BRM1為兩棺一槨,分為甲、乙兩室,青銅禮器主要放置于外棺右側(cè),而這三件編鐘則散落于其中。通過對(duì)BRM1乙中所出銅器銘文得知,該墓大多青銅器為伯自作自用,這座墓葬隸屬于伯旨無疑。通過與上例竹園溝所出銅器對(duì)比得知,該墓時(shí)代晚于上例,這套甬鐘時(shí)代被斷為昭、穆時(shí)期,即西周早期晚段,或是早中期之際。
(三)陜西長(zhǎng)安縣普渡村長(zhǎng)甶墓M699
1954年,在陜西長(zhǎng)安縣普渡村長(zhǎng)甶墓M699出土甬鐘三件(M699:4、M699:3、M699:2)[6]。墓葬位于陜西省西安市長(zhǎng)安縣普渡村斗門鎮(zhèn),該墓出土大量隨葬器物,其中包括玉器、陶器,以及青銅器。墓內(nèi)的青銅器分三層存放,三件編鐘位于中層。根據(jù)發(fā)掘簡(jiǎn)報(bào)所述,三件甬鐘舞壓在鼎口上,口向上,內(nèi)有燒過的木燼,底下有很細(xì)致織物痕跡,上有甬鐘的壓印。
該套甬鐘的年代可從同墓的盉上銘文得知,銘為:“惟三月初吉丁亥,穆王在下淢居。穆王饗醴,即井伯大祝射。穆王蔑長(zhǎng)甶以逨即邢伯,邢伯氏演部姦。長(zhǎng)甶蔑曆,敢對(duì)揚(yáng)天子不丕休,用肇作尊彝”[7]。這篇銘文為此墓出土青銅器中最長(zhǎng)一篇,記錄了作器年代屬于西周穆王時(shí)期,因此該套編鐘當(dāng)屬西周中期前段穆王時(shí)期所有。
二、河南地區(qū)
河南地區(qū)是商王朝的發(fā)源地與文化集中地,這里不但包括以二里崗文化、殷墟文化為主的商文化,還包括夏代二里頭文化,這些文化同時(shí)組成了著名的夏商文化,可見河南地區(qū)在考古學(xué)研究中有著重要地位。
雖然周初經(jīng)歷了武王克商,但是河南乃是商人后裔的聚集地,這使得河南地區(qū)具有鮮明的商代遺風(fēng)。而周朝雖建都于陜西地區(qū),但對(duì)河南地區(qū)的管理周王依然重視。由于周王對(duì)河南大部分地區(qū)實(shí)施了分封,這才有了西周時(shí)期的應(yīng)國(guó)(今今河南省寶豐以東、魯山東南及平頂山市區(qū)一帶)、管國(guó)(今河南鄭州)、魯國(guó)(今河南魯山縣)、蔣國(guó)(今河南獲嘉縣)、密國(guó)(今河南新安縣)、邢國(guó)(今河南溫縣)等封國(guó),這些國(guó)家均是由周王朝直接分封的姬姓國(guó)。至此,西周時(shí)期的河南成為了周文化與商文化交融且碰撞的地區(qū),這種文化關(guān)系表現(xiàn)在音樂上更是在東周“鄭衛(wèi)之音”中極為明顯。
河南地區(qū)的西周早期編鐘主要包括河南省平頂山市郊魏莊發(fā)現(xiàn)的三件(或?yàn)樗募┙巡仞姟_@套編鐘并非科學(xué)發(fā)掘所得,而是一農(nóng)民在挖紅薯窖時(shí)所得,該農(nóng)戶稱該套甬鐘出土?xí)r堆放在一起,無其他遺物共存[8]。因此其歸屬以及相關(guān)隨葬品無從考證,但是這套編鐘從其形制觀察來看,并結(jié)合陜西地區(qū)的三套編鐘來看,其年代大體應(yīng)屬于穆王末期或穆、恭之際[9],這套編鐘也是平頂山地區(qū)出土最早的西周樂器。
三、山西地區(qū)
山西作為考古大省,音樂物質(zhì)遺存也極其豐富。出土樂器不但包括早期石質(zhì)樂器,還包括大量青銅樂器,而青銅樂器中以鐘類數(shù)量最多,如晉侯穌鐘、曲村晉侯M9編鐘、楚公逆鐘、太原金勝存編镈等。這些青銅鐘類樂器多出自晉南地區(qū),主要是因?yàn)樯轿鞯貐^(qū)的諸侯國(guó),如晉國(guó)(山西晉南翼城、曲沃一帶)、魏國(guó)(今山西芮城)、北虞國(guó)(今山西晉南)、霸國(guó)(今山西臨汾大河口一帶)、倗國(guó)(山西絳縣橫水一帶)等國(guó)家,大多聚集在山西南部。過去出土的大量編鐘主要集中于西周中晚期,以及東周時(shí)期。就西周編鐘的發(fā)現(xiàn)情況而言,山西地區(qū)主要包括:
(一)山西曲沃天馬—曲村M9
1992年,山西天馬—曲村晉侯墓地M9出土四件一組編鐘(該套編鐘由于測(cè)音數(shù)據(jù)有誤,暫姑認(rèn)為可能為一組),該墓未經(jīng)盜掘,編鐘組合應(yīng)是完整的。墓葬位于墓地東北側(cè),為一槨兩棺,墓主人為一代晉侯晉武侯。編鐘出土?xí)r位于槨室南端,該套編鐘保存狀況極差,形制雖清晰,但紋飾已幾乎無法辨認(rèn),發(fā)掘者將其定位西周穆王前后[10]。根據(jù)同墓出土的其他器物可知,這四件晉國(guó)編鐘的時(shí)代,應(yīng)該晚于國(guó)編鐘和長(zhǎng)甶編鐘,估也屬于穆王時(shí)期后段[11]。
(二)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地[12]M1
該墓位于山西省運(yùn)城市絳縣西部。2004年秋,此處多座墓地被盜掘,運(yùn)城市文物局開始對(duì)此處墓地進(jìn)行搶救與挖掘,并將新發(fā)現(xiàn)的兩座帶墓道的大墓,命名為M1、M2[13],通過大量青銅器銘文含有“倗”字可知,這兩座墓屬于西周倗國(guó)墓地,此處的倗國(guó),文獻(xiàn)未見記載。但曾經(jīng)也出土了一些與倗國(guó)相關(guān)得青銅器,如天馬曲村曾出土的倗簋、保利藝術(shù)博物館藏倗伯鳥尊等,此倗應(yīng)與倗國(guó)相關(guān)。關(guān)于族屬問題,經(jīng)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謝堯亭先生考證,倗國(guó)為媿姓,狄人也。通過傳世的西周鼎、簋等銘文可知,倗與畢乃是互婚。傳世的倗中(仲)鼎、倗□生鼎、橫水墓地出土的銅簋(M2508:2)銘文都顯示倗為媿姓,倗與姬姓的晉、畢、芮等國(guó)聯(lián)姻[14](以下倗國(guó)概述均如此)。M1為一槨二棺,與M2為夫妻并穴合葬墓。M1的四件銅器上有“倗伯作畢姬寶旅鼎”字銘,可知墓主人為倗伯夫人畢姬,可能與周同為姬姓[15]。而畢是西周顯族,為姬姓,畢氏曾在王室任要職[16]。該墓隨葬品包括車馬器、青銅器、玉器等。青銅禮器置于外棺與槨之間,主要在槨室內(nèi)外棺南側(cè)的西端[17],其中就包括五件青銅編鐘(暫時(shí)定名為M1:1、M1:2、M1:3)(見圖1)。該墓未被盜擾,應(yīng)為完整組合,但編鐘出土?xí)r為散落狀。該墓銅鼎、仿銅陶鬲,以及特有荒帷中鳥紋來看,該墓時(shí)代應(yīng)為西周中期穆王時(shí)期或略晚[18]。同時(shí)觀察五件編鐘,從其外形來看與西周早期編鐘相比,紋飾更為精致,體質(zhì)略修長(zhǎng),但整體風(fēng)格仍屬于周鐘形制。

圖1 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地M1編鐘擺放情況[19]
(三)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地M2
整體概述如上,這套編鐘與M1的數(shù)量相同(見圖2),也為五件一組,但是這種組合形式,并不多見,目前所見僅此兩例。但該套編鐘從紋飾與形制來看,似為兩套編鐘拼湊而成,但經(jīng)過測(cè)音可知確為一組。但是對(duì)于五件一組組合形式,亟待日后對(duì)M1實(shí)測(cè)后,方可進(jìn)一步確定這種組合實(shí)際存在。關(guān)于編鐘的時(shí)代,由于兩座墓葬屬于夫妻合葬墓,且結(jié)合鼎、簋,以及酒器組合形式等特征來看,該套編鐘年代應(yīng)與M1相近,同為西周穆王時(shí)期或略晚[20]。

圖2 絳縣M2編鐘[21]
(四)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地M1011
整個(gè)絳縣橫水墓地從2004年開始發(fā)掘,工作持續(xù)三年,共發(fā)掘204座墓葬,M1011與M1、M2均屬于二期墓葬。該墓位于M1北偏東北方向,墓葬大小與M1、M2類似。M1011墓主為男性,隨葬品具體情況見附表7,青銅禮器主要分為食器、酒器與水器。而隨葬酒器的多為高級(jí)貴族,結(jié)合整個(gè)絳縣橫水墓地情況來看,所有出土銅鐘的墓葬均為隨葬酒器的墓葬[22]。同時(shí)該墓葬有腰坑并且伴有人殉,我們知道腰坑起源于新時(shí)期時(shí)代,在商代二里崗、殷墟文化中腰坑與人殉得以大量使用,它們是身份與地位的象征,同時(shí)該墓出土青銅鼎上有“倗伯”作器的記載[23]。以上云云,均說明M1011墓主人身份及地位較高,據(jù)考證為倗國(guó)中期倗伯,名字不詳,年代應(yīng)不晚于穆王時(shí)期。七件編鐘(M1011:66、67、68、69、70、71、72)從紋飾與形制來看分為兩組二式,第一組為大型甬鐘(M1011:66、67、69、72),第二組為小型甬鐘(M1011:68、70、71),尺寸差異較大。該套編鐘在紋飾上也有較大出入,具體論述見下文。
(五)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1
該墓由于盜掘的原因最終發(fā)現(xiàn)于2007年5月,2009年5月至2011年5月進(jìn)行大規(guī)模搶救性發(fā)掘。該墓位于山西省南部翼城縣以東6000米處,該墓地包含西周墓葬1500余座。
整個(gè)墓地屬于文獻(xiàn)缺失記載的霸國(guó),橫貫西周直至春秋初年。M1發(fā)掘于2008年,墓具為一棺一槨,含有腰坑,坑中葬狗,同時(shí)墓葬中除了大量青銅器與陶器外,還包含原始瓷器[24],這都說明墓主人身份與地位較高。隨葬品位于室內(nèi)棺槨之間或棺蓋上,其中青銅器數(shù)量最多,包括禮器、樂器、兵器和工具等。樂器部分不但包括三件編鐘,同時(shí)還有三件鐃與兩件句鑃(根據(jù)方建軍先生對(duì)實(shí)物觀測(cè)后認(rèn)為并非是句鑃,實(shí)則為鉦[25]),發(fā)掘簡(jiǎn)報(bào)將這些樂器稱之為一組八件[26]。其中編鐘為三件,編號(hào)分別為M1:19、23、20,由于該墓地學(xué)術(shù)價(jià)值的重要性長(zhǎng)期展覽于各地,因此該套編鐘暫且未能進(jìn)行測(cè)音研究。這三件編鐘尤為值得注意,從形制來看有別于以往發(fā)掘的西周編鐘,外形更接近于庸,即小鐃。方建軍先生將這種形制的編鐘稱之為“庸式編鐘”(見圖3),但是這種形制的編鐘大河口M1乃是孤例,其余地方尚未見此類型編鐘。這種形制編鐘的出現(xiàn)具有重要意義,它為甬鐘起源于北方編庸(小鐃)提供了重要的佐證,進(jìn)一步說明了它們之間的繼承關(guān)系。關(guān)于這套鐘的年代,可以通過其余青銅器紋飾判斷,例如M1:251的青銅罍、M1:9的簋所使用的渦紋與商代無異。而M1:275—1的青銅卣所使用的蟬紋也與商代所用無異。發(fā)掘簡(jiǎn)報(bào)將大河口墓地的墓葬年代定為西周中晚期,M1定為西周中期早段,但是墓中出土的一些青銅器則具有西周早期風(fēng)格,并且包含晚商遺風(fēng),樂器方面尤其是編鐃于編鐘最為明顯,這說明這些青銅器使用時(shí)間較長(zhǎng),上限似能追溯至西周早期,并且有學(xué)者持相同觀點(diǎn)[27]。同時(shí)竹園溝M13曾出土一件小鐃,這件小鐃形制與和紋飾與晚商小鐃一致,唯甬部出現(xiàn)了用于懸掛的干,這可以說明小鐃在當(dāng)時(shí)不但可以置奏、執(zhí)奏,到了西周早期已開始嘗試懸掛演奏。而這件小鐃的年代被斷為西周早期成康之際,這件“過渡時(shí)期”的小鐃在當(dāng)時(shí)被一些學(xué)者認(rèn)為是小鐃向甬鐘發(fā)展的孤例,現(xiàn)在大河口M1編鐘的出現(xiàn),為甬鐘起源于小鐃提供了有力的證據(jù)。因此筆者作此估計(jì),該套編鐘的時(shí)代應(yīng)大致為西周早期早段,約為成康之際。

圖3 M1出土的“庸式編鐘”[28]
(六)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1017[29]
發(fā)掘情況與M1相同,墓主人為西周中期一代霸伯,隨葬品包含大量青銅器、玉石器、海貝等。數(shù)十件青銅器置于墓主頭前棺槨之間,其余青銅器發(fā)現(xiàn)于棺槨之間或棺蓋上,包括酒器、樂器、兵器等[30]。三件編鐘(暫定為M1017:1、M1017:2、M1017:3),從形制與紋飾來判斷,與陜西竹園溝M7的3件組編鐘相同,遺憾的是M1017編鐘其中一件由于整個(gè)鐘面被朽木覆蓋,因此暫存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工作站。筆者所見的兩件編鐘通過與竹園溝M7對(duì)比可知,這件覆蓋朽木的鐘應(yīng)為最大的低音鐘。這套編鐘當(dāng)屬于李純一先生所歸納的周鐘,其年代應(yīng)晚于竹園溝M7,時(shí)代大致為昭穆之際。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編鐘的編次與組合在發(fā)生著遞增變化。同時(shí)從形制來看這些編鐘除了大河口M1之外,均受周文化影響,有些編鐘甚至與周原地區(qū)出土的編鐘相似。因此不得不說西周時(shí)期受分封制的影響,倗國(guó)與霸國(guó)在很多方面與陜西的周文化相一致,并存在繼承與發(fā)展關(guān)系。
四、湖北地區(qū)
以往湖北地區(qū)所出土的編鐘大多集中在東周時(shí)期,且匯聚了大量的精品,如曾侯乙編鐘、湖北棗陽(yáng)九連墩M2編鐘等。該地區(qū)早期的編鐘不多見,出土多為單件或殘鐘。直到2010年隨州葉家山墓地的發(fā)掘,才得以豐富湖北地區(qū)西周編鐘的資料。
湖北隨州葉家山墓地位于隨州市東北,2010年由當(dāng)?shù)卮迕癜l(fā)現(xiàn),并在2011年對(duì)墓地進(jìn)行了全面發(fā)掘,共發(fā)掘63座墓葬與一座馬坑[31]。隨葬品數(shù)量較大,涉及銅器、陶器、瓷器等,通過對(duì)這些器物的判斷可以得知這是一座西周早期墓地,同時(shí)結(jié)合青銅器銘文中的“曾侯”二字,可知這座墓地應(yīng)與東周的曾侯有關(guān),據(jù)考證曾國(guó)為姒姓。
2013年3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duì)葉家山曾國(guó)墓地的第二次發(fā)掘主要包括77座墓葬,其中的M111與M28均為帶墓道的墓葬,我們知道墓葬中的墓道大多是權(quán)力和地位的象征,因此M111應(yīng)為貴族一級(jí)墓葬,M111為此次發(fā)掘中最大的墓葬。墓葬中設(shè)有二層臺(tái),主要放置青銅禮器、酒器與水器,值得注意的是在東部二層臺(tái)中放有原始瓷器,這中情況與前文所述霸國(guó)M1情況一致,同時(shí)在西二層臺(tái)放置編鐘與少量兵器[32],足可說明墓主人身份極為顯貴。根據(jù)一些青銅器銘文來看,主要內(nèi)容多與曾侯犺、曾侯諫有關(guān)。四件編鐘(發(fā)掘簡(jiǎn)報(bào)謂之5件,乃是將镈鐘算在內(nèi))便發(fā)現(xiàn)于此墓西側(cè)二層臺(tái)的中間位置,此套編鐘根據(jù)鉦篆四邊的紋飾來看可分為兩組,出土?xí)r交錯(cuò)排列。一組為以雙陽(yáng)線夾小乳丁為界(M111:7、M111:11),一組為以雙陽(yáng)線夾聯(lián)珠紋為界(M111:8、M111:13)。該鐘的年代由黃鳳春先生定為昭王之世[33]。發(fā)掘簡(jiǎn)報(bào)稱這套編鐘“應(yīng)是目前我國(guó)西周時(shí)期所見年代最早、出土數(shù)量最多的一套編鐘”[34]恐不屬實(shí)。首先,就年代而言,與竹園溝M7相比,組合形式得到了邁進(jìn),發(fā)展為4件組,年代上應(yīng)晚于其,同時(shí)黃鳳春先生將該套編鐘斷為昭王之世,而竹園溝M7則為康昭之際[35],進(jìn)一步說明這套編鐘應(yīng)晚于竹園溝M7,因此稱其為年代最早恐不適;其次,作為編鐘第二基音標(biāo)志的“X”形紋飾,也是其晚出的一個(gè)標(biāo)志。
上舉諸例,不但包括早年的考古發(fā)現(xiàn),同時(shí)也涵蓋最新的考古發(fā)現(xiàn),所涉及的封國(guó)主要集中于中部地區(qū),大多分布于黃河流域,僅一處位于長(zhǎng)江流域。若按照音樂文化區(qū)來劃分主要囊括中原音樂文化區(qū)、北方音樂文化區(qū),以及南方音樂文化區(qū)[36]。現(xiàn)在來談?wù)勥@幾套編鐘的共性:
——從文化屬性來看,這幾套編鐘所涉及的族屬,多為西周時(shí)期的異姓地方封國(guó),這些地區(qū)在西周時(shí)期,接受周王統(tǒng)治,深受周文化影響,但是從隨葬品、葬具,乃至祭祀情況來看,均摻雜著地方土著文化,有些甚至含有晚商文化遺風(fēng)。這些封國(guó)文化體現(xiàn)出既有與周文化一致的共性,又包含著屬于自己的個(gè)性特點(diǎn)。
——從用器者以及器主的角度來看,這幾套編鐘大多屬于貴族一級(jí)所享有,有些甚至是國(guó)君一級(jí),如晉侯墓地M9、倗國(guó)墓地M2等,這說明青銅器這種重器,在當(dāng)時(shí)由于受分封制的影響,以及禮樂制度的束縛,與其他隨葬品已經(jīng)有了明確的界限劃分。
——從伴出狀態(tài)來看,這幾套編鐘均不是單獨(dú)存放,不存在于諸如后世所謂的“樂器坑”中(如甘肅禮縣大堡子山遺址樂器坑、新鄭鄭韓故城遺址樂器坑),大多是與酒器、食器等盛儲(chǔ)器共出,說明當(dāng)時(shí)的樂器在墓主生前乃與這些盛儲(chǔ)器置于同等重要地位。
——這幾套編鐘在出土?xí)r均未發(fā)現(xiàn)鐘架,即簨虡(sǔnjǜ)。簨虡作為編鐘的一部分,在東周時(shí)期多為常見,尤以南方地區(qū)荊楚一帶居多。李純一先生結(jié)合其所見在《中國(guó)上古出土樂器綜論》中對(duì)簨虡有具體論述[37]。以上墓葬均無簨虡出現(xiàn),唯一的南方曾國(guó)M111編鐘也未見簨虡。推測(cè)有多種原因所致,如木質(zhì)結(jié)構(gòu)年久已朽,或是雨水侵蝕等,但結(jié)合現(xiàn)有考古資料確實(shí)未見。■
注釋:
[1] 王友華.西周前期黃河流域甬鐘用制分析——兼析西周前期樂懸制度的演進(jìn)軌跡[J].中國(guó)音樂學(xué),2009,(04).
[2] 張之恒.中國(guó)考古通論[M].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9,10:299.
[3] 寶雞市博物館.寶雞竹園溝西周墓地發(fā)掘簡(jiǎn)報(bào)[J].文物,1983,(02).
[4] 盧連成,胡智生.寶雞 國(guó)墓地[M].文物出版社,1988,10.
[5] 寶雞茹家莊西周墓發(fā)掘隊(duì).陜西省寶雞市茹家莊西周墓發(fā)掘簡(jiǎn)報(bào)[J].文物,1976,(04).
[6] 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huì).長(zhǎng)安普渡村西周墓的發(fā)掘[J].考古學(xué)報(bào),1957,(01).
[7] 同上。
[8] 孫清遠(yuǎn),廖佳行.河南平頂山發(fā)現(xiàn)西周甬鐘[J].考古,1988,(05).
[9] 李純一.中國(guó)上古出土樂器綜論[M].文物出版社,1996,8:184.
[10] 北京大學(xué)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二次發(fā)掘[J].文物,1994.
[11] 方建軍.西周早期云紋編鐘的再認(rèn)識(shí)[J].交響,2007,(02).
[12] 也可稱之為橫北墓地、橫北村墓地。
[1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發(fā)掘簡(jiǎn)報(bào)[J].文物,2006,(08).
[14] 謝堯亭.倗、霸及其聯(lián)姻的國(guó)族初探[A].中央研究院歷史語(yǔ)言研究所會(huì)議論文集之十三——金玉交輝——商周考古、藝術(shù)與文化論文集,2013,11.
[15] 吉琨璋等.山西橫水西周墓地研究三題[J].文物,2006,(08).
[16] 同31。
[1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發(fā)掘簡(jiǎn)報(bào)[J].文物,2006,(08).
[18] 同上。
[19] 圖片采自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發(fā)掘簡(jiǎn)報(bào)[J].文物,2006,(08).
[2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地[J].考古,2006,(07).
[21] M2所有照片由侯馬工作站拍攝,版權(quán)為筆者所有,未經(jīng)授權(quán)不得使用。
[22] 同37。
[23] 同37。
[24] 一般情況下,在西周時(shí)期隨葬品中既有青銅器,又有原始瓷器的墓葬,則說明墓主人身份、地位高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謝堯亭所長(zhǎng)認(rèn)為,在北方地區(qū)和中原地區(qū),出土于原始瓷器的西周墓葬,一定是高級(jí)貴族墓。有原始瓷器的墓葬必有青銅器出土,但有青銅器的墓葬不一定含有原始瓷器。
[25] 方建軍.論葉家山曾國(guó)編鐘及有關(guān)問題[J].黃鐘,2014,(01).
[2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河口墓地聯(lián)合考古隊(duì).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J].考古,2011,(07).
[27] 劉樹滿.霸國(guó)、倗國(guó)青銅器整理研究[D].陜西師范大學(xué).
[2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呦呦鹿鳴——燕國(guó)公主眼里的霸國(guó)[M].科學(xué)出版社,2014:160.
[29] 毛悅,謝堯亭.大河口西周墓地M1青銅樂器及其意義[J].大眾考古,2018,(01).
[3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河口墓地聯(lián)合考古隊(duì).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J].考古,2001,(07).
[3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發(fā)掘簡(jiǎn)報(bào)[J].文物,2011,(11).
[3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第二次考古發(fā)掘的主要收獲[J].江漢考古,2013,(09).
[33] 黃鳳春,胡剛.說西周金文中的“南宮”——兼論隨州葉家山西周曾國(guó)墓地的族屬[J].江漢考古,2014,(02).
[34] 同上。
[35] 同上。
[36] 關(guān)于音樂文化區(qū)的分期問題可參見方建軍《商周樂器文化結(jié)構(gòu)與社會(huì)功能研究》一書,第63—67頁(yè)。
[37] 李純一.中國(guó)上古出土樂器綜論[M].文物出版社,1996,8: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