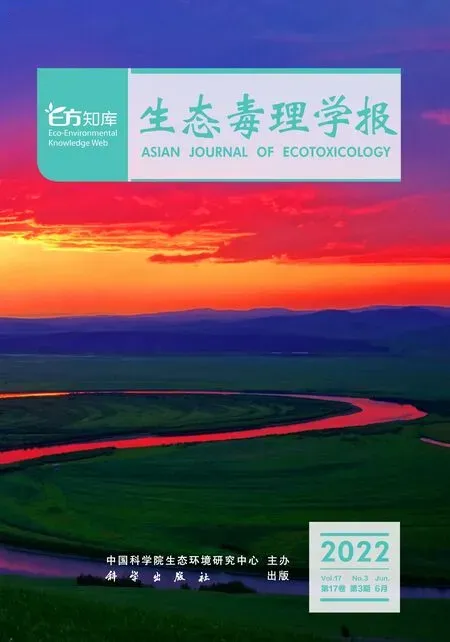殺生劑對細菌耐藥性影響機制的研究進展
陳慧敏,何良英,高方舟,白紅,何璐茜,張敏,*,應光國,劉芳
1.華南師范大學環境研究院,廣東省化學品污染與環境安全重點實驗室&環境理論化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廣州 510006
2.華南師范大學環境學院,廣州 510006
3.華南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廣州 510631
殺生劑在廣義上指能有效控制或殺死細菌、真菌、病毒及藻類等微生物的一類具有廣譜性質的化學制劑[1]。按化學功能基團劃分[2],殺生劑可分為以下7類:(1)無機化合物,如銀、汞和銅等重金屬;(2)烴類、鹵代烴和硝基化合物,如低毒的聯苯用于水果的包裝和儲存;(3)醇類、酚類及其衍生物,如六氯苯用于化妝品;(4)醛類、酮類、有機酸及其衍生物,如甲醛用于倉庫等的消毒;(5)胺類、胺鹽和季銨鹽類化合物,如苯扎氯銨等;(6)有機元素化合物,如有機汞、有機錫和有機砷等化合物;(7)雜環化合物,如添加于潤滑劑的呋喃西林等。按用途劃分,可分為抗菌劑、消毒劑和防腐劑[3]。其中,抗菌劑和消毒劑具有幾乎相同的作用,即殺死或控制微生物的生命周期[4]。抗菌劑通常存在于化妝品、洗手液、洗發水、面霜、牙膏、漱口水及消毒濕巾等個人護理品中[3]。消毒劑廣泛用于環境或物體表面清潔,如飲用水和游泳池水的氯化,醫療設備和空氣加濕器及空調設備的有效消毒等[3]。此外,消毒劑還可抑制孢子生長繁殖[1]。防腐劑則用于制藥和食品中,以防止微生物在這些產品中繁殖,也用于保存木材、皮革、塑料、涂層膜和紡織品。殺生劑類化合物固有的殺菌、消毒和防腐等屬性使其對環境中土著微生物群落具有潛在風險[3-5]。
抗生素耐藥性是全球關注的焦點[6-7]。這是一種微生物對用于治療或預防的抗生素藥物產生耐藥性的現象,該現象妨礙臨床疾病的治療,導致廣泛的公共衛生和經濟挑戰[8]。世界衛生組織將“抗生素耐藥性”列為“2019年全球健康十大威脅”之一,2020年又提出將“對抗耐藥性”列入“2021年需要追蹤的10個全球健康問題之一”[9]。抗生素耐藥快速傳播的主要原因是人類醫療健康和畜牧業中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和濫用。然而,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除抗生素作為細菌耐藥性的直接選擇壓力外,殺生劑、重金屬等非抗生素物質對細菌耐藥性的發展也發揮著共選擇作用[10-12]。
近十幾年來,殺生劑作為一類新型有機污染物得到人們廣泛關注[13-15]。我國是人口和消費大國,殺生劑的使用量不可小覷,加之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暴發,殺生劑的消費量更急劇上升[16]。雖然殺生劑的使用確實極大地降低了人類與許多傳染病相關的發病率和死亡率,然而使用后的殺生劑會殘留于空氣、土壤和水環境等受納環境中,其土著微生物群落受殺生劑脅迫,通過交叉選擇和共同選擇來發展抗性特征,從而引起環境中耐藥性的發展和傳播,危害生態系統的穩態[17]。盡管已有研究報道了殺生劑的作用機理,但關于殺生劑對細菌的耐受機制及對抗生素耐藥性傳播的影響機制仍然不夠明了,本文結合殺生劑作用機制及其環境歸趨,對殺生劑的抗生素耐藥性影響機制研究展開進一步概述。
1 殺生劑的作用機制及其環境歸趨(Mechanisms of biocide action and its environmental fate)
1.1 殺生劑使用現狀及環境檢出率
各類殺生劑充斥于人類的生活中,它們不僅限于醫學領域,也作為日常消費品廣泛使用,消費者幾乎每天都接觸含有殺生劑成分的產品[17-18]。在新冠疫情持續暴發的背景下,2020年全球表面消毒劑的銷售額總計45億美元,比2019年增長超過30%[19]。據估算,我國三氯生(triclosan,TCS)和氯咪巴唑(climbazole,CBZ)的年使用量分別高達100 t和345 t[20-21]。Data Bridge Market Research公司在一份全面的殺生劑行業市場研究報告中指出,2020—2027年間殺生劑市場預計將以5.0%年增長率增長,預計2027年將達到97.9億美元[22]。
近年來,殺生劑的環境歸趨得到廣泛關注。殺生劑在水、土壤及空氣等受納環境中大量檢出,甚至有研究在人體乳腺組織中檢出尼泊金酯類防腐劑[23]。表1匯總了近年來不同國家從不同受納環境中檢出的典型殺生劑的濃度分布。已有大量調查研究發現殺生劑普遍存在于污泥農用土壤、地表水環境和沉積物、污水處理廠進出水口及其受納河流等受納環境中,且部分濃度可高達μg·L-1或μg·g-1級別[5,24-28]。

表1 全球各種受納環境中檢出的典型殺生劑的濃度分布Table 1 Distribution of typical biocide concentrations in various receiving environment around the world
2018年有研究者調查了華南高度城市化地區水生環境中19種目標殺生劑的檢出情況[5],河流系統中檢測到目標殺生劑中的17種,在地表水中羥苯甲酯(methylparaben,MHB)、氯咪巴唑和避蚊胺(diethyltoluamide,DEET)的平均檢出濃度相對較高,其中氯咪巴唑濃度高達276 ng·L-1。在惠州和東莞采集到的降雨徑流樣品中廣泛檢測到18種目標殺生劑,兩地檢出濃度較高的殺生劑都為避蚊胺和多菌靈(carbendazim,CAR)。對于惠州的降雨徑流,避蚊胺和多菌靈的最高濃度均>300 ng·L-1;而對于東莞的降雨徑流,二者最高濃度甚至高達1 629 ng·L-1和2 572 ng·L-1。2019年,在對泰國8個污水處理廠和受納水環境(淡水和河口系統)中19種殺生劑的發生和歸宿的研究結果表明,在污水和地表水中檢測到羥苯甲酯的最大濃度為15.2 μg·L-1,污泥和底泥中三氯卡班(triclocarban,TCC)的最大濃度為8.47 μg·g-1,且在魚樣品中檢測到三氯生的最大濃度為1.2 μg·g-1[29]。2017年,?stman等[30]在11個瑞典污水處理廠的進水口、出水口及消化污泥中檢測到此前尚未報道過或報告數據非常有限的季銨化合物(quaternary ammonium compounds,QACs),例如氯己定(chlorhexidine,CHX)、氯化芐氧乙銨(benzoxyethylamine chloride,BEC)、氯化十六烷基吡啶(cetylpyridine chloride,CPC)和地喹氯銨(dequalinium chloride,DQC)。季銨化合物是顆粒相中含量最高的物質,其中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銨(cetyl trimethyl ammonium bromide,CTAB)含量高達370 μg·g-1,而苯并三唑(benzotriazole,BTA)是水相中高檢出率物質,含量高達24 μg·L-1。
1.2 殺生劑對細菌的作用機制
不同于具有特異性細胞靶標的抗生素,殺生劑的活性范圍很廣,在細菌細胞上通常具有多個非特異性靶位點[38-40]。許多學者對殺生劑的作用方式進行了廣泛的綜述和總結[41-42]。殺生劑的作用機制可根據其作用于微生物細胞的不同關鍵組成部分來確定,主要分為3個層次的作用機制:與細胞外部組分的相互作用、與細胞質膜的相互作用和與細胞質組分的相互作用(表2)[1]。某些殺生劑兼具2個或2個以上的作用機制。

表2 常見殺生劑細胞作用位點Table 2 Targeted site of typical biocides in cell
1.2.1 與細胞外部組分相互作用
不同于革蘭氏陽性菌細胞,革蘭氏陰性菌因具有磷脂雙分子層構成的內膜和細胞外部不對稱的外膜組成的多層包膜結構,形成低滲透性保護[43]。一些陽離子表面活性殺生劑專門作用于這道滲透屏障。它們與細菌細胞的細胞外部組分相互作用,導致細胞疏水性的變化,但自身活力可能不受影響[1]。常用的苯扎氯銨(benzalkonium chloride,BAC)和CHX通過與革蘭氏陰性菌細胞壁和外膜的負電荷相互作用,破壞并穿透其細胞壁和外膜,達到細胞質膜和細胞質內的靶位點,導致細胞失去滲透調節能力[44-46]。還有些殺生劑能誘導細菌的裂解或溶解。如次氯酸鹽,除與細胞壁相互作用外,還可誘導革蘭氏陰性菌裂解[1,42]。低濃度的苯酚、福爾馬林和氯化汞也能導致正在生長的大腸桿菌(Escherichiacoli)、鏈球菌(Streptococcus)和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被迅速溶解[1,42,47]。高濃度的陰離子表面活性劑,如十二烷基硫酸鈉(sodium lauryl sulfates,SLS)和十二烷基醚硫酸鈉(sodium lauryl ether sulfate,SLES),也能裂解革蘭氏陰性菌[1,42,48]。
1.2.2 與細胞質膜相互作用
細胞質膜常被認為是殺生劑的主要攻擊靶點[45,49-51]。由于不同殺生劑的化學結構不同,其對細胞質膜產生的作用效果也各不相同。“膜活性劑”一詞多用于抗菌藥物,泛指在細菌細胞的細胞質膜水平上具有活性的化合物,如季銨化合物、雙胍類、多尼泊金酯類、酚類和醇類等[1]。對膜的損傷大致分為以下3種形式:物理破壞、質子動力(PMF)的耗散和相關酶活性的抑制。
1.2.2.1 細胞質膜的裂解
細胞質膜的裂解通常表現為細胞內成分的滲漏,先是鉀離子,后是無機磷酸鹽、在260 nm處有吸收的氨基酸和物質、核酸及蛋白質[52]。這一類作用機制的殺生劑主要包括:季銨化合物、雙胍類、強氧化劑和醇類等。
季銨化合物不僅作用于細胞外部成分,還會導致膜損傷,進而引起細胞內成分滲漏。陽離子表面活性劑CTAB在殺菌濃度下作用于細胞膜的脂質成分進而裂解細胞[42]。陰離子活性劑,例如低濃度SLS可誘導大腸桿菌原生質球的裂解[42,53];十二烷基胍醋酸鹽也被證明在低濃度下能迅速滲透丁香假單胞菌(Pseudomonassyringae)的外膜和胞質膜,并與細胞磷脂和蛋白質結合,引起細胞內容物的滲漏,最終導致細胞裂解甚至細胞死亡[54]。
雙胍類殺生劑中最常見的包括CHX和聚六亞甲基雙胍(polyhexamethylene biguanide,PHMB)。CHX在低濃度時導致細胞內容物的高泄漏率[52]。CHX與細胞膜上相鄰的2個酸性磷脂基團相結合,導致膜的滲透性降低,并引起膜及其相關酶的滲透調節和代謝能力以及轉運系統功能的伴隨改變[45,52]。PHMB在低濃度下具抑菌作用,而在高濃度時具殺菌作用[55]。其生物殺滅機制為作用于膜磷脂[42],隨后非特異性破壞細胞膜內成分[55-56]。
強氧化劑中過氧化氫也能誘導膜損傷,其產生的自由基可作用于細胞內外的一系列靶點[3]。其靶細胞膜磷脂內的多不飽和酸被羥基自由基氧化,導致細胞裂解,隨后釋放的細胞成分被氧化[57]。醇類中的乙醇和異丙醇[58]、苯乙醇和苯氧乙醇[42]都是膜裂解劑,誘導細胞質膜功能的喪失。其他化合物如有機酸及其酯也可能導致細胞內成分的滲漏[1]。肉桂醛被證實顯著增加大腸桿菌和金黃色葡萄球菌(S.aureus)的細胞膜通透性,導致細胞質膜與細胞壁分離、細胞壁和細胞膜裂解及細胞質內容物泄漏[59]。還有研究指出酚類殺生劑氯二甲苯酚(p-chloro-xylenol,PCMX)可能干擾細胞膜并導致細胞內容物滲漏[60]。
1.2.2.2 質子動力的耗散
質子動力指細菌建立并維持的一種跨越細胞質膜的質子電化學梯度[61]。質子動力參與細菌的ATP合成、氧化磷酸化、主動運輸、細胞分裂及鞭毛運動等關鍵過程[62-63]。質子動力的崩潰直接造成這些功能途徑被抑制,從而導致細菌活力的喪失。例如五氯苯酚(pentachlorophenol,PCP)通過強化細胞膜對質子的滲透性來解偶聯氧化磷酸化,從而導致跨膜質子梯度的電勢耗散[64]。有研究證實氯己定能抑制糞腸球菌(Enterococcusfaecalis)與膜的結合并抑制可溶性ATP酶的活性[65-66]。二硝基苯酚已被證明在弱酸性環境下作為解偶聯劑破壞線粒體中的電化學質子梯度,導致ATP合成的驅動力喪失[67]。低濃度苯氧乙醇誘導大腸桿菌的質子易位且抑制氧化磷酸化途徑[68]。苯并異噻唑酮(benzoisothiazolone,BIT)通過破壞質子動力影響金黃色葡萄球菌中葡萄糖的主動轉運和氧化、含硫醇酶、ATP酶及3-磷酸甘油醛脫氫酶的活性[65]。
1.2.2.3 與其他酶系統的相互作用
殺生劑還可與嵌于細胞質膜的蛋白質酶類相互作用而達到抑菌或殺菌效果。例如,三唑類藥物氟康唑(fluconazole,FLC)通過作用于麥角甾醇途徑的羊毛甾醇去甲基化酶,進而抑制真菌質膜上麥角甾醇的生物合成[69]。低濃度六氯苯酚抑制電子傳遞鏈參與酶類的膜結合部分[1]。乙醇對大腸桿菌參與糖酵解、脂肪酸和磷脂合成及溶質攝取過程中的酶有抑制作用[42]。苯氧乙醇有抑制細菌TCA循環酶的作用[70]。此外,一些殺生劑能與蛋白酶類活性的關鍵基團——硫醇基團反應或使其氧化而影響其活性,導致細胞被抑制或失活。如氯和釋氧劑,其殺菌效果可能由一系列膜結合酶和胞內酶的硫醇(或其他基團)的氧化作用引起[71];又如廣泛用作防腐劑的苯并異噻唑酮和異噻唑啉酮(methylisothiazolinone,MIT)[42],MIT作為親電子試劑特異性作用于呼吸酶,抑制細菌新陳代謝并導致其死亡[72-73]。
1.2.3 與細胞質組分相互作用
細胞質中含有各種具有不同功能的酶、核酸、核糖體、蛋白質和脂質等組分,它們雖不是殺生劑的主要靶點,但仍可造成可逆或不可逆的細胞損傷。
1.2.3.1 與核酸的相互作用
作為抗菌染料的結晶紫和吖啶均被證明能與核酸相互作用。吖啶除與質子競爭細胞表面的陰離子位點外還能與胞內DNA分子結合[1,74];結晶紫能與大腸桿菌中的核酸分子發生絡合反應[75]。有研究證實8×10-4mol·L-1的抗瘧藥奎納克林,通過阻斷DNA合成并強烈抑制RNA和蛋白質的合成實現對大腸桿菌的殺菌作用[76]。鄰苯二醛(o-phthalaldehyde,OPA)被指出會引起熒光假單胞菌的DNA損傷[77]。基于乙醇的殺生劑影響細胞壁形成的同時還抑制DNA和RNA的合成[78]。烷基化劑如環氧乙烷,與細菌蛋白質和核酸中的氨基、巰基和羥基相互作用[79]。苯氧乙醇通過抑制胸腺嘧啶、尿嘧啶和葡萄糖的同化作用進而抑制大腸桿菌DNA和RNA生物合成[70]。
1.2.3.2 與核糖體的相互作用
核糖體通常作為被殺生劑破壞的次要目標位點。過氧化氫形成的羥基自由基會攻擊細胞成分(包括脂類和蛋白質),作用于核糖體并抑制細菌代謝[66,79]。在使用殺生劑根除石油和天然氣作業中脫硫弧菌(Desulfovibriovulgaris)的機理研究中,BAC被指出具有特異性靶向核糖體結構[80]。還有研究指出乙醇可能通過作用于核糖體和RNA聚合酶進而使mRNA和蛋白質合成解偶聯[81]。
1.2.3.3 與其他細胞成分的相互作用
除核酸和核糖體外,殺生劑還會與細胞質其他成分發生反應。例如,TCS作用于細菌脂肪酸合成中的烯酰基-酰基載體蛋白還原酶[82-84]。CHX已被證明能引起細胞質凝固[52]。烷基化劑和氧化劑因具有高度活性而與細菌發生強烈反應。其中環氧乙烷作用于核酸的同時攻擊其他細胞成分,包括蛋白質[79];過氧化氫作用于核糖體的同時氧化脂質、蛋白質和酶中的硫醇基團[1]。OPA通過與氨基酸的親核中心反應進而促進蛋白質交聯[77]。致死劑量下的MIT會影響蛋白質上的硫醇基團[73]。醛類殺生劑甲醛和戊二醛可與蛋白質或核酸的游離氨基發生交聯,戊二醛主要作用于外膜的脂蛋白,阻止膜結合酶的釋放[85-86]。
2 殺生劑耐藥菌的形成和耐受機制(Emergence of biocide-resistant bacteria and its tolerant mechanisms)
2.1 不同環境中殺生劑耐受細菌的流行情況
細菌對殺生劑的耐受性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被提及,隨著殺生劑在各行各業的廣泛使用,細菌殺生劑耐受性現象在食品加工、醫療和養殖等多種環境中普遍發生,耐藥菌株檢出率呈現明顯增加(表3)。

表3 全球分離得到的殺生劑耐藥菌株Table 3 Isolated biocide-resistant strain around the world

續表3分離菌株Isolates殺生劑耐藥Resistant biocides遺傳決定因素Genetic determinants分離來源Source of separation參考文獻ReferencesMRSA CC30BAC、過氧化氫、甲醛、次氯酸鈉、氫氧化鈉BAC, Hydrogen peroxide, Formaldehyde, Sodium hypochlorite, Sodium hydroxideqacG、qacC丹麥豬Denmark pig[97]Campylobacter jejuniTCS、CHX-美國肉雞雞舍墊料The litter of American broiler chicken houses[98]
食品中存在的抗殺生劑及抗生素的人畜共患病原體對公眾健康構成直接威脅。有研究在乳制品制造環境中分離純化出了殺生劑耐藥細菌[88]。該研究對來自山羊奶酪或牛奶生產的中小型企業的120株細菌分離株進行篩選,獲得19株殺生劑耐藥菌株,分別屬于乳球菌屬(Lactococcus)、乳桿菌屬(Enterococcus)、腸球菌屬(Lactobacillus)、芽孢桿菌屬(Bacillus)、埃希氏菌屬(Escherichia)、腸桿菌屬(Enterobacter)和螺桿菌屬(Helicobacter)。部分菌株對殺生劑和抗生素具有多重耐藥特征。除檢出sul1、acrB、blaCTX-M、blaPSE和mdfA等抗生素耐藥基因外,還檢出了qacEΔ1和qacA/B等殺生劑耐藥基因。還有一些研究報道了食源性大腸桿菌降低了對QACs的敏感性[89-92]。其中Jiang等[93]從645份零售肉類樣品中分離出179株大腸桿菌菌株,并從中檢出了sugE(c)、ydgE/ydgF、mdfA、emrE、qacEΔ1、qacE、sugE(p)、qacF和qacH等QAC抗性基因。同時有研究者從德國食品生產工廠分離到的93株李斯特菌(Listeriamonocytogenes)菌株中檢測到15株苯扎氯銨耐藥株,在其中13株菌株中發現了qacH和emrC等賦予苯扎氯銨耐受性的耐藥基因[92]。
醫院及醫療機構等衛生保健環境中,具殺生劑和抗生素耐藥性的高致病性病原體同樣令人擔憂。有研究發現源自阿爾及利亞醫院的大部分大腸桿菌分離菌株對殺生劑有耐受性,其中六氯酚和苯扎氯銨的最小抑制濃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s,MICs)均可高達128 mg·L-1。同時該研究指出反復暴露于殺生劑不僅會增加對殺生劑耐藥菌的選擇,且可能有助于抗生素耐藥機制的表達和傳播[94]。最近,Youssef等[95]調查了埃及醫院內耐多藥的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resistantStaphylococcusaureus,MRSA)臨床和環境分離株的殺生劑敏感性情況。該研究收集到114株臨床和8株環境MRSA,其中75株臨床菌株和6株環境菌株對戊二醛、氯甲酚、氯己定、溴棕三甲銨和聚維酮碘等殺生劑的敏感性降低。
養殖相關環境是殺生劑使用頻率較高的場所之一,包括畜牧業(家禽養殖場、養豬場和養牛場)和漁業(水產養殖場)等都會利用殺生劑進行消殺,因此相關殺生劑耐藥菌株的分離情況也層出不窮。在德國3個肉雞育肥場收集到93株大腸桿菌菌株,其中有9株分離株顯示出對至少一種殺生劑(甲醛、氯甲酚、過氧乙酸和苯扎氯銨)的敏感性降低[91]。從美國水牛養殖場的水牛牛皮和糞便樣本中分離得到145株腸道沙氏門菌(Salmonellaenterica)菌株,研究結果顯示所有菌株均對三氯生敏感且均對氯己定產生耐藥,近1/3的菌株對苯扎氯銨具有低水平抗性[96]。有研究從使用豬場殺生劑(苯扎氯銨、過氧化氫、甲醛、次氯酸鈉和氫氧化鈉)的丹麥豬中分離出MRSA CC30,并首次從中檢測到qacG和qacC耐藥基因[97]。從美國肉雞雞舍墊料分離到96株空腸彎曲桿菌菌株,其中99%的菌株對三氯生具有抗性,32%的菌株對氯己定具有抗性[98]。
2.2 細菌對殺生劑的耐受機制
殺生劑對細菌細胞造成的選擇壓力誘導其引起應激反應,導致細菌表達相應的抵抗機制來防止殺生劑的有害影響[104]。細菌對殺生劑的耐藥機制分為先天固有,即由染色體控制的內在自然特性;后天獲得,即由于遺傳物質突變或通過水平基因轉移(以轉座子或質粒等可移動遺傳元件的形式)獲得耐藥基因[1,85,105]。細菌對殺生劑的耐受機制如下。
2.2.1 細胞膜滲透性降低
細菌細胞中滲透屏障的存在會限制殺生劑的滲透,降低殺生劑的吸收濃度或使其無法進入靶細胞,最終導致失效[85]。相較于革蘭氏陽性菌,革蘭氏陰性菌對殺生劑具有更高的耐受性。因為革蘭氏陰性菌具富含脂多糖(磷脂雙分子層對殺生劑不滲透為主要原因)的不對稱外膜,加之外膜蛋白的存在,使得細胞滲透性降低,阻礙殺生劑的吸收和擴散,所以導致革蘭氏陰性菌對殺生劑不敏感[106]。同時,細菌細胞膜表面較小孔徑的孔蛋白基因ompC表達上調,能降低細菌細胞膜對殺生劑的透過性[107]。其中銅綠假單胞菌(P.aeruginosa)、洋蔥假單胞菌(P.cepacia)、變形桿菌(Proteussp.)和斯氏普羅威登斯菌(Providenciastuartii)等革蘭氏陰性菌對某些殺生劑具有較強抗性[108]。
2.2.2 生物膜形成
生物膜指細胞通過胞外聚合物附著在基質表面所形成的微生物群落,這是一種細菌應對外界刺激的機制,能阻遏殺生劑的滲透[81]。生物膜的形成賦予細菌對殺生劑的耐受性,其降低藥物敏感性的機理一直是實驗研究的主題[81,109]。這些機制除減少殺生劑進入細菌細胞外,還包括生物膜和殺生劑之間的化學相互作用、微環境的調節(產生營養和氧氣受限且饑餓的細胞)、生物膜內殺生劑降解酶的產生及群體感應等[110]。現已累積了大量生物膜形成對殺生劑耐藥性的影響研究。例如,有研究首次報道了亞致死濃度苯扎氯銨脅迫下的腸道沙門氏菌的生物膜細胞群體能對其產生適應性反應[111]。Henly等[112]對長期暴露于殺生劑的8株菌株的生物膜形成情況進行比較,發現殺生劑暴露在很大程度上導致生物膜形成的增加,特別是暴露于苯扎氯銨和三氯生后均有7株分離株的生物膜形成增加。Buzón-Durán等[113]研究了亞最低抑菌濃度下(sub-MICs)苯扎氯銨、磷酸三鈉和次氯酸鈉對MRSA形成的生物膜結構和活力影響,發現次氯酸鈉實驗組的菌株生物膜形成能力增長。還有研究報道當銅綠假單胞菌和表皮葡萄球菌(S.epidermidis)以生物膜的形式存在時,對妥布霉素和苯扎氯銨的耐受性增加了100倍[73,105,114]。
2.2.3 外排泵
外排泵是最常見的耐藥機制之一,它廣泛存在于細菌中,是一種依賴能量驅動主動向外泵出殺生劑等化合物且不發生目標物改變或降解的藥物外排系統[106]。外排泵通過降低細菌胞內殺生劑有效濃度而實現耐受。與細菌多重耐藥有關的外排泵主要有以下5類:主要易化家族(major facilitator superfamily,MFS)、小多藥耐藥家族(small multi-drug resistance,SMR)、多藥與毒物外排家族(multidrug and toxic efflux,MATE)、耐藥結節分化家族(resistance-nodulation-division,RND)和ATP結合盒家族(ATP binding cassette,ABC)[115-116]。外排作為降低殺生劑敏感性的機制已得到充分證實。多項研究為質粒介導的苯扎氯銨耐藥性提供證據。有研究報道來自肉類加工設施中分離得到的李斯特菌分離株存在編碼MdrL和Lde外排泵的染色體定位基因,且證實了分離株對苯扎氯銨的耐受性與質粒攜帶的bcrABC盒有關[117]。有學者觀察到金黃色葡萄球菌臨床分離株對苯扎氯銨和氯己定敏感性的降低與季銨化合物誘導編碼的外排泵QacA、QacB、QacC和QacG有關[118-119]。Maseda等[120-121]將粘質沙雷氏菌(Serratiamarcescens)反復暴露于濃度遞增的氯化十六烷基吡啶,發現細菌通過表達SdeAB外排泵獲得對殺生劑和抗生素的耐藥性,并證實了耐藥菌株中SdeAB外排泵的增強表達是受sdeS基因突變的影響。
2.2.4 殺生劑失活
殺生劑失活或降解是微生物對殺生劑的另一個固有抗性,即通過酶降解、活性基團替換或化學轉化直接使化合物失活[105,122]。目前已有相關報道描述了細菌中將殺生劑酶促轉化或滅活成無毒形式的現象[123]。Kümmerle等[124]對大腸桿菌耐甲醛菌株VU3695的甲醛耐藥機制的研究發現,其抗性機制是基于甲醛脫氫酶對甲醛的酶降解。有研究發現源自土壤的惡臭假單胞菌(P.putida)TriRY菌株和木糖氧化產堿反硝化菌(Alcaligenesxylosoxidanssubsp.denitrificans)TR1菌株的高水平三氯生抗性,有賴于細菌對三氯生的降解[125-126]。Hay等[127]分離自污水處理廠活性污泥的營養缺陷型鞘氨醇單胞菌株(Sphingomonas),在復雜培養基上生長時能夠部分礦化三氯生,將約35%的[14C]三氯生轉化為[14C]CO2。Nishihara等[128]發現一株能降解雙十烷基二甲基氯化銨(didecyldimethylammonium chloride,DDAC)的熒光假單胞菌(P.fluorescens)TN4,該菌株能通過N-脫烷基化過程將季銨化合物降解,產生對季銨化合物的高度耐受性。
2.2.5 靶位修飾
此外,細菌可通過在結合位點處或附近產生突變或酶促修飾對靶位進行改變,使殺生劑無法與細菌結合,從而減少殺害作用[129]。抗生素由于作用靶點的特異性,靶位變更介導的耐藥性被廣泛研究。而殺生劑耐藥性和抗生素耐藥性的靶位改變機制不同,通常細菌不太可能通過靶位改變對殺生劑產生耐受性,因為殺生劑往往具有多個作用位點[129]。目前關于導致殺生劑耐藥的靶位改變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氯生耐藥性。已有大量研究證實大腸桿菌對三氯生的耐藥性是通過細菌脂肪酸合成中的烯酰基-酰基載體蛋白還原酶編碼基因fabI基因的錯義突變獲得[82-84]。
3 殺生劑對細菌抗生素耐藥性的影響(Influence of biocide on the bacterial antibiotic-resistance)
隨著對細菌抗生素耐藥性控制問題的全球共識的達成和疫情背景下殺生劑消耗量的增加,越來越多的研究證實環境中常檢出的殺生劑是細菌耐藥性發展和擴散的驅動因素。環境中多種低濃度水平殺生劑的積累可對細菌造成長期脅迫,通過細菌抗生素耐藥性共同選擇作用,導致細菌耐藥性的演變和傳播[130-131]。殺生劑對細菌抗生素耐藥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促進抗生素耐藥基因(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ARGs)的水平轉移和共選擇機制。
3.1 水平基因轉移
抗生素耐藥細菌攜帶的ARGs可以在細菌種內和種間進行水平基因轉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HGT),加劇了抗生素耐藥在全球的出現和傳播[132]。因此HGT被認為是抗生素耐藥性傳播和擴散的重要途徑。HGT通常由轉化、轉導和接合3種機制介導[133]。細菌通過HGT獲得具有殺生劑耐藥基因的可移動遺傳元件(mobile genetic elements,MGEs)來獲得抗性。其中,插入序列、轉座子、整合子和基因盒可以在細菌內的DNA分子間移動,共軛轉座子和質粒可以在細菌之間移動,它們都是傳播抗生素耐藥性遺傳決定因子的重要載體。抗生素是傳播抗生素耐藥性的關鍵驅動力,但非抗生素物質對ARGs轉化的貢獻通常被忽視。最近,有研究首次提供證據[134],證明非甾體抗炎藥、布洛芬和降脂藥等6種常見的非抗生素藥物顯著促進了外源性ARGs的細菌轉化,且可能是通過促進細菌活性、增強應激水平、過度產生活性氧和增加細胞膜通透性來助力非抗生素藥物的ARGs轉化。該研究強調了非抗生素藥物通過促進轉化途徑促進ARGs水平基因轉移的重要性,這無疑引發對殺生劑對細菌抗生素耐藥性傳播的思考。
現已有研究報道了亞抑制濃度殺生劑通過提高接合轉移頻率,進而促進抗生素耐藥性的傳播。例如Jutkina等[135]首次證明TCS和CHX能在亞抑制濃度下顯著誘導耐藥性的接合轉移頻率。Han等[132]選擇了5種QACs揭示影響抗生素耐藥性傳播的機制,結果顯示QACs耐藥基因在浙江省三大流域中普遍存在,并且與整合子基因intI1及7個ARGs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QACs通過增強細菌細胞的膜通透性并刺激細菌產生活性氧,進而可能促進細菌之間質粒RP4的接合轉移。有研究證實了常用殺生劑乙醇對枯草芽孢桿菌(B.subtilis)菌株之間接合轉座子Tn 916的影響,結果顯示亞抑制濃度乙醇將Tn 916的轉移頻率顯著增加5倍,表明暴露于亞抑制濃度的乙醇可能會誘導Tn 916及其抗性基因的轉移[136]。Jin等[137]發現了飲用水中的氯消毒對抗生素耐藥性傳播構成威脅,研究表明,氯化作用使處于生理感受態細胞的耐氯損傷細菌的質粒轉化頻率比未處理的細菌高550倍,且極易從周圍環境中吸收游離的ARGs,從而促進ARGs的水平轉移。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收集的關于由于殺生劑持續暴露而導致抗生素耐藥基因水平轉移的信息仍不夠充分。
另外,有研究指出細菌SOS反應會促進HGT的發生[138]。細菌SOS反應是對環境不斷變化的響應系統之一,該系統通過誘導一系列參與DNA修復和重組的基因表達來應對DNA損傷,直接干擾DNA復制、抑制細胞壁合成或產生活性氧都是SOS反應的潛在激活因素。抗生素能有效激活細菌的SOS反應已在一些研究中得到證實[139-141]。同時,人類會向環境中釋放大量包括殺生劑在內的非抗生素污染物,造成的環境狀態波動會誘發細菌SOS反應。確有研究指出殺生劑造成的選擇壓力會觸發細菌SOS反應[17,142]。
3.2 共選擇機制
殺生劑與抗生素不同,前者通常以殺滅濃度被有意地置于各種外界環境中。盡管對殺菌劑本身的耐藥性發展存在一些擔憂,但關于耐藥性最大的擔憂是它們主要通過共同和交叉選擇機制共同選擇抗生素耐藥性的潛力。與抗生素相比,對選擇和共同選擇所需的殺生物劑濃度的研究較少。
接觸殺生劑也可能增加抗生素耐藥性并導致多重耐藥的事實已經被人們慢慢認可。大量文獻描述了殺生劑的使用與細菌抗生素耐藥性增長之間的聯系[1,85,143]。AKimitsu等[144]發現,QACs暴露會增加MRSA菌株對苯唑西林和β-內酰胺的耐藥性。Langsrud等[145]將大腸桿菌暴露于亞抑制濃度的BAC,觀察到細菌對BAC和氯霉素的交叉耐藥性。Mc Cay等[146]在添加BAC的情況下對銅綠假單胞菌進行富集連續培養,結果顯示該適應性細菌對BAC的耐受性提高了12倍,同時對環丙沙星的耐藥性顯著增加了265倍。Kim等[147]闡明了BAC暴露共同選擇抗生素耐藥性的潛在遺傳機制,包括BAC耐受基因和ARGs位于同一MGEs中、pmrB基因的突變以及外排泵基因的上調。Tandukar等[148]還探討了BAC暴露和微生物群落抗生素耐藥性的聯系,研究發現,暴露后的微生物群落對BAC及3種抗生素(青霉素G、四環素和環丙沙星)的敏感性顯著降低,其中BAC和青霉素耐藥性增加的耐藥機制為降解或轉化,而對四環素和環丙沙星的耐藥性增加主要歸因于外排泵的活性提高。
殺生劑對抗生素耐藥性的共同選擇的潛力已被廣泛報道,殺生劑驅動共同選擇主要通過協同抗性(cross resistance)和交叉抗性(co-resistance)2種機制實現。協同抗性指編碼殺生劑抗性和抗生素抗性的基因位于同一可移動遺傳元件上,能在新的微生物-宿主系統中轉移和表達[17,85,149]。Roedel等[91]發現從德國肉雞育肥場分離到的殺生劑耐藥株,其殺生劑耐藥基因qacEΔ1和sugE(p)同時位于含有抗生素耐藥基因sul1和blaCMY-2的移動遺傳元件上。殺生劑和抗生素的細菌耐藥機制相似,因此殺生劑暴露會引起抗生素的交叉耐藥。交叉抗性指賦予殺生劑和抗生素產生耐藥性的基因編碼于同一耐藥機制[17,85,149]。有研究首次證明臨床上分離得到的銅綠假單胞菌中三氯生和抗生素的交叉耐藥性是由三氯生暴露后過度表達MexCD-OprJ多藥外排泵介導的[82]。MexAB-OprM多藥外排泵的過度表達是導致不同生態位銅綠假單胞菌中苯扎氯銨和抗生素的交叉耐藥性的主要促成因素[101]。有研究者針對空腸彎曲桿菌(Campylobacterjejuni)和結腸彎曲桿菌(Campylobactercoli)開展進化實驗,確定了5種殺生劑(三氯生、苯扎氯銨、氯化十六烷基吡啶、醋酸氯己定和磷酸三鈉)對抗生素(紅霉素和環丙沙星)的交叉耐藥性[150]。食品工業中的空腸彎曲桿菌對殺生劑的適應通過增強生物膜的形成(生物量、表面覆蓋率、粗糙度和生物膜的表面粘附力顯著增加)來介導與抗生素之間的交叉耐藥性[151]。有研究對亞抑制濃度殺生劑(氯酚、苯扎氯銨、戊二醛和氯己定)條件下的腸道細菌大腸桿菌進行了實驗室適應性馴化,發現與多藥外排蛋白、孔蛋白和RNA聚合酶上相關基因(mdfA、acrR、envZ、ompR、rpoA和rpoBC)的突變以及分別調控的雙組分系統和生物膜形成等途徑,是與抗生素產生交叉抗性背后的機制[152]。Wand等[153]利用氯己定適應性誘導肺炎克雷伯菌(Klebsiellapneumoniae)對粘菌素的交叉抗性,發現其抗性與雙組分調節劑phoPQ以及與MFS外排泵基因smvA毗鄰的TET抑制基因smvR的突變相關。最近的一篇研究[142]對消毒劑次氯酸鈉的耐藥機制進行深入探討,結果顯示MuxABC-OpmB外排泵上muxA和muxB多藥外排基因的表達及細胞膜滲透性的降低介導了假單胞菌對殺生劑和抗生素的交叉耐藥。
由此可見,隨著殺生劑的廣泛使用而導致其在受納環境的殘留,脅迫環境微生物抗生素耐藥性的產生和傳播成為一大環境挑戰。
4 展望(Research prospect)
結合殺生劑的受納環境檢出率、環境耐藥菌株分離率及其對細菌耐藥性傳播與發展的影響,現有研究表明殺生劑廣泛存在于環境介質中并對人類健康及生態環境構成潛在威脅。目前,關于殺生劑對細菌耐藥性影響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現在:(1)評價殺生劑抗性的臨界點仍不夠清晰,缺少相應的標準評價體系;(2)關于殺生劑的耐藥機制研究仍不夠明確,尤其是殺生劑失活及靶位變更引起的殺生劑抗性;(3)關于針對具體某一殺生劑的深入研究仍較為缺乏,目前僅對三氯生的作用機制研究得較為透徹;(4)關于殺生劑驅動抗生素耐藥性傳播的機制研究仍不夠成熟,對殺生劑抗性基因水平轉移的研究較為有限,尤其對于殺生劑抗性基因是否能通過轉導或轉化機制轉移,值得進一步研究。
鑒于目前全球殺生劑使用量的日益增加、環境中殺生劑耐藥菌株的頻繁檢出以及對抗生素耐藥性傳播的促進,顯然需要加強謹慎使用現有殺生劑的意識。為了正確評估和防控殺生劑對抗生素耐藥性污染的生態風險,最大限度地減少殺生劑對細菌抗生素耐藥性的發展和傳播,需要抓緊進一步明確殺生劑耐藥性的標準評價體系,利用多學科研究手段加強對殺生劑耐藥機制的研究,進而為新藥的開發和揭示殺生劑與抗生素耐藥性的共選擇機制提供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