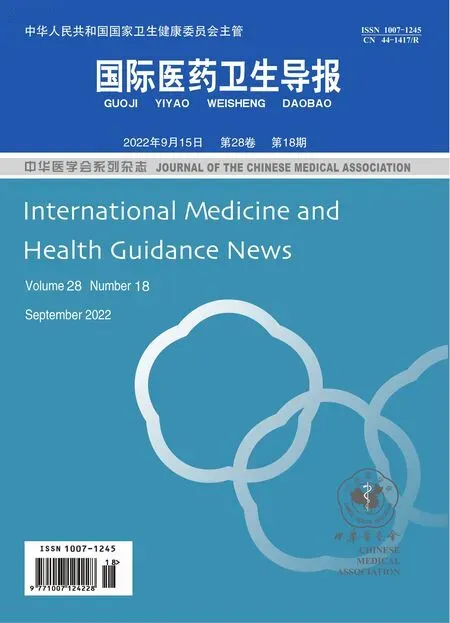腮腺分泌性癌1例
相龍全 馬廷廷 王慧 張孝常 林凡忠 張光海
1濟寧市第一人民醫院病理科,濟寧 272000;2濟寧市第一人民醫院放射科,濟寧 272000;3濟寧市第一人民醫院消化內科,濟寧 272000
類似乳腺分泌性癌(mammary analogue secretory carcinoma,MASC)現已被確認為一種獨特的原發性唾液腺腫瘤,以t(12;15)(p13;q25)易位導致ETV6-NTRK3基因融合為特征,其組織學、免疫表型和分子特征與乳腺分泌性癌(secretory breast cancer,SBC)相同[1]。自2017年該腫瘤被第4版世界衛生組織(WHO)頭頸部腫瘤分類收錄后,采用分泌性癌(secretory carcinoma,SC)命名。SBC臨床上生長緩慢,主要發生于年輕女性[2],而SC多見于中年人。Boon等[3]回顧了279例病例,男女比例約為1.5∶1。SC通常被認為是低級別腫瘤,常因腮腺緩慢生長的無痛性腫塊而就診[1,4]。自從2010年Skálová等[1]首次將SC描述為唾液腺中的一個獨特實體以來,人們對該腫瘤一直有著濃厚的興趣,包括一系列描述形態學、免疫組織化學甚至超微結構的病例報道和文獻綜述[4-5]。盡管如此,其診斷仍具有挑戰性,SC常被誤診為涎腺腺泡細胞癌(acinar cell carcinoma,AciCC)[3],需要我們通過形態學、免疫組織化學甚至分子生物學的聯合診斷。據報道,涎腺腫瘤的發病率為3例/10萬人[6],而SC占所有涎腺腫瘤的比例不足0.3%[7],由于已發表文章的數量有限,尚不能形成規范化的治療方案。因此,我們通過對1例28歲青年男性患者腮腺SC進行報道,旨在提高對該病的認識,為制定規范化治療方案提供綿薄之力。
病例資料
患者,男性,28歲,2016年5月16日因“右耳前無痛性腫物1年”入濟寧市第一人民醫院。患者1年前發現右耳前腮腺區一“紅棗”大小腫物,按壓時無疼痛,否認感冒發熱時腫脹感,否認消長史及生長加速史,表面皮膚無破潰、麻木,1年來腫物生長緩慢,無明顯變化,B超檢查,提示:右腮腺占位,淋巴結可考慮,混合瘤不能排除。為進一步確診,遂來院就診。查體:一般情況尚可,神志清,心肺聽診無異常,肝脾肋下未及,頜面部左右基本對稱,無明顯畸形,右耳前可觸及一大小3.0 cm×3.0 cm×3.0 cm腫物,局部無觸壓痛,表面皮膚色澤無異常,皮溫不高,表面光滑,質硬邊界清,活動度差。入院腮腺MR平掃:右側腮腺淺葉見一類圓形異常信號影,大小1.8 cm×1.8 cm×1.6 cm,T1加權像(T1WI)呈等級高信號、T2加權像(T2WI)呈混雜高信號影,信號不勻,局部邊界欠清晰,磁共振彌散加權成像(DWI)呈高低混雜信號改變(圖1),雙側頜頸部見多發小淋巴結影。影像學提示右腮腺占位性病變。在完善相關檢查,排除手術禁忌后,于全身麻醉下行右腮腺全葉及腫物切除術+面神經解剖術+鄰位瓣轉移修復術,術中完整切除腫物及腮腺全葉,注意保護面神經。術后將組織送檢病理科。大體:灰白灰黃色組織1塊,大小5.0 cm×3.0 cm×1.0 cm,切開,切面見一腫物,大小2.2 cm×1.8 cm×1.0 cm,切面灰紅,質軟,其余切面灰黃色,質中。鏡下觀察:組織學形態以微囊狀,乳頭狀生長為主,微囊結構中含有嗜酸性分泌物,腫瘤細胞相對均勻,呈圓形或者卵圓形,具有低級別的泡狀核、細顆粒染色質和明顯的中央核仁。細胞核被淺嗜酸性顆粒或空泡狀細胞質包圍。有絲分裂和壞死罕見(圖2)。免疫組化:腫瘤細胞波形蛋白、mammaglobin、細胞角蛋白7和S-100蛋白陽性(圖3),DOG-1和p63陰性。

圖1 腮腺分泌性癌患者腮腺MR平掃。A為T1加權像(T1WI)右側腮腺病灶內見等級高信號,B為T2加權像(T2WI)右側腮腺病灶呈混雜高信號

圖2 腮腺分泌性癌患者病理特征(HE染色)。A為40倍鏡下示癌細胞呈乳頭-囊性排列;B為400倍鏡下示癌細胞圓形/卵圓形,輕度異型性,胞質豐富,細胞核被淺嗜酸性顆粒或空泡狀細胞質包圍,“→”為微囊結構中嗜酸性分泌物

圖3 腮腺分泌性癌患者癌細胞免疫組化結果。A為胞質Vimentin陽性;B為胞質mamag lobin陽性;C為胞質CK7陽性;D為胞質、胞核S100陽性
討 論
Skálová等[1]在2010年首次記錄了SC的臨床和病理特征,認為它是一種獨特的低級別涎腺SC,與SBC相似,以染色體t(12;15)(p13;q25)平衡易位導致12號染色體上的ETV6基因和15號染色體上的NTRK3基因融合為特征。乳腺和唾液腺組織來源于同一個外胚層,且具有相同的導管腺泡結構[8]。SC占 所有 涎 腺 腫 瘤 的 比 例<0.3%[7],根 據Jung等[9]1990年 至2012年的回顧性研究,SC的平均診斷年齡為46歲,一般范圍為14~77歲,兒童和青少年病例少見。在首篇文章對其描述后,許多SC已經在腮腺、下頜下腺、鼻竇、唇和頰黏膜的小涎腺、皮膚、甲狀腺、肺[10],甚至外陰[11]中報道。其中,約70%位于腮腺,不到1/4病例來自口腔內的小唾液腺,其他部位不太常見。腮腺SC臨床上生長緩慢,最常見的癥狀是持續數月至數年緩慢生長的無痛腫塊[1-6],盡管高達25%的病例可能有局部淋巴結轉移,但很少發生遠處轉移或高級別轉化[12]。而罕見的高級別轉化具有臨床侵襲性,會增加腫瘤的播散率及患者病死率[13]。在Skálová等[1]報道的3例接受腮腺切除術的高級轉化型SC患者中,其中2例接受了術后放療,另1例因病情嚴重,無法完成放療。3例患者在確診后2~6年內均死于轉移性疾病。
SC是一個獨特的實體,大多數情況下,組織病理學結合適當的免疫組化檢查即可診斷[1]。SC呈膠狀,切面呈白色至灰色。顯微鏡下,腫瘤呈分葉狀,由纖維間隔分隔為局限性結節性腫塊,大量細胞外分泌物質染色呈周期性PAS淀粉酶陽性。腫瘤細胞排列成多種形式,包括微囊性、大囊性、乳頭狀、實體型和管狀結構[4]。本病例主要表現為微囊性和乳頭狀生長模式。腫瘤細胞相對均勻,具有低級別的泡狀核、細顆粒染色質和明顯的中央核仁,細胞核被淺嗜酸性顆粒或空泡狀細胞質包圍,有絲分裂和壞死罕見[1,14]。常可見腫瘤侵犯周圍涎腺組織,少數病例侵犯神經,不常見侵犯血管[1]。其中,以嗜酸性和空泡狀細胞質及小細胞核的中小型細胞增殖為其主要特征[12]。最近,又報道一項新的診斷特征,在SC病例中,除腫瘤的實性/囊性成分外,還可見核膜不規則[15]。免疫組織化學檢測中,SC不同程度表達S-100、mammaglobin、細胞角蛋白、上皮膜抗原、波形蛋白;不表達肌上皮或基底細胞標記物,如P63、DOG-1、Calponin、CK5/6、CK14和平滑肌肌動蛋白[16]。在這些抗原中,mammaglobin和S-100對SC的細胞學診斷靈敏度高達95%。我們通過檢測波形蛋白、mammaglobin、細胞角蛋白7和S-100蛋白陽性,DOG-1和p63陰性,以及聯合其組織學特征,將其診斷為SC。對于診斷不清,尤其是細胞形態學特征支持但缺乏確切免疫組化染色的病例,可通過應用分子檢測技術進行鑒別,包括FISH檢測ETV6基因重排,RT-PCR檢 測ETV6 NTRK3融 合 轉 錄 物[17]。WHO在2017年頭頸部腫瘤的分類認識到,將分子醫學進展納入臨床實踐將不可避免。
少數情況下,由于涎腺腫瘤的起源、組織形態學特征、免疫組化表達、甚至基因改變等方面的相似性,使得涎腺腫瘤的病理診斷具有挑戰性。回顧性研究發現,SC常被診斷為AciCC、導管內癌(intraductal carcinoma,IDC)、黏液表皮樣癌(mucoepidermoid carcinoma,MEC),以及多形性低級別腺 癌(pleomorphic low-grade adenocarcinoma,PLGA)[16,18]。(1)AciCC:SC最常被誤診為AciCC[3],AciCC主要發生在腮腺,是一種低度惡性腫瘤,5年生存率為83.3%。AciCC具有細胞學和結構多樣性的特點,由漿液性腺泡、夾層導管樣、鉤狀、空泡狀、透明和非特異性腺細胞組成,排列成固體/小葉、微囊、乳頭狀囊性和濾泡狀生長模式,與SC相似[19]。大多數SC患者以前被診斷為“酶原缺乏”的AciCC[6]。經典的AciCC表現為嗜堿性細胞質,含有酶原顆粒,比SC具有更多的細胞多樣性[4]。免疫組化顯示DOG1強陽性,而不對S100、mammaglobin染色,這與SC染色正好相反[20]。Pinto等[21]也證明DOG1陰性,S-100、mammaglobin陽性是SC的有效篩選工具。鑒別AciCC和SC的最大挑戰是酵母菌顆粒缺乏的AciCC,它有豐富的嗜酸性空泡狀細胞質而不是顆粒狀嗜堿性細胞質,也可以是S100陽性[5]。這種情況下,分子生物學發揮重要作用,AciCC缺乏ETV6基因重排的存在。根據這一認識和標準,先前診斷為AciCC的多個病例被重新歸類為SC[4]。(2)IDC,以前稱為低級別涎腺導管癌或篩狀囊腺癌,現在被認為是一種與傳統的涎腺導管癌無關的獨特實體。與SC一樣,它通常出現在腮腺,在口腔、頜下腺和小涎腺中也有報道[22]。IDC與SC在結構上有著驚人的相似性,有囊性、篩狀、乳頭狀和實性結構以及嗜酸性分泌物。在細胞學特征上,兩者均為低級立方細胞,偶有微絨毛狀嗜酸性細胞質,伴有圓形或卵圓形細胞核,核仁不明顯[5]。免 疫 組 化 中,兩 種 腫 瘤S100和mammaglobin陽性[22-23]。主要區別是大多數IDC顯示出完整的肌上皮層,與導管內生長一致[23],可通過肌上皮細胞標記物(如P63、calponin或SMA)與SC進行鑒別。(3)MEC:SC與MEC都能產生親堿性分泌物[8],有必要將兩者區別開來。一般情況下,MEC由黏液細胞、中間型細胞和表皮樣細胞組成,而SC中沒有鱗狀細胞和黏液細胞,易于鑒別。然而,囊性結構在低級別MEC病變中也很常見,導致形態學上與SC相似[5],此時需要免疫組化鑒別。MEC免疫組化中S100和mammaglobin陰性,p63陽性,SC與之相反[14]。(4)PLGA,通常發生在小涎腺部位。它同時表達S-100和mammyglobin,缺乏泡狀粉紅色的細胞質。在PLGA中,結構的廣泛變化為其特征,包括小葉、小梁、單層小管、篩孔、乳頭和實體型,細胞成條索狀或旋渦狀排列。與SC需要ETV6來確認診斷[20]。
另外,在不同的病例報道中使用了不同的成像方式,包括超聲、CT和MRI。SC在超聲上呈低回聲,在MRI的T1期呈高信號,同我們的影像學表現相一致。內出血最近被認為是一種能區分SC和AciCC的發現,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么我們的病例顯示病變T1信號增強。超聲引導下的細針穿刺抽吸活檢(fine needle aspiration biopsy,FNAB)是一種合適的檢查手段,大多數報道的病例包括FNAB[7],超聲引導下的FNAB顯示豐富、形態一致的涎腺上皮細胞,并伴有輕微的細胞異型性,以及可能存在的輕度核膜不規則和小到突出的核仁。FNAB表現為具有乳頭狀特征的上皮性低度涎腺腫瘤[4,7,12]。但并非所有的FNAB檢查結果都能提供準確的診斷[24]。由于SC與其他涎腺腫瘤相似,有時很難用FNAB鑒別。即便如此,細胞學特征仍有助于我們考慮這一實體。
SC通常進展緩慢,其治療常遵循低級別惡性涎腺腫瘤的治療方法,包括對局部侵襲性較小的疾病進行全外科切除[25]。大多數患者在手術切除后預后良好,隨訪期間無遠處轉移。而對于存在高度轉化的SC,常在頸清掃的基礎上進行根治性手術,然后進行輔助放療[24]。但是目前還沒有關于頸清掃的標準臨床指征文獻[13]。隨著分子技術的發展,基因靶向治療顯示出巨大的治療潛力。恩曲替尼是種很有前途的口服制劑,為酪氨酸激酶抑制劑,Drilon等[26]報道了1例女性SC患者,她接受了恩曲替尼治療。在最初影像資料中,可以觀察到患者腫物縮小。遺憾的是,她對該藥產生了耐藥性。盡管如此,本研究仍為后續靶向藥物干預的研究提供了依據[26]。
SC是一種低度惡性涎腺腫瘤,近幾十年來,由于SC的罕見性以及與涎腺類腫瘤組織學的相似性,尚未有明確的診斷標準。現今根據其典型的形態學、免疫組織化學,以及獨特的分子學特征,降低了其診斷難度。但由于目前的病例較少,其確切特征、治療結果及預后尚有爭議。本報道旨在提高對這一診斷的認識,為頭頸部腫瘤的進一步完善以及制定標準化的治療方案提供綿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