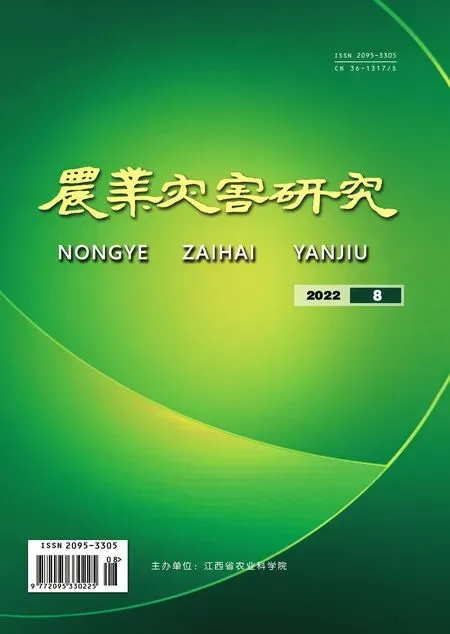普陀區域海霧特征初步分析
金正婷,樂方瓊
舟山市普陀區氣象局,浙江舟山 316100
海霧是由于受海洋和大氣相互作用的影響,發生在濱海、島嶼及海面上空低層大氣中凝結的水滴和冰晶,使大氣水平能見度小于1 km的一種天氣現象。其出現會嚴重影響沿海地區海上交通和作業安全。普陀區地處浙江北部,舟山群島東南部,位于長江口南側、杭州灣外緣的東海洋面上,以漁業、旅游業、船舶、海上交通運輸業為主線。海霧發生時,海上能見度降低會給上述行業造成嚴重影響,比如航線停運、游客滯留、海難事故等問題。
為方便研究海霧,王彬華[1]依據海霧形成的機制及所處洋面的環境特點,將海霧分為平流霧、混合霧、輻射霧、地形霧4種類型。實際海霧的生消與發展是各種影響因素相互交錯的復雜過程,且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征,其預報分析具有地域針對性。陳燕麗等[2]利用沿海觀測資料探討了北部灣海霧的年際、年代際和月分布特征,以及該地區海霧氣候變化特征的可能原因。黃彬等[3]發現,黃海海霧呈逐年遞增的年際變化,且集中發生在春夏季,一日之中主要出現在夜間至早晨。王亞男等[4]根據歷史觀測資料,分析了我國黃海和東海沿海在冷空氣影響下發生海霧的氣候規律和海霧形成的海洋、氣象條件。
擬根據歷史觀測資料分析舟山普陀沿海海霧發生的氣候特征,海霧形成的水文、氣象條件,并就該地區海霧形成的天氣類型進行分析,以期為普陀沿海海霧預報服務提供參考。
1 資料選取
采用資料主要包括1991—2020年普陀國家一般氣象站觀測資料、2014—2020年普陀區其他8個大霧預警指標站的逐小時地面觀測數據和海洋氣象浮標站數據資料。參照中國氣象局《地面氣象觀 測 規 范》(GB/T 35221—2017)[4]對 霧的定義,規定1 h平均大氣能見度低于1 km、相對濕度高于90%的判定為出現大霧,若一天之中任一個觀測時次任一觀測站出現大霧,則這一天為該觀測站的1個大霧日。日統計是按照氣象學上以北京時間20:00為日界的標準進行統計的。
2 普陀海霧的氣候特征
1991—2020年,普陀霧日共計1 378 d,年平均霧日為45.9 d,為現常年霧日,較1981—2010年常年霧日多8.7 d。從圖1可以看出,1991—2020年間的霧日整體分為1991—2013年和2014—2020年2個階段,前者平均霧日34.7 d,后者平均霧日82.9 d,是前者的2.4倍。其中,1991—2013年的年霧日相差相對較小,年最少霧日20 d(2009年)與年最多霧日51 d(1991年、1993年)相差31 d。從2014年開始,年霧日急劇上升,2014年霧日為88 d,為2009年霧日的4.4倍,為1991年和1993年霧日的1.7倍。2014年之后,年霧日基本處于高值,其中2015年和2016年霧日分別高達104 d和108 d,僅2017年霧日有所下降,但也高于1991年和1993年。此次劇增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觀測方式的轉變,2014年起,普陀站開始采用能見度儀自動觀測能見度,相對人工目測,更加敏感、客觀、準確。
從1991—2020年月平均霧日數(圖2)可看出,普陀一年四季均可以形成霧,但月際變化顯著。11月—翌年5月,霧日呈階梯狀遞增,最多5月為8.8 d。從全年來看,普陀海霧多發生在3—6月,其中4月、5月、6月為普陀海霧最頻發月份,占全年霧日的55%。7月開始隨著氣溫逐漸升高,海霧出現日數開始減少,降低至3.9 d。8—10月霧日數最少,均少于1 d。11月開始,霧日又緩慢增多。這主要是區域性海陸熱力性質差異和大尺度環流調整共同作用的結果。

圖2 普陀常年(1991—2020年)的平均月霧日
受海陸分布、局地環流以及太陽輻射的日變化影響,海霧在沿岸和島嶼附近海區呈現明顯的日變化特征。采用2014—2020年普陀各海島能見度站點逐小時能見度觀測資料分析可知,普陀區域的海霧多出現在夜間至早晨,17:00以后霧的出現頻率逐漸提高,主要集中在夜晚至下半夜,到次日06:00頻率達到頂峰,07:00頻率急劇下降,說明此時多為霧開始消散的時間,12:00~15:00霧的頻率最低。霧季最盛的4—6月,有時平流霧往往持續幾十小時,甚至更長時間而不消散。

圖3 普陀2014—2020年逐時次霧頻率分布
3 普陀海霧的天氣類型
海霧的生成和維持與海洋和大氣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通過分析2011—2020年普陀海霧數據總結得出利于普陀區域產生海霧的主要天氣形勢,大致分為以下4類。
3.1 低壓倒槽型
冬春季節,尤其是3月,在我國東北一帶有一暖性高壓脊,華南一帶副熱帶高壓穩定盤踞,脊線呈東西向,西南地區南支槽活躍,海霧發生前,高空西南氣流顯著,為海霧的生成提供了必要的暖濕條件。地面西南地區出現西南低壓,其低槽向東或東偏北方向伸展至江蘇一帶地區,有的倒槽發展,在本地或東海形成一個閉合的氣旋,浙江沿海處在低壓槽附近(靜止峰前沿或暖鋒前后)。受其影響,普陀海域處于一致的偏南氣流中,沿岸吹東南或南風,當風力不大時,容易生成海霧,生成時間可以在一天中的任何時間段(白天比例較高),維持時間一般在1~2 d之間。一旦高空東亞大槽東移,普陀轉受槽后西北氣流控制,暖濕氣流輸送通道被切斷,加之地面風力增大,海霧消散。
3.2 兩高間均壓場型
一般在春季和冬季蒙古河套地區的冷高壓一直向南,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呈帶狀或塊狀穩定在臺灣以東的洋面上,朝鮮半島附近低壓,鋒面往西南方向一直延伸至華南地區,導致浙閩沿海至華南沿海都是相對低壓區。同時,孟加拉灣有南支槽活動,西南暖濕氣流導致普陀海域低層相對濕度增大,天氣常常為陰雨相間,且風力很小,風向較亂,大氣相對濕度趨于飽和,從而生成海霧。此類型海霧日變化較小,維持時間為1~2 d。
3.3 高壓后部型
高壓后部型包括西風帶高壓入海和副熱帶高壓西伸北抬2種情況,前者多見于冬末、春季,后者多見于初夏。冬末春初西風帶高壓經大陸東移入海后,高壓變性為暖中心,一般位于東海東部海域,沿海受高壓脊控制,濕度明顯增大,導致近海面層又暖又濕,低層大氣層結趨于穩定并產生逆溫層,普陀海域受高壓后部的偏南或東南風影響,濕度較大,有利于海霧的形成。初夏季節,西太平洋副高西伸加強北抬,普陀海域處于副高西側,暖濕空氣被吹送至沿岸,地面上看其處于高壓后部,為偏南風。這種形勢下的海霧一般在早晚生成,維持時間一般在1 d左右。
3.4 高壓底部型
冬季,東亞大槽東移影響我國海區,沿海受槽底偏西氣流控制,對應地面上冷高壓南下,當高壓中心東移入海(一般位于黃海附近)不久,普陀海域處在高壓中心或底部,弱冷鋒附近,弱冷空氣在東北氣流的引導下,流向普陀沿海海面,使近地面層上空的氣團驟然冷卻,相對濕度增大,大氣趨于飽和,從而形成海霧。此類型海霧一般在早晚生成,維持時間一般在1 d左右,比例較低。
具體探討2011年1月—2020年12月10年間這幾類天氣形勢占比,倒槽(低壓)型的海霧有73例,占總數的54%;由兩高間均壓型的有11例,占總數的8%;由入海高壓后部型的有30例,占總數的22%;高壓底部型的有21例,占總數16%。可見,普陀海域海霧發生主要是受倒槽(低壓)型的影響,其次為入海高壓后部,冷高壓位于黃海高壓底部,弱冷鋒附近,在適合的條件下,也容易產生大范圍的海霧。
普陀3—6月霧日最多,且各種天氣類型的霧均可發生,其中發生頻率倒槽型>高壓后部型>高壓底部型>兩高間均壓型;10年間8月普陀未出現霧過程,9月、10月各出現1次,且都為倒槽(低壓)型;11月—翌年1月開始有霧形成,總量偏少,各種天氣類型的霧均有。
4 普陀海霧形成的氣象和水文條件
普陀區域海霧多是因暖空氣平流至冷海面上形成的平流冷卻霧,其生消及其發展過程與氣溫、氣溫露點差、氣海溫差、相對濕度、風向風速等氣象水文要素有著密切關系。在普陀區域海霧的形成過程中,高敏感因子有氣溫、氣溫露點差、氣海溫差、相對濕度和風向風速。當氣溫高于7.8℃低于26.1℃時,可能有霧生成,但有霧時氣溫主要集中在10.0~24.5℃之間;氣溫露點差主要集中在0~1.4℃之間;海溫集中分布在10.6~24.6℃之間,氣海溫差集中分布范圍為-1.5℃~3.0℃。相對濕度基本在90%以上,其中相對濕度達到96%~100%時,產生海霧的概率更高。風向多為東南偏南風、南風和東南風,第二象限和第三象限風向相對出霧概率較小。風力通常在0.8~10.3 m/s之間(1~5級),集中分布為1.6~7.4 m/s之間(2~4級)。綜合風向和風速的統計表明,當出現2~4級的東南偏南風時,海霧出現的次數最多。風向的逆轉如偏南風轉為偏北風則容易使海霧消散(表1)。

表1 影響普陀海霧的氣象和水文要素的極值及集中范圍
5 結論
(1)普陀區域近30年(1991—2020年)氣候資料統計得出,年平均霧日為45.9 d,較1981—2010年常年霧日多8.7d。一年四季均有海霧生成,3—6月最多,且日變化明顯,霧主要于夜間至下半夜生成,上午逐漸消散。
(2)普陀區域產生海霧的主要天氣類型包括低壓倒槽型、兩高間均壓場型、高壓后部型和高壓底部型,發生頻率大小依次為倒槽型>高壓后部型>高壓底部型>兩高間均壓場型。
(3)普陀區域海霧是在適宜的氣溫、氣溫露點差、氣海溫差、相對濕度和風場等水文、氣象條件下形成的。當氣溫大于10℃且小于20.5℃,氣溫露點差0~1.4℃,氣海溫差在 l.5℃~3℃,相對濕度達到96%~100%,海域盛行東南偏南風,風速在2~4級時,有利普陀區域海霧的發生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