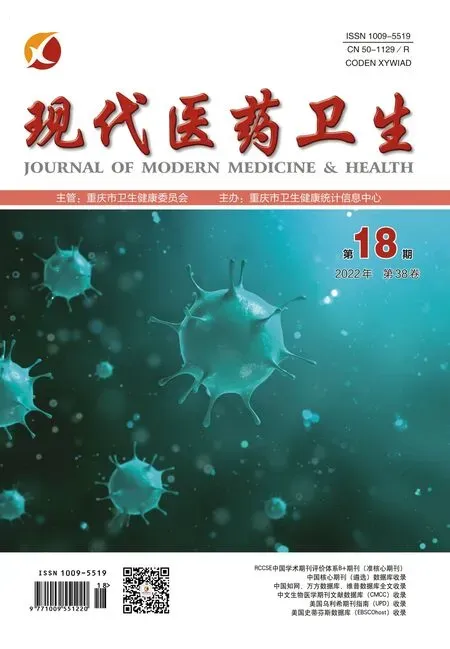中醫綜合療法聯合神經阻滯治療糖尿病痛性周圍神經病變的臨床效果和安全性*
陳書梅,張又之,杜 紅,肖 娟,梁澤容△
[重慶市紅十字會醫院(江北區人民醫院):1.內分泌科;2.疼痛科,重慶 400020]
糖尿病神經病變是糖尿病最常見的慢性并發癥[1]。糖尿病診斷后10年內,約60%~90%的患者會出現不同程度的神經病變[2],其中以疼痛為主要臨床癥狀的痛性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PDPN)最為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和工作能力,往往給患者及其家庭造成巨大的經濟和心理負擔。PDPN是臨床上頗為棘手的問題,常規西醫治療效果較差。研究顯示,在常規西醫治療基礎上分別加用中藥、針灸、穴位注射或神經阻滯等其他治療措施,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PDPN的緩解率[3-5]。因此,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中藥、針灸等中醫綜合療法聯合神經阻滯治療PDPN的臨床效果和安全性,旨在為臨床治療PDPN提供新的思路。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2019年3月至2021年8月于本院內分泌科住院治療的PDPN患者120例作為研究對象,其中男51例,女69例,年齡40 ~90歲。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將其分為A、B、C、D組,每組各30例。治療過程中,D組脫落4例,其余3組無脫落。本研究經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糖尿病診斷標準:參照世界衛生組織1999年糖尿病診斷標準[1]。PDPN診斷標準:除符合2017年版《中國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6]對于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診斷標準外,患者還有不同程度皮膚、肢體的疼痛,包括針刺痛、燒灼痛、撕裂樣疼痛等。納入標準:(1)符合上述糖尿病和PDPN的診斷標準;(2)年齡大于或等于18歲;(3)自愿加入本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1)1型糖尿病、特殊類型糖尿病或和妊娠期糖尿病;(2)患有糖尿病急性并發癥;(3)肝功能受損:有明顯臨床癥狀或體征的肝臟疾病、急性或慢性肝炎、谷丙轉氨酶(ALT)或谷草轉氨酶(AST)大于或等于正常值上限的2.5倍;(4)腎功能受損,估算腎小球濾過率(eGFR)<45 mL/(min·1.73 m2);(5)凝血功能異常;(6)急性心肌梗死,根據紐約心臟病協會心功能分級Ⅲ/Ⅳ級、左室射血分數小于或等于40%的充血性心力衰竭及腦血管事件(卒中);(7)合并嚴重缺氧及感染性疾病;(8)存在嚴重胃腸道疾患;(9)根據藥品說明書,存在對研究相關藥物過敏;(10)非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所致疼痛。
1.2方法
1.2.1治療方法 A組給予PDPN常規西醫治療。(1)控制血糖:進行糖尿病飲食及運動指導,使用口服降糖藥或胰島素將患者空腹血糖控制于4.4~7.0 mmol/L,非空腹血糖低于10.0 mmol/L,避免低血糖;(2)控制血壓:使用口服降壓藥,控制患者血壓低于140/90 mm Hg(1 mm Hg=0.133 kPa);(3)控制血脂:根據患者血脂水平睡前口服辛伐他汀20 mg/d或阿托伐他汀20 mg/d;(4)抗血小板:睡前口服阿司匹林腸溶片(Bayer S.p.A,國藥準字J20171021,100 mg/片)100 mg/d;(5)營養神經:口服甲鈷胺片[衛材(中國)藥業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143107,0.5 mg/片]0.5 mg,3次/天;(6)抗氧化應激:采用硫辛酸(重慶藥友制藥有限責任公司,國藥準字H20066706,0.15 g/支),0.45 g加入0.9%氯化鈉注射液250 mL,靜脈滴注,1次/天;(7)改善微循環:注射用胰激肽原酶(常州千紅生化制藥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023177,40單位/支),40單位,肌肉注射,1次/天;(8)抑制醛糖還原酶:口服依帕司他膠囊(揚子江藥業集團南京海陵藥業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040840,50 mg/粒)50 mg,3次/天。B組在A組的基礎上,請中醫科醫師會診進行辨證論治,根據患者自身情況加用中藥內服。C組在A組的基礎上,請中醫科醫師會診進行辨證論治,根據患者自身情況加用中醫綜合療法,包括中藥內服、針灸、穴位注射等。D組在A組的基礎上,請中醫科醫師會診加用中醫綜合療法,并請疼痛專科醫師會診,根據患者疼痛的神經解剖范圍及肌電圖結果,在超聲引導下進行神經阻滯。4組患者均持續治療14 d。
1.2.2指標監測 (1)視覺模擬評分法(VAS):使用一條長約10 cm的標尺表示疼痛的程度,兩端分別為0分端和10分端,0分表示無痛,10分代表最劇烈的疼痛,請患者在標尺上最能描述此刻疼痛程度的位置作出標記,由臨床醫師測量其數值,作為疼痛評分[7]。(2)多倫多臨床評分系統(TCSS):該評分為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的綜合評估工具,由癥狀評分(6分)、反射評分(8分)、感覺檢測評分(5分)等3個部分組成,其診斷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的適合截斷點為TCSS≥6分,具有較高的敏感度和準確性。TCSS分值越高表示病情越嚴重[8]。(3)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PSQI):該指數量表從睡眠質量、入睡時間、睡眠時間等7個方面評估所有患者治療前、后的睡眠質量,總分為21分,評分越高表示睡眠質量越差[9]。(4)安全性評估:觀察所有可能與本研究藥物、治療措施相關的不良反應,包括胃腸道反應、過敏、肌肉酸痛、眩暈、嗜睡、心悸等。

2 結 果
2.14組患者一般資料及生化資料比較 4組患者在性別構成、年齡、糖尿病病程、體重指數(BMI)、腰圍、血壓、糖化血紅蛋白、AST、ALT、尿素、肌酐、尿酸等方面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說明4組患者具有可比性,見表1。

續表1 4組患者一般資料及生化資料比較
2.24組患者治療前后VAS評分比較 治療前,4組患者VAS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4組患者VAS評分與治療前比較均顯著降低,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組間比較,4組治療后VAS評分由高到低分別為A組、B組、C組、D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4組患者治療前后VAS評分比較[M(P25,P75),分]
2.34組患者治療前后TCSS評分比較 治療前,4組患者癥狀評分、反射評分、感覺評分及TCSS總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4組患者癥狀評分、反射評分、感覺評分及TCSS總分與治療前比較均顯著降低,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癥狀評分組間比較,B組、C組、D組治療后癥狀評分均顯著低于A組,D組治療后癥狀評分顯著低于B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反射評分組間比較,C組治療后反射評分顯著低于A組,D組治療后反射評分均顯著低于A組、B組、C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感覺評分組間比較,C組治療后感覺評分顯著低于A組,D組治療后感覺評分均顯著低于A組、B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TCSS總分組間比較,4組治療后TCSS評分由高到低分別為A組、B組、C組、D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4組患者治療前后TCSS評分比較[M(P25,P75),分]
2.44組患者治療前后PSQI評分比較 治療前,4組患者PSQI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4組患者PSQI評分與治療前比較均顯著降低,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組間比較,A組和B組治療后PSQI評分相近,C組和D組治療后PSQI評分相近,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C組和D組治療后的PSQI評分均顯著低于A組和B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2.5不良反應 僅D組有1例患者在進行神經阻滯后出現明顯的下肢麻木感,觀察12 h后自行緩解,在后續神經阻滯治療中未再出現該不良反應。

表4 各組患者治療前后PSQI評分比較分)
3 討 論
PDPN患者數量眾多,但以積極控制血糖、血脂、血壓等危險因素,營養神經,改善微循環,抗氧化應激,抑制醛糖還原酶及聯合止痛藥物為主的常規西醫治療效果較差,疼痛難以得到快速有效的緩解,嚴重影響患者的正常生理和心理狀態,可出現睡眠及情感障礙、營養失調、運動受限等問題,且醫療資源消耗較大。因此,探索治療PDPN的新思路迫在眉睫。
近年來,祖國醫學在治療PDPN上取得了一定進展。中醫認為該病屬于“消渴痹癥”范疇,在常規西醫治療基礎上對PDPN患者進行辨證論治,分別或聯合加用中藥內服、針灸、穴位注射等治療措施均能在不同程度上緩解PDPN患者的疼痛癥狀,VAS評分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且可有效提高神經傳導速度[10-13]。方穎等[14]在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大鼠模型中發現,黃芪桂枝五物湯能減輕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的機制,可能是因為抑制核因子κB(NF-κB)激活并引發白細胞介素(IL)-1β、腫瘤壞死因子(TNF)-α等炎癥細胞因子釋放,進而抑制氧化應激和過度炎性反應。既往研究表明,神經阻滯對緩解神經性疼痛也有較好的效果。周圍神經阻滯技術是麻醉疼痛科常用的麻醉和治療手段,以局部麻醉藥物浸潤神經叢,阻斷疼痛信號傳入,可改善下肢的血液循環,快速有效地緩解疼痛[15]。研究顯示,腰2交感神經節阻滯和坐骨神經阻滯均能使PDPN患者的VAS評分明顯下降,神經傳導速度明顯提高[15-17]。但中藥、針灸、穴位注射等中醫綜合療法聯合神經阻滯是否能進一步提高PDPN的緩解率,國內外尚少見相關報道。
本研究將PDPN患者分為4組,在常規西醫治療基礎上,分別加用中藥、中醫綜合療法、中醫綜合療法聯合神經阻滯,探討聯合不同治療措施是否能進一步提高疼痛緩解率,顯著改善患者神經損傷相關臨床表現。結果顯示,4組治療14 d后,VAS評分,TCSS中的癥狀評分、反射評分、感覺評分,以及TCSS總分均較治療前下降,這與趙瑩雪等[10]、鄧秀敏等[11]、張翼生等[16]的研究結果相一致。除此之外,本研究結果還顯示,4組治療后的VAS評分和TCSS總分隨著不同治療措施的增加呈逐漸下降趨勢,在常規西醫治療基礎上加用中醫綜合療法聯合神經阻滯時下降幅度最為明顯,提示中醫綜合療法聯合神經阻滯能進一步提高PDPN患者疼痛緩解率,顯著改善神經損傷相關臨床表現。研究表明,約85.5%的PDPN患者存在睡眠障礙,易合并或誘發焦慮、抑郁情緒,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18]。因此,本研究應用PSQI評分對各組患者治療前、后的睡眠質量進行了評估。結果顯示,4組患者治療后的睡眠質量均較治療前改善,而C組、D組對睡眠質量的改善作用相較于A組和B組更為明顯,提示聯合不同治療措施能提高疼痛緩解率,改善患者神經損傷相關癥狀,從而進一步改善患者的睡眠質量。而D組對睡眠質量的改善情況未能優于C組,考慮原因可能是睡眠受多種因素影響,如情緒、環境、生活習慣、其他糖尿病并發癥等,混雜因素較多,單一PDPN癥狀的改善不足以顯現出2組患者睡眠質量的差異。安全性方面,本研究觀察了所有可能與藥物、治療措施相關的不良反應,包括胃腸道反應、過敏、肌肉酸痛、眩暈、嗜睡、心悸等,僅D組有1例患者在進行神經阻滯后出現明顯的下肢麻木感,觀察12 h后自行緩解,在后續神經阻滯治療中未再出現該不良反應,說明中醫綜合療法和神經阻滯不良反應少,總體安全性較高。本研究有4例脫落病例,均為D組患者。究其原因,主要為患者在治療過程中認為西醫常規治療聯合中醫綜合療法及神經阻滯的治療方案較為繁瑣,當疼痛癥狀得到有效緩解后,不愿再按此方案治療直至療程結束。這也提示臨床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可根據患者疼痛癥狀的嚴重程度及緩解情況,為患者個體化制定和調整治療方案。
綜上所述,在常規西醫治療基礎上,加用中醫綜合療法聯合神經阻滯可快速有效緩解PDPN的疼痛癥狀,臨床療效顯著,且總體安全性較高。雖相較于其他PDPN研究,本研究選取的研究時間較短(14 d),但更符合實際臨床工作中患者所期望的神經性疼痛緩解時間,特別是對住院患者有較大的參考價值。本研究不足之處在于樣本量較小,且未對中醫綜合療法聯合神經阻滯治療PDPN的機制展開進一步的探討,后續的研究可利用動物模型從分子水平對其機制進行更深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