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發(fā)型母乳性黃疸與嬰兒排便頻次的相關(guān)性
熊晶晶 ,張園園 ,李檬 ,陳艷 ,劉梅 ,黃永坤
(1)昆明醫(yī)科大學(xué)第一附屬醫(yī)院兒科,云南 昆明 650032;2)云南省檢驗(yàn)醫(yī)學(xué)重點(diǎn)實(shí)驗(yàn)室,云南 昆明 650032)
遲發(fā)型母乳性黃疸(late-onset breast milk jaundice,LBMJ)指的是黃疸出現(xiàn)緊隨著生理性黃疸的發(fā)生或減輕之后,膽紅素超過生理范圍,峰值可在生后2~3 周,持續(xù)4~6 周或可延長到2~3 月,一般停母乳喂養(yǎng)2~3 d 后癥狀明顯減輕的病理性黃疸[1]。延遲性黃疸發(fā)生的最大風(fēng)險(xiǎn)因素是純母乳喂養(yǎng)[2],但LBMJ 的病因及機(jī)制尚未完全明確,目前認(rèn)為與尿苷二磷酸葡萄醛酸基轉(zhuǎn)移 酶(uridine diphosphate glucuronosyl transferase,UDPGT)活性異常、膽紅素腸肝循環(huán)增加、遺傳等因素有關(guān)[3],其中,大多數(shù)學(xué)者支持膽紅素腸肝循環(huán)增加學(xué)說[4]。母乳和新生兒腸道中含有豐富的β-葡萄糖醛酸酐酶(β-glucuronidase,β-GD)、嬰兒胃腸激素變化[5]、嬰兒特定腸道菌群[6]以及母乳中的表皮生長因子等[7]因素均可以使嬰兒腸道中的未結(jié)合膽紅素含量增加,進(jìn)而引起膽紅素的腸肝循環(huán)增加而導(dǎo)致LBMJ 的發(fā)生。因此,本研究分析嬰兒日齡、排便頻次和母乳喂養(yǎng)頻次等與膽紅素腸肝循環(huán)途徑有關(guān)的因素及其與LBMJ 的相關(guān)性,為進(jìn)一步探討LBMJ 的相關(guān)膽紅素腸肝循環(huán)學(xué)說提供臨床依據(jù),也為進(jìn)一步明確LBMJ 的病因提供參考依據(jù)。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20 年8 月至2021 年7 月昆明醫(yī)科大學(xué)第一附屬醫(yī)院兒科和保健科門診就診的102例嬰兒,所有樣本納入標(biāo)準(zhǔn)[1]:(1)年齡 < 6 月;(2)純母乳喂養(yǎng);(3)足月出生,生長發(fā)育及營養(yǎng)狀況正常;(4)采樣前4 周未服用過微生態(tài)制劑及抗生素。排除標(biāo)準(zhǔn):(1)感染性腹瀉、肛管直腸異常疾病、先天性神經(jīng)肌肉異常、肌張力減退、內(nèi)分泌代謝紊亂、藥物所致便秘,家族性胃腸道遺傳病史等;(2)近2 周大便次數(shù)、顏色、性狀明顯改變的嬰兒。其中,黃疸嬰兒納入標(biāo)準(zhǔn):(1)符合LBMJ 嬰兒的診斷標(biāo)準(zhǔn)[1];(2)采樣前未使用過光療、肝酶誘導(dǎo)劑、藥用炭、瓊脂、蒙脫石散,微生態(tài)制劑等治療。排除標(biāo)準(zhǔn):(1)新生兒溶血、感染、缺氧、肝功能障礙、膽道閉鎖,先天性遺傳代謝疾病等其他原因所致的病理性黃疸;(2)吃奶、睡眠、尿便顏色、體重增長等一般情況異常的嬰兒。本研究經(jīng)昆明醫(yī)科大學(xué)第一附屬醫(yī)院倫理委員會(huì)審查,所有嬰兒的家長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研究方法
按照不同排便頻次的嬰兒分為排便頻次增多組(A組,n=37):排便頻次 > 3 次/d;排便頻次減少組(B組,n=34):超過4 d 排便1 次;排便頻次正常組(C組,n=31):3 d 內(nèi)排便1 次或排便≤3 次/d。同時(shí)填寫日齡、性別、是否為遲發(fā)型母乳性黃疸,每日母乳喂養(yǎng)頻次等問卷資料。
1.3 統(tǒng)計(jì)學(xué)處理
采用SPSS 25.0 及R 語言(Version 2.15.3)進(jìn)行分析,偏態(tài)分布計(jì)量資料用M(P25,P75)描述,多組資料的比較用H秩和檢驗(yàn);分類資料或等級(jí)資料用n(%)描述。分組變量為單項(xiàng)有序分類資料,指標(biāo)變量為分類無序資料時(shí)用χ2檢驗(yàn);雙向有序分類資料用趨勢性χ2檢驗(yàn)或確切概率法;樣本和環(huán)境因子間的相關(guān)性分析用冗余分析;P<0.05 為差異具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
2 結(jié)果
純母乳喂養(yǎng)兒的日齡與其不同排便頻次有統(tǒng)計(jì)學(xué)的差異(Hc=7.800 7,P=0.020 2)(表1);排便頻次改變與有無LBMJ 無統(tǒng)計(jì)學(xué)差異(χ2=5.864 9,P=0.053 3),見表1,但經(jīng)趨勢性卡方檢驗(yàn)發(fā)現(xiàn)LBMJ 的發(fā)生率隨著排便次數(shù)的增多而增高(χ2=5.759 3,P=0.016 4);嬰兒的性別(χ2=0.554 5,P=0.757 9)、母乳喂養(yǎng)頻次(χ2=5.063 6,P=0.280 8)與其不同排便頻次差異無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見表1。

表1 不同排便頻次純母乳喂養(yǎng)嬰兒的一般情況比較Tab.1 Comparison of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infants who were exclusively breastfed at different defecation frequencies
為了進(jìn)一步了解排便頻次、LBMJ、喂養(yǎng)頻次、年齡等因素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納入P值 < 0.3 的因素進(jìn)行多元直接梯度分析又稱冗余分析(redundancy analysis,RDA),發(fā)現(xiàn)LBMJ 與嬰兒排便頻次和喂養(yǎng)頻率呈正相關(guān),并且這3 個(gè)環(huán)境因子均與嬰兒日齡呈負(fù)相關(guān),見圖1。

圖1 環(huán)境因子RDA 圖Fig.1 RDA diagram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3 討論
新生兒黃疸消退延遲的相關(guān)性因素有感染、圍生期因素、母乳、溶血等[8],而LBMJ 占絕大部分[9]。目前LBMJ 發(fā)生機(jī)制及精準(zhǔn)治療方案研究尚存爭議,所以研究LBMJ 的相關(guān)因素至關(guān)重要,可以為進(jìn)一步明確LBMJ 的病因提供參考依據(jù)。
本研究發(fā)現(xiàn)嬰兒日齡越小,哺乳的頻次越多,排便頻次會(huì)增加,LBMJ 的發(fā)生率越高。母乳的哺乳頻次增多容易使母乳攝入量增多,導(dǎo)致嬰兒的排便頻次增加,排便頻次增加時(shí),腸道內(nèi)容物在腸道內(nèi)停留的時(shí)間縮短,使得腸道內(nèi)的膽紅素進(jìn)入腸肝循環(huán)減少,相反,當(dāng)排便頻次減少時(shí),腸道內(nèi)容物在腸道內(nèi)停留的時(shí)間延長,致使腸道內(nèi)的膽紅素進(jìn)入腸肝循環(huán)增多而出現(xiàn)黃疸。但筆者的研究發(fā)現(xiàn)LBMJ 發(fā)生率并不是隨著排便次數(shù)增多,膽紅素腸肝循環(huán)減少而下降,說明LBMJ發(fā)生的主要原因并非是腸道內(nèi)容物排泄頻次減少導(dǎo)致的膽紅素腸肝循環(huán)增加這個(gè)途徑。母乳和日齡較小嬰兒腸道中具有更高的β-GD[3,10],β-GD 通過分解膽紅素-葡萄醛酸脂鏈,產(chǎn)生未結(jié)合膽紅素,增加膽紅素腸肝循環(huán)[11]。新生兒的特定腸道菌群和母乳也可以調(diào)控β-GD 活性[12],Zhou S 等[13]發(fā)現(xiàn)母乳性黃疸患兒腸道菌群失調(diào),雙歧桿菌豐度顯著降低,半乳糖代謝途徑異常。茹彩旺等[14]也發(fā)現(xiàn)母乳性黃疸的新生兒糞便和母乳中降低β-GD 活性的雙歧桿菌豐度下降,而雙歧桿菌與血清的總膽紅素呈負(fù)相關(guān),間接提示母乳和新生兒腸道的雙歧桿菌不足與母乳性黃疸有關(guān),這均說明LBMJ 的膽紅素腸肝循環(huán)增加原因可能與雙歧桿菌豐度增高導(dǎo)致的β-GD 活性增加有關(guān)。另外,李亞璇等[15]發(fā)現(xiàn)母乳外泌體miR-16-5p 可能調(diào)節(jié)大腸桿菌影響新生兒腸肝循環(huán),另有研究發(fā)現(xiàn)人乳中的細(xì)胞因子IL-1β 增加可能通過影響肝臟攝取、排泄、結(jié)合膽紅素和腸道重吸收膽紅素途徑引起LBMJ[16],同時(shí)也發(fā)現(xiàn)表皮生長因子明顯下降與LBMJ 有關(guān)[7],但它們?cè)贚BMJ 中的作用和機(jī)制均有待進(jìn)一步研究。同時(shí),母乳中的膽固醇等脂質(zhì)物質(zhì)也與遷延性高未結(jié)合膽紅素血癥有關(guān)[17],以及嬰兒遺傳背景也影響膽紅素腸肝循環(huán)途徑。
綜上所述,LBMJ 的膽紅素腸肝循環(huán)途徑增多與嬰兒的排便頻次相關(guān)性較小,而可能與母乳和新生兒腸道中自身β-GD 活性較高、腸道菌群及其他途徑有關(guān)。同時(shí),本研究發(fā)現(xiàn)隨著0~6 月齡嬰兒日齡越小,母乳喂養(yǎng)頻次越多,嬰兒的排便頻次也增加,LBMJ 發(fā)生率越高,為LBMJ 的病因研究提供了參考依據(j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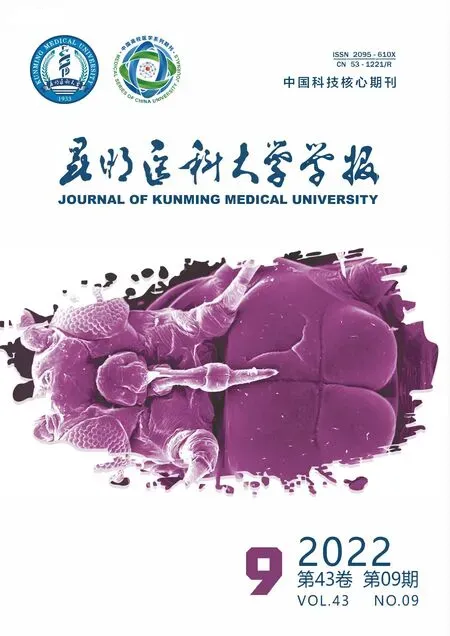 昆明醫(yī)科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22年9期
昆明醫(yī)科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22年9期
- 昆明醫(yī)科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的其它文章
- 昆明醫(yī)科大學(xué)假肢矯形工程專業(yè)通過國際教育標(biāo)準(zhǔn)認(rèn)證
- 蛋白質(zhì)S-亞硝基化與消化系統(tǒng)腫瘤關(guān)系的研究進(jìn)展
- FOCUS-PDCA 程序干預(yù)模式在腦卒中出院患者延續(xù)性護(hù)理中的應(yīng)用
- TBL-PBL-CBL 聯(lián)合教學(xué)模式在心內(nèi)科臨床實(shí)習(xí)中的應(yīng)用
- 人類胎盤的葡萄糖轉(zhuǎn)運(yùn)機(jī)制及GDM 對(duì)胎盤葡萄糖轉(zhuǎn)運(yùn)的影響
- LC-MS/MS 法檢測血液和尿液中東莨菪堿和阿托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