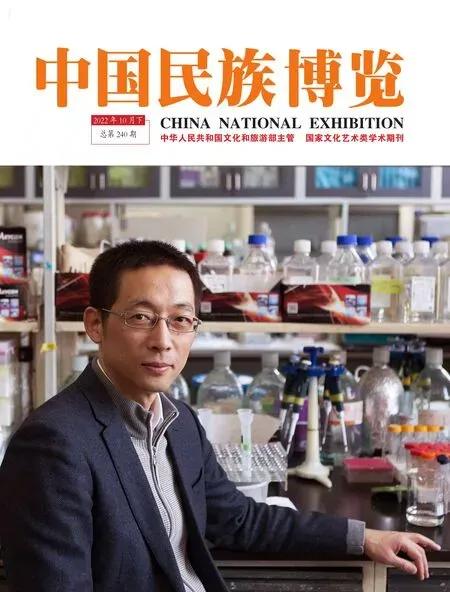道家審美視角下的老君巖造像美學(xué)意蘊(yùn)研究
劉琴姐
(廈門工學(xué)院博雅教育學(xué)院,福建 廈門 361021)
清源山位于泉州北郊,素有“道教圣地”之稱。據(jù)《泉州府志》載,清源山開發(fā)于秦,鼎盛于宋元。現(xiàn)存宋元石造像、摩崖石刻600 多處,雕鑿于北宋的老君巖,是我國體量最大、最具藝術(shù)價(jià)值的道教石雕。
為何在宋代的泉州會出現(xiàn)如此大體量的道教造像?為何這尊雕像具有渾然天成的藝術(shù)感染力?其審美特征為雕刻藝術(shù)提供怎樣的藝術(shù)參照?本文將從四個(gè)角度來探討。
一、老君巖產(chǎn)生的“精神氣候”與“經(jīng)濟(jì)氣候”
丹納在《藝術(shù)哲學(xué)》中提到,一種藝術(shù)形式的出現(xiàn),依賴于“精神氣候”[1]的形成。“經(jīng)濟(jì)氣候”是社會發(fā)展的風(fēng)向標(biāo),也是精神文明體系的基礎(chǔ),因此,“精神氣候”與“經(jīng)濟(jì)氣候”相互關(guān)聯(lián),共生互動(dòng),一起促成特定藝術(shù)形式的產(chǎn)生。老君巖誕生于宋代的泉州,便有賴于其特定的“精神氣候”與“經(jīng)濟(jì)氣候”。
道家思想來源于《周易》《道德經(jīng)》,學(xué)術(shù)界認(rèn)為,道教創(chuàng)始于東漢末年的太平道和五斗米教。自此,老子被奉為“太上老君”,《道德經(jīng)》《正一經(jīng)》被奉為經(jīng)典。古代閩南先民崇拜自然山川,盛行巫卜鬼神之風(fēng)。晉朝衣冠南渡,道教隨中原宗教文化傳入,結(jié)合當(dāng)?shù)毓砩癯绨荩俪砷}南宗教文化的多元態(tài)勢。泉州府建立的第一座道觀稱白云廟 (玄妙觀的前身),建于西晉太康三年,成為泉州道教史發(fā)展的重要里程碑。
宋朝官方在承襲儒釋道兼容的基礎(chǔ)上扶持道教。由于宋徽宗篤信道教,大量道觀建于宋代。為此風(fēng)氣所傳,泉州也興起建造道觀的風(fēng)潮。諸多著名道觀,始建于宋代。位于泉州涂門街的通淮關(guān)岳廟,就是始建于宋代[2],至今仍香火鼎盛。東鳳山東岳行宮、萬歲山真武廟,泉州城內(nèi)的天后宮、龍宮廟、凈真觀,以及惠安崇真觀、安溪通元觀等,這些散布極廣的道觀,說明泉州歷史上道教的興盛。宋代泉州官吏時(shí)常親自主持祈風(fēng)、祭海等活動(dòng),利用宗教活動(dòng)來推動(dòng)泉州港的興盛。泉州清源山老君巖造像,就是在宋朝政府重道的“精神氣候”下產(chǎn)生的。它是泉州現(xiàn)存最著名的道教遺跡,見證了一個(gè)時(shí)代道教的繁榮。最初,老君巖造像周邊有真君殿、北斗殿等道觀,年久傾廢,僅剩老君巖端坐天地間,與大自然和諧相融。
宋代的泉州港成為對外貿(mào)易的第一大港口,在對外文化交流當(dāng)中,儒家、道家作為華夏傳統(tǒng)文化代表,在多元文化薈萃的泉州成為主流。隨著海上交通的發(fā)達(dá),道教文化也隨著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傳播國外。商貿(mào)鼎盛,民間資本雄厚,在“重道”的氛圍中,必然會雇用能工巧匠來修建道教殿宇及造像,這便是老君巖造像所依賴的“經(jīng)濟(jì)氣候”。可以說,老君巖造像標(biāo)志著宋代泉州道教藝術(shù)的興盛,也見證了“海絲”文化的活躍。
二、雕刻技法蘊(yùn)含“道法自然”的審美追求
閩南石雕經(jīng)歷了晉代、南北朝、隋唐的發(fā)展,到了宋代,造像技術(shù)日臻成熟,雕刻語言和技法也日漸豐富。最初,閩南石雕主要服務(wù)于宗教,一方面體現(xiàn)在宮廟的建筑架構(gòu)以及寺內(nèi)亭臺樓閣的建造雕刻上,另一方面體現(xiàn)在對神佛造像及傳統(tǒng)墓葬石像生的雕刻上。建于宋代的泉州東西塔,以其精美的佛道人物、祥禽瑞獸雕刻,不僅反映當(dāng)時(shí)閩南石雕技藝的精湛水平,也體現(xiàn)宋代人崇尚精巧細(xì)膩的審美取向。
老君巖石像同樣建于北宋,卻并沒有刻意呈現(xiàn)精巧細(xì)膩的時(shí)代審美,而是由整塊天然巖石來略加修飾雕鑿而成,其衣紋簡潔,略作陰刻處理,并無較大起伏,凸顯樸素天真的審美趣味。清代《泉州府志》記載:“石像天成,好事者略施雕琢。”[3]為何在崇尚精妙細(xì)膩之美的時(shí)代,會出現(xiàn)這樣一種“略施雕琢”的寫意手法?這值得我們探討。
近觀之,石像做跨鶴坐姿,左手扶膝,右手靠著小矮幾,雙目深邃曠遠(yuǎn),兩耳垂肩,須眉皓然。老君巖造像衣褶簡潔分明,刀法柔而有力,須發(fā)雕刻細(xì)膩精到,層次分明。其樸素而神態(tài)畢現(xiàn)的韻味,疏密有致的雕刻線條,質(zhì)樸混沌的,天人合一的意境,使之充盈著藝術(shù)的生命力。最妙在于眼部雕刻“有眼無珠”,沒了瞳孔的聚焦,眼神顯得極為空遠(yuǎn),如此巧妙的處理手法,凸顯“空納萬物”語義(語出蘇東坡“空固納萬物”),“空”代表著含容與接納的狀態(tài),因此可以承受萬物。這種空遠(yuǎn)眼神,亦恰到好處地契合《道德經(jīng)》的“大方無隅”。遠(yuǎn)觀,整座雕像峨然而坐,似乎從天地間生長出來一般,極為和諧。這種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法正是對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的闡釋。老君巖造像從整體到細(xì)部,與《道德經(jīng)》文本深度契合,說明了兩個(gè)問題:1.文化傳播往往訴諸符號,當(dāng)時(shí)濃郁的道教文化氛圍,影響了老君巖的雕造者,他在對老子思想深刻把握的基礎(chǔ)上,以其特殊的雕塑符號,將道家經(jīng)典文本思想外化為藝術(shù)形象。2.老君巖雕造者絕非普通小工匠,無論從其對道家文本的把握還是對藝術(shù)手法的選擇,都體現(xiàn)出其高超的領(lǐng)悟力和藝術(shù)表現(xiàn)能力。
類似的形象塑造,我們可以在北宋李公麟《維摩演教圖》中看到,圖中維摩詰也是跨鶴坐,一手扶膝,一手倚幾,神情泰然,作論述狀。整幅作品用墨線勾描,人物造型嚴(yán)謹(jǐn),筆法精妙。遒勁圓轉(zhuǎn)的游絲描和鐵線描相輔相成,既巧妙刻畫了人物神態(tài),又演繹了佛教教義。佛像畫自晚唐興起崇尚華麗之風(fēng),后世相沿成習(xí),后來宗教意識式微,壁畫形式減少,立軾形式漸多,于是更趨于細(xì)致精工。《維摩演教圖》人物造型及細(xì)部裝飾顯然受此影響。繪畫佛像,除了法相和手印外,還有相對嚴(yán)謹(jǐn)?shù)亩攘俊H宋锷駪B(tài),要表現(xiàn)佛的智慧與功能“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無缺”。因此維摩詰居士面容飽滿,嘴角眉宇間透露出莊嚴(yán)、慈悲與靜穆。對比同時(shí)期兩件作品,可以看出,道教與佛教審美追求的異同。老子所謂“道法自然”,莊子所謂“素樸而天下莫能與之爭”[4],皆推崇不事雕琢、樸素天真的自然之美。道家美學(xué)追求,正是自然樸拙之美,是不紋飾之美,是意在象外之美,這種審美趣味在老君巖造像中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它給我們的啟示是:藝術(shù)佳品應(yīng)循自然之勢,一氣呵成,不事紋飾,而達(dá)到氣韻生動(dòng)的境界。
三、樸素審美成就道教造像的特殊氣質(zhì)
道家作為傳統(tǒng)文化重要部分,與儒家審美理念有顯著差異,儒家強(qiáng)調(diào)“仁”與“善”的追求,表現(xiàn)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強(qiáng)調(diào)藝術(shù)“美”與倫理“善”的統(tǒng)一。相對儒家審美的“守秩序”,道家審美為世人營造寬廣無礙的自由意境,主張不拘泥世俗之美,追求一種超越,去掉人為造作,恪守自身質(zhì)樸本性,追求自然的大美。這種樸素的審美理想,在歷代道教造像中,得以充分體現(xiàn)。據(jù)史料,道教最初僅供奉神位而不供奉神像,由于印度佛教的傳入,佛教造像的興起,刺激了中國傳統(tǒng)雕刻藝術(shù),因此道教也有了造像活動(dòng)。縱觀藝術(shù)史,道教造像相對較少,現(xiàn)存較有影響力的有西魏大統(tǒng)老子碑,開鑿于宋代的四川石門山摩崖造像,開鑿于元代的山西太原龍山石窟、四川青城山的三皇造像以及本文主要關(guān)注的泉州清源山老君巖。
道教的造像技術(shù)和風(fēng)格,隨著道教文化的發(fā)展和時(shí)代審美的變化,在不同的朝代和地區(qū)呈現(xiàn)出不一樣的風(fēng)貌,但總體而言,道教的造像相對佛教造像更為樸素和簡潔,人物造型及表現(xiàn)手法都相對簡單,從這一側(cè)面,似乎可反映出道家追求“自然”“樸拙”的審美意趣。
傳統(tǒng)道教形象通過“以形傳神”來體現(xiàn)內(nèi)在思想。早期道教人物造像皆是清骨秀像,著寬大道袍,衣紋線條勻稱,通常采用深直平梯式,以浮雕技法,細(xì)密而凸起。始鑿于北魏末年盛于隋唐的四川鶴鳴山道教石窟造像,便是道教早期至隋唐造像的代表。1 號窟乃圓雕立體道教造像,現(xiàn)存于露天。造像面頤豐滿,身著寬領(lǐng)道袍,右手下垂,左手五指并攏,掌心向外往上舉,手勢顯然受佛教造像的影響,但整體形象古樸,與佛造像之華麗迥異,給人以嚴(yán)肅莊重之感。早期“五斗米教”人物造像大都集中在四川地區(qū),鶴鳴山的“五斗星紋圖”,極具代表性地將“五行”學(xué)說和“五斗經(jīng)”“五斗米”內(nèi)涵集中呈現(xiàn),以其獨(dú)特的藝術(shù)符號,建立早期道教造像的藝術(shù)語言體系。
隋唐時(shí)期,道教造像在統(tǒng)治者的扶持下蓬勃發(fā)展。在道家審美的統(tǒng)攝之下,道教造像的雕刻語言和表現(xiàn)形式,一直有其獨(dú)特的風(fēng)格傾向,即表情淡然、仙道風(fēng)骨、衣紋簡潔、手法樸素。開鑿于北宋紹圣至南宋紹興二十一年間的四川重慶石門山石刻,是大足石刻中規(guī)模最大的佛、道二教結(jié)合的石刻群,尤以道教造像最具特色,被譽(yù)為“宋代道教藝術(shù)絕巔”。[5]
石門山道教造像造,雕刻手法粗獷而生動(dòng),將神之威嚴(yán)與人活潑巧妙結(jié)合。如2 號窟的千里眼雕像,眼若銅鈴,肌肉豐健,簡潔粗獷而富有張力。10 號窟道教文官造像,儒雅清秀,衣紋舒展,以樸素的造型呈現(xiàn)仙道風(fēng)骨。石門山道教造像的清秀、傳神,在道教石刻造像史上堪稱經(jīng)典,這得益于宋代精致細(xì)膩的審美取向,但與同時(shí)期的佛教造像相比,道教造像仍顯得衣著樸實(shí)、頭飾簡單、紋飾舒展。這里蘊(yùn)含著道教一以貫之的“見樸抱素”審美取向。相比同樣雕鑿于北宋的清源山老君巖,以其“精美傳神、渾然天成”的藝術(shù)風(fēng)格,從更深層面蘊(yùn)含著道家的審美意趣,以形布道,將道家“清靜無為”“大巧若拙”的思想展現(xiàn)無遺,可謂體現(xiàn)了道家審美的精髓。
山西太原龍山石窟,主窟開鑿于元代太宗年間,共8 窟,有道教石雕像66 尊,是中國現(xiàn)存規(guī)模最大的元代道教石窟群[6]。經(jīng)過歷代發(fā)展,元代道教造像已相當(dāng)成熟,此時(shí)風(fēng)格仍是凝練、莊重,滲透道家審美趣味,雕像衣飾簡練、褶皺分明,無太多裝飾,與佛教石窟雕像風(fēng)格相左。道家文化和審美意趣,對于道教造像的影響極為深遠(yuǎn)。從道教文化的角度去探究道教雕塑的審美造型和藝術(shù)表現(xiàn),[7]以及這種表現(xiàn)形式和審美產(chǎn)生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一項(xiàng)課題。
四、道家審美對其他石雕的影響
歷來無數(shù)學(xué)者對“道家文化”做了大量研究和探索。道家學(xué)說以老子提出的“道”為基點(diǎn)建立理論體系,把“道”作為宇宙本體,萬物規(guī)律,認(rèn)為“道”是超越時(shí)空的神秘存在;老子、莊子提出的“清凈無為,抱樸見素,大道至簡、守一、坐忘”等思想,被后世推崇發(fā)揚(yáng),[8]雖然作為世俗宗教的道教與道家學(xué)說不可同日而語,但也頗受其影響,而道家審美也深刻影響了中國傳統(tǒng)美學(xué)的審美趣味,形成一套獨(dú)立于西方審美之外的東方美學(xué)體系。
在藝術(shù)界一直存在寫實(shí)和寫意兩個(gè)范疇,寫實(shí)是對客觀事物的描摹,忠于自然,如鏡子照物,強(qiáng)調(diào)“像”。寫意強(qiáng)調(diào)“神似”,把事物作為寄情對象,從而擺脫時(shí)空觀念和自然屬性的約束,“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語出《莊子·齊物論》),在這種道家觀念指導(dǎo)下,天地造物隨其剪裁,從宏觀上把握物象,追求藝術(shù)表達(dá)的自由[9]。可以說,“寫意”是探索其隱藏在表象之下的精神世界,這是讀懂作品精神內(nèi)核的鑰匙。“寫意”對中國藝術(shù)起到積極的推動(dòng)作用,歷代藝人在繪畫、書法、雕塑、建筑、民間工藝等多個(gè)領(lǐng)域進(jìn)行了多種探索,從而形成獨(dú)特的藝術(shù)面貌。
這種探索,我們在漢代石雕作品可窺見端倪,并似乎可將之視為該類探索的開端。在陜西霍去病墓石雕中,一組以“馬踏匈奴”為主體雕塑的石刻作品屢屢被人們提起,成為美術(shù)史上的經(jīng)典佳作,甚至成為一個(gè)時(shí)代風(fēng)貌的代言。一組石雕作品能有這么大的威力,這與其背后潛藏的審美方式和時(shí)代精神有著深層的聯(lián)系。馬踏匈奴石雕戰(zhàn)馬外形簡練有力,整體追求軀體彪悍的風(fēng)格,馬蹄下的人模糊不清,與馬交織,細(xì)節(jié)若隱若現(xiàn),遠(yuǎn)觀則呈現(xiàn)一種龐然之氣。而伏虎、躍馬、臥象等石雕則按照石材原有的形狀,在關(guān)鍵部位精雕細(xì)刻,其他部位略加雕琢,以浪漫寫意的手法、豐富的表現(xiàn)力和高度的概括性來彰顯對象的神情和動(dòng)感,風(fēng)格樸拙、氣勢豪放,暗合“道法自然、大道至簡”的道家審美,也讓我們聯(lián)想到莊子的“得意而忘言”,以及由此派生出的王弼的“得意忘象”。
將霍去病墓石雕與道家思想聯(lián)系起來,并非無厘頭的牽強(qiáng)附會。一種藝術(shù)形式的出現(xiàn),往往有某種思想學(xué)說在引領(lǐng),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思想氣候”。恰恰在東漢,道教作為一種新的宗教形式產(chǎn)生了,他們推崇道家思想,并影響了中國文化數(shù)千年之久。從上文我們探尋的歷代道教造像的樸素審美可得知,道家審美取向在中國傳統(tǒng)審美文化體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我們也可做大膽假設(shè),在宋代泉州,老君巖雕造者在構(gòu)思老子造像表現(xiàn)手法時(shí),從歷朝各種藝術(shù)手法中選擇了最契合老子文本解讀的表現(xiàn)形式,從而溯源到“馬踏匈奴”的寫意精神。對于一位領(lǐng)悟力極高的巧匠來說,通常是見多識廣并對各種風(fēng)格技藝了然于胸,在面對不同雕鑿對象時(shí),可靈活運(yùn)用或精微或雄渾或樸拙的不同風(fēng)格,以達(dá)到“傳神”的藝術(shù)高度。此位巧匠在對老子文本深刻把握的基礎(chǔ)上,以“大巧若拙”的寫意手段,展現(xiàn)了對道家精神境界精微的體認(rèn)觀照,對宇宙物象體貼入微的辨察。
雖然縱觀我國數(shù)千年石窟歷史,類似于霍去病墓石雕這種氣勢磅礴的大寫意表現(xiàn)手法并沒有在佛教造像上得到大力弘揚(yáng)。例如,始鑿于北魏的云岡石窟,早期“曇曜五窟”,呈現(xiàn)樸素和偉岸的風(fēng)格,與道家樸素大氣審美尚有一些聯(lián)系,可到了中期,云岡則以精雕細(xì)琢、裝飾華麗著稱,展現(xiàn)了富麗堂皇的北魏時(shí)期藝術(shù)風(fēng)格。[10]到了晚期,窟室規(guī)模變小,人物形象趨于清瘦俊美,開啟了“瘦骨清像”的佛造像風(fēng)格。這一發(fā)展軌跡與“樸實(shí)凝練、天然渾厚”的道家審美越走越遠(yuǎn)。隨著道教的逐漸式微和佛教的幾度興衰,到了清代,佛教造像石刻較少,多為泥胎、銅塑,工藝登峰造極,身材、五官、衣紋、配飾等追求“精致”,與道家審美迥異。由于統(tǒng)治階級的關(guān)注較少,此時(shí)道教只是作為一種傳統(tǒng)宗教在民間流行,塑像的質(zhì)量和數(shù)量都有所欠缺,且保存不多。道教造像雖式微了,但其審美意趣仍深刻影響一代代雕塑創(chuàng)作者。
在泉州惠安崇武古城海邊的“魚龍窟”群雕中,我們猛然瞥見那“混沌之氣”“天然雕飾”的道家審美的身影。這組“大地巖雕”和浙江大鹿島巖雕,都是中國美院教授洪世清在20世紀(jì)90 年代,歷經(jīng)數(shù)載嘔心瀝血的藝術(shù)結(jié)晶。洪世清融合浮雕、圓雕和線雕等多種技法,以夸張變形的大寫意手法,因石賦形,依海而鑿,盡顯自然美、殘缺美的魅力。其作品粗獷渾厚、蒼莽奇崛,成為中國當(dāng)代巖雕代表之作。這是對秦漢雄渾大氣藝術(shù)風(fēng)格的承繼,是對宋代老君巖“以石賦形”藝術(shù)手法的呼應(yīng),是對“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審美趣味的完美詮釋, 也體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藝術(shù)對“意”的表達(dá)。
在雕塑家吳為山的《孔子》《老子》《魯迅》等作品中,我們同樣看到那種“混沌之氣”,那種“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理論。他的寫意人物,主要特點(diǎn)是展現(xiàn)形態(tài)的夸張意象、凸顯人物的隱性特征、將自然意象山水流韻融入雕塑,構(gòu)建人物雕塑的獨(dú)特意境。其中《老子》以18 米的超大體量和混沌滄桑,給人以巨大的審美沖擊。其樸拙、厚實(shí)、深邃的審美特質(zhì),如同老子的思想一樣,簡潔而豐富、深刻而博大,其弓背敞懷的形態(tài),凸顯虛懷若谷、玄妙之門的意象,使老子的形象與思想同樣巍然聳立。此類作品是雕塑家受道家“道法自然”審美追求影響的有利佐證,其寫意形態(tài),呈現(xiàn)“見素抱樸”的自然之美,也闡釋了藝術(shù)佳作所蘊(yùn)含的“氣韻生動(dòng)、本乎自然”氣質(zhì)。而這也正是對道家審美的發(fā)揚(yáng),是研究道家審美風(fēng)格脈絡(luò)的珍貴資料。可見,道家審美文化中“道法自然”“見素抱樸”等經(jīng)典命題,很大程度影響著中國造像藝術(shù)寫意風(fēng)格的形成和發(fā)展。
五、結(jié)語
綜上,本文以泉州老君巖為切入點(diǎn),梳理道教石造像的樸素審美的大體脈絡(luò)。從道教文化的角度去探究道教雕塑的審美造型和藝術(shù)表現(xiàn)及其影響,是值得深思的一項(xiàng)課題,為當(dāng)代雕塑家提供摹古與創(chuàng)新的參考依據(jù)。筆者認(rèn)為,以老莊為代表的的道家審美文化的繼承與發(fā)揚(yáng),在當(dāng)下仍具有極大的現(xiàn)實(shí)意義。道家“道法自然”“混沌之氣”的美學(xué)意趣,成為東方審美的特質(zhì),植根于中國傳統(tǒng)諸多石雕像領(lǐng)域,以其特有的自然旨趣、直覺觀照,豐富了中國當(dāng)代雕塑美學(xué)的思想創(chuàng)構(gòu)及精神意蘊(yù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