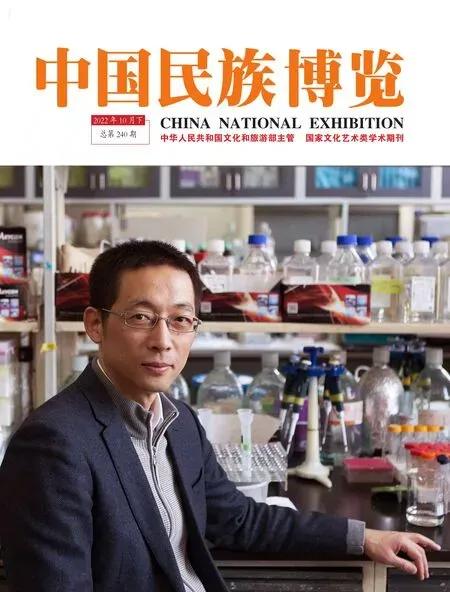論《儒林外史》中的“孝”
馬 寧
(聊城大學文學院,山東 聊城 252000)
泱泱中華五千年的文明,以孝治國的制度與“孝”文化源遠流長、經久不衰,引領著社會風氣。吳敬梓出生于清代官宦之家,家風淳樸,敬奉儒家圣賢之道,治家尤重孝道的傳承。吳敬梓崇尚蘊含深情的“真孝”,在其批判力作《儒林外史》中也多方面描寫孝子孝行,歌頌人間真情;亦或是不孝子惡行,抨擊人性的虛偽,社會的黑暗。
《儒林外史》中關于“孝”的人物故事描寫,不乏多樣出彩之處。吳敬梓通過描寫王冕、杜少卿、武書等孝子恪守孝道的情節來闡釋“孝”的內涵,顯示出他們對傳統儒家孝義的推崇,這也深刻體現出吳敬梓對儒家孝道的認同贊揚和經典傳承。同時,對于匡超人、牛浦郎、荀玫等不孝子故事情節的精心刻畫,展現出吳敬梓對沉迷科舉功名以致品行受到毒害的不孝子的鄙夷,深刻抨擊在名利面前人性的虛偽脆弱、不堪一擊以及社會風氣下行的敗壞之象。吳敬梓刻畫“孝”較為全面,介于“真孝”與“不孝”的迂孝,他以郭孝子驚天地的尋父行為,書迂孝的典范。
吳敬梓想通過《儒林外史》體現的孝道精神,匯聚于楔子王冕身上。“說楔子敷陳大義”,王冕是小說的隱括,飽含著吳敬梓對“孝”的希望與期許。王冕自小順從母親安排為秦老放牛求生活,因天性聰慧自學畫荷花名于方圓縣城,手頭富足不忘孝敬老母親,后拒絕高官賞識留老母孤身一人逃離本縣避難,歸來后一心要養家孝敬母親,因抵觸做官向往隱逸生活,于一座深山度過余生。王冕的孝在于知進退卻不忘母,錢財利誘卻不泯滅孝敬尊親之心。吳敬梓通過王冕這一人物展現出美好的家庭倫理關系,為《儒林外史》中塑造的其他孝子形象樹立了一個評判標準,預示著唯有母慈子孝方能彰顯孝道精神,構建和諧的家庭關系,促進社會正氣之風。
一、《儒林外史》中的“孝”
何為“孝”?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云:“孝,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1]” “孝”,從字的構成上來看就像孩子背著老人,“孝”字的本義是子女如何“善事父母”的一種道德觀念,因而孝是子女對父母的一種善行和美德,是家庭中晚輩在處理與長輩的關系時應該具有的道德品質和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簡而言之,盡心奉養并順從父母稱為“孝”。“真孝”正是吳敬梓透過《儒林外史》想要弘揚的高尚道德精神。
怎樣做才能“孝”?《論語》有云:“弟子入則孝,出則悌”[2];“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2];“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2]; “父母唯其疾之憂”[2];“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2]。《孝經》云:“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后能事親[3]。”由此可知,發自真心地贍養孝敬父母,在追求自身獨立的情況下尊重父母的要求,時而委婉諫言以此達到家庭和睦溫馨狀態,踐行孝道理應如此。于古典中窺測孝道內涵,可觀吳敬梓在《儒林外史》角色形象的具體刻畫中,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了陪伴、順從、逝后三種情況下的孝行為。
(一)陪伴之孝
兒女承歡膝下可謂難得的孝道。吳敬梓的父親吳霖起辭官回鄉卻一病不起,雖床榻度日卻不曾被子輩拋棄,遺憾的是吳老爺偏在吳敬梓榮升秀才欲享福之際魂歸黃泉。十年如一日的精心陪伴是吳敬梓夫婦愛的凝聚,更是孝的彰顯。
與吳敬梓真實情況類似的“陪伴之孝”在作品中可找到對應的人物及情節,如杜少卿與武書孝行便同為“陪伴之孝”。杜少卿的父親視婁太爺為知己,有如親兄弟般的交情。婁太爺居于杜少卿家三十年,日復一日的接觸與陪伴使婁太爺在杜少卿心中勝似親人,如父親般的存在。漫漫人生路,人總有生老病死的一天。自婁太爺身體大不如前、日漸衰弱始,杜少卿便接入家中細心照料,將婁太爺的生活打理得細致入微,小到茶水飯食都離不開杜少卿親自查驗監督,這份用心直至婁太爺歸去才結束。孝子武書奉侍母親也是如此,為不拋棄老母孤身一人艱苦度日而選擇不爭取科考功名,一心照顧母親,直到母親病逝才走上科考之路。
杜少卿與武書雖同為“陪伴之孝”,細論卻有所不同,根據文中孝子所在處境及孝敬親輩的方式,筆者將其分為“溫情之孝”與“苦情之孝”兩種孝行。
1.杜少卿溫情暖人間
杜少卿的孝道蘊含深情且飽含暖意。即便家道中落,因繼承祖輩遺產、富甲一方的杜少爺依舊是豪奢度日。在照料婁太爺生活方面,杜少卿不僅安排仆人、藥材如流水般支持花銷,更是“愛屋及烏”變賣田產來接濟老人的兒孫。杜少卿雖為婁太爺殫精竭慮,但是資本的充裕使他盡孝的故事洋溢著歡情與溫馨。
2.武正字苦情化天地
武正字與杜少卿不同,作為一個沒有顯赫家世的窮書生,他所盡的孝是以奮斗征程的時間與異于常人的信念做支撐,可謂“苦情之孝”。武正字回虞博士的話中“門生少孤,奉事父母在鄉下住。只身一人,又無弟兄,衣服、飲食都是門生自己整理[4]”。可見武正字家中清貧且負擔較重,雖滿腹才情卻為侍母棄考,足見武正字孝道之苦。
《儒林外史》中“溫情之孝”體現出的樸素真摯情感,“苦情之孝”中書寫出的辛酸勵志故事,讓我們懂得不論是從前還是現在,為人子女要在生活富足時牢記父輩撫養之艱辛,窮困貧乏時亦不棄生養父母,這便是吳敬梓所推崇的基本孝道觀。
(二)順從之孝
悉心聽取父母給予的正確建議,在實現自我價值的同時行孝事、盡孝心便是“順從之孝”。年邁的老父親蕭昊軒僅有蕭云仙“一棵獨苗”,欲盡孝心的兒子想陪伴父親直至終老,卻被這位有格局的慈父以“貪圖安逸”“不孝之子”等名頭責備其不愿討個人前程。在父親的勸導鼓勵下,蕭云仙遠離故土于疆場奮力廝殺、屢建戰功,多年崢嶸歲月、浴血沙場使他聲名鵲起,正值升官發財之際卻被朝廷七千兩“官債”逼得只得回鄉求助老父親蕭昊軒的幫助。世事難料,不成想這是與蕭老的最后一面,正當蕭云仙因官債愧疚之時,蕭昊軒卻以“人以忠孝為本,其余都是末事”的勉勵之語讓蕭云仙釋懷,如此追求事業的簡單道理使云仙如醍醐灌頂般通透[4]。
拋家舍業的陪伴一定不是最好的孝行。《論語》云:“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5]”深受封建社會思想荼毒的蕭云仙在父親的建議下馳騁沙場以實現人生價值,雖未在父母身邊行完整的孝道,但是卻因聽取父母建議孝心依舊而獲得父親的支持與贊揚,這何嘗不失為一種孝道?
吳敬梓以“蕭云仙孝父”的故事警告世人,人當知有所為而有所不為。身為子女,最不能忘盡孝之心,更不能忘盡孝應以實現自身價值為前提。一生碌碌無為,得過且過,不思進取,難道是孝行嘛?誠然否,父母希望我們靠自身實力闖出一片天地,不管是通過執劍沙場掙功名,文筆揮就寫官名,還是運營商賈賺美名的方式,都是在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同樣也是一種盡孝表現。
(三)逝后之孝
“逝后之孝”作為父母在世之孝的有效補充,使盡孝的時間軌跡及孝行顯得更加圓滿完整。《儒林外史》中余持、余特兩兄弟尊賢敬長且明事理,不貪富貴而遷墳,力排封建世俗偏見,不違本心料理父母身后事,孝心可鑒天地。余家兩兄弟父母葬禮上的“千子一哭”與范進的丁母憂、荀玫母親老死一哭、鮑廷璽父親淺哭用意不同,結合“陪伴之孝”“順從之孝”來看,吳敬梓對之如此大費周章意在“一石三鳥”:一是準確把握在世與離世的完整孝道時間;二是借文人及村民之言反襯兩兄弟孝心;三是透過清代社會繁雜的喪禮規制來反映當時濃厚的封建迷信色彩,批判世俗民眾內心的憨態。
透過余持、余特兩兄弟“逝后之孝”的孝道行為,可知吳敬梓通過《儒林外史》所傳達出的孝道觀,即“愛屋及烏”:父母死后,兄弟和睦,盡守孝道,不逾矩、恪禮節,這是吳敬梓心中的孝道藍圖。
二、《儒林外史》中的“不孝”
何種程度可判定為不孝?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6]”不孝的行徑是多樣的,范圍面也較廣,如因錢財而拋父棄母、對長輩忤逆不尊等皆可視為不孝的表現。在《儒林外史》這部長篇巨制中,吳敬梓分別從遺棄、忤逆、逝后三個方面講述了不孝子的種種惡行表現,實則是借不孝之筆揭人性之實,諷刺世道之惡。
(一)遺棄之不孝
母親十月懷胎生兒女,父母含辛茹苦養成人。身為子女,父母教養幾十年,如此恩情不答,自行歡愉之事卻棄父母于陋室茍活,視為不孝。《儒林外史》對于不孝子的角色塑造及各情節的發展有不同于孝子的尋常設計。不孝子之一——匡迥,他的人生之路被塑造得極具戲劇性,成名前后性情品質上的極大反差映射出了一種理念:“孝”是否會因名利等外在因素而變質,極富諷刺意味。
匡迥起初可謂孝子中的典范,自覺因無法侍奉父母生活為恥,生活中為贍養父母、孝敬尊親所做的孝事更是觸人心扉,如擔心父親出恭困難,竟如小羊跪乳般雙膝跪地幫助父親減負,如此可見其品行之善,孝心之堅。但世人唯利是圖,走上科舉功名后的匡迥卻三次棄養父母,在贍養父母問題上態度更是發生了天翻地轉的改變,與之前的匡迥可謂截然不同,如為趕科考拋下年邁無人照料的父母一月有余,致使家中老人常以淚洗面。可見匡迥的心境已經被浸染變質,品行腐壞,以至于有了后來的“西湖名士”“假婚書”“為金躍替考”“重婚”等趨之若鶩的瘋狂行為,可以說匡迥已然為功名做到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了。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匡迥的墮落受外在綜合原因的影響。匡太公曾對匡迥說“功名到底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緊的。我看你在孝弟上用心極是難得,卻又不可因后來日子略過得順利些,就添出一肚子里的勢利見識來”,便揭示匡迥淪陷難自拔的原因主要有三:意志不堅、交友不慎、貪圖功名[4]。世人圖利而來,為利而往,利字當頭,盡孝主體亦或不保崇德向善的初心。吳敬梓正是通過匡迥這一形象警示后人在面對名利時要守住道德底線,勿忘為人初心。
(二)忤逆之不孝
《儒林外史》中牛浦因其叛逆本性及被名利侵蝕的內心,行徑齷齪,對祖父更是忤逆不尊,實乃大逆不孝之子。牛浦年少時品行叛逆不端,雖愛閱讀書籍卻喜偷書;為自己新婚有地可睡而驅趕祖父睡柜臺,卻也無動于衷;貪戀牛布衣聲譽遠揚四海,不想隨其學習知識卻一心只想冒名頂替。滿嘴的“之乎者也”卻一副道貌岸然的禽獸嘴臉,不顧祖宗家業使得生活漸露難堪,祖父牛老兒怒其不爭、不求上進而活活氣死。
世人追名逐利,科考成為捷徑,八股取士后“之乎者也”更是文人的桎梏。因此牛浦不孝,并不單是天性使然,更多的是利欲熏心,八股害人,使牛浦跌入名利場無法自拔。如若牛浦視名利如糞土,又何來這不孝之輩?天性使然也好,八股取士之果也罷,歸根結底是名利侵蝕下道德敗壞所致,因此聽取父母之言定有可取之處,這不僅是傳承孝道美德,更是勉勵自身以提升德行素質的佳徑。
(三)逝后之不孝
父母死后,兒女做何為不孝?不葬、不敬、家庭不睦,是為父母逝后三大不孝。《儒林外史》中不盡“逝后之孝”的不孝子數量較多,諷刺深刻。
1.施二為發家鬧遷墳
施御史家弟兄兩位,施大進士出身,施二沉迷科考但苦于無果,遭風水先生算計執迷于遷母墳,《儒林外史》四十四回記“乃兄中了進士,他不曾中,都是大夫人的地葬的不好,只發大房,不發二房,因養了一個風水先生在家里,終日商議遷墳[4]”。在風水先生蠱惑下,施二不顧兄長嚴令禁止,為發家中舉強遷母墳,落得個墳內熱氣傷致瞎眼。如此滑稽的諷刺揭示出君子應謀正道發家,不孝于長更是百害而無一利。
2.荀員外推呈丁母憂
父母死后依舊制子女需守三年喪期,視為盡孝。《儒林外史》中范進按舊制呈丁母憂,書中記“賢契績學有素,雖然耽遲幾年,這次南宮一定入選”,可見為父母守孝期是盡孝的一種規制表現[4]。書中另一人物荀玫卻恰恰相反,第七回記荀玫“就醒轉來,就要到堂上遞呈丁憂”,卻在選官之際為求一官半職聽信老道王惠“現今考選課、道在即,你我的資格都是有指望的。若是報明了丁憂家去,再遲三年,如何了得?[4]”的讒言,為逃三年孝期手段盡施。功名利祿對人性的侵蝕,使荀玫空有一副文人皮囊,卻不具“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犀利地諷刺出當時官場的黑暗以及人性的虛偽善變。
3.嚴致中霸道奪家產
兄弟之間同氣連枝、和睦扶持是悌,更是對逝后父母的孝心與慰藉。嚴氏兄弟,大哥嚴致中,暴力貪婪;弟弟嚴致和,吝嗇自私。嚴致和因病早逝,留與趙氏所生之子卻因天花離世,萬貫家業無人繼。嚴致中為人肆無忌憚,為奪嚴致和家產罔顧倫理綱常,將自己兒子作為奪財籌碼強行剝奪弟媳趙氏權利,以娶妻為由入主正房霸占家產。古往今來,不論父母在世與否,兄弟姐妹間守孝悌是孝敬父母亙古不變的基礎,更是關鍵所在。
三、《儒林外史》中的“迂孝”
(一)何為迂孝
漢代推行“以孝治國”,經后世歷朝歷代推崇、地方過度提倡、民眾爭相效仿,迂孝隨之產生。迂孝在孝文化的發展中未曾間斷,如“郭巨埋兒”“王祥臥冰”等都是廣為人知的迂孝故事。究竟何為迂孝?迂孝介于“真孝”與“不孝”之間,是子女過度順從父母的結果,如若父母不苛求或能夠及時制止子女盲目盡孝,迂孝便不會產生。因此,迂孝是子女和父母在“孝”的認知上出現錯誤所導致的過度“孝”行為。
(二)以何見“迂”
吳敬梓在《儒林外史》第三十八回中用一半篇幅講述了“郭孝子(即郭鐵山)萬里尋父”的感人故事。他在尋父期間路遇猛虎、智斗賊人,雖路程艱辛卻不改尋父初衷,好在二十年如一日的堅守讓他遂愿,順利找到父親王惠且送其終老。為何說郭孝子是迂孝行為,究其根本,雖說郭鐵山孝行驚世駭俗,但盡孝的標準應視子女與父母雙方情況而定,如若此孝行徒勞且過度,那便是迂孝典型,“郭孝子、萬里尋父記”正如是。
郭鐵山的父親——王惠,晚年及第,苛政斂財且背著叛國奸臣的罵名,為不連累家庭、求得一線生機,于殘燭之年化作和尚隱姓于成都府茍存于世。然郭孝子所處社會時代“子欲養而親不待”視為子之過,王惠尚且在世,如若不尋父那便是于個人、于社會有違綱常的雙重不孝。二十年間郭孝子為尋父雖精神可嘉但碌碌無為,這便是為盡孝而盡孝、失去自我價值的迂孝。郭孝子的故事情節透露出我們在行孝過程中應堅定立場、愛護父母,分辨社會道德與輿論導向,履行贍養父母的義務。
(三)孝的真正內涵
迂孝是過度的“孝”行為,如若子女與父母行為雙方達到平衡狀態,保持良好的雙向互動關系,那便是吳敬梓所推崇的真正的孝道精神。這要求父母明事理、愛護晚輩,不倚老賣老;子女講原則,尊敬長輩,不盲目追隨。以此達到和諧狀態,促進社會良好風氣的形成。
牛浦無視牛太公的辛勞致家庭不和,匡太公樸素善良為子考慮卻落得個被拋棄的下場,鮑廷璽雖孝順卻逃不過鮑老太安排的惡姻緣,由此可見:只是子女或者父母一方輸出愛意無法達到孝的和諧狀態,只有子女與父母間雙向互動才能真正做到孝德仁愛,這要求父母明事理且愛晚輩,子女講原則并有主見,如王冕與其母,慈母孝兒;婁太爺與杜少卿,和諧溫馨;蕭昊軒與蕭云仙,志同道合,以此達到和諧狀態,促進社會良好風氣的形成。
孝是子女與父母之間雙向付出后達到的一種互動和諧效果,缺一不可。孝道,是子女對含辛茹苦的父母的報答回饋,是父母寄托在子女身上的殷切期望,更是維穩社會和諧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
四、結語
吳敬梓的人生經歷曲折坎坷,他對人性的虛偽、科舉的弊端以及社會的黑暗有切身的感觸。吳敬梓將“孝”作為挖掘主題的一條線索,將《儒林外史》中形形色色的文人貫穿其中。從這些鮮活的人物形象中我們窺得“孝”的三個層面:“真孝”“不孝”“迂孝”。作者以平實語言傳遞出“真孝”的溫情,以諷刺滑稽的情節揭示出“不孝”的慘痛下場,以郭孝子萬里尋父的迂孝揭示“真孝”的真正內涵,進而得出孝的本質,其實是子女與父母之間雙向互動的結果。
“孝”不僅貫穿小說全文,放眼望去,更貫穿整個中華文化。古有“奉先思孝”,“孝”“德”相佐的思想,揚真孝、棄迂孝、忌不孝;歷代帝王以其為治國之道,推行孝治,“舉孝廉”、修《孝經》。而今又有“百善孝為先”的口號宣揚,“感動中國十大人物”的孝道弘揚。“孝”是一件治世不可或缺的工具,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的基石,它如絲絲紋路,穿插在這幅深奧的文明長卷之下,反映人性與文明,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孝”是中華文明的根,是國家的魂,更是社會和諧穩定、欣欣向榮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