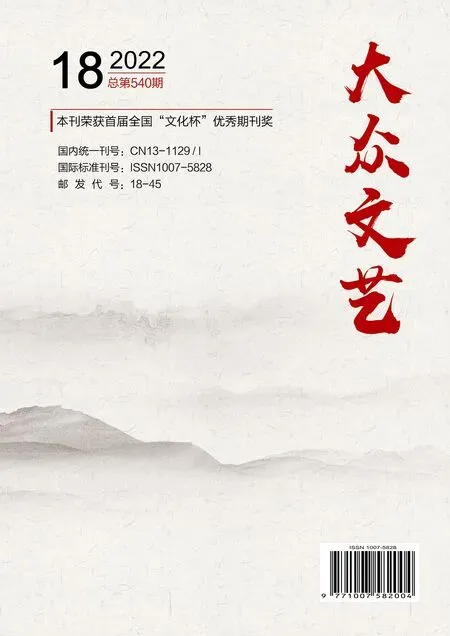鄉村文化品牌傳播媒介的系統研究*
田 瑾 王曉華 王 軒 趙亞偉 侯力丹 王曉琳
(河北工業大學,天津 300130)
鄉村振興戰略是在經歷了2005年新農村戰略,2017年確立的鄉村振興戰略,這一戰略通過城市來反哺農村,將空間資源創造的價值還給所在地的農民。從物質基礎層面要求從生產發展的到產業興旺,鄉村才有持續創造地域文化品牌的基礎和新動力,媒介系統依賴理論,詮釋了受眾究竟是如何依賴媒介及媒介資源與社會體系發生互動、滿足需求、達成自我目標。因此,打造互聯網絡媒介傳播體系,將城市與鄉村形成捆綁式經濟體,帶動地方區域經濟發展與文化品牌的傳播。目前,國內各鄉鎮在論述中均有提及傳播媒介,形成有效傳播力,但較少有從傳播媒介的系統、智媒的視角分析鄉村文化品牌多維度傳播的方法和路徑。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中就指出“聚焦產業促進鄉村發展”,河北省鄉村振興局提出“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接續推進鄉村振興”。
一、鄉村文化品牌的內涵
鄉村文創品牌主要是針對區域質量獨特且品質較高的產品類,因缺失文化品牌的建構無法助力其走進大眾市場或銷售平臺,文章通過鄉村振興與打造鄉村文化品牌傳播價值的關鍵時機,通過媒介傳播平臺的互聯互通,增加大眾對鄉村特色文化了解的附加值,形成域特色文化品牌及相關品類來助推品牌強農。如:江西萍鄉武功山“綠色春茶”、山東威海“文登西洋參”、江西吉安“萬福田田菜”、河北“灤南蝦油”“灤南蝦醬”產品、邯鄲白蓮藕、張家口“崇禮彩椒”、河北安平特色種植產業等。
有觀點指出鄉村文創品牌包含三個層面的內容:首先,突出鄉村區域特色,挖掘并保持原鄉文化的特質和形象,如河北省新河打造的“一村一品”;其次,是形成市場競爭效應,即能夠在同品類市場競爭中走品牌興農、品牌強農的發展道路,通過市場占有率贏得客戶的心智,如陜西富平曹村鎮持續走強農、惠農、富農的政策發展;再次,是提升鄉村品牌空間、營造國際農特產品輸出、探索創新合作路徑。如四川省精心打造出《川字號》農產品品牌,納溪特早茶、浦江雀舌等為中國建立區域農特產品增加了驅動力,逐步實現鄉村文化品牌對鄉風文明的促進作用。
隨著后疫情時代與互聯網經濟的快速迭代,使得鏈接移動媒介平臺兩頭的供應方與需求方加快了對于鄉村特色農產品、特色果蔬類衍生產品以及具有鮮明文化屬性的文創產品開發已經進入了普通家庭生活消費的視野。從2019年《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可以看出,鄉村文化品牌與數字媒介傳播產業就已經開始共創共融。“互聯網+”以及5G基站的建設已經將移動媒介資源帶入鄉村,逐漸成為夯實鄉村文化建設的基礎,對挖掘優秀鄉村文化資源;貫徹數字經濟理念,開展農村文化產業經營活動,打造鄉村文化品牌建立了良性循環帶。
二、鄉村文化品牌的傳播意義
1.資源的平臺化拉近了鄉村與城市之間的距離
鄉村文化的民俗建設與藝術資源豐富,促進城鄉循環有序的發展需要借助平臺資源進行有效信息整合。溯源對于鄉村文化來說具有本質意義,為進一步挖掘鄉村本土多元價值,聚焦產業促進鄉村發展提供思路。互聯網平臺對于鄉村居民影響力逐漸提升,在積極推進電子商務平臺進鄉村的行動中,有效實施“數商興農”工程,將優培的農產品品類實現文化品牌的高品質、高標準化。2014年,微信在農村興起,農戶通過多媒介平臺打造互聯互通的鄉村文化傳播載體,多路徑資源平臺的建設是鄉村文化產業發展的基礎和前提,依托互聯網平臺形成信息傳播的直接輸出口,有效連接鄉村與城市的多端同頻傳播,一方面為城市游子關注家鄉動態,了解鄉村發展動態實時呈現;另一方面使得鄉村文化通過二次傳播,為鄉村文化品牌擴大了影響力,為國家大力發展數字鄉村建設、推動智慧鄉村賦能。
2.尋找鄉村文化的母體,建立起品牌符號系統
鄉村文化品牌依托天然的地理優勢、優沃的文化資源、藝術以及生態宜居振興的基礎上營造出品牌屬性,這一系統將傳遞出鄉村文化母體的對內歸屬感和對外傳播影響力。對于品牌來說,它是企業的文化資產,是一套符號系統。如西貝莜面,從初期定位西北菜,文化母體是西北農村,因此在整個店面、品牌的符號系統都是西北農村形象,經品牌升級后的西貝文化內涵是“I LOVE 莜”,整個品牌符號的文化母體發生了改變,具有了信息符號傳播時尚屬性。所以鄉村文化品牌的符號體系需要具備信息可識別、可記憶的溝通力。一直深耕于鄉土文化的獨特區域,嘗試將農產品帶入市場,通過產品定位、目標人群分析、銷售區鏈傳播等建立起鄉村文化品牌,繼而能夠形成品牌的自傳播與自運行,這一過程極大了增顯鄉村地方特色、地方風格和區域精神,推動鄉村的生態文明建設。
文化品牌塑造的過程中,品牌概念的生成并不僅僅來自生產制造者的觀點。它讓我們更容易進入消費者世界,了解消費者的想法。我們要創造的是需要讓人們記住的鄉村文化符號,怎么選擇品牌最典型的特征呢?首先就是建立品牌符號系統,實現產品在社會使用中的意義疊加。符號學原理:任何一個符號解釋都會向多方向衍生,解釋者不同,得出完全不同的意義。有時候符號解釋的歧義越多越好,開放性越大,品牌符號建設帶來的空間就越大,反之,品牌符號就喪失了開發平臺。符號表意,是一個開放的過程,人類文化活動的多義性由此而來。
3.多平臺媒介互聯傳播,有利于鄉村文化品牌產業化發展
文化品牌的訴求與媒介傳播為鄉村打開了市場平臺,使得一部分區域由被動變為主動,因此媒介平臺在服務多元受眾的同時,應思考并加強對傳播另一端人群的關注度,構建互聯網媒介平臺精準服務的可行性。特別適用于極具本土地域特色且質量較高的產品,因缺失文化品牌的關系無法助力進入市場產業化。
通過多平臺媒介的互聯傳播,能夠為鄉村振興在產業方面的互動與融合帶來促進作用,這一路徑為鄉村文化奠定基礎的同時也贏取客戶的心智。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是為大眾明確了鄉村文化品牌的核心價值;其次,鄉村文化需要進入大數據平臺,助力傳播優質原鄉文化產品與品牌,多媒平臺資源空間的拓展,是實現傳播的全鏈覆蓋的前提;再次,鄉村文化品牌從依托互聯網平臺到線下實體產業的綜合發展體系形成良性循環,從產品到服務以滿足不同消費者的多元需求。
三、鄉村文化品牌傳播媒介系統的發展演化
在1976年由鮑爾·洛基奇和梅爾文·德弗勒提出了媒介系統依賴理論。全球信息數據網絡化的加速,使得原有的媒介系統由單維轉向“混合媒介系統”(Hybrid Media System),每一個現代人都在進行大量的傳播活動,不論是面對面的溝通或是通過介質等大眾傳播載體,核心都是在尋找并獲得信息。“媒介”概念是一個多學科、跨專業的領域,文化品牌的大眾傳播需要“媒介”思維。鄉村文化品牌媒介傳播方法也要做出相應改變。目前更有學者認為,互聯網的聯通使得鏈接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成了手機端、PC端、APP平臺的即時信息傳播,把“永久在線”(Permanently Online)視為互聯網媒介傳播時代的變革屬性。媒介系統在“信息場”的大環境中,為鄉村文化品牌搭建創新、創業平臺提供了動力。
1.傳播媒介工具塑造的轉維認知
馬歇爾·麥克盧漢提出關注作為傳播工具的媒介本身,也就是媒介即信息。而傳播學的視角只是把媒介作為傳播的工具和渠道,對傳播內容給予強烈的關注。但從發展關系中看到關鍵內容是媒介本身不斷的發展和變化。伊萊休·卡茨(Elihu Katz)也從傳播學理論看到重要改變在于:“大部分的傳播研究皆致力于調查這樣的問題——媒介對人們做了什么,而如果將研究的問題轉換成——人們用媒介做了什么,整個傳播研究的面貌就會改觀。”我們在塑造工具的時候,工具也在塑造我們,轉維認知拓寬了傳播媒介的內在屬性。
2.文化品牌與傳播媒介共創數字化鄉村平臺
媒介融合的時代下,人們已經習慣了不再僅僅通過單一的形式來獲取知識和數據,而是通過音視頻、文字、APP平臺客戶端、網絡直播交叉、短視頻等獲取信息,這些新媒介技術在逐漸塑造我們的行為習慣。鄉村具備互聯網和移動端的大數據記錄:我國農村網民規模已達到2.84億。媒介的變化,對人們的組織方式、思維方式、行動方式都會產生持續的影響。鄉村文化想象的源代碼助推互聯網數字平臺,反饋真實鄉村帶動經濟發展,如鄉農通過短視頻、APP以及兩微一端創造并分享一手的鄉風生活、鄉景美食和生活態度,在帶來了數據流量的同時也積極為鄉村發展創造了價值。
數字平臺上的內容融合已逐漸市場化,以山東煙臺蘋果、湖北洪湖蓮藕等一大批農產品成為電商媒介傳播的“爆款”,為建立鄉村文化品牌、搭建農產品流通新平臺拓寬了道路。第三產業將與第一和第二產業深度融合,作為信息時代的游牧民族,不斷通過各種方式采集資源,進而為鄉村文化多媒同傳、共創建立品牌和服務。
3.品牌媒介傳播提供鄉村文化創新循環
受眾3.0后大眾傳播時代,媒介從口碑傳播,到報紙廣告,電視廣告,互聯網廣告,社交媒介宣傳發展,順應時代和經濟的發展,受眾從視覺和聽覺雙重感官循環延伸,傳播的速度和廣度大大增加,在時間和空間上都具有顛覆性的突破。對于鄉村這一獨特的地域空間文化,首先,視覺形象系統的傳播需要更具情感性和識別性,明確新時代品牌定位的核心價值,建立信息的溝通與傳達;其次,鄉村文化品牌定位、受眾分類、營銷與流通媒介構建迭代循環,破圈嘗試新的媒介社交與傳播方式,避免信息繭房的束縛,創新鄉村文化產品在媒介傳播過程中的情感賦能;再次,發揮視覺信息傳播的優勢與功能屬性,加強互聯網智媒傳播的廣泛性、獨特性,再現麥克盧漢提出的“媒介即訊息”。
結語
綜上所述,鄉村文化品牌傳播媒介系統的發展,是社會文化、互聯網、媒介傳播、人工智能協同共融的過程;是數字媒介、視覺文化、信息傳播、印刷媒介多學科交叉共生的過程,在這個復雜的演化過程中逐漸形成自組織、自傳播的跨媒介思考,綜合化呈現媒介系統的所有權結構和消費方式。隨著文化品牌傳播媒介的深化和共創,鄉村在地特色發展將通過交互技術以及可視化、感官化設備的優化,對未來跨學科的創新媒介開發,鄉村文化品牌傳播媒介的系統將不斷更迭和豐富。受眾對于媒介傳播系統的認識也會隨之轉變,這為鄉村文化品牌的構建帶來全新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