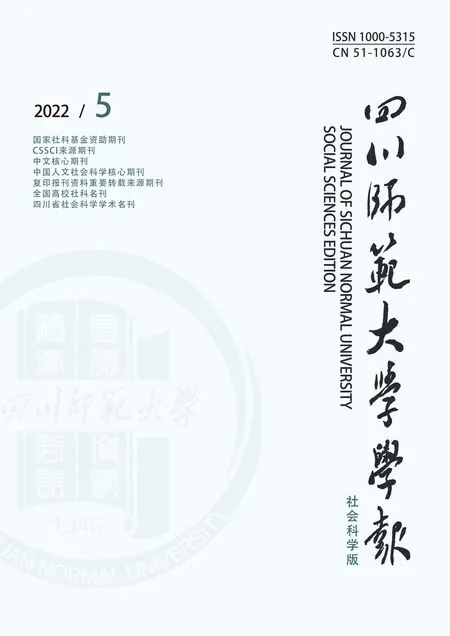社聯“馬列主義的大眾化”的意涵、指向及其能力建構
——以《社聯盟報》為重點的考察
劉愛章
目前對20世紀30年代的左翼文化團體包括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戲劇家聯盟、美術家聯盟、教育家聯盟(以下分別簡稱“左聯”、“社聯”、“劇聯”、“美聯”、“教聯”)以及電影小組、音樂小組的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其中尤以左聯研究最為充分。緊隨左聯之后成立的“姊妹團體”社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傳播史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對社聯的研究還比較薄弱,除20世紀八九十年代形成一次熱潮(1)1985年5月20日,上海市舉行了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成立55周年紀念大會。次日,舉行了紀念社聯成立55周年座談會。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編《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成立55周年紀念專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以及史先民編著《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資料選編》(中國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構成社聯研究基礎資料。史先民、任守春《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成立的意義及其歷史地位》(《史學月刊》1985年第3期),徐素華、于良華《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概況》(《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徐素華編著《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史》(中國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武克全《30年代中國社聯的活動及其歷史功績》(《學術月刊》2000年第8期),是這一時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外,其后對社聯的討論,僅散見于一些論文和著作(2)周鎏剛《社聯與馬克思主義的早期傳播——一個學術史的視角》,《觀察與思考》2016年第5期,第37-44頁。。上海市檔案館選編的“上海檔案史料叢編”之《社聯盟報》“是現今發現的左翼團體機關刊物保存最全、時間最長的一種,它的出現,對我們研究‘社聯’后期的歷史是非常有價值的文獻史料”(3)孔海珠《左翼·上海(1934-1936)》,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頁。。雖然檔案出版社1990年5月就出版了《社聯盟報》,但是鮮見學界對它的深入挖掘和利用。本文以1933年下半年社會科學研究會(簡稱“社研”)并入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改稱中國社會科學者聯盟(簡稱仍為“社聯”)為界,將1930年5月20日成立、1936年春解散的社聯的歷史劃分為社聯前期和社聯后期兩個階段,以《社聯盟報》為重點,探析社聯“馬列主義的大眾化”的多重意蘊。
一 社聯“馬列主義的大眾化”的來龍去脈
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大眾化”是一個流行語,這與左翼文化團體對大眾化的重視和宣揚直接相關,其中左聯對大眾化的討論最為熱烈,由此,“文藝大眾化”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一個重要論題。社聯則直接提出了“馬列主義的大眾化”口號并為此開展了一系列活動。
(一)“大眾化”:從革命文學到馬克思主義
“大眾化”的討論肇始于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倡導初期。1926年4月13日,郭沫若在廣州寫成《革命與文學》一文,其中寫道:“文學是革命的函數。文學的內容是跟著革命的意義轉變的,革命的意義變了,文學便因之而變了”,身處革命時代,青年“應該到兵間去,民間去,工廠間去,革命的漩渦中去,你們要曉得我們所要求的文學是表同情于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學,我們的要求已經和世界的要求是一致,我們昭告著我們,我們努力著向前猛進!”(4)郭沫若《革命與文學》(1926年4月13日),《創造月刊》1926年第1卷第3期,第7、11頁。該文發表在《創造月刊》第1卷第3期。后期創造社大力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其先鋒李初梨認為:郭沫若該文“是在中國文壇上首先倡導革命文學的第一聲”(5)李初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1928年1月17日),《文化批判》1928年第2號,第3頁。。1928年初,后期創造社、太陽社對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宣揚遭到梁實秋的反對。同年6月,梁實秋在《新月》第1卷第4號上刊文指出:“大多數的文學”是矛盾的、沒有意義的名詞,“大多數就沒有文學,文學就不是大多數的”,“無論是文學,或是革命,其中心均是個人主義的,均是崇拜英雄的,均是尊重天才的,與所謂的‘大多數’不發生若何關系”(6)梁實秋《文學與革命》,《新月》1928年第1卷第4號,第6、8頁。。同年9月20日,已經脫離創造社的郁達夫主編的《大眾文藝》創刊,郁達夫在該刊發表《大眾文藝釋名》一文提出:“文藝是大眾的,文藝是為大眾的,文藝也須是關于大眾的”,但是“文藝應該是大眾的東西,并不能如有些人之所說,應該將她局限隸屬于一個階級”(7)郁達夫《大眾文藝釋名》(1928年8月),《大眾文藝》1928年第1期,第1-2頁。。對此,后期創造社成員彭康撰文批評說,郁達夫所謂“大眾”是以“小我”為出發點的,并且用“小我”偷換了“普羅列塔利亞”的概念(8)彭康《革命文藝與大眾文藝》,《創造月刊》1928年第2卷第4期,第118頁。。
1929年3月,其后成為社聯盟員的杜國庠(署名林伯修)在《海風周報》1929年第12號上發表了《1929年急待解決的幾個關于文藝的問題》一文。他寫道:“普羅文學,它是普羅底一種武器。它要完成它作為武器的使命,必得要使大眾理解;‘使大眾愛護;能結合大眾底感情與思想及意志,而加以抬高。’這是普羅文學底實踐性底必然的要求;同時,也是普羅文學底大眾化問題底理論的根據。因為普羅文學,如若不能達到使大眾理解底程度——大眾化,它便不能得到大眾的愛護,便不能結合大眾底感情與思想及意志而加以抬高;又怎能夠戰勝資產階級文學而從它的意德沃羅基底支配之下奪取大眾呢?”(9)林伯修《1929年急待解決的幾個關于文藝的問題》,《海風周報》1929年第12號,第5頁。從掌握的資料看,該文是最早提出“大眾化”概念的文章。而《大眾文藝》則成為討論文藝大眾化的一個重要平臺,該刊1929年11月出版第2卷第1期(主編自此改為陶晶孫)(10)姚辛編著《左聯詞典》,光明日報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頁。,在左聯成立前,該刊組織過“文藝大眾化的諸問題”筆談(11)姚辛《左聯史》,光明日報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頁。。魯迅曾在1930年3月出版的《大眾文藝》第2卷第3期上發表《文藝的大眾化》(12)魯迅《文藝的大眾化》(1930年3月),《大眾文藝》1930年第2卷第3期,第639-640頁。一文。
1930年3月2日左聯成立后,它還設有文藝大眾化研究會(又稱大眾文藝委員會),其任務是研究文藝大眾化的理論,創造大眾化的文藝作品,開展對反動大眾文藝的批判,組織領導工人夜校和群眾讀書會、讀書班,推進文藝大眾化運動等,鄭伯奇、吳奚如、何家槐曾先后擔任該委員會主任,艾蕪等參加過有關工作(13)姚辛《左聯史》,第8頁。。左聯成立后,《大眾文藝》編輯部舉辦過一次“文藝大眾化座談會”、兩次“我希望于大眾文藝的”筆談,形成了文藝大眾化問題討論的第一次熱潮。1932年夏、1934年夏秋,又分別形成了文藝大眾化問題討論的第二、第三次熱潮,當然每次討論的側重點有所不同(14)茅盾《文藝大眾化的討論及其它》(1980年11月2日),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545-555頁。。
先期成立的左聯關于文學(文藝)大眾化討論的風潮,不能不對隨后于1930年5月20日成立的社聯有所影響:社聯、左聯均與后期創造社存在承繼關系,而后期創造社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倡導者,對大眾化有自己的主張;而且,左聯成立時加入的社會科學家較多,經中共中央同意,社會科學家從左聯中分離出來,單獨成立了社聯(15)姚辛編著《左聯詞典》,第79頁。,社聯盟員杜國庠等對大眾化問題就有著深刻的見解。
社聯成立后不久公布的社聯綱領規定了五項主要任務,其第二項、第四項分別是:“研究并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使它普及于一般”,“有系統地領導中國的新興社會科學運動的發展,擴大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16)新思想社編輯部《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底成立及其綱領》,《新思想月刊》1930年第7號,第6頁。。這兩項任務實際上已經賦予了“馬列主義的大眾化”以具體內涵。
(二)從瞿秋白“馬列主義的科學大眾化”到社聯“馬列主義的大眾化”
1931年秋,左翼文化運動的實際領導者瞿秋白,在為中央文委起草的文件《蘇維埃的文化革命》中,首次提出了“馬列主義的科學大眾化”。在這篇關于大眾化理論的重要文獻中,瞿秋白闡述了四個重要觀點。
其一,中央文委的任務是“在文化戰線上,動員廣大民眾來參加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工農蘇維埃革命”。這實際上就是要發動和領導蘇維埃的文化革命。“這種革命的文化運動,必須是勞動民眾自己的文化革命”,因此,“革命的文化運動的大眾化,就是目前最重要的中心問題”。
其二,蘇維埃的文化革命對革命文化團體包括社聯提出的總體要求是“為著文化運動的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而斗爭”,在白色區域“開展革命的普洛的教育運動”。為此,在白區需要“利用和爭取一切公開的可能,發動‘平民教育運動’和識字運動”,“在大眾之中,反對一切宗教迷信以及資產階級的科學和哲學理論,而進行馬列主義的科學大眾化的運動”。
其三,“馬列主義的科學大眾化的運動”“必須和大眾的斗爭以及日常生活聯系起來”。為此,應該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宣傳到廣大的群眾之懷”。這就需要“有系統的有計劃的艱苦的工作”,“在群眾之中建立鞏固的組織上的基礎”和“從工人群眾之中鍛煉出文化運動的干部”。
其四,要反對“‘左派’機會主義和對于機會主義者的調和態度”,反對“對于大眾化路線的怠工”,反對“學究主義和小團體主義”(17)瞿秋白《蘇維埃的文化革命》(1931年秋),《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7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231頁。。
經過瞿秋白“馬列主義的科學大眾化”相關論述,“馬列主義的大眾化”這一更為簡化的提法已是呼之欲出。實際上,省去“馬列主義的科學大眾化”中的“科學”二字,不僅僅是簡化而已,“馬列主義的大眾化”默認了一個前提:“馬列主義”是“科學”。1933年5月1日出版的《社聯盟報》第4期,較早明確使用了“社會科學之大眾化”(18)《上海總會過去三個月的工作檢查與今后三個月的計劃》(1933年5月1日),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3頁。的提法;1934年5月出版的《社聯盟報》第15、16期合刊,最早使用了“馬列主義的大眾化”提法,且出現在標題中:《編輯部的工作計劃與工作報告——為馬列主義的大眾化而斗爭》(19)杜生《編輯部的工作計劃與工作報告——為馬列主義的大眾化而斗爭》(1934年5月),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頁。。此后,“馬列主義的大眾化”多次出現在《社聯盟報》中(20)例如《七、八、九三個月的工作計劃大綱》在篇末提出了三個口號,第二個即為“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眾化而斗爭!”參見:《七、八、九三個月的工作計劃大綱》(1934年6月20日),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頁。,并有具體的任務安排。
(三)社聯“馬列主義的大眾化”的多重內涵
社聯所指的“馬列主義的大眾化”,具有多方面的內涵。如果把“馬列主義的大眾化”理解為有意識地在社會大眾中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那么,自社聯成立時起,“馬列主義的大眾化”就已走向自覺,社聯本身就是中共推進“馬列主義的大眾化”的產物。但是,1931年瞿秋白就已提出“馬列主義的科學大眾化”,社聯前期的刊物并未把它作為口號明確提出,直到1934年,社聯后期的內部刊物才提出“馬列主義的大眾化”并經常使用,“馬列主義的大眾化”應有其他所指。《社聯盟報》雖未對“馬列主義的大眾化”作出理論上的闡釋,但是從社聯后期的一系列實踐活動中,還是能夠概括出“馬列主義的大眾化”異于以上所述的新內涵。
其一,就研究和介紹馬克思主義的主體而言,在中共上海組織不斷遭受嚴重破壞、中共黨員人數急劇下降的情況下,社聯盟員已取代中共黨員成為馬克思主義傳播的主體力量來源。雖然不少社聯盟員同時也是中共黨員,但是直接把他們和馬克思主義傳播聯系在一起的外顯身份是社聯盟員;此外,還有一批最初未加入中共但已信奉馬克思主義并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社聯盟員。
其二,“馬列主義的大眾化”中的“大眾”指的是誰?與黨中央關于中國革命的動力“已經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21)《政治議決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379頁。的認識相適應,“大眾”乃是“工農大眾”。當時社聯還認為:小資產階級是要分化的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傾向特指錯誤的傾向,知識分子屬于小資產階級,但小資產階級是否屬于“大眾”,當時社聯在理論上并未給出答案,但在實踐中,為了使他們“接受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理論”(22)王木林《軍事訓練的意義及怎樣反對它》(1935年5月5日),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46頁。,社聯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象包括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學生。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以工農大眾為對象的“馬列主義的大眾化”中的“化”該如何實施?對此,社聯從兩方面著手:一是立足于被教育者的地位,“對象化”自己的生活,即“生活要與對象同化”,即“去接近工人,生活要工人化;去接近學生,生活要學生化;接近小市民、黃色(包)車夫,生活要小市民、黃包車夫化,才不妨礙著我們工作的進展”(23)K《怎樣做突擊工作》(1935年12月30日),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71-272頁。;二是立足于教育者的地位,即“嚴格地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闡發正確的社會科學的理論”(24)《工農教育委員會通告》(1934年6月10日),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頁。,“灌輸社會科學常識”(25)社聯工教會《工教會×××業××會教育大綱》(1934年11月24日),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57頁。這里灌輸的對象是工人。,“灌輸他們馬列主義的革命學識”(26)(社聯)工農教育委員會《關于農民教育方針的決定》(1935年6月30日),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頁。這里的“他們”指農民。,“提高工農大眾的理論水準”,“激發工農大眾的斗爭情緒”,“加強工農大眾的革命認識”(27)《工農教育委員會通告》(1934年6月10日),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頁。。在這里,社聯盟員對工農大眾既要立足于被教育者的地位,同時也要立足于教育者的地位,這個內在矛盾如果說在白區工作時還不明顯的話,那么當社聯盟員奉調到達延安在紅色區域中真正面對工農大眾時,階級出身為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包括左翼知識分子就需要重塑主體性來直面這個內在矛盾了。
二 社聯“馬列主義的大眾化”的實踐指向:與國民黨展開對青年的爭奪
國民黨當局對左翼文化運動進行了殘酷的迫害和鎮壓,包括頒布《宣傳審查條例》、《出版法》等對左翼文化書籍刊物進行限制直至查禁,派遣流氓特務瘋狂襲擊左翼文化團體,拘捕、刑訊并秘密殺害左翼分子,以及培植御用文人詆毀馬克思主義和進步的思想文化(28)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1921-1949)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369頁。,構成了國民黨政府文化“圍剿”的譜系。
1930年6月15日,時任社聯第一任黨團書記的朱鏡我寫道:“從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相繼成立以來,中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已經聯合分散的力量,集中在統一的戰略之下,開始計劃的活動,而意識地使文化運動配合到整個的革命策略之下,號召廣大的革命分子,參加實際的革命斗爭,駁斥一切的反革命的思想,而確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在文化領域上的領導權……全中國的革命分子,不敢落后的智識階級,應該站在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之下,為中國革命,為中國新文化之創造而參加斗爭,參加左翼作家聯盟或社會科學家聯盟而盡其一分子的任務!”(29)朱鏡我《中國目前思想界底解剖》(1930年9月10日),王慕民編《朱鏡我文集》,海洋出版社2007年版,第330-331頁。
朱鏡我認為,在階級斗爭尖銳化并將要達到頂點的時候,沒有中間的道路、中間的立場,因此,“誰不愿藏身在反動的營壘之中,誰就應該走進革命的陣線”(30)。朱鏡我《中國目前思想界底解剖》(1930年9月10日),王慕民編《朱鏡我文集》,海洋出版社2007年版,第331頁。在國共兩黨分野、政治“極化”的狀況下,“馬列主義的大眾化”運動是1928-1929年新興社會科學運動的繼續和發展。它圍繞使馬克思主義理論“普及于一般”,以及明確聲言,這一運動是“馬列主義的大眾化”的文化運動所采取的具體行動。這就不可避免地表現出明顯的政治意圖,具有文化反“圍剿”的性質和意義,其實質是對青年的爭奪。
對社聯而言,從使馬克思主義理論“普及于一般”到“馬列主義的大眾化”,它們之間的差異不在于要不要“大眾化”,而在于明確“大眾化”的對象后,對“大眾化”策略的靈活掌握和生動實踐。在這方面,社聯所做的工作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為青年學生編寫“新興社會科學”通俗讀物,進行讀書指導
社聯盟員柯柏年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1930年3月22日,上海南強書局首次出版了柯柏年編寫的《怎樣研究新興社會科學》一書,印數為200冊,后追加到2000冊,4個月內就銷售一空;同年8月29日,已是社聯盟員的柯柏年修訂該書并出版了增訂本,又印了2000冊。這本書(增訂本)所講的“新興社會科學”,實際上是輔以淺顯例證的“因果律”、“辯證法”。該書第一章《新興社會科學之意義》提出:“自然科學之任務,是要在自然現象中發見自然的因果律;社會科學之任務,是要在社會現象中發見社會的因果律。”(31)柯柏年編《怎樣研究新興社會科學》,上海南強書局1930年增訂版,第8頁。對此,該書闡述道,縱然“社會是由許多具有自由意志的個人構成的”,但是“社會中的個人底自由,是很有限制的;他只能在自然的條件和社會的條件所容要之限度內自由選擇”(32)柯柏年編《怎樣研究新興社會科學》,第8-9頁。。這樣,該書就借機宣傳了中國實際問題中的因果律:“自由競爭的結果,必然引起獨占”,“國際資本主義之侵略弱小民族【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必然引起弱小民族之國民革命運動”,“生產額超過需要額,必然使物價低落”,“中國關稅改用金單位,必然使物價高漲”,“外國商品之侵入中國,必然使中國的手工業破產”(33)柯柏年編《怎樣研究新興社會科學》,第11頁。等。而這些觀點,都是中共關于中國社會問題重要論斷的組成部分。
柯柏年還提出形式邏輯是舊社會科學的方法。他認為:“形式邏輯把一切事物,視做是不變動的,是互相隔離而孤立的”(34)柯柏年編《怎樣研究新興社會科學》,第11頁。。這實際上是把“形式邏輯”混同于“形而上學”。盡管存在這樣的錯誤,但柯柏年宣揚唯物辯證法為研究社會現象的高級方法則值得充分肯定,況且,他區分了唯心辯證法與唯物辯證法,介紹了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范疇、基本規律。他指出:“只有唯物論的辯證法才是正確的,只有那運用著唯物的辯證法之科學,才能把握著事物底本質。”(35)柯柏年編《怎樣研究新興社會科學》,第23頁。
柯柏年還強調,處于當時代的資本主義世界,社會科學也分化為兩大敵對陣營,“一是布爾喬亞氾的社會科學,一是普羅列塔利亞特的社會科學”(36)柯柏年編《怎樣研究新興社會科學》,第23頁。,即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和無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并稱后者為“新興社會科學”,指能夠運用唯物辯證法去研究社會現象(37)柯柏年編《怎樣研究新興社會科學》,第24頁。。此書是寫給“中學生——尤其是中途退學及無經濟能力進學校但有能力閱讀中文書的青年們——讀的”(38)柯柏年編《怎樣研究新興社會科學》,第2頁。。這種以對象為中心、以對象的可接受程度為寫作依據的撰述方法,適應了當時青年學生的文化水平和實際需要,即在動蕩不安的時空場域,通過閱讀去建構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從而錨定人生航向。
該書第二章為《自修的方法》,第三章為《自修的書目》并有附錄兩件(《英文書的書目》和《介紹最近出版的中文書》)。其從青年的實際需求出發提供具體的讀書指導,所列書目基本上都是介紹唯物史觀、唯物辯證法、剩余價值論、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等經典著作或中外馬克思主義理論名家著作編譯,在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青年學生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
從其熱銷狀況可以推定,該書得到了青年們的認可。正如馬克思所說:“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39)卡·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1843年10月中-12月中),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9頁。社聯盟員指導青年讀書,實質上是與國民黨展開的一場對青年的爭奪賽。
社聯前期,除了盟員個人層面的讀書指導外,社聯整體層面的讀書指導,突出表現在社聯創辦《書報評論》(BooksMonthlyReview)。《書報評論》,1931年1月15日出版第1卷第1期,3月1日出版第1卷第2、3期合刊,4月15日出版第1卷第4期,5月25日出版第1卷第5期,8月25日出版最后一期即第1卷第6期。1932年4月1日出版的《研究》(社聯刊物,只出一期)刊載署名為王彬的文章《社會科學的任務》,也屬讀書指導性質的論文。
社聯后期,社聯盟員柳湜、艾思奇在《申報》流通圖書館讀書指導部的工作,也屬同樣性質。《申報》流通圖書館擁有3萬讀者,其中青年學生數千人。其內設的讀書指導部,在社聯盟員主持下成為進步思想傳播的中心之一。1934年,讀書指導部主任柳湜以柳辰夫的筆名出版了《怎樣自學社會科學》一書,他在該書自序中寫道,“關于社會科學大眾化,目下實在還差得甚遠,作者今后甚愿在這方向更加努力,從事通俗編著”(40)柳湜《〈怎樣自學社會科學〉自序》(1934年3月20日),《柳湜文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728頁。,并提出了“馬列主義的大眾化”的學理性原則,即理論與實踐打成一片。就艾思奇出版的《哲學講話》,李公樸評價說:“這本書是用最通俗的筆法,日常談話的體裁,融化專門的理論,使大眾的讀者不必費很大氣力就能夠接受。這種寫法,在目前出版界中還是僅有的貢獻。”(41)李公樸《〈哲學講話〉編者序》(1935年12月),《艾思奇全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9頁。
柳湜、艾思奇面向青年的“馬列主義的大眾化”實踐,從社會效果看,起到了引導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啟蒙作用,從學理啟示看,他們已把內容和形式(尤其是語言)的通俗化置于大眾化的視野之中,從而拓寬了大眾化的內涵。
(二)開展工農教育工作的實踐
社聯后期,建立了工農教育委員會。1933年5月1日出版的《社聯盟報》第4期最早提及“工農教育工作”。社聯檢討說,該項工作“成績不好”:工人讀書班“完全塌了臺”,同年1-3月,新開展工作的只有一所包括成人和兒童共計130余人的小學校和一處與教聯共同領導的農民讀書班。社聯檢討、分析得出的原因有:參與該項工作的社聯盟員只有七八人、工農教育委員會對該項工作沒有全盤計劃、社聯盟員在開展該項工作時存在為教書而教書的傾向(42)《上海總會過去三個月的工作檢查與今后三個月的計劃》(1933年5月1日),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頁。。為了改進工農教育工作,社聯號召社聯盟員“脫去小布爾喬亞的外衣到工廠中去!到農村中去!”(43)《為工農教育工作組織工作告每個革命的盟員》(1933年5月1日),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8頁。
1934年6月19日,社聯組織部對其盟員結構的分析顯示:在全部200位社聯盟員中,學生盟員占50%、有100人,工人盟員只有6人,沒有農民盟員。這還是社聯常委會檢討工農教育工作1年后的盟員組成狀況。社聯滬西區指出,“或是因為生活習慣的隔閡,或是因為語言的障阻,或是因為經驗的不夠,或是因為方法的缺乏”(44)《滬西區四、五兩月工作的檢討》(1934年6月),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119頁。,學生盟員占主體而工、農盟員又極少的社聯,工農教育工作極其落后。但同時,社聯認為“工農教育的工作是社會科學大眾化主要的任務”(45)(社聯)工農教育委員會《工教的工作檢查與今后計劃》(1934年11月24日),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頁。,社聯負有“把馬列主義底社會科學的理論,深入到工農大眾里去”(46)《工農教育委員會通告》(1934年6月10日),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頁。的使命,社聯為完成該項使命提出了諸多設想。
其一,社聯工農教育委員會提出,向社聯各級組織和全體盟員征稿編印工農讀物。其書目有:“(一)國民黨為什么不打日本(在印刷中)。(二)怎樣才能得到新生活?(三)中國的工農。(四)蘇聯的工農。(五)階級與政黨。(六)資本是從那里來的?(七)我們需要怎么樣的工會?(八)農村為什么破產的?(九)怎樣才能復興中國農村?(十)果真有‘神’嗎?”并且工農教育委員會已經注意到編印工農讀物中的語言文字問題,提出“文字須求通俗,竭力避免術語的應用,最好多舉實例來驗證理論”(47)《工農教育委員會通告》(1934年6月10日),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9頁。。
其二,社聯著力批評了“替工農說話,讓工農說話”的計劃僅僅停留于決議的情況。指出,工農教育工作不只是工農教育委員會的工作,而是社聯全體盟員的工作,并提出要對工農分子“灌輸”社會科學的基本常識(48)(社聯)常委會《常委會關于工農教育的決議》(1934年11月24日),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54-55頁。,以及強調實行“灌輸”的前提是提高工農大眾的革命文化水準(49)(社聯)工農教育委員會《工教的工作檢查與今后計劃》(1934年11月24日),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頁。,對農民而言,首先還得向他們的封建意識進攻,這就要用自然科學的常識來破除他們的迷信和保守性(50)(社聯)工農教育委員會《關于農民教育方針的決定》(1935年6月30日),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83-84頁。。
社聯后期,對工農教育工作方面提出的一系列設想符合“馬列主義的大眾化”的要求,但是工作實績很小。1935年初,社聯盟員中工人盟員占比雖然一時達到了1/5,但同時社聯卻流失了一些學生盟員,署名為“璘”的社聯盟員反思說:“知識分子參加革命大多從思想出發,同時知識分子的生活中的小資產階級的殘渣,更須要深刻的認識來洗刷,并且要說服一個同學是需要較高的理論的。”(51)璘《怎樣開展學生運動》(1935年2-4月),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32頁。相比較而言,社聯在以青年學生為對象的“馬列主義的大眾化”的實踐中實績很大,同時它留下了大眾化的學理啟迪,而在以工農大眾為對象的“馬列主義的大眾化”的實踐中實績雖小,但它也留下了開展工農教育工作的閃光思想。
三 社聯“馬列主義的大眾化”的能力構建:加強自身建設
社聯不斷加強自身建設是其具備“馬列主義的大眾化”能力的基礎。由于反映社聯前期自身建設的資料匱乏,這里的研究集中于社聯后期的自身建設,其史料基礎是《社聯盟報》(1933年5月1日-1935年12月30日)。由于社聯成立時就制定了明確的綱領,這一綱領基本貫穿了社聯始終,因此社聯后期的自身建設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反映出社聯自身建設的整體內容。其自身建設包括思想理論建設、宣傳能力建設、基層組織建設以及作風建設等四個方面。
(一)思想理論建設
社研并入社聯,其積極影響是社聯盟員人數大幅增加,聲勢得以壯大;消極影響則是大部分社聯盟員理論水平不高。1933年5月1日出版的《社聯盟報》,刊載了《上海總會過去三個月的工作檢查與今后三個月的計劃》。社聯在工作檢查中指出:“馬克斯紀念特刊按其性質說,是社聯應該負起主要責任的工作,但是社聯對于這一工作事前沒有全體的計劃,只分配七八篇文章,而這些文章多半是經過三催四催甚至催到十幾遍,遲了一多月才交來。”(52)《上海總會過去三個月的工作檢查與今后三個月的計劃》(1933年5月1日),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頁。這其中固然有其他原因,但最根本性的原因,是當時多數社聯盟員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不高。
1934年5月30日,社聯一位盟員坦率地指出“盟員的理論水平低下”,提出“提高理論的水平,使各個人的認識漸漸趨向一致”的任務(53)(社聯)一盟員《關于研究部的工作計劃的一個私見》(1934年5月30日),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190頁。。同年6月出版的《社聯盟報》刊載了社聯滬東區自我檢討的文章,其中寫道,個別盟員“要他看書等于要他的命”,“無系統的看書,不能在最短時期內獲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髓”(54)《檢查滬東區的工作》(1934年6月),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頁。。社聯滬西區也尖銳地指出,盟員“對于學理的研究,多皆忽視”(55)《滬西區四、五兩月工作的檢討》(1934年6月),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119頁。。
同年12月25日,社聯常委會《關于召集各種研究班的決議》發表,其中也自我批評道,“對于盟員沒有加緊地執行教育工作,沒有計劃地提高理論水準”(56)(社聯)常委會《關于召集各種研究班的決議》(1934年12月25日),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64-65頁。。該決議寫明,在“不少的忠實而勤勉的盟員同志,要求加強研究工作”的情況下,社聯常委會決定召集各種研究班,其一,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自己,“在理論活動上獲得馬列主義的正確理解,建立理論斗爭的堅固堡壘,不僅要嚴格檢查自己的認識,不容許有理論上的偏向,而且還要對于有傾向的理論進攻”;其二,盟員之間相互學習共同提高,“對于本組的同志,應該隨時把握具體的事實,給以理論上的訓練。同時,對于其他小組的研究工作,還要在可能范圍內予以指導。懂得多的講解給懂得少的同志聽,懂得少的應該去問懂得多的同志。盟員對盟員都是同志,要講組織的友愛,互相教育,互相批評”(57)(社聯)常委會《關于召集各種研究班的決議》(1934年12月25日),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65-66頁。。
為努力提高盟員的理論水平,社聯常委會認為,首先應召集研究班。其包括政治研究班、經濟研究班和哲學研究班,各研究班有各自的研究題目。以哲學研究班為例,應研究“一般意識形態。現代哲學——法西斯——新黑格爾——中國反對派的哲學根據。基本法則。哲學史”。社聯常委會還打算召集列寧主義研究班、組織問題研究班和婦女問題研究班(58)(社聯)常委會《關于召集各種研究班的決議》(1934年12月25日),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第66、67頁。。
(二)宣傳能力建設
其一,建立社聯出版部。社聯在1933年5月前沒有自己的出版部,在出版馬克思列寧主義文獻上存在“極度的困難”。因而打算自同年5月起,在3個月內建立起出版部,公開營業,資本金2000元向社聯內外募集,“對現有馬列主義文獻作一詳細調查”并出版小叢書(59)《上海總會過去三個月的工作檢查與今后三個月的計劃》(1933年5月1日),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頁。1934年5月,社聯編輯部制訂了出版小叢書的具體計劃,“分為基礎理論與實際問題兩部”,“基礎理論”包括:唯物辯證法、歷史的唯物論、經濟學、帝國主義、第三期、政治理論。“實際問題”包括:中國經濟問題、中國農業問題與農民運動、今日之太平洋問題、白銀問題、法西斯運動、蘇聯的建設。共12類。參見:杜生《編輯部的工作計劃與工作報告——為馬列主義的大眾化而斗爭》(1934年5月),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4-25頁。。后來,該出版部成功建立,時間不晚于1934年6月(60)《出版部通告》(1934年6月),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7-28頁。。
其二,交流出版壁報、標語經驗。在20世紀30年代,壁報、標語等屬于當時代大眾傳播的重要媒介。對此項工作,社聯組織提出了明確而細致的要求。其指出:公開壁報“黨派色彩不宜過度明顯”,“編輯的方法到裝潢一點也不可馬虎了事,使人不〔都〕想去看”,秘密壁報“根據我們宣傳的提綱與口號單進行,并且與當地實際情形聯系起來”,壁報要貼在“惹人注目的地方”,貼好后“最好叫一個自己的人去用驚奇的眼光去讀,以引人去看,并且觀察看報的人的態度,再利用另一方式去宣傳他組織他”,從這個意義上說,宣傳也是一種發展組織的方式,“貼在工廠附近和農村里的壁報,文字要通俗有趣,每句話都要合乎他們的要求”(61)《加緊標語壁報的工作》(1933年5月1日),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1頁。。至于標語,一要注意內容,能吸引群眾注目;二要注意地點,選擇白天路過人多的地方;三要選擇地方,抬頭即可望見,同時字要大(62)L·P《寫標語的一點經驗》(1935年12月30日),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66-267頁。。1935年1月15日出版的《社聯盟報》第23期,刊出了社聯盟員沈定華(署名“靜”)《怎樣建立壁報出版刊物》(63)靜《怎樣建立壁報出版刊物》(1935年1月15日),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06-213頁。的長篇報告,對提高社聯盟員的宣傳能力具有直接指導價值。
其三,打入中間地帶的刊物。這突出表現在社聯后期上層人物的活動中,比如社聯盟員艾思奇、柳湜進入《申報》流通圖書館讀書指導部工作;艾思奇、鄧拓等在中間地帶的刊物《中華月報》(國民黨汪精衛派系出版的刊物)、《新中華》(中華書局主辦)上公開發表文章。
(三)基層組織建設
社聯前期的組織機構(64)《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簡章》(1930年7月25日),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編《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成立55周年紀念專輯》,第251頁。如表1所示。社聯后期,其組織機構發生變遷,呈現出條塊分割的結構特點。從社聯行政領導機構看,1932年二、三月間,社聯第二次全體盟員大會開除了社聯首屆主席鄧初民的盟籍,從現有資料看,其后社聯不再設主席一職。社聯后期在行政上實行集體領導制度,設有常委會,其第六、七、八任黨團成員如何通過兼任職能機構如社聯宣傳部部長等職務,來組成常委會,還有待研究。社聯在北平、廣州、日本東京等地設有分盟,它們與上海社聯的具體關系,也有待研究。
根據《社聯盟報》提供的情況,從橫向看,社聯常委會下設的專門部有組織部、宣傳部、財務部、研究部、編輯部、出版部以及工農教育委員會;從縱向看,社聯在上海設有總會,下設滬東區(簡稱東區)、滬南區(簡稱南區)、滬西區(簡稱西區)和第一直屬分會,社聯各區由社聯各區區委會領導,各區區委會設有書記一職。各區所屬盟員一般編入第幾小組或區第幾分會,有時某幾個小組合成區第幾分會,這樣社聯小組或社聯某區第幾分會或零散未編入小組的盟員就成為社聯的基層組織。

表1 社聯前期的組織機構
社聯的基層組織是社聯開展各項活動的組織依托,其建設的主要內容有:通過間接宣傳(出版壁報、書寫標語、編辦雜志等)或直接與民眾交談發展社聯外圍組織(如讀書班、識字班、俱樂部、座談會、兄弟團、姊妹團、同鄉會等(65)(社聯)常委會《常委會關于工農教育的決議》(1934年11月24日),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55頁。),并在條件成熟時,將外圍組織中的成員“提拔”為社聯盟員;開會進行形勢分析或理論研討,形成堅決支持蘇維埃、支持紅軍的立場和觀點,努力撰寫相關論文;推銷社聯出版的書籍報紙,繳納盟費、募捐或特捐,“對財政要有積極的關心,對聯盟要表示物資的忠實”(66)《財務部為募集出版基金告全體盟員同志》(1934年6月20日),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43頁。,等等。社聯組織并強調,需要研究“如何使組織德模克拉西化;如何提拔新干部;如何執行自我批判,克服機會主義和官僚主義”(67)田靜《為組織活動的合理化而斗爭》(1934年5月25日),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187頁。,不斷加強社聯基層組織建設,“小組里好比一個龐大的富裕的礦山,須要我們去開采。如采得法,可獲得不少的比寶石更貴的產物”(68)李璘《給常委會一封公開的信》(1935年2-4月),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19頁。。
社聯前期盟員規模:社聯,1930年5月成立時共有盟員40余人,1933年5月之前為120余人;社研,1930年冬成員約有二三百人,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約為一千二三百人。1933年下半年社研并入社聯時,兩組織均已遭到較嚴重破壞。
社聯后期盟員規模:社聯滬東區,1934年6月,57人,10月,38人;社聯滬南區,1934年3月初,36人,4月6日前,10人,5月,32人,7、8月間,19人;社聯滬西區,1934年4月,24人,4月底,19人,6月,28人,12月底,37人;社聯第一直屬分會,1935年1月,10人。(69)資料來源: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綜合了該檔案第二部分“社聯各區分會的工作計劃和報告”提供的盟員人數信息。參見:《社聯盟報》,第117、121、123、150-151、104、107、114-115、118、123、136、150-151頁。
1934年6月19日,社聯組織部提交的《組織部的自我批判》一文,對社聯組織狀況作了如下分析:“現在我們檢查自己隊伍的構成分子,得出百分比率如下:學生50%,職員35%,失業者10.5%,工人3%,作家0.5%,教授0.5%,兵士0.5%”(70)《組織部的自我批判》(1934年6月19日),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195頁。,社聯的外圍團體有抗日會2個、讀書會4個、研究會2個、兒童團1個、婦女會1個、工人班2個、補習學校1個,全部人數54人。該文并稱,這個數字不及社聯盟員人數的1/3,參照社聯各區分會人數情況,可以推斷,這個時間節點社聯盟員人數約為200人。
(四)作風建設
作風建設最鮮明的特點有二。
其一,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無論是社聯的專門部,還是社聯在上海的四個分會(包括它所屬的基層組織),其制定和完善工作計劃、檢查和總結工作計劃完成情況是社聯開展工作的一項基本制度。工作計劃和總結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自我檢討,在國民黨文化“圍剿”的嚴峻形勢下,進行自我檢討、不斷改進工作,是社聯存在和發展的必然要求。如1934年6月18日,社聯研究部在《社聯盟報》第17期上發表《研究部底自我批判與工作計劃——為擴大強化馬列主義的思想武裝而斗爭》一文,對自己的工作進行的自我批評(71)《研究部底自我批判與工作計劃——為擴大強化馬列主義的思想武裝而斗爭》(1934年6月18日),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2頁。;同年6月,社聯滬西區在《社聯盟報》第17期上發表自我批評文章《滬西區四、五兩月工作的檢討》(72)《滬西區四、五兩月工作的檢討》(1934年6月),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121頁。,并且毫不客氣。再如社聯某盟員WS《給盟報編者的一封公開信》,一連指出《社聯盟報》編者在編輯第15、16期盟報中的六個缺點,其中包括社聯常委會公開信排版靠后,從而減少了盟員對它的注意力。此外,還批評社聯盟報對“歐化、日本化的字句”不加改正等(73)WS《給盟報編者的一封公開信》(1934年6月),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196-198頁。。應該說,這些批評從現在看來也是很有見地的。
其二,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社聯開展各項工作具有鮮明的現實政治指向,這就決定了它將一以貫之地遵守社聯綱領中“理論與行動的合一”的原則。社聯盟員沈定華在《怎樣建立壁報出版刊物》一文中提出:“我們的壁報或刊物,對于各種反革命派別的欺騙及武斷宣傳,應成為一個有力的輕騎隊。”(74)靜《怎樣建立壁報出版刊物》(1935年1月15日),上海市檔案館編《社聯盟報》,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13頁。從《社聯盟報》看,這項原則在社聯專門部和四個分會中得到了很好的貫徹。但是真理向前跨越一步就是謬誤,理論聯系實際時注重實際是應當的,但是要更好地做到理論聯系實際,就必須首先掌握好理論,這里指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總體而言,社聯領導層在這方面的優良作風是值得借鑒的,社聯基層在一定程度上過于重視實際的偏差是能夠理解的,這是與他們相對較低的文化水平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聯系在一起的。
四 結論:以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推進理論創新和理論武裝
1940年1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發表講演時指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兩種反革命的“圍剿”即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也有兩種革命的深入即農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其結果是兩種“圍剿”都慘敗了,其中最奇怪的是,“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的一切文化機關中處于毫無抵抗力的地位,為什么文化‘圍剿’也一敗涂地了?這還不可以深長思之嗎?”(75)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02頁。
社聯作為“革命文化團體”具備文化團體屬性,但其根本宗旨是“革命”——以文化為手段、以工農大眾為對象、以推進中共領導的革命斗爭為旨歸。社聯的理論論爭和實際斗爭都具有鮮明的政治指向:反對國民黨的文化“圍剿”,動員廣大民眾參加農村革命,客觀上形成了農村武裝斗爭和中共白區工作包括左翼文化運動相互支撐的工作格局。毛澤東認為:“革命文化,對于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準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戰線中的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這個文化戰線上的各級指揮員。”(76)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08頁。在這個意義上,應該充分肯定社聯及其“馬列主義的大眾化”的歷史貢獻和地位,包括有力推動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為全民族抗日救亡運動的興起作了思想理論準備,促進了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77)史先民、任守春《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成立的意義及其歷史地位》,《史學月刊》1985年第3期,第75-76頁。。
社聯“馬列主義的大眾化”實踐具有同國民黨爭奪青年的初始動機和客觀效果,但也有其張力和限度。其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中的局限性主要有兩點。
其一,從客觀上看,一是由于國民黨當局持續的劇烈的“圍剿”,農村革命隊伍和左翼文化隊伍被分割在不同空間,相互間理論和實踐難以結合。毛澤東指出:“在‘五四’以來的文化戰線上,文學和藝術是一個重要的有成績的部門。革命的文學藝術運動,在十年內戰時期有了大的發展。這個運動和當時的革命戰爭,在總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實際工作上卻沒有互相結合起來,這是因為當時的反動派把這兩支兄弟軍隊從中隔斷了的緣故。”(78)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848頁。毛澤東對文學和藝術部門的分析,也適用于當時處于同樣環境的社聯。而突破這一局限,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到延安后與根據地人民群眾的完全結合就有了客觀可能和現實需要。二是中共通過中央文委、經過社聯黨團領導社聯,當第二次和第三次“左”傾路線在中央領導機關占據統治地位時,社聯及其“馬列主義的大眾化”理論和實踐不可避免會出現偏差,包括如何正確認識社聯盟員的階級出身構成,如何正確處理進行理論論爭與參加實際斗爭的關系。
其二,從主觀上看,一是在極為艱難的環境中,社聯組織常遭破壞,社聯盟員流動性大,具有較高理論水平的盟員會轉崗到更加重要的工作崗位,新增盟員中不少人由于文化層次和理論水平不高,在推進“馬列主義的大眾化”上存在能力不足的情況。二是社聯從其綱領和簡章上制定了高標準嚴要求,但是社聯盟員特別是新增盟員在立場、感情、話語等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其階級出身即小資產階級的影響,“馬列主義的大眾化”工作對象狹窄,社聯在組織上也存在“關門主義”傾向,“馬列主義的大眾化”的主觀目的與客觀效果之間存在明顯差距。
上述局限性中,主觀方面受制于客觀方面,客觀方面是主要的,主觀方面是次要的。
社聯在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上的歷史局限性,黨在延安時期率先實現突破。一方面,有了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正確引領。遵義會議“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新階段”(79)《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頁。。1938年10月,毛澤東提出“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他同時提出,必須摒棄“洋八股”、“空洞抽象的調頭”和“教條主義”,“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80)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4頁。。毛澤東這一重要論斷是其對中國革命最重要的貢獻之一,不僅指引抗日戰爭取得勝利,而且對指導中國建設具有深遠意義(8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二),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版,第522頁。。他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重大命題,不僅為黨的理論創新指明方向,而且其內涵包括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82)孫力、陳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機理》,《黨政研究》2021年第5期,第76頁。。其后,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等文章中,提出革命的文化工作者(知識分子)正確認識大眾化的內涵,在立場、態度、感情、語言等方面同人民群眾完全結合在一起,在普及工作的基礎上做提高工作,經過干部教育群眾、指導群眾,為大眾的動機和被大眾歡迎的效果必須統一起來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觀點,緊密結合時代特征,進一步豐富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使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沿著正確方向推進。
另一方面,從上海亭子間到革命根據地的絕大多數革命文化工作者(知識分子)主動加強主觀世界改造,努力提高自身理論水平,原社聯盟員朱鏡我、潘梓年、杜國庠、王學文、沈志遠、許滌新、何干之、柳湜、艾思奇等積極參與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加強馬克思主義學理性研究和運用,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普及,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形成與發展提供了寶貴養料和豐富素材(83)王海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經典著作編譯與傳播研究(1919-1949)》,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332頁。,留下了以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理論和實踐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經驗。
2009年11月12日,習近平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關系問題,提出其核心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84)習近平《關于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幾點學習體會和認識——在中央黨校2009年秋季學期第二批進修班開學典禮上的講話》(2009年11月12日),《學習時報》2009年11月16日,第1版。。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其第六部分《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歷史經驗》,提出“十個堅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人民至上、堅持理論創新等不僅深刻揭示了黨和人民事業不斷成功的奧秘所在,而且也深刻揭示了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根本路徑。從社聯“馬列主義的大眾化”理論和實踐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包含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并為其指明正確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揭示了黨的理論創新的內在機制;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然要求,是黨的理論武裝及時跟進黨的理論創新的必要步驟,并且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原始材料,注入不竭動力。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國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理論創新每前進一步,理論武裝就要跟進一步。由此,也就提出了理論武裝新的任務。深入研究社聯“馬列主義的大眾化”歷史,進一步探討社聯盟員的馬克思主義觀、社聯盟員與“有機知識分子”等問題,對于取得對社聯的“歷史的理解”,對于緊密結合時代特征把握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特質,對象化、分眾化、互動化推進理論武裝工作,都頗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