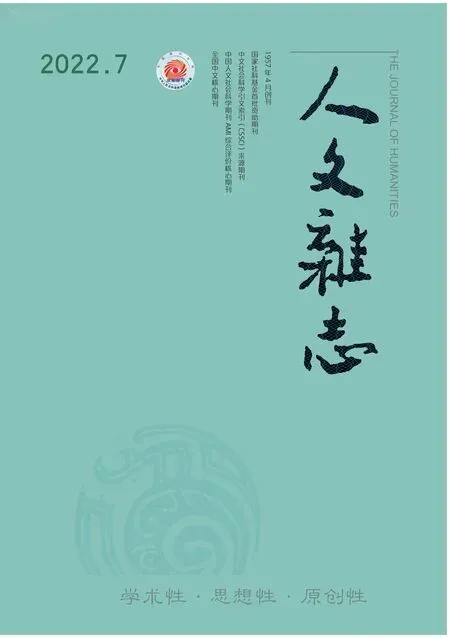錢鍾書的中國傳統文論之現代轉換路徑
關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兩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創造性轉化,就是要按照時代特點和要求,對那些至今仍有借鑒價值的內涵和陳舊的表現形式加以改造,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和現代表達形式”;“創新性發展,就是要按照時代的新進步新進展,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加以補充、拓展、完善,增強其影響力和感召力。”
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傳統文論,若要在全球化現代化背景下,真正回答“中國傳統文論在哪里”,以實現自我革新適應新的文化環境,勢必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傳統文論的現代轉換實質上就是“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堅持“三會一課”制度,推進黨的基層組織設置和活動方式創新,加強基層黨組織帶頭人隊伍建設,擴大基層黨組織覆蓋面,著力解決一些基層黨組織弱化、虛化、邊緣化問題。弱化、虛化和邊緣化問題精準指出了現在基層黨建的突出矛盾和薄弱環節,切中基層黨建工作要害,為基層黨組織指明了今后工作目標和努力方向。我們要堅持問題導向,在基層黨組織弱化、虛化和邊緣化問題上下足功夫,直面問題,對癥下藥,開好處方,補齊短板,把黨建工作抓具體、抓深入、抓到位,筑牢戰斗堡壘,確保黨的執政基礎堅如磐石。
“近百年來,中國美學文論學在西方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不斷擴張中,艱難地生產著自己的文化和美學新思維,在歐風美雨中不斷吐納吸收的同時變更著自己的美學文藝學立場。”
中國傳統文論的現代轉換,自王國維開始,已歷經百年,且成果豐碩。無疑,百年來的中國傳統文論現代轉換,增進了傳統文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增強了傳統文論的“影響力和感召力”。例如,王國維嘗試闡發中國文學作品當中的“人生根本問題”;
胡適將社會進化論思想引入中國文學研究;聞一多借鑒西方神話學研究中國文學;王元化參照西方文論闡釋中國文藝的普遍規律。同時,“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成為學界關注的重要話題。”
1996年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組織的“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學術研討會圍繞“現代轉換”、如何轉換進行了討論,一致認為“古代文論必須進行現代轉換,現代文論必須從古代優秀傳統中尋求資源;當前古文論研究家和現代文藝理論家,應該攜起手來,共同擔負起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文藝學的光榮職責。”
2007年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年會,圍繞“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化的論爭”等話題進行了討論,其中“本土性”立場成了共識,“應當采取何種路徑備受關注”。
2017年中國文學批評研究會主辦的“當代中國文論:反思與重建”學術論壇同樣關注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
由此可見,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是中國文藝理論工作者關注的重點話題。而他們關注的重點都離不開傳統文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在傳統文論的現代轉化進程中,前人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他們為我們提供了許多珍貴的、頗具啟發性的經驗。”
錢鍾書無疑是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他不僅是中國文論進入自覺期的標志性人物,而且其《談藝錄》《管錐編》《舊文四篇》是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換的典范。在某種程度上,錢鍾書的學術研究,既是對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換的階段性總結,又是面向未來的前瞻性的探索。胡曉明、殷國明、張文江等學者,圍繞“新辭章學”“中國本位”“人類學術”“中西互注”等問題探討了錢鍾書古代文論現代轉換的意義與價值。鑒于“認識他們所獲得的成就,評論他們的不足,對后來者是會有助益的”,
所以考察錢鍾書如何面對各方理論資源、如何對傳統文論進行現代轉換——“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對于中國傳統文論現代轉換的深化,具有積極的參照意義和啟示作用。
一、“以我為主”融匯中西理論資源
對于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舍、推陳出新”。
而對于中國傳統文論,要實現現代轉換與推陳出新,意味著“以我為主”融合中西理論資源,做到既要合理利用傳統文論話語,又要在與世界文明互鑒當中融匯世界文論精華,“發掘傳統文論的現代意義”,推動傳統文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使其凸顯“自身”的主體性,發揮當下以及未來的闡釋力,提升其世界影響力。
此工藝與氬弧焊打底工藝相比,具有操作設備簡單,減少背面充氣難度,抗風能力強等優點,適用于不易進行背面充氣保護進行返修的位置。但同時對焊工的技能水平也有更高層次的要求,需要焊工手穩、經驗豐富、觀察能力強,并且對鎳基材料的焊接性有足夠的掌握、對缺陷的分析透徹。
在錢鍾書看來,“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
與此相應,他的中國傳統文論現代轉換,通過“中西打通”,“以尋求中西共同的詩心文心為目的”。
這意味著他旨在通過古今中外的“全人類智慧的結晶”探尋中西文藝的“契合”之處、共通之處。而他在“尋求中西共同的詩心文心為目的”的過程中,通過對傳統文論的再闡釋、對經史子集的文學化解讀、對民俗學倫理學跨學科的對話,推進了中國傳統文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錢鍾書認為,實現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既要掌握“西學義諦”,又要使西方文論與中國文藝現實“相得”。在他看來,西方文論之“玄諦”,與中國文藝作品之“佳著”,“利導則兩美可以相得,強合則兩賢必至相阨”。
換言之,援引西方文論闡釋中國文藝作品,既要準確理解西方文論,又要準確把握中國文藝作品,在兩者的契合之處進行“利導”,才能使“玄諦”(西方文論)與“佳著”(中國文藝作品)“兩美可以相得”。無論是“利導”,還是“參禪貴活,為學知止”,均意味著中國傳統文論的現代轉換是“以我為主”的“洋為中用”,要有“本土意識”,要立足于“本土性”,要使西方文論與中國文藝作品“相得”,從而解決本土問題,“以我(中國傳統文論)為主”而不是使中國文藝作品附會西方文論。有學者指出這是“中國本位”的學術。“‘中國本位’就是中國‘固有血脈’和‘本來面目’,就是‘民族自覺’和‘文化自信’,就是‘不舍己殉人’。”
錢穆也強調“中國本位”,強調“‘民族自覺’和‘文化自信’”。不過,錢鍾書與錢穆的“中國本位”并不完全相同。中國傳統文論的現代轉換,很大程度上也是傳統文論的“現代性”焦慮,包含著文化的焦慮、“身份認同危機”以及文化的自尊和對抗意識。錢穆堅守“中國本位”,對中國傳統的強調,均有濃厚的文化自尊與對抗意識,不僅對抗西方,而且對抗新文化運動。比如在《中國文學論叢》的再版序言里,錢穆坦承道:“民國初興,新文學運動驟起,詆毀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甚囂塵上,成為一時之風氣。而余所宿嗜,乃為一世鄙斥反抗之對象。余雖酷嗜不衰,然亦僅自怡悅,閉戶自珍,未能有所樹立,有所表達,以與世相抗衡。”
“與世相抗衡”也就是與“新文學”、與“西方文學”相抗衡。錢鍾書與他們的相同之處在于,他們都是力圖擺脫“以西方為中心”“蘊含著中國文學理論建立自我主體性的強烈愿望”。
而不同之處在于,錢鍾書沒有像他們那樣強調“中西對立”“新舊對立”,并沒有他們那么濃厚的對抗意識,在錢鍾書看來,中西互為主客,不存在“誰指導誰”,不存在“誰對抗誰”。畢竟,錢鍾書不僅反思了西方理論,也反思了中國傳統文藝理論的思想體系。
其三,“尋求共同詩心”,走向“契合而非相授受”,建構“文論共同體”。有學者認為:“從20世紀20年代引進西方文藝理論,到90年代的探索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討論雖然進行了很多年,卻沒有收到預期的理想效果,現在反思起來,其中的原因之一在于我們過于執著中西文論的區分。這種區分導致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中西文藝思想之間的聯系,過于強調它們之間的差異,從而不能很好地將它們思想中的積極因素融合起來進行考慮。”
相較許多學者執著于“中西文論的區分”,錢鍾書更加注重中西方文論之間的“同”與“通”,善于將二者之間的積極因素融會貫通。錢鍾書認為,中西“學說有相契合而非相授受者”。
換言之,中西文學有著“共同詩心”,中西文論有著價值“共同體”。比如他論述“易之三名”以駁斥黑格爾“嘗鄙薄吾國語文”“不宜思辨”之觀點;
比如他認為中國古代民間諺語不亞于狄德羅的理論文章,唐代一首詩堪比萊辛的分析等。
他對中西“詩與畫”“詩與樂”“詩與史”“離騷”的訓詁和闡釋,均屬此類。正如上文所述,錢鍾書的這些理念,是對“以西方為中心”的批評與反思。“自19世紀末以來,中國對西方思想的引入存在一種 ‘沖擊與反應’的模式”,“這種模式促成了傳統的出場”,這種模式暗含了“以西方為中心”與傳統的“某種被動性”。
由于“以西方為中心”,中國學術界長期以西方文論指導學術研究,包括“運用西方文論闡釋中國經驗”,以中國經驗印證西方理論,以及強調中國某些學說源自印度和西方等。其中,以西方為標準隱含著中西方文論“‘誰指導誰’的理論話語權爭奪”。
在錢鍾書之前,熊十力、錢穆等學者就對此進行了檢討。相較熊十力、錢穆等學者強調“中西對立”、傳統文化的優越性,錢鍾書則追尋中西“共同的詩心”與價值觀的契合。通過“中西打通”,“從文學觀念的提出與中國文學話語范疇的闡釋到中國文學經驗的滲透與融合”,錢鍾書注重了話語建設。
他將中國文論“本土性”的內容與西方文論互相參照,既努力使西方文論本土化,又有意識地結合了中國傳統文論特點,努力使中國“本土性”的內容成為“世界文論”。錢鍾書直接注重傳統文藝的“本土性”內容,將中國文藝的“本土性”內容與西方文論等量齊觀,以尋求中西共同的“文心”。這種對中國傳統文論的現代轉換,注重中西文論“同”的“打通”,追尋“中心共同詩心”,某種程度上是在建構中西文論共同體。這意味著“按照時代特點和要求”,立足中國傳統文論,面向世界,旨在解決中西文論面臨的共同問題。錢鍾書主張“以我為主”建構中西文論共同體,意味著否定了“以西方為中心”,跳出了“中西對立”,妥善處理了中西理論資源的關系。
其一,“尋求共同詩心”,推進中國傳統文論的“創造性轉化”。在闡釋《關雎·序》及《正義》一節時,錢鍾書道:“按精湛之論,前謂詩樂理宜配合,猶近世言詩歌入樂所稱‘文詞與音調之一致’;后謂詩與樂性有差異,詩之‘言’可‘矯’而樂之‘聲’難‘矯’。”然后,通過訓詁與闡釋,他不僅區分了“情詞雖異而‘曲’、‘調’可同”,以及“情‘詞’雖異,則‘曲’、‘調’雖同而歌‘聲’不得不異”,將“初做樂者,準詩而為聲”“聲既成形,須依聲而作詩”與現代的“上譜”“配詞”相對應,而且指出《正義》后半“更耐玩索”,與“古希臘人談藝”“近代叔本華越世高談”殊途同歸,均闡明了詩與樂的本質差異——“言詞可以偽飾違心,而音聲不容造作矯情,故言之誠偽,聞聲可辨,知音乃可以知言”。
不難看出,對于“詩與樂”“言與聲”這些均屬“至今仍有借鑒價值的”部分,錢鍾書結合新的時代語境,通過“中西打通”,融匯中西資源,對其內涵和傳統形式進行了改造,“賦予了其新的時代內涵和現代表現形式”,
實現了傳統文論的“創造性轉化”。他對“艮其背”的解讀,亦是這樣的“創造性轉化”。通過解讀“背”的“不見可欲”“見不可欲”之二義,將《詩經》《西游記》《紅樓夢》當中的“背”“背面”“背前”與“面后”視為“艮其背”的文學展現,改造了其內涵和傳統形式,并參照西方文學,賦予其“真質復不在背而在內,當發覆而不宜革面”的新的內涵與表現形式,既豐富了傳統文論的當代形象,又實現了傳統文論的“創造性轉化”。結合《高僧傳》、古代文學名著以及英德詩歌、莎士比亞戲劇,錢鍾書認為中國的“艮其背”“反面一照,只見一個骷髏兒”與西方的“汝面姝麗,汝背則穢惡可憎”“揭黃金匣盒,中乃骷髏”“不謀而合”,皆意味著“共同詩心”——“真質復不在背而在內,當發覆而不宜革面。然作者寄意,貌異心同,莫非言惡隱而美顯,遂炫目惑志爾”。
錢鍾書對傳統文論的“創造性轉化”,不僅僅是對其內涵和形式的現代化轉化,更重要的是激活了傳統,使傳統經學、傳統詩詞、傳統謠諺重新煥發生命進入中國文論史當中,擴大了傳統文論的疆域,推進了古典資源多方位的“創造性轉化”。
在拉特納普勒一分為二的卡魯河的古河床孕育了這個國家三分之一的寶石,也使它成為亞洲最大的寶石礦區。這個地區的寶石不僅產量大得驚人,質量也好得出奇。這個世界上最富足的寶石礦床歷盡千百年來的歷史長河,如今穩立南亞寶石業中心的位置。
二、“尋求共同詩心”推進傳統文論的“兩創”
對此,錢鍾書的中國傳統文論現代轉換路徑是中西“打通”。錢鍾書的“中”,不僅包括中國傳統的詩詞、隨筆、小說、戲曲,而且包括中國傳統的經史子集,還包括廣泛的民間文化如謠諺等。錢鍾書的“西”,不僅包含了“西方”,而且包含了“泰西”,即他“凡所考論,頗采‘二西’之書,以供三隅之反”。
因此,他的“中西打通”,既是“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打通”,又是文史哲的打通、不同藝術學科(比如繪畫、民俗學)的打通。由此可知,錢鍾書采用西方理論資源,目的是闡釋中國文藝。也就是說,他以“以中國文藝為主為需要”,而融匯中西理論資源,而“中西打通”。比如他結合西方美學的“混含”,闡釋中國的“虛涵”,以說明“此乃修詞一法,《離騷》可供隅反”。
以引用上萬種著作、130多萬字篇幅的《管錐編》為例,這本著作涵蓋了古今繪畫、詩詞、隨筆、小說、戲曲以及俗語,
涉及中國傳統的經史子集、西方的文史哲等人文學科。具體在寫作上,錢鍾書的“中西打通”,以文言札記體的形式,“以中國學術傳統的專書之學對應西方學術研究的專題之學,以百科全書式的集部之學統攝西方分門別類的人文科學”。
與其他學者重視宏觀理論不同,錢鍾書推重中外“三言兩語式”之精辟見解,且“多引證類比而少論證裁斷”。在錢鍾書的視野里,西方文論、中國傳統文論與中外文藝作品、諺語俚語當中的“三言兩語”是平等的、相通的。錢鍾書并非以西方文論闡釋中國文論以解讀中國文藝作品,而是將西方文論、中國文論、中國文藝作品置于平等的位置,使它們互相對照、互相闡發。因此,錢鍾書的“中西打通”,并不同于以往的“中西互注”。比如王國維的“中西互注”是將西方文論引入《紅樓夢》評論,他“把西方叔本華的理論引入《紅樓夢》評論之中,由此在《紅樓夢》中發現了具有人類性的美學涵義和藝術價值”,其中以叔本華“饜即生厭”的悲劇觀將《紅樓夢》視為“悲劇中之悲劇”;朱光潛的“中西互注”是將西方美學、心理學理論與中國傳統詩詞相結合,“他的著作《詩論》就是以克羅齊的直覺說等西方美學理論研究中國舊詩的一部詩學著作”,其中以西方古典美學中的“靜穆”觀念解讀錢起詩的高境界;
王元化的“中西互注”是“中外結合、文史哲結合、古今結合”,參照西方文論考察中國傳統文論,其中他參照西方文論中的創作活動中的主客關系,考察傳統文論的《物色篇》心物交融說,闡釋王國維的境界說與龔自珍的出入說。
而錢鍾書的“中西打通”,具有主動性的“以我為主”,涵蓋的傳統更廣,涉及的國別更多,觸及的學科門類更多,包容性更強,更有利于全面深入合理利用傳統話語資源,更有利于融匯世界文論精華。因此,與曾經出現過的反傳統傾向不同,錢鍾書非常重視中國傳統文論,將中國傳統文論中“本土性”的東西上升到與西方文論同等的高度。比如他結合西塞羅的修辭學、萊辛的名著以及蘇軾的詩句,提出“‘無聲詩’即‘有形詩’和‘有聲畫’即‘無形畫’的對比,和西洋傳統的詩畫對比,用意差不多。”
據此可知,錢鍾書批評中國傳統文論現代轉換的“以西方為中心”,強調具有主動性的“以我為主”,恰恰與其高度重視傳統理論資源相一致,體現了他對傳統文化的自覺與自信。
突然,幾枝步槍啪啪地響起。不用說,是國軍的一支偵察小分隊,他們與這撥鬼子遭遇上了。槍聲一響,受了驚的大洋馬便嘶鳴著四散開去,不一會兒,有馬撞了地雷,轟轟作響。一匹馬朝陳大勇方向撞來,眼看要踩上了,陳大勇猛地站了起來,照著馬上的鬼子猛扣扳機。
錢鍾書的這些認識,也與他對西方文論進行了深度反思密切相關。錢鍾書不僅拒絕“附會”兩方理論,而且對西方理論予以批評與反思,思考了西方文論的有效性與局限性。他指出:“許多嚴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學體系經不起時間的推排銷蝕,在整體上都垮塌了,但是他們的一些個別見解還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時效。”
“許多嚴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學體系”自然包括西方的思想和哲學體系。反思西方文論的錢鍾書,也就順理成章地批評處處“以西學坐標”或過度依賴西方文論的學術研究。也就是說,他批評中國普遍存在的“附會”“西學”現象,與其反思與懷疑西方文論一脈相承。值得注意的是,錢鍾書對西方文論的批評與反思,發生在其晚年,是隨著其作品的不斷修訂完善而出現的,并非始初就有。錢鍾書批評西方文論的觀點來自《讀〈拉奧孔〉》一文。這篇文章屬于“舊作”,發表于1962年,后于1979年結集為《舊文四篇》出版。然而,其對西方文論的批評,用錢鍾書的話說,乃是“經過一番修繕洗刷以至油漆”而成。
1979年的《讀〈拉奧孔〉》,借第一部分的新增內容,他申明了自己對理論著作、思想體系整體否定的態度,也就是增加了大量篇幅,反思了西方文論。比如他批評黑格爾“不知漢語”以致“無知而掉以輕心,發為高論”。
再如他批評“西洋文評家談論中國詩時,往往仿佛是在鑒賞中國畫”而“只從外面看了大概,見林而不見樹”。
可見錢鍾書對西方理論的警惕與反思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初期。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是“西學”在中國占據主導乃至泛濫的世紀,許多學者不僅言必稱“西學”,而且處處以“西學”為坐標,其弊病甚為嚴重。這時常使中國學術研究成了西方文論的“注腳”,“給人們的印象是仿佛置身外國說著外國的事,與中國文學實踐毫無關系,如果發生了一些什么關系,那總是顯得生吞活剝、生搬硬套”。
錢鍾書批評王國維,看似是不滿后者并未真正理解“西學”,實則是對普遍存在的中國文論“附會”西學的反思,是對“以西方為中心”的傳統文論現代轉換的反思。
不過,盡管他在傳統文論現代轉換的過程取得了重大成就,掌握了更多的西學“義諦”,認識到西方文論強制闡釋中國經驗的弊端,擴大了中國傳統文論的疆域,但錢鍾書中西“打通”仍存在不足。其局限在于:一是“其范圍基本在文史哲之間,而對于文史哲的兩端,科學與宗教,致力似有所不足”,使“若干判斷有時略欠精微”;
二是“其著作打通文史哲,基本向度是從文學打通到史哲,而不是從史哲打通到文學,有時就把一些有意義的問題忽略了”,比如闡釋了“詩可以怨”的文學之旨,卻相對忽視了“詩”之“興、觀、群”的歷史、倫理、政治向度;
三是錢鍾書的打通“主要還是致力于片段思想以及句子層面上”,卻忽視了“整體思想”。
這些與他的治學旨趣、偏好息息相關。首先,他否定中國傳統文論以及西方文論的思想體系。“片言只語”固然有著不亞于中國傳統文論以及西方文論思想體系的精辟見解,但中國傳統文論、西方文論的思想體系及其背后的方法論、哲學思想和理論命題仍然具有重要價值,對于中國傳統文論的現代轉換仍然富有啟迪。其次,錢鍾書以學術上的前輩為思想上的仇敵,處處反駁他們的觀點,明顯限制了他的學術視野與論述深度。可以說,錢鍾書不僅批評了王國維,而且批評了中國學術史包括文論史上的多數人。這導致錢鍾書忽視了王國維等前輩學人構建本土化文論的合理性,“難得體會對方的好處與貢獻”,
進而否定他們的價值與意義,致使他的傳統文論現代化轉換建構缺乏足夠的包容性與開放性。最后,其堅持“小說、詩歌、戲劇”與“哲學、歷史、社會學”不可直接“等為一家”,比如一直批評陳寅恪的“以史證詩”,
某種程度上忽視了“文史哲”之間的雙向奔赴,導致“解讀文本會遺失一些歷史變化的信息,因而不能真正了解歷史生命的幽深處”,
缺乏一定現實關懷。
與此相應,一旦以中國文藝作品附會西方文論則是強制闡釋,將導致“既丑且愚,則天下之棄物爾”。
因此,他批評王國維使用西方文論的“悲劇”觀念闡釋中國古典戲劇以及借助叔本華哲學解讀《紅樓夢》,是“作法自弊”的“附會”。盡管王國維借助西方文論研究《紅樓夢》在傳統文論現代轉換上“開風氣之先”,但錢鍾書并不認可。然而,從錢氏所言“此非僅《紅樓夢》與叔本華哲學為然也”可知,以《紅樓夢》附會叔本華哲學、中國文藝作品與西方文論的“強合則兩賢必至相阨”并非個案。即直接援引西方文論闡釋中國文藝作品,而導致“作法自弊”的“附會”,不僅僅是王國維的問題,而且是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換研究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問題。
其二,“尋求共同詩心”,推進中國傳統文論的“創新性發展”。在“尋求共同詩心”的過程中,他注重通過“中西打通”將中國傳統文論范疇創造性地“活移”為文學理論的核心理論。“通感”屬于中國傳統文論范疇。而錢鍾書通過對古今中外具體文學作品的考察,闡發了其“通感”理論,從而使“不同的文化語境和文本中藝術魅力的契合和相通之處”得以呈現,從而使我們發現“通感”“不僅是一種感性的創作心理狀態,而且是一種文藝美學的理論境界”。
他對“詩可以怨”的闡發,亦屬此類。他通過《詩可以怨》,結合西方作家的比喻與劉勰的“蚌病成珠”,闡發了中西的相通之處,即“蚌病成珠”“非常貼切‘詩可以怨’、‘發憤所為作’”。
這樣的“活移”,在錢著中比比皆是。此外,他從古典文學拈取“黃昏意象”“不樂生子”“桃夭”“天地擬象”等重要“意象”,“且將西方文學中的相類題材與意象,貫通互釋,融會雅俗,打通古今”。
錢鍾書使用的“通感”“詩可以怨”“意象”等主要話語都來自中國傳統文論資源,他并沒有對這些話語進行簡單移植,而是以“中西打通”的方式將它們主動和西方文論對話、融合,實現了以中國傳統文論范疇統攝中西文學經驗。他的這些“活移”,既尋求了“共同詩心”,又通過“中西打通”對傳統文論的內涵進行了“補充、拓展、完善”,推進了傳統文論的“創新性發展”,增強了傳統文論的“影響力和感召力”。換言之,在知識學的構建中,錢鍾書通過推進傳統文論的“創新性發展”,“加強其跨文化交鋒與交融的能力,提升對不同文論觀念進行批判與吸納的話語論辯力,推進以傳統文論之精華融入世界文學經驗之中,在創造性闡釋中彰顯其生命力與理論的合法性,把傳統文論資源化成當代文學理論的理念與概念范疇的有機組成部分”,
很大程度上解決了中國傳統文論的合法性危機,為中國傳統文論現代轉換、走向世界樹立了典范。
三、錢鍾書對傳統文論“兩創”的啟示
胡曉明指出:“從王國維‘以外來觀念解釋中國材料’開始,晚清詩學就啟動了‘中西比較進路’”,而錢鍾書無疑是“這個傳統”的“一個集大成者”,“無疑為中國詩學的現代生機,開出一條新路”。
不僅如此,錢鍾書的相關學術研究“是對漸趨式微的中國本位學術的重振,是對西方強勢學術研究范式的反撥,具有極大的前瞻性,在當今重新建構中國學術思想研究體系的時代大背景下,具有不可忽視的參照意義和啟示作用”。
和魯迅一樣,錢鍾書從自己的側面,“以自己的實踐和努力,對中國文化走向世界進行了多種有意義的探索”,他“那種審視、把握、判斷中國古今文化的眼光,及其所取得的經驗,無疑具有極大的啟發性”。
考察錢鍾書對中國傳統文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對于中國傳統文論現代轉換的不可忽視的參照意義和啟示作用在于:
從表3中可以看出,溶液終點pH值對除氯影響不大,但溶液pH值為2.0時,鉍損失量較大,所以除氯宜選擇終點pH值為3.0~5.0。在調節pH值時,選擇了氫氧化鈉、堿式碳酸鋅、堿式硫酸鋅來調節,如果長期使用氫氧化鈉,鈉離子會一直在溶液中富集,不可取。為不引入雜質,同時加入量較少,采用堿式碳酸鋅較為合適。
首先,對中國傳統文論應有“自知之明”與充分自信,強化“創造性轉化”。“自知之明”意味著既要搞清楚中國傳統文論的特點,明白中國傳統文論“來歷、形成的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發展的趨向”,
重視中國傳統文論“對現實的介入和實用性的價值”,通過加強知識學梳理等方式,凸顯中國傳統文論的“本土性”“民族性”的內容,又要清醒認識現實,承認自身的差距與缺失,在尊重文論普遍規律的基礎上,自主選擇適合自己的文論樣式,找到中國文論和西方文論之間的“接榫之處”,實現中國文論的“除舊開新”,充分彰顯中國文論的獨創性和“世界性”。也就是說,要處理好特殊性與普遍性、民族性與世界性、自我性與他者性的關系,尊重自己的傳統,主動向全球其他地區的文論學習,通過“創新,使中國文論的普世價值常新”,
在創新民族形式、賦予中國味道的同時,實現中西“會通”,賦予中國文論“普世價值”,使得中國文論在突破了傳統的同時“繼續并更新了”傳統,使之“不斷擴展著自己的空間與疆域, 并在不斷創新中獲得自己生命活力”,使之實現“跨文化的傳播和開展,并在不同文化語境中接受考驗與生發”,“獲得更大范圍內的認同”。
其次,走向平等交流對話模式,注重跨學科的多維溝通,推進“創新性發展”。鑒于西方文論“如同水墨畫中泅散開的筆墨,與中國現代文論界限模糊,形影相隨,構成它的色澤和質感”,
一方面要積極“拿來”西方文論,另一方面要加強中西文論的平等交流對話,通過加強中國傳統文論的“創造性轉化”,推進中西文論共同體建設,豐富世界文論多樣性,“本著互補、互識的原則積極地參與到全球化時代世界性文化景觀的共建中來”。
注重跨學科的多維溝通,意味著既要打通文史哲,又要關注文史哲與科學、宗教、心理學的溝通;既要從文學打通史哲、宗教、心理學,又要從史哲、宗教、心理學打通文學;既要闡發中國傳統文論的文學意義,又要闡發中國傳統文論的歷史、倫理、政治向度;既要注重“片段思想以及句子層面”的深度解讀,
又要具備整體意識和現代意識,加強理論與話語體系的建構。
最后,富有“本土意識”,積極回應時代,深化當代闡釋,增強“感召力和影響力”。聚焦“本土化的歷史性進程與本土化價值創造問題”,全面梳理總結中國傳統文論現代化轉換百年來的經驗,積極介入現實,處理好與時代精神的關系,要從回應時代出發,表達思想內容,并“尋找與之相適應的最好的表現形式”。
換言之,中國傳統文論現代化轉換,一方面不能固守馬克思主義經典話語、西方文藝理論、中國傳統文論本身, 而是要注重當下的意識形態、語言媒介、接受機制,充分認識西方文論與中國經驗不可“等為一家”,另一方面要尊重前人的探索與成就,總結前人經驗得失,使中國傳統文論現代化轉換關注中國現實、介入中國現實、解決中國問題,通過中西融通深化傳統文論的“創新性發展”,使其在世界學術范圍內做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