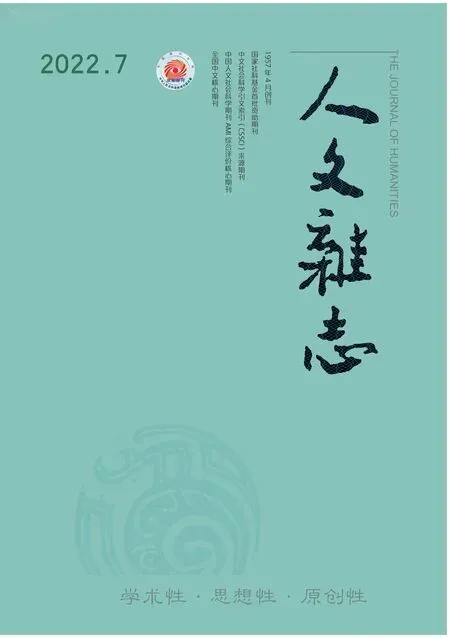論孔子的人性觀及其展開形態*
人性論是儒家哲學的一個基礎,也是諸儒分判的重要依據。在孔子時代,它還沒有成為學術思想的核心主題。儒家對人性的理論關注,實起于七十子后學時代。但孔子作為儒家源頭,后世一切儒學思想,都希望可以折中于夫子。于是,站在后世的角度,如何追溯孔子的人性觀,如何了解孔子的人性思想與七十子后學乃至孟荀的人性論之間的關聯,就成了一個不可回避的理論問題。它不僅關涉孔子真面目的認定,更關涉儒學思想史的同一性,乃至道統相續問題。故對孔子人性觀的探討,為學界所重視。
但孔子人性觀的討論,易落入兩個誤區:其一,認為孔子關于人性無甚發明,只抓住一句“性相近也”以為只是經驗的觀察,未能深入其內部了解到孔子人性觀的復雜結構;其二,把后學思想附益到孔子身上,或者以《易傳》的相關說法為孔子的主張,又或者直接以孟子性善論的問題意識,返回《論語》尋找零星的證據,而不注意兩者關切、思路與背景的不同。其實,孔子人性思想的探討和論定,一方面是要回到孔子自身的問題關切,呈現其了解人性的方式和初衷;一方面是要在思想史的角度,揭示他的人性觀何以引導和引發了后世儒家人性論的次第展開。
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的判語
孔子與孔子后學之間學術風向的轉變,子貢有一個切近的觀察和精要的判斷:
比如說,在講授“空間四邊形”相關內容的過程中,倘若老師僅僅依靠板書展示空間四邊形的平面版本,就會讓不少學生產生或認為“空間四邊形的兩個對角線是相交的”誤解,不利于學生建立空間立體概念。通過多媒體手段顯示旋轉運動的“空間四邊形”的三維圖形,讓學生可以真正感受到空間立體圖形的存在,從而培養學生的空間想象能力,讓學生通過觀察三維圖形加深理解“原來這兩條線根本沒相交!”。而在展示微課課件的過程中,可以讓學生獨立地發現“不在同一平面的兩條直線”,并為將來學習“異面直線”埋下伏筆。由此可知微課程可以產生傳統教學方法無法達到的教學效果,從而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積極性。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
但這句話從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歷史上有很多爭論。
隨著民生事業社會管理進程的不斷推進,殯葬行業較之以往無人愿意提及,到現在已經成為涉及民生的社會關注焦點。國家對改進殯葬行業服務質量的急需,逝者家屬對親人未盡情懷的過度表達期待,社會媒體對殯葬行業關注度的提高,使殯葬行業從業者從過去被漠視、被輕視,到迅速推至大眾視野,成為備受關注的民生工程的執行者。這是時代發展、社會需求的直接體現。因此,在現代社會殯葬文化的背景下,獲得具有崇高職業價值感和堅定社會責任感,將是青年一代從業人員更為注重的。
(2)餌料來源 中華鱉的餌料主要來自于兩方面,一是天然小雜魚、蝦、螺類等,二是人工投喂的飼料。為保證中華鱉的野生品質,應以天然餌料為主,人工投喂為輔。人工餌料選擇海水小雜魚、冰鮮淡水魚肉為宜。
所謂“夫子之文章”,據《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季氏》)子思又說:“故夫子之教,必始于《詩》、《書》,而終于禮樂,雜說不與焉。”(《孔叢子·雜訓》)故學者大多認同,“文章”指《詩》《書》禮樂。文采著見于外,故曰“夫子之文章”。但“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一句,則聚訟紛紛。或認為,夫子確有“性與天道”之論,只因子貢學力不到,故不曾聞;
或認為,夫子有“性與天道”之論,子貢終于幸聞其說,故感慨之。
子貢聞或未聞不能確定,但夫子有“性與天道”之論,則是傳統諸家的共同主張。至于夫子“性與天道”之論的存在形式,又有不同說法。或認為,寓于夫子之文章當中,在于學者的實踐體認;
或認為,在于《易傳》《春秋》兩部晚年著作之中,子貢未得其傳。
宋儒之所以說這句話是“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嘆美之言”,實是出于不得已。一來,按照傳統說法,《易傳》為夫子所作,無疑有很多“性與天道”之論。于是,子貢的“不可得而聞”,一轉手就成了朱子的“罕言”。二來,對于宋儒來說,“性與天道”的義理傳承,也不能化約為某部經典的文本傳承。若連子貢之賢,都沒有資格與夫子精微之論,實在難以令人信服。至于清儒認定夫子“性與天道”之論直接對應于《易傳》(或加《春秋》),則只有在漢學強調經學師承甚于義理傳承的大背景下才有可能。宋儒不是沒有注意到《易傳》與“性與天道”的關系,
但他們看到的是夫子義理系統之所及,而不是文獻傳承之分派。然而,今日若以歷史的眼光看,孔子與《易傳》的關系到底該如何了解,又是一個值得玩味的問題。兩者或有內在的淵源,卻不能直接等同。至于《春秋》,雖是孔子所修,但說它代表夫子的天道之論,源于漢儒《易》與《春秋》的對比闡發,實是后人思想上的認定。
回到文本本身。至少在字面上,子貢的意思是比較清楚的。子貢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從后半句可以確認,子貢確不曾聞夫子“性與天道”之論。
但“夫子之言”的表述,又似乎暗示了夫子曾經說過。這也是諸家立論的一個基礎。若說夫子有過“性與天道”之論,但子貢沒有機會聽聞,從子貢的資歷、地位和能力來看,總是說不過去。在此,“夫子說過”和“子貢不聞”就構成了矛盾。宋儒取了前者,為了解決這個矛盾,便說這是子貢聽后的“嘆美之辭”。但又有違于文本的字面含義。事實上,聯系當時的思想處境,所謂“夫子之言”,未必是夫子的實情,而可能來自他人的宣稱。
依托潿洲島獨特資源所形成的不可替代和不可復制的產品優勢,面向中高端市場,打造以休閑度假為核心,集海洋文化、休閑運動、海島養生、南珠文化、時尚生活、主題娛樂、海島度假等功能于一體的國內一流、國際知名的休閑度假海島,使之成為旅游改革發展創新先行區、綠色生態宜居示范區和國際海島休閑度假勝地(簡稱“兩區一勝地”)。
基于對通脹的擔憂,1994年2月4日至1995年2月1日,美聯儲將基準利率從3.25%逐步提升至6%,總加息幅度2.75%。前三次是每次上調0.25%,隨后四次各加息0.5%,最終將基準利率提高至6%的水平。期間,上證指數經歷了三個階段(圖1):首先延續之前的下跌走勢,從800點左右跌至最低325點,然后迅猛反彈并創出1052點的新高,再大幅震蕩回落約50%。
經濟市場的國際化發展,對人才的素質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進而導致高校在培養人才方面不斷進行探索和變革,目前,英語已經成為國際化人才的必備素質之一,其中英語口語更是至關重要,也正是基于此背景,本文將著重分析高校英語口語測試的必要性,通過可行性策略的提出,希望能夠切實促進高校英語口語教育的發展,提高學生們的綜合素質,具有重要的社會現實意義。
皇侃《義疏》引或云:“此是孔子死后子貢之言也。”
這一說法未必有直接證據,卻很可能說中了歷史的事實。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卒年不詳。但從年齡上看,他完全可以親歷孔子弟子以及再傳弟子的思想討論。孔子死后,子貢身處“性與天道”之論盛行,且往往將之系為孔子之言的思想語境之中。面對這樣的狀況,子貢說出這樣一句話,乃是從一位孔門耆宿的立場,表明他所認識的孔子之教和孔子之言,以便在“子曰”盛行的思想時代,為夫子之人與夫子之言正名。
這種分判與認定的工作,實是孔子死后核心弟子的重要責任。《論語》一書,最初也是為此而編定的。《漢書·藝文志》記載:“《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論語》的原材料,主要是各位弟子私下記錄或追憶的孔子言論,類似于宋明的語錄。但不同弟子所聞不同,回憶、記錄不免摻雜自己的理解,造成相互之間的矛盾,甚至有違于夫子之意。故弟子們聚在一起,討論、甄別相關材料,撰定一本能夠真正反映孔子其人其道的言行匯編,作為七十子共同推尊的經典,就成了當時一件緊要之事。
但這不是一蹴而就的,從孔子之死直到曾子之死,跨度數十年。
此間也需要大弟子出面,確定孔子人格與思想的特征,作為甄別眾多“子曰”材料的依據。子貢的這句話,便是對孔子思想品格的一種論定。準此可知,七十子后學時代一度盛行的有關“性與天道”的“子曰”文獻,并非直接出于孔子之口。這樣一來,《論語》不見“性與天道”之論,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某種意義上,子貢之言已經為此定調,已經為什么材料符合孔子的思想品格,能夠編入《論語》劃定了界限。編纂過程中對材料的嚴格篩選,使得《論語》保存了夫子思想的原貌,與先秦其他的“子曰”文獻相比,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和權威性。
不過,子貢的話只是否認了七十子后學所宣稱的“性與天道”之說是夫子之言,卻也不是說孔子對“性”或“天道”完全沒有想法。在《論語》中,就有一章表達了孔子對“天道”的基本理解,且這段對話正好發生在孔子與子貢之間。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陽貨》)子貢擔心,如果孔子不說,弟子們便無從受教,也無法傳述孔子之學。孔子反問道:“天說了什么呢?春、夏、秋、冬運行不已,飛潛動植生生不息,天說了什么呢?”這段對話雖然沒有出現“天道”之名,但無疑表達了孔子對天道的根本理解,以及夫子效法天道的實踐主張。
這一章,或許就代表了“夫子之言天道”的邊界。
孔子死后,七十子后學開始關注“性與天道”的問題。據王充所說,周人世碩,以及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等都討論了人性問題,皆以為人性有善有惡,并提出了養性說(《論衡·本性》)。其中,密子賤、漆雕開是孔子弟子,世碩、公孫尼子是再傳弟子。子游的《性自命出》(郭店簡、上博簡),對人性的存在、活動、作用方式等作了系統的闡明。至于“天道”之論,更是習見。如《禮記》的《中庸》《禮運》《樂記》諸篇,更不用說《易傳》中可能形成于戰國中期的《彖傳》等篇。且這一時期,“性”與“天道”的關聯,也被強調了出來。如《性自命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構建了“天—命—性—情”的邏輯;而《中庸》“天命之謂性”,把這一關系以更簡潔的方式提示了出來。要之,“性與天道”之論,無疑是七十子后學核心的思想主題之一。
古代“性”字源于“生”。故一般即從“生而有”或“生而然”來了解和界定“性”的概念。如《荀子·性惡》:“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論》:“性者,本始材樸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性是自然如此,而與后天社會化的習得或修飾相區分,故又謂之質樸。但并不是所有“生而有”的東西都會被認定為“性”。事實上,人性論探討的往往是人的諸種表現及其最初原因。故《荀子·正名》說:“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所謂“不事而自然”,指的是先天稟賦(所以然)所決定的現實表現(生)。此稟賦是“性”,此表現亦可稱之為“性”,兩者是一貫的。后者就生命活動的特征或方向以言性。故唐君毅說:“一具體之生命在生長變化發展中,而其生長變化發展必有所向。此所向之所在,即其生命之性之所在。此蓋即中國古代之生字所以能涵具性之義,而進一步更有單獨之性字之原始。”
這是有一定道理的。“性”所包含的方向義在早期儒學中,表現為從人的“好惡”角度了解具體人性。(《性自命出》《樂記》等)
二、“性相近,習相遠”:孔子對人性的基本認定
要之,依據《論語》來了解孔子的人性觀(而不是《易傳》或其他“子曰”文獻),無疑是一個更加可靠的選擇。
孔子對人性的判定,最重要的是以下這一章: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陽貨》)
朱子注:“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于善則善,習于惡則惡,于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氣質之性,相對于義理之性或天命之性而言,后者是純粹的理,為人人之所同,故不可言“近”;可以言“近”者,必是兼氣質而言。但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的區分,基于純粹善性的認定。在孔子時代,討論人性的善惡不是當務之急,也不符合孔子一貫的思想進路。相較于普遍化、理論化地探討人性問題,孔子更加關注個體差異化的實踐。
以上貴州喀斯特石林有關資料,源自于貴州山水旅游資源勘察開發設計院的有關研究成果,是創建“多彩貴州風,山地公園省”的重要科學依據。
其實,“性相近也”與“習相遠也”一樣,源于經驗的觀察。其目的不是要說明人性是什么,或人性怎么樣,而是以“性相近”為參照,強調“習相遠”的重要性,以作為對一般學者的勉勵之辭。孔子認為,人的天生資質固有差別,但對于現實人生來說,后天習行更具決定性的意義。說性相近,正是為了著見后天習行的重要性。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也。”
錢穆說:“本章孔子責習不責性,以勉人為學。”
可謂中的。唐君毅認為:“今若就孔子之將‘性相近’與‘習相遠’對舉之旨以觀,則其所重者,蓋不在克就人性之自身而論其為何,而要在以習相遠為對照,以言人性雖相近,而由其學習之所成者,則相距懸殊。……此即孔子不重人性之為固定之性之旨,而隱涵一‘相近之人性,為能自生長而變化,而具無定限之可能’之旨也。”
切中了本章的要旨。
孔子說“性相近”,是針對一般人來說的。孔子同時肯定,還有天生資質特別好或特別差的人。接著上章,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陽貨》)可視為對“性相近”的補充。皇侃曰:“夫降圣以還,賢愚萬品。若大而言之,且分為三:上分是圣,下分是愚,愚人以上,圣人以下,其中階品不同,而共為一。此之共一,則有推移。”
此說大體符合孔子的意思。孔子所謂“上知”與“下愚”,不是指普通人,毋寧說是人中的特例。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季氏》)從“知”的角度區分了四種資質。所謂“生而知之”,相應于“上知”,特指天生的圣人。
孔子雖然設定了“上知”與“下愚”,但這兩種人在現實中幾乎是不存在的。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當時已經有人說孔子是生而知之的圣人,孔子予以否認。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冶長》)孔子說,十戶人家的小村子,必有天資與他相近的人。可見,孔子自認為只是中等資材,至少不是天賦卓絕。在《論語》中,比“生而知之”降一等的叫“善人”。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于室。”(《先進》)程子曰:“踐跡,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跡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圣人之室也。”
善人天生資質很好,即便沒有前人的規范與途轍,依賴自身的本性行事也不至于為惡,甚至還有一定的教化之功。但由于沒有主動為學的愿望和動機,能力與境界也只能停留于此,沒有進一步深造之可能,無法窺見圣人之奧。在孔子看來,即便是善人,在現實中也很難遇到。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述而》)孔子說,圣人與善人他都未嘗親見;他能見到的,是由為學而成就的君子,以及具有為學潛質的有恒者而已。這樣一來,對于孔子來說,現實的人幾乎不可能僅憑天生資質行事,而無需后天的修習。與此同時,孔子除了在見宰予晝寢,說了“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公冶長》)的氣話之外,也沒有指出誰是完全不可移的“下愚”。相反,即便是一向習于不善的互鄉童子來見,孔子也盡力接引:“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述而》)可見,孔子認為,現實的人都可以而且應該通過學習獲得自我完善。這是孔子“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的真實意旨。
除了“唯上知與下愚不移”(《陽貨》),學者還會關注這一章。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雍也》)也是將人分為上中下三等。但嚴格來說,這一區分是針對具體的教學實踐而言的。張敬夫曰:“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于身之弊,亦終于下而已矣。”
既是教學之法,則無論中人上下皆是可移之人,只是各自依循的道路有深淺高下之不同而已。此章與“上知下愚”之說,旨趣有別。
三、因“好”成“學”:孔子對人性的區分及其內在關切
在《論語》中,唯有以上兩章直接提到了“性”字。學者對孔子人性思想的討論,很多也僅限于此。但從思想的角度說,不直接使用“性”字,也能表達有關人性的觀念。
孔子提出“性相近,習相遠”,是為了確證:人人皆可為學,人人皆須學以成德,學以為君子。但在現實中,人與人之間天生資質的差別,不但是真實的,而且是顯著的。賢與愚之間有巨大的差距,賢與賢之間也有偏向的不同。對此,孔子有清晰的認識。《孔子家語·六本》記載,子夏問于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于丘。”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于丘。”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于丘。”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于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為事先生?”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詘,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在此,“回之信”“賜之敏”“由之勇”“師之莊”可以認為是各自美質及其自然發展的結果。孔子說顏回的忠信、子貢的機敏、子路的勇敢、子張的矜莊,都要勝過自己,未必是謙辭。
但這些作為生命原始的質樸,本身并不自足。其片面的發展或不合理的表達,亦會造成人生的局限。故相對于天生的美質,孔子更重視后天主動的為學。四子都需要通過后天的修習,以彌補自身美質的不足,實現為真正的德行。這正是四子一心師事孔子的原因。
孔子對人性的了解和判斷,源于實踐成德的基本立場。首先,他不對人性作普遍化的、理論化的探討,而是關注人性的具體性和特殊性。孔子的目的,是從為己之學的立場,引導學者基于自身的特質,展開差異化的成德道路。其次,他不把人性視為固定的事實,而是從學者好惡的表現,看到內在的傾向性與可能性。這兩點,都直接源于孔子為己之學的基本立場和內在關切,與后世主題化的人性論思想有所不同。
天生的美質,往往通過對相應德行的自然偏好表現出來。故《論語》中,孔子以“好德”的形式了解弟子的本性。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陽貨》)從孔子的言說方式和目的看,“好某不好學”的說法,是以前者為既定的前提,以后者為努力的方向。在此,“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剛”六者,與“好學”相對,可以理解為不同弟子的天性與資質。如顏淵之仁、子貢之知、子路之勇、申棖之剛,
等等。但對于孔子來說,此六者作為天生稟賦,只是實踐的前提而非德行的究竟。若不經由好學的道路以完成之,便會落入諸般弊病之中。換言之,即便有了對德行的天性偏好乃至擅長,還要通過好學的途徑加以自覺的培養,才能實現為真正的德行。在此,同樣可以看到,孔子的教學之道,是以資稟為起點,為學為途徑,成德為旨歸。
綜上所述,COPD急性加重期患者持續給予鹽酸氨溴索治療16d的療效優于8d,也能增強抗炎作用,值得臨床推廣。
好德除了是部分弟子天生美質的表現,也是成德實踐的一般要求。故孔子常以“好德”勉人。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學而》)能“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已經不錯了,但人不能停留于已知、已得,做到這一層之后,便須進求更高一層。故孔子說“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如果說“無諂”與“無驕”是從消極的方面誡勉學人,那么“樂”與“好禮”,則是從積極的方面引導學人。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雍也》)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
知有此道、此德,還只是一個認知問題。好此道此德,則有了實踐的動力。至于樂之,已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而能在身心上受用。孔子認為,在成德實踐中,好善、好德、好道是關鍵環節。因為它包含了濃厚的實踐意向,可以引導學人沖破自然生命的重重窒礙,期于自覺自主的道德人生。
在現實中,一時的“好德”容易興發,難在貫徹始終。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雍也》)冉有自認為好(悅)夫子之道,只恐自己能力不足,不能完全依循。但在孔子看來,這是托詞。真正的好,完全自足于己,與任何事實的計較皆無關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里仁》)所謂“好仁”,不是一個若存若亡的意向,而是切實將之視為生命最精純的至高追求。以這一標準衡量,恐怕也只有真正的仁者,才能稱得上真正的好仁者。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實際上,孔子的意思是,他沒有見過能以好德為內心真實追求的人。這種意義上的“好德”,是孔子對弟子的期許。
故在《論語》中,我們可以區分出幾個層次的“好德”:一是天生的原始傾向,如“六言六蔽”章所言“好仁”“好知”之類;二是作為成德實踐的內在要求,或為己之學的關鍵環節的“好”;三是已然實現和完成了的,作為有德者之表征的“好”。前兩者是從工夫上說,無論出于天性抑或出于后天,“好德”是成德之學的必要條件;后者是從效驗上說,“好德”是為學境界的一個表征。于是,在孔子那里,“好德”成了一個貫穿成德實踐之終始、兼攝工夫與效驗、上下齊講的概念。后來,曾子《大學》以“誠意”為第一步工夫,
子思《中庸》以一個“誠”字,貫通工夫與境界、德與道、天與人,源頭可追溯至此。
再者,對于七十子后學來說,孔子是天生的圣人、共同的宗主。后學但有言說,必追溯于孔子,導歸于孔子。這既是對先師的尊重,也是借先師以自重。故彼時代的儒學言論,每每冠以“子曰”。但到底是孔子的原話,還是學者對孔子思想的推論和發揮,則不好說。荀子批評子思:“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然而猶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荀子·非十二子》)所謂“五行”,明明是子思根據往舊見聞、自造新說的結果,卻要宣稱是出于孔子之言。其實,子思對這個問題有自己的理解。魯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也。”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于人者,雖非其正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孔叢子·公儀》)可見,在子思時代,已經有人質疑子思所宣稱的孔子之言,實際上只是子思自己的想法。但子思認為,這些話雖然未必是孔子所親說,卻合于孔子之意。可知,子思是在“不失其意”的意義上作“子曰”的宣稱的。按照這一邏輯,任何對孔子思想的內在發展,皆有理由宣稱為孔子之言。這或許不僅僅是子思的想法,也是當時較為普遍的觀念。由于這個原因,七十子后學“性與天道”的探討,很可能假托夫子之言為之。這種意義上的“夫子之言”,雖然體現了思想的連續性,卻不符合歷史的事實。
四、孔子人性觀的結構及其展開形態
孔子認為,資質的差異是無法回避的東西。學者必須在承認當前之所是,獲得充分自我認知的基礎之上,開展切身、有效的為學活動。以子路初見孔子為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子路初見孔子,冠戴雄雞式的帽子,身配公豬皮飾的劍,凌暴孔子。孔子以禮樂修養施設誘導,贏得了子路的欽佩,他轉而師事孔子。孔子究竟是如何“設禮稍誘”的,《史記》沒有記載。據《孔子家語·子路初見》:“子路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也哉?’孔子曰:‘……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而受教。’”(亦見《說苑·建本》)這或許就是初見設教的情況。孔子問子路喜歡什么,問的其實是志在何學。但子路以為是在問他向來喜好什么物件。前者是面向未來,以自身的升進為問;后者則是靜止地,以當下或向來所擅長者為說。可見,自然的人生與為學的人生,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和生命情態。在子路看來,其天生美質無修飾之必要。就如南山的竹子,不用揉制矯正自然筆直,砍下來用,可以穿透犀牛皮革,這些都是不學而能的。在此,南山之竹可謂是子路的真實寫照。孔子說道:在尾部安上羽毛,打磨前端,制成箭,不是可以穿透得更深嗎?子路這才信服受教。孔子順著子路的性好,又使他意識到了學對自身成長的必要性,使向來專注于自身之所是的局促生命,向著無限升進、無限可能的實踐人生開放。后來,孔子對子路的教誨,雖有《詩》《書》禮樂的常課,也會照顧到子路的特殊性格,順著子路“好勇”的天性而給予針對性的引導和節制。可見,孔門的教學,是以學者的“性之所近”為前提。從教的一面說,這是孔子的因材施教;從學的一面說,則是學者的切己之學。
雖然孔子沒有更多明確的人性論表述,但從《論語》的某些章節,又似可以推論孔子對人性所懷有的態度。比如,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
徐復觀認為,這是對人性的一個普遍判斷。他說:“此處之‘人’,乃指普遍性的人而言。既以‘直’為一切人之常態,以罔為變態,即可證明孔子實際是在善的方面來說性相近。”
然而,此說實難成立。其一,它的前提,是把“生”字理解為出生。而正如朱子所說:“此‘生’字是生存之生。”
孔子是說,人類的生存必以直道為基礎,罔道之行之所以可能,也以直道為前提。其二,“人之生也直”,甚至也不是人的現實,而是理想。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衛靈公》)直道而行,乃是三代之民的人生實態。而孔子時,直道而行往往受黜。故孔子說“人之生也直”,應是回顧上古黃金時代,展望理想的人世生活,而不是對人性做一個普遍的斷語。
當外教在課堂上布置任務或者發問時,學生在不確定的情況下會選擇使用交互交際策略中的猜測,即猜測外教所說的內容,并詢問外教或者其他同學自己的猜測是否正確。這種情況下,外教會馬上明白學生沒有完全理解,并放慢語速或者換另外一種說法再解釋一遍,直到學生完全理解。學生會經常使用“Is it…”或者“Do you mean…”等句式進行猜測式提問。
相較之下,下面一章更容易讓人推測孔子對善性的肯定。
人們對于智能產品的追求是無止境的,隨著消費需求結構的升級換代,消費者更加熱衷追求品質生活,互聯互通的智能家居產品正成為未來市場發展的新趨勢。國內的智能家居系統正在不斷攻破技術瓶頸,豐富使用功能,提升用戶體驗,未來,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智能產品價格逐步走低,智能家居將會進入到更多普通消費者家中,我們將身處一個充滿著更多智能設備,物物互聯的智能家居時代。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
但凡身外的東西,求是一面,所求是一面。求不等于得,求而不得者往往如是。唯有自身具足的東西,求便可得,不受限于另外的條件。仁,是內在的道德情感,以及由之而來的居心,它是完全發于自身、活躍于自身的。甚至“欲仁”的“欲”中,已滲透了仁的意思。故孔子說“我欲仁,斯仁至矣”,實是對仁的內生性、內在性的一種肯定。孔子雖然沒有明確肯定人人性中都有此仁,但孔子的這句話,當適用于一般人。于是,徐復觀說:“孔子既認定仁乃內在于每一個人的生命之內,則孔子雖未明說仁即是人性,但如前所述,他實際是認為性是善的。”
嚴格來說,仁具有內生性和內在性,未必是說它現成地就在那里,也可能只是說它若生成、存在,則必是源于、居于內在的。如竹簡《性自命出》云:“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仁是性中生出的,但這種生出不具有必然性。若是后一種意義,我們便不能推論說孔子認為人人性中有(現成的)仁,更不能推論說孔子擁有性善的觀點。
“崇尚實干、精益求精”。蘇州人民歷來做事精細奪巧,做人則崇尚實干。特別是將崇尚實干的精神與精益求精的態度緊密結合,把工匠精神融入了產業和城市發展中,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勁頭,一步一個腳印地推進高質量發展。黨的十九大以后,蘇州推出勇當“兩個標桿”、落實“四個突出”、建設“四個名城”等十二項“三年行動計劃”,詳細排出今后三年的重點任務、具體項目、完成節點,每項行動計劃都有若干子計劃,做到細化量化形象化。
除此之外,孟子曾引孔子的話,用來說明仁義禮智是“我固有之”的。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孟子·告子上》)
朱子注:“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
人情皆好此懿德,其普遍性意味著它是內在于人性的。若孟子的引文真實可靠,則至少從這一句可以看到孔子確有對人性中善的方面的直接肯定。從“好”的角度了解人性,也與孔子思路一致。
但與此同時,孔子對人性的陰暗面也有深刻的洞察。孔子感嘆,“三年學,不至于谷,不易得也”(《泰伯》);又嘆,“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衛靈公》)如此種種,莫不切于學者的通病。又,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季氏》)血氣是人的構成條件,本身難說好壞,若表達為“好色”“好斗”與“好得”,則正學者所當戒。孔子沒有把這些上升到人性層面加以認定,但不難想象,若讓他來說人性的內容,必不會回避這些面向。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嘗試對孔子人性觀的結構作一刻畫:人性是有個體差異的(差別一般不大,故曰“性相近也”,也不排除極端情況,即“上智與下愚”);性中有善的成分,也有不善的成分,通過好惡表達出來(如“好德”“好色”“好斗”之類);人生的現實,取決于后天的養成,一個重要方式是順著性之好惡而來的引導和塑成(因“好”成“學”)。借用后世的說法,孔子持有的應是一種形式的“性有善有惡論”。
孔子的人性觀,在七十子后學時代獲得了進一步的闡明。
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性)書》一篇。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論衡·本性》)
王充提到的孔子弟子和再傳弟子,大體都主張“人性有善有惡”,所謂“有善有惡”,既可以理解為個體之內的部分區分(善的部分、惡的部分),也可以理解為人際之間的個體差別(有的人善、有的人惡)。這可以說是對孔子人性觀的明確化。周人世碩所說的養性論,則又可以說是站在人性論的立場重新表述“習相遠”。可見,七十子后學的人性論,基本上把握住了孔子人性觀的要義,可以視為其展開形態。
復合鉆鉸刀包括刀頭和刀柄兩部分,刀頭由直槽鉆頭、鉸刀和倒角局部復合而成,鉸刀為四齒直槽結構,刀柄為直柄,整個刀具構造為整體式刀具。
這一狀況,也得到了出土文獻的印證。郭店竹簡《性自命出》云:“好惡,性也;所好所惡,物也。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勢也。”“好惡,性也”,從好惡的角度了解人性,這是孔子的真意。“善不善,性也”,認為人性之中有善的部分,也有不善的部分,哪一部分表達出來成為生命主導性的樣態,取決于后天。這也與孔子之意相通。最值得注意的是開篇第一句:“凡人雖有性,心無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悅而后行,待習而后定。”大意是說,人性雖是天生的,但唯有經過物的引發、順悅而行,通過不斷的習養,最終才能穩定為現實的人生形態。這分明就是孔子“習相遠也”的意思。作者實是在性情論的思想道路上,對孔子“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的判斷作了重構式的表述。
可見,七十子后學的人性論雖有具體的差異,但大體承襲了相同的框架。這種一致性,源于他們共同的思想源頭——孔子。當然,從孔子到七十子后學,也包含了思想上的轉進。孔子秉持一個純粹的實踐立場,人性的觀察和判別皆為此服務;七十子后學則需通過對人性的主題性闡明,為其所主張的為學道路作鋪墊。這也是時代思想發展之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