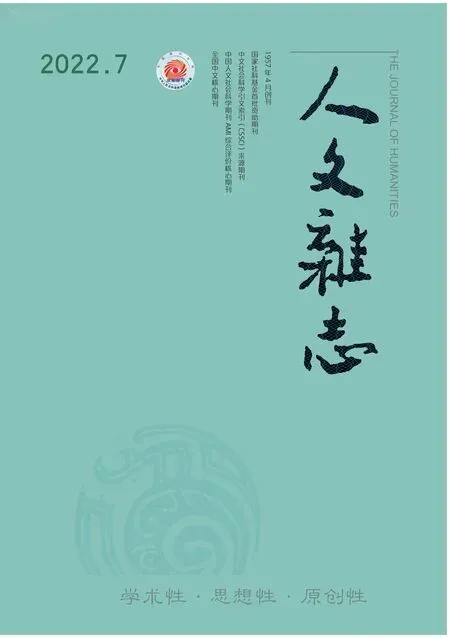歷史真理與理性差序:《格薩爾》學術史寫作問題*
《格薩爾》學術史寫作應該遵循《格薩爾》學術歷史事實、學術發展的歷史規律,以及學術歷史意義。《格薩爾》學術史寫作是以學術發展的歷史史料為基礎,是對這些史料的甄別和重新發現。《格薩爾》學術史寫作要強調多維視野和多種理解范式,要對《格薩爾》的搜集、整理、翻譯、出版和研究進行較為全面、系統和科學的歸納和總結。《格薩爾》學術史的構成是多元的,這與《格薩爾》本身的“史詩性”品格、“大百科全書式”的內涵有著重要的關聯性。《格薩爾》史詩的豐富性、復雜性以及融涵性,共同決定了《格薩爾》學術史寫作思路和方式。我們可以從歷史與理性、史料與編纂兩個量度對《格薩爾》學術史寫作的認知差序和理性差序進行實證性分析和理論性闡釋,進而提出史實與真理兩個學術史寫作的維度,以實現《格薩爾》學術史研究的客觀性、真實性和價值意義,從而達成對《格薩爾》史詩學術研究歷史的科學、合理、有效、完整理解的寫作目的。
一、歷史與理性:《格薩爾》學術史寫作的認知差序
《格薩爾》研究者眾多,但研究者的水平參差不齊,且每個研究者由于所處時代不同,政治認知、社會利益、個人道德、學養水平等差異較大,不同學者的研究成果的價值區別也較大。因此,《格薩爾》學術史寫作既要重視其包含的連續性“歷史真理”中的相對性,也不可忽視其不連續性“理性差序”的具體性。歷史真理是指歷時性發展中普遍與具體的基本統一性問題,包含著真理的諸多特征,體現為客觀與主觀、絕對與相對的辯證統一,是具體的、真理的一個動態建構過程。《格薩爾》學術史寫作中的“歷史真理”體現為學術史書寫者與《格薩爾》這一研究對象在具體歷史條件與范圍中的一致性,即“期待的客觀性所隱含的主觀性”
的相對狀態。認知差序是指因人的認知水平、個體情感、社會政治經濟因素等方面的差異而形成的理性能力的局限性、相對性與有限性。由于人類認知差序,不同歷史階段的格薩爾學研究都會受到具體歷史條件和時代語境的限制,每位格薩爾研究者個人所獲得的“歷史真理”都具有相對性,是帶有一定主觀認識色彩的相對真理。《格薩爾》學術史的寫作就是揚棄“歷史真理”的相對性和人類認知差序的具體性,從而構建起真正的“真實的”“客觀的”史實、史觀和史論。
1.3 中藥拉丁名與基源植物的拉丁學名在對中藥整體認知中的作用 使用中藥基源植物正確的拉丁學名,是在藥典中準確檢索到與之對應的中藥材及其制劑信息的重要手段。同時使用上述4種檢索方式,便于學生認識中藥材中文名、拉丁名和基源植物的拉丁學名之間的對應關系。加上藥典正文的描述,便于進一步從性狀、鑒別等方面對基源植物、藥用部位建立起整體認識。中藥基源植物的拉丁學名和中藥材的拉丁名是國際上通用的名稱,準確掌握與使用有利于國際間的交流與合作研究。
人類的理性存在著明顯的差序。這里的差序是指按照一定的次序或關系所產生的級差。費孝通說,“這個人和人往來所構成的網絡中的綱紀,就是一個差序,也就是倫。”“‘倫’的本意,即‘共同表示的是條理,類別,秩序的一番意思’。”
每個格薩爾學研究者,由于認識水平、個體道德、政治主張,以及社會利益等方面的差異,其學術研究成果也會或多或少烙上印跡。具體而言,這些差序體現在歷史認知、資料真偽和歷史編纂幾個方面。歷史認知是《格薩爾》研究者因主觀原因造成的個體差異。這些原因主要有主觀偏差、有意歪曲,以及先入為主的民族自我認同等。曹丕曾言:“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暗于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
面對同一文本對象,常有“貴遠賤近”之嫌。由于《格薩爾》研究者擁有不同的文化教育背景、人生經歷和宗教信仰等,因此他們會從不同的側面和維度介紹和解釋《格薩爾》,即使在此一過程中難免對《格薩爾》的“研究歷史”“研究史料”等作出有失客觀的歷史解釋,但其研究在一定的時代語境當中也具有相對的真理性,就如克羅齊所言:“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
從歷史哲學的角度來看,學者按照自己當代現實生活的價值標準和推理邏輯編寫出來的《格薩爾》研究,也是真歷史。譬如,以《格薩爾》學術史中的對史詩的文化觀照為例,法國著名藏學家桑德拉·大衛-妮爾的《嶺·格薩爾王的超人一生》(1934)對格薩爾的經歷予以論述,她認為格薩爾使人們的思想有可能達到最終的自我實現的教義,關注于宗教的神秘性,而缺乏關于宗教深層意義的思考。卡蒂亞·巴菲特里爾《“愿新的事物從古老中誕生!愿古人為現在服務!”瑪沁縣的格薩爾節日(安多2002)》(2009)一文闡述了格薩爾與阿尼瑪沁山的守護關系,詳細描述、分析了紀念活動中的儀式、史詩表演等,進一步研究了格薩爾現代發展與當下意義。美國學者陶音魁的《超越吟游詩人的藏族〈格薩爾〉史詩:世界屋脊上的體裁生態系統》(2019)一文超越了傳統的史詩認識論,借由與格薩爾相關的諺語和本土化微觀敘事,探究了《格薩爾》的體裁生態系統。
他們的研究都是處于不同文化背景當中,以不同的視角和維度進行切入和展開的,具有一定的認知差序和局限,但也具有相對的歷史真理和價值意義,即使在歷史語境和認知差序的雙重限制之下,有些研究依然能夠脫穎而出,抵擋時間的洪流而屹立于歷史的長河之中。如談到《格薩爾》研究,就要論及法國學者石泰安的《藏族格薩爾王傳與演唱藝人研究》(1959)、《格薩爾和他的祭祀》(1970)、《格薩爾史詩》(1980),還有在國內出版的《西藏史詩和說唱藝人》(石泰安著、耿昇譯、陳慶英校訂,中國藏學出版社,2012年)。作為學術研究史料,石泰安的學術著作,包括他譯成法文的《嶺地喇嘛教版藏族〈格薩爾〉王傳譯本》《格薩爾生平的西藏畫卷》等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這些著作為我們研究《格薩爾》以及《格薩爾》學術史樹立了典范和榜樣,并時刻啟示著后世的學者,縱使歷史理性和認知差序的問題讓我們只能無限接近歷史真理,而無法徹底抵達真理之境,但苦心鉆研、實事求是的研究論著,終究可以抵擋住時間的沖刷、占據相對真理的高地而為人尊重。
《格薩爾》學術史的寫作應該強調“歷史敘事”的真實性,應該秉持中國傳統史家的“實錄”精神,應該從各種史料和證據中進行客觀還原,應該在《格薩爾》各學科中尋找史料和證據的“可驗證性”。在英國史學家邁克爾·奧克肖特看來,歷史包含兩種要素:(1)在特定時間內發生的各種事件;(2)人的頭腦中收集起來的事件。歷史既是過去的事實又是現在的檔案。檔案的真實性依賴于過去事實的真實性。
在特定時間內發生的各種事件,需要借助證據才能具體認識,是一種“歷史的事實”。由人的頭腦收集起來的這些事件,是主體的直接感知和體驗,是一種“現在的事實”。歷史與現在,在時間的隧道中共振,生成“歷史的真實”與“真實的歷史”。關于《格薩爾》學的知識資料“在我國20世紀前的大約700多年時間里,約有40多種藏文史書典籍記載了不同身世的歷史(或傳說)人物——格薩爾的活動”。
如何對這些文獻資料進行梳理、甄別,既要有當下的學術眼光,同時也要從“真實性”和“學術性”兩個維度,對這些“過去的事實”“現在的檔案”進行學術考察。這實際上就是人類理性存在著差異的折射。就《格薩爾》研究資料來看,這種差序主要體現在歷史文獻資料的真偽、歷史認知和歷史編纂方面。
《格薩爾》研究歷史文獻資料的真偽,既有研究者主觀意圖的原因,也有客觀歷史因素。具體而言,一是《格薩爾》流傳久遠,有一個不斷接受、認可,最終神圣化的過程,這一過程中形成的史料汗牛充棟,我們需要對其加以辨別和甄選。如任乃強對“藏三國”進行了考辨,可參見《〈藏三國〉的初步介紹》《關于〈藏三國〉》《關于格薩爾到中國的事》。
在徐國瓊看來,“格薩爾王故事的來源,有一部分可能在格薩爾生存的年代,人們就以集體創作和口頭說唱的方式在民間流傳”。
在流傳過程中,一方面是說唱藝人的活態傳承,另一方面是文人的記錄、加工、整理和再創作。由此,在民間產生和流傳著各種各樣的不同抄本。比較有代表性的版本有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年出版的劉立千《格薩爾王傳》,甘肅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王沂暖、華甲《格薩爾王——貴德分章本》,寶文堂書店1987年出版的降邊嘉措、吳偉《格薩爾王全傳(上、中、下)》,甘肅民族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王興先主編《格薩爾文庫》,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角巴東主《格薩爾王傳》,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10—2019年出版的《〈格薩爾〉藝人桑珠說唱本叢書(藏譯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西北民族大學格薩爾研究院編纂的30冊《格薩爾文庫》;此外,還有西藏社科院出版的說唱本,青海文聯出版的精選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的精選本等,以及國內關于《格薩爾》史詩的漢譯、民譯、外譯、回譯等多種版本。
不同的研究者,閱讀的版本不同,形成的閱讀接受、體驗、判斷和認知也不同。研究者的學術研究在某種程度上說,依賴于這些“文本”所承載的信息。但我們也要明白,歷史在發展,時代在進步,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研究。這里所說的學術研究的時代性,主要指的是符合時代學術研究的新觀念、新思維和新的表達方式。這也即是影響人類理性差序的時代性因素。
廣墾橡膠集團是2002年經農業部批準成立,由廣東省農墾集團公司控股,集天然橡膠種植、加工、銷售和研發于一體的大型國有跨國集團企業。集團注冊資本19.48億元,資產總額近100億元,在國內外擁有60余家天然橡膠種植、加工、貿易企業,2所科研機構以及32個橡膠種植基地農場。廣墾橡膠集團是農業產業化國家重點龍頭企業,先后榮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誠信橡膠產業服務商、中國橡膠貿易十強企業、中國走進東盟十大成功企業、全國農業先進集體、廣東省五一勞動獎狀,以及國家和省級名牌產品等榮譽稱號。
二、史料與編纂:《格薩爾》學術史寫作的理性差序
沒有大起沒有大落的時候,許峰打來了電話,她當時差點兒把電話摔了,是啊,有電話號碼啊。可是她自己都不明白,她那么想念,卻沒有想過給許峰打個電話,或發條短信。
當我們從歷史學歷時化的角度去觀察《格薩爾》的研究,就會發現處于不同社會時間和空間的學者,對《格薩爾》的認知也具有較大的差序問題。譬如20世紀五六十年代和20世紀80年代對《格薩爾》的民族學研究就存在很大的認知偏差問題。當然,21世紀以來和20世紀的《格薩爾》民族學研究也存在一定的認知偏差。如《格薩爾》研究界普遍認為,王沂暖等老一代學者翻譯的《格薩爾》部本是比較好的版本。事實上,《格薩爾》史詩是活態的史詩,是在不斷地傳唱中豐富和發展的。今天的《格薩爾》藝人和扎巴、玉梅、阿旺嘉措、阿達爾等藝人的生存語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些時代元素加入了說唱部本。如果比較一下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格薩爾》部本和2018年版30卷《格薩爾文庫》,其潛在的變化可見一斑。80年代的部本雖然故事主干基本完善,但是唱詞相對比較簡短,而《格薩爾文庫》則是在廣泛搜集和整理了大量藝人說唱的史料后編纂和整理的,其唱詞較為豐富和多樣,篇幅相對較長。在學術研究中,我們強調回到歷史文化語境,就是“為了達到我們的目的,通過觀察歷史的視覺呈現能夠最具啟發性地闡明古典秩序”。
這種“古典秩序”的闡明事實上就是一種以回歸的方式進行對話而由次序和關系所產生的級差,也即“差序”。《格薩爾》史詩雖然原初形成于藏族社會和藏族文化,但在“北傳”的流布過程中,進入到了蒙古族、裕固族、土族等北方民族,甚至遠傳到西伯利亞地區。《格薩爾》史詩在“南傳”過程中,則進入到了白族、納西族,以及喜馬拉雅南麓各民族。可以說,從中亞到東北亞都有《格薩爾》史詩在傳唱。而對《格薩爾》史詩的學術研究和考察,可以上溯到公元9至13世紀以“贊頌歌”形式對其進行的討論。當然這種討論和我們今天所談及的學術研究相差甚遠。國外對《格薩爾》史詩進行的學術研究,較早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1957年蒙古國學者策·達木丁蘇倫的《“格斯爾”的歷史源流》,1959年法國學者石泰安的博士論文《西藏史詩和說唱藝人》。綜上,國內國外研究的語境和視角有著較大的差異,得出的研究結論也不盡相同。可以說在《格薩爾》史詩學術研究的歷史敘事中,存在著民族、地域、國家和人類理性差序。
二是格薩爾是英雄的化身,《格薩爾》史詩本身承載著“人民要求和平統一、社會安定的美好愿望”。降邊嘉措在談到藏族先民的社會理想與美好愿望時說,“真、善、美與假、惡、丑之間的斗爭,像一條紅線,貫穿了《格薩爾》;對真、善、美的熱烈向往和執著追求,成為整部史詩的主旋律。”
《格薩爾》既是“民族共同體”,也是“政治共同體”和“道德共同體”。在《格薩爾》研究中,“民族”“政治”“道德”就成為三個有效的研究視角。關于“共同體”,鮑曼有一個詩意的描述:“‘共同體’意味著的并不是一種我們可以獲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種我們將熱切希望棲息、希望重新擁有的世界。”
我們套用鮑曼的說法,可以這樣表達,作為“民族、政治、道德共同體”的《格薩爾》意味著的并不是我們已經拓展了《格薩爾》研究空間和獲得了《格薩爾》研究成績,而是我們將熱切希望重新擁有一種整體性視野,拓寬研究思路,超越“單向層面”與“整體視閾”之間的矛盾。這三個維度,或者說是三重視閾,“出發點不同,闡發的概念不同,建立的理論不同,進而實現的理論訴求不同”。
正是這樣不同的層面和維度,才能夠為《格薩爾》學術史研究提供“整體性”學理依據。當然,從“民族共同體”的維度對《格薩爾》進行學術研究的成果較多,但由于人類認識的理性差序,我們對《格薩爾》學術史的把握也存在著一定的相對性和有限性,且在歷史編纂、歷史資料方面也存在較大差序。在尕藏才旦看來,“格薩爾時代是‘神授王權’‘天子下凡’的時代,它體現的正是原始社會開始解體、奴隸制國家開始萌芽的特殊歷史階段”。
這一時代,生產力低下,物質匱乏,是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過渡時期,母權制痕跡明顯。在《格薩爾》史詩中,“缺乏宗教色彩,只有神話色彩,圖騰拜物很明顯”。
研究者往往對史詩產生的歷史語境了解得不深入,尤其是一些初入史詩研究的學人,其研究成果和史詩所承載的歷史及時代內涵有著明顯的差序,這就影響了研究成果的真實性、可靠性和科學性。在進行學術史料的梳理時,既需要“祛蔽存真”,也需要“解蔽”和開放。人類理性差序,既有客觀理性的因素,也有主觀自我的原因。重新回到《格薩爾》史詩本身,回到《格薩爾》史詩生成和流變的歷史語境,站在新時代的高度重新審視《格薩爾》史詩研究,才能真正做到“正本清源、守正創新”。
三是在《格薩爾》史詩的編纂過程中,也應關注到西方理論和方法的借鑒與運用,既有“別求新聲于異邦”的拿來主義,也出現了對這些理論和方法的生吞活剝,尤其是在后現代主義、解構主義思潮下,學術研究相對化、碎片化和虛無化。新時期以來,《格薩爾》史詩受西方理論和方法的影響,出現了一批以西方理論為軸心范式的研究成果。在今天看來,這些成果一方面拓展了《格薩爾》史詩的研究空間,打開了一些“塵封”的意義世界,另一方面這些新理論、新方法、新視角遮蔽了《格薩爾》史詩中蘊涵的民族的、文化的、歷史的質料。當然,研究者個人興趣與經歷也往往影響著學術研究和學術判斷。在《格薩爾》學術史研究中,我們要努力做到“格物致知,信而有證”。
在聶珍釗看來,“這種學術史研究的視角避免了研究者個人的主觀局限性”。
因此,應辯證地看待他人的研究成果、學術觀點,對這些成果和觀點進行有機融通和吸收借鑒,做到真正的學術創新。
3.格蘭杰因果檢驗。利用格蘭杰因果分析對數據指標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得出人民幣匯率預期(DNDF)、境內外利差(DLC)與貨物貿易跨境資金流出(DLOHW)之間的格蘭杰因果關系(如表3所示)。從結果來看,人民幣匯率預期(DNDF)與貨物貿易跨境資金流出(DLOHW)之間存在雙向格蘭杰因果關系,境內外利差(DLC)與貨物貿易跨境資金流出(DLOHW)之間也存在雙向格蘭杰因果關系,且人民幣匯率預期(DNDF)對貨物貿易跨境資金流出(DLOHW)的影響較境內外利差(DLC)對貨物貿易跨境資金流出(DLOHW)的影響顯著。
從兩個世紀對《格薩爾》史詩文化觀照的對比來看,其研究成果具有不同內涵,呈現出中心向外延展的趨勢,這也是人類認知差序在《格薩爾》學術史書寫中的具體體現。問題是,我們如何以一種“問題意識”來面對這些學術史料,如何讓這些學術史料在當代生發出應有的意義和價值來。同時,我們也要避免過分強調“當代性”或者“時代性”。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學術,我們既不能“厚古薄今”,也不可“厚今薄古”。《格薩爾》學術史的研究要克服主觀謬偏,要將個性與風格有機地融通于學術史的研究中,要“蓋文疑則闕,貴信使也”。
在《格薩爾》史詩研究中,有意歪曲的情況較少,但也存在對研究對象的不客觀對待現象,尤其是先入為主的民族自我認同問題更為明顯。在一段時期內,“《格薩爾》被定為‘大毒草’,禁止說唱、搜集、出版、發行,一些民間藝人與格薩爾工作者受到殘酷迫害。”
《格薩爾》被譽為藏民族的“心靈史”“文化史”“大百科全書”,先入為主的民族自我認同問題和《格薩爾》在藏族人民心目中的位置有著密切關系。
訪談中,莊浩一再強調時代背景對于創業的重要性。在她看來,其趕上了中國發展速度最快的十年,而這個時期正是個人能力體現的最佳時機。確實,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涌現了一批“下海”試水的勇者,其在享受著急速擴容的經濟規模和不斷升級的消費能力所帶來的發展紅利的同時,也會面對因未跟上快速發展步伐而被淘汰的窘迫,所以創新成為企業發展甚而生存的必然。
在《格薩爾》學術史的寫作和研究中,史實和真理是兩個重要的思考維度。學術史寫作中的“史實”不是歷史敘事中的“實情”,也不是學者學術歷史的還原,而是對學術歷史的“絕對真理”的把握。我們可以通過對這些學術研究史料的梳理和勘探來構建學術史實,這在《格薩爾》學術史的研究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格薩爾》研究起步早,但起點低,高質量、系統性、理論性的研究不夠,也較為零散,這就為《格薩爾》學術史的寫作和研究帶來一定困難。如何彌補《格薩爾》學術歷史的“碎片化”,如何從這些“碎片化”的學術歷史中淘洗出有價值有意義的東西,是我們必須直面的問題,也是進一步推動《格薩爾》學術研究的意義旨歸。
三、史實與真理:《格薩爾》學術史寫作的兩個維度
總之,《格薩爾》學術史的研究就是要追求“客觀真理”。當然這種追求一定要以“史實”為基本依據,要做到“凡研究一個時代思潮,必須把前頭的時代略為認清,才能知道那來龍去脈。”
對歷史和傳統進行重新認知、判斷和評價,這也是學術史研究的題中之意。以一種更具問題意識的方式,對《格薩爾》史詩進行學術史和學科史研究,是一種避免形式主義和低水平重復研究的有效之法。王學典認為,“歷史研究有兩大任務,一是發現和清理事實,二是說明和解釋事實。”
可以說,在《格薩爾》學術史研究中,也有兩大任務,一是發現和清理《格薩爾》學術研究事實,二是說明和解釋這些學術事實。如何做好這兩大任務,是《格薩爾》學術史研究重點考慮的問題。筆者以為,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著手:一是從《格薩爾》學術史流變的視角來確立《格薩爾》學術史研究的研究范疇、基本問題和理論依據。二是《格薩爾》學術史研究應該包涵史料譜系、問題譜系、方法譜系和價值譜系,并且這四個方面是內在的、共生的和互動的關系。三是從《格薩爾》史詩本身出發,思考《格薩爾》學術史研究在整個《格薩爾》學科體系建構過程中的意義和價值。當然,由于研究者的理性制約和《格薩爾》學科發展的規律,每個階段的研究成果都允許被質疑和批評,這樣才能在揚棄中走向建構。
對《格薩爾》進行學術史研究,我們既可以采取中國古代史家所主張的“實錄”,也可以取用西方史家對“事實”進行闡釋的做法。不同歷史時期,《格薩爾》學術研究成果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即便是同一歷史時期,學術成果的代表性、標志性、典型性也有所區別。這也就是皮爾斯所說的“具體的事實一定是發生在某種條件下的描述中”。
Charles S. Peirce, “The Law of Mind,” , vol.2, no.4, 1892, p.555.
譬如早期的《格薩爾》研究就以搜集、整理為主。降邊嘉措認為,《格薩爾》“手抄本的大量出現,是在11世紀前后,隨著后弘期佛教的發展,得到廣泛流傳,這就是所謂‘伏藏’本《格薩爾》故事。藏語叫‘德仲’的那些被稱作‘掘藏大師’的僧侶文人,對于手抄本的撰寫和傳播,曾經做出過重大貢獻……他們可能就是藏族歷史上最早從事《格薩爾》搜集、整理的僧侶文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對《格薩爾》進行了較大范圍的調查、搜集與整理。如西北民族學院翻譯科和藏文教研室組織人員深入甘南、青海、四川藏區,從民間搜集、整理到《天嶺》《誕生》《賽馬》《降魔》《八十英雄傳》《姜嶺》《象雄宗》《朱古兵器宗》《大食財宗》《世界公桑》《香香藥物宗》《松巴犏牛宗》等20多部史詩文本。1979年之后對《格薩爾》進行了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搶救性搜集、整理工作,“到1997年6月,全國共搜集到藏文手抄本、木刻本289部,除去異文本,約100部。”
直至1997年召開的第五次全國《格薩爾》工作會議才明確提出,《格薩爾》工作重點由搶救性的搜集、整理逐漸轉向以記錄、整理、翻譯、編纂、出版、研究為中心的綜合性工作。當然,這一時期也有一些重要的學術論著產生。代表性的著作有:降邊嘉措的《格薩爾初探》《〈格薩爾〉與藏族文化》、楊恩洪的《民間詩神——格薩爾藝術研究》、王興先的《〈格薩爾〉論要》、趙秉理的《格學散論》、何峰的《〈格薩爾〉與藏族部落》、角巴東珠的《〈格薩爾〉疑難新論》等。這些著作從不同層面對《格薩爾》史詩進行了開拓性研究,其代表性、標志性、典型性也有所不同。譬如降邊嘉措的《格薩爾初探》、王興先的《〈格薩爾〉論要》是綜合性研究,是格薩爾學科建設的奠基性著作,可以當作教材來使用。
在《格薩爾》學術史研究中,我們也明白,史實不等同于客觀事實,不是絕對真理。我們只有通過構建史實,以一種歷史敘事的方式“客觀還原”。當然,在這種“客觀還原”中也會或隱或顯地夾雜著論者的某種價值判斷。如何將這種“真理”與“真實”貫穿于《格薩爾》學術史的寫作中,是我們必須要考慮的問題。一是有效縫合“碎片化”的研究史料,從而建構起客觀歷史史實的闡釋體系。研究資料是“碎片化”的,即便是標志性的學術論著,也由于《格薩爾》史詩本身的博大和豐富性而使研究呈現多層面多角度性。這些從不同層面和不同角度對《格薩爾》史詩的研究,統攝在學術史的視野中就會獲得差異性判斷。此外,《格薩爾》史詩研究史料眾多,誠然“時至今日,沒有哪位歷史學家掌握了與其課題有關的全部資料”。
G.R.Potter,ed., , 1, ,1493-152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pp.xvi-xvii.
從11世紀有記載的整理研究至今,《格薩爾》史詩說唱部本和寫本較多,僅西北民族大學就曾編纂出版《格薩爾文庫》3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國外格薩爾研究史料,由于語言和翻譯的限制,一些較有學術價值的文獻亦難以窮盡。當然,就我們現在收集到的研究史料來說,“從其中納入自己的概念之中、從而納入自己的認識之中的東西,與他必須舍棄的東西相比,簡直是極其微不足道的。”
對已有的研究史料進行學術甄別、歸納和抽象,從而得出合乎邏輯的結論,其意義和價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二是對《格薩爾》史詩研究史料中“共性”和“類性”問題的研究,既是方法論的凸顯,也是對“事物異質性原理”的深刻揭示。所謂“方法論的凸顯”是指這些“共性”和“類性”問題,是對大量《格薩爾》史詩研究史料的綜合、歸納、類比和抽象,是一種透過“材料”對“本質”的揭示。當然,“史學家所運用的研究方法在理論上都存在缺陷,我們只能選擇較合理和較好的方法。畢竟,一切事物除了異質性外,還具有共性和類性。”
共性和類性也是我們進行《格薩爾》學術史研究的邏輯基礎。我們通過對《格薩爾》文學研究、語言學研究、史學研究、民族學研究、宗教學研究、民俗學研究、藝術研究、藝人研究,以及比較研究等的文獻史料疏證,發現《格薩爾》學術史的研究還可以從這些方面拓展,即《格薩爾》發展史、《格薩爾》搜集整理史、《格薩爾》藝術史、《格薩爾》翻譯史、《格薩爾》藝人成長史、《格薩爾》版本史、《格薩爾》多學科研究史等。我們在對《格薩爾》研究史料的綜合、歸納、類比時,生成了一些新的《格薩爾》學術史研究論域。這些論域的深入探討,又從共性和類性方面豐富和發展了《格薩爾》學術史。
三是學術史與其他學科的“融合”與“互動”,從而在更為深廣的層面上激活《格薩爾》學術史。《格薩爾》學術史包涵的內容豐富,卻又涉及門類較廣,文學、語言、文獻、版本、民俗、民族、文化、史學、藝術、宗教、軍事、社會等學科都在《格薩爾》研究中有著深度融合。《格薩爾》史詩與這些學科的跨界融合與對話,又構建起了新的《格薩爾》學術史體系。譬如《格薩爾》版本學研究,“我們首先應該從版本學的角度理順各種文本之間的關系,才能較全面、系統地整理、翻譯、研究《格薩爾》。對《格薩爾》版本的整理、翻譯、研究,首先應該區分早期版本和現代藝人的版本。”
《格薩爾》版本眾多,僅曼秀·仁青道吉就“搜集到四百多部《格薩爾》藏文原著,其中鉛印本有較早期的版本(包括木刻本、手抄本、掘藏本,以及其鉛印本)二百二十五部,現代藝人說唱記錄整理本一百多部,以及其他版本一百多部。”
可見,對《格薩爾》史詩進行版本學研究很有必要。如果沒有《格薩爾》版本學的縱深化研究,就會給《格薩爾》學術史的寫作帶來諸多困惑和問題。
四是辯證地看待“史實與真理”。“史實與真理”既是辯證的,又是互為一體的。對于《格薩爾》學術史寫作,我們不能只把它看作史詩觀念和知識體系來描述,而更應該將其置于藏族民族歷史文化發展的長河之中,用“民族宗教”和“歷史文化”來把握,這樣方能理解作為民族史詩的《格薩爾》,也才能將史詩學術研究博大精深的“學問”之下的“詩意”“溫情”與“想象力”表達出來。真理具有時間性,也是相對的。以《格薩爾》史詩研究中格薩爾身份辨析這一學術探究而論,該論題體現出《格薩爾》學術史書寫中歷史真理的相對性。早期《格薩爾》史詩研究中,對格薩爾身份的思考更為具體,以考據其歷史真實性作為核心,傾向于為格薩爾賦予一種切實存在的特性。例如,貝利(H.W.Bailey)在《龜茲研究》(1952)中提出于闐文文獻里記載有“格薩爾王子”,《格薩爾王傳的歷史源流》(莫斯科 1957)則考證了格薩爾就是11世紀的宋代青唐吐蕃首領唃廝啰,
等等。隨著研究的深入,關于格薩爾身份的研究不再拘泥于真實性的探究,而是拓展為更普遍、抽象的思考。例如,諾伊·廷格斯坦在《拉達克的歌曲、文化表征與混雜》(2013)一文中論述了格薩爾形象的演變,在辨析格薩爾君主身份之外,還探討了其另一重“前佛教原型”形象。
Noe Dinnerstein, “Songs,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Hybridity in Ladakh,” , , vol.32,no.1, 2013, p.16.
從整體《格薩爾》學術史書寫來看,早期研究對格薩爾身份的辨別與表述,試圖為格薩爾賦予一個與宏壯史詩描述適配的高貴出身,而后期研究逐漸轉變為在“先驗性”統攝下探究其形象與意義。這一學術史書寫的變化,體現了《格薩爾》學者在不同時期對《格薩爾》史詩這一研究對象價值判斷的不同,是歷史真理相對性的具體呈現。在一定時間段,對《格薩爾》史詩學術研究史料、史實的認知具有“真理性”,而超過這一時期,認知就會發生很大的變化,甚至會出現后來的認知顛覆了前面的認知。恩格斯說:“誰要在這里獵取最后的終極的真理,獵取真正的、根本不變的真理,那么他是不會有什么收獲的,除非是一些陳詞濫調和老生常談。”
人的認知是有限的,是相對的。人的認知往往受時代、個體經歷、地域文化,還有教育背景等因素的影響,可以說,任何人都不可能達到至高真理,“因為一旦把真理凝定起來,認識就會陷入死胡同。”
面對豐富駁雜的《格薩爾》研究史料,只有“通過我們的有限性、我們存在的特殊性,才在我們所在的真理方向上開辟了無限的對話”。
“對話”既是一種研究姿態,也是一種研究方法。同時,只有“對話”才能有效激活“史實”與“真理”,才能將“史實”與“真理”辯證統一于《格薩爾》學術史研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