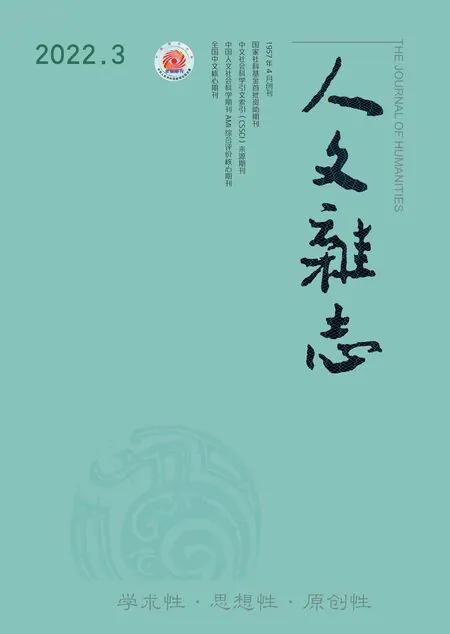秦、漢“太上皇”政治文化透視*
——從“家人父子禮”到“朝廷君臣禮”
“太上皇”的名號與“皇帝”名號一樣,和皇權政體緊密相關,但對其研究稍顯不足。
且在已有論述中,秦漢“太上皇”通常是被置于同一視域下予以整體性言說。在筆者看來,秦、漢“太上皇”盡管在制式名號上雷同,然兩者內在的意蘊卻存有一定差異。
一、賴宗廟神靈:始皇帝“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
“太上皇”作為中國政治文化中有著特殊意蘊的稱謂,由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中央集權帝國的締造者——秦始皇所創設。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載:
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 ‘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
我們看到,在“皇帝”名號創設過程中,不僅有諸大臣的廣泛參與和深入討論,更有內蘊上的諸多考量。相形之下,“太上皇”的出爐則簡易許多。乃始皇帝取“皇帝”之“皇”,與其時社會習用之語——“太上”相組合,用以“追尊”故父莊襄王。
“不行!一千個理由也好,一萬個理由也罷,就是倆字:不行!”馬國平狠心說,“給你兩條路:要么你卷起鋪蓋、摘下領花,走人;要么用血汗書寫你的軍旅生涯,作為你給菊花結婚的禮物!自己選!”……
對于“太上皇”緣何僅稱“皇”而不及“帝”,一說以為重在彰顯其“德”,以“皇者”之德大于“帝”,司馬貞《索隱》云:“按:《本紀》秦始皇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已有故事矣。蓋太上者,無上也。皇者德大于帝,欲尊其父,故號曰太上皇也 。”
對于“皇”和“帝”,張蔭麟先生以為,“戰國以前,人主最高的尊號是王,天神最高的尊號是帝。自從諸侯王稱王后,王已失了最高的地位,于是把帝拉下來代替,而別以本有光大之義的‘皇’字稱最高的天神。但自從東西帝之議起,帝在人間,又失去了最高的地位了。很自然的辦法,是把皇字挪下來。”
即是說,用“皇”而不用“帝”,實乃秦始皇為了表達對莊襄王這位在位僅幾年的君王政治功業的肯定,
故用“皇”而不用“帝”彰顯之。一說則以為言“皇”,是為了凸顯其與現實政治中實際擁有政治權力的“天子”即“帝”的區別,在于“不欲治國”。太上,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也。”
裴骃《集解》云:“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即始皇帝追封其父“太上皇”,更多的旨在突出自己“稱帝的獨一無二、唯我獨尊的權威性。即使是養育他的生身之父也不能染指這一帝字。”
而“皇”前配以“太上”,作為“極尊之稱也”,
則是基于身為開創了“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之功的“皇帝”之父,在社會層次序列中自當“等之最居上者”。
即是說,在專制皇權政體之下,作為皇帝之父,雖不能染指皇權,但禮制上卻是可以享“太上”之尊位與榮光的。
高校圖書館在閱讀推廣工作中,要緊跟潮流不斷創新,微信的普及為圖書館的閱讀推廣工作提供了更多可能。基于微信小打卡組織的閱讀推廣活動形式簡便,讀者參與門檻低,能夠激發讀者閱讀興趣,引入學生團隊進行策劃和管理,使活動更加貼近大學生活,采用線上線下結合的方式,相互促進相互補充,提高讀者的粘性。充分利用微信平臺的新功能,拓展閱讀推廣渠道,簡化活動形式,打破時間空間限制,讓更多的學生能夠參與活動,提高閱讀推廣的品質。
考秦“太上皇”,乃始皇帝為已故之父莊襄王進行的追封。作為已故的太上皇,自然少卻了對現實政治中皇權政體以及皇權主義秩序的困擾與沖擊。故其更多透視的應是始皇帝承襲三代以來的血緣貴族統治,基于人倫血緣,對祖先宗廟神靈的禮遇與尊崇。“宗廟”原是起源于祖先崇拜的自然親情和祭祀活動,“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
“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
“古者廟以祀先祖。”
“尊其先祖而以是儀貌之,故曰宗廟。”
即其本初“強調的是先祖與子孫后代之間明確可溯的血緣世系”。
隨著社會等級的發展,宗廟禮制亦不斷擴充,尤其是“當宗廟的禮制性與社會階層、等級等現象發生聯系后,其所謂‘以親親之義經尊尊之義’的宗法——政治功用也愈發明顯,宗廟逐漸成為維系貴族階層宗族關系的和維護社會等級秩序的重要手段。”
自三代以降,“宗廟”在政治文化中占據了相當重要的地位。誠如學者所言,“承宗廟”“在先秦政治生活中已經成為語言定式”。
秦滅六國,創建首個中央集權大一統帝國,以郡縣代替分封,盡管如此,基于血緣宗法的宗廟制度并未隨之而消亡,相反,在皇權政體中,“承宗廟”成為帝王的首要責任,“宗廟重于君”,
且“是否‘可以承宗廟’,是決定最高執政者人選的決定性條件”。
即是說,宗廟不僅是“敬祖”的重要表現形式,更成為從親緣解釋王權合理傳遞的重要來源。
觀之始皇帝, 反復宣傳祖廟的庇護是自己取得勝利的主要原因之一,“賴宗廟,天下初定”。
對此,劉澤華先生揭示道,“在那個時代,祖宗崇拜是論證現實合理的重要理論之一,也是人們普遍接受的一種價值觀念。”
考諸秦,在其尚為僻居西隅的諸侯國時,對祖先宗廟就已經相當重視。有學者通過對陜西鳳翔馬家莊1號建筑群遺址的考察,認為在該遺址中,“宗廟建筑與朝政宮殿平起平坐,此現象鮮明反映了先秦之前帝王對王權的重視程度,同時體現出政治體系基本都是以血統關系維持。”
由此揭示出早在春秋時期,秦已然相當重視宗廟文化,尤其注重宗廟在王國政治中的功效。此外,早在大一統帝國建立之前,其就已有遵從周制,
追尊逝去祖先的做法。
如“襄公始為諸侯,莊公已稱公者,蓋追謚之也”。
故《日知錄集釋》卷一四“太上皇”條:“《秦始皇本紀》:‘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是死而追尊之號,猶周曰‘太王’也。”
由此而論,秦始皇追尊其故父為太上皇,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宗廟血緣,對三代“追尊”風尚的一種承襲;另一方面同時也是對于祖先所開創洪烈的認同,“自繆公以來,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為諸侯雄。”
觀之被追尊為“太上皇”的莊襄王,雖然在位僅僅幾年,但卻給秦王嬴政留下了豐厚的政治遺產:
在工程問題中目標函數通常具有特殊性,很適合應用極小極大值算法求解,但是計算量的龐大和非線性限制了極小極大值算法的應用。隨著計算機技術的快速發展,極小極大值算法在工程設計、電子線路規劃、對策論和博弈論等很多領域有著越來越廣泛的應用,備受關注。在大多數工程問題中,極小極大值問題具體的數學模型如下式所示:
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
在介紹集成學習的基本概念基礎上,研究了當前集成學習方法的評價標準,分析了常用的分類器集成學習算法和結果整合集成方法,對集成學習方法有綜合充分了解。
對于“皇帝”,不僅身為貴族的項羽意欲“取而代也”,
連庸耕之陳涉,也同樣存有“富貴”“鴻鵠之志”,
待得稱王,更是“夥,涉之為王沈沈者”。
劉邦在尚為匹夫時亦認為“大丈夫當如此矣”!
也就是說,劉邦雖然平民出身,但“意識中卻很清楚的仍然愿做舊時的貴族”,
也更想做至尊至貴的皇帝。這由其初登帝位,看到昔日一同打天下的兄弟而今的群臣在朝堂上“飲酒爭功,醉或妄呼”,甚或“拔劍擊柱”時心里的“患之”“厭之”窺得一斑。待得叔孫通定朝儀,“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無敢觀嘩失禮者”,劉邦則發出“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的由衷興嘆。
對此,有學者揭示道,“凡作群眾領袖的,不論他原來所屬的階級高低,他們最終的目的都是為個人爬上更高的階級,為取得富貴。得到富貴以后,自然成為貴族,不論何人并無任何的階級自覺。”
也就是說,“人分尊卑貴賤是當時普遍存在的社會事實”,而“在尊卑貴賤中,思想家們幾乎一致認為君主是至尊至貴者”。
如此,西漢王朝承秦之制尤其是承襲以“皇帝”為核心的大一統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也就成為合乎觀念的邏輯的必然。于是,我們看到,西漢政權一面“過秦”一面卻繼承秦帝國所開創的皇權政體以及皇帝制度,甚或對于始皇帝所創制的“太上皇”
也一并“仿”之。
要之,始皇帝追尊已故父莊襄王為“太上皇”,一方面是基于三代王權體制下,王位世襲,子繼父位。秦王嬴政的王位即來自于傳統王權體制,故承襲三代以來的宗法血緣對于祖先宗廟神靈的認同,其更多的是基于血緣人倫的情感認知,即“太上皇更多的是一種源于血源天性的父權象征”。
同時也通過祭祀創業者及其繼承者,始皇帝進一步確認了“自己的權力淵源”。
另一方面,則是以“太上皇”來彰顯始皇帝自身所取得的“自上古以來,三皇所不及”之大一統偉業。故秦始皇之追尊“太上皇”,既有對三代王權時代追尊遺風的承襲,亦有藉此彰顯皇權的考量。
我們可以看到,“漢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
被共推為“皇帝”,憑的是其“高材疾足”“繇一劍之任”
而“功”最“盛”,以及其“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與天下同利也”
的“德”最“厚”。即便如此,初為皇帝的劉邦,內心似乎并不具有秦王嬴政“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后世,其議帝號”
的自信與當仁不讓,反而是在諸侯上疏“拜上皇帝尊號”時“三讓”,甚或有“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的些許惶恐。即是說,其時雖然有了皇帝制度,但“皇權體制遠遠未達到充分穩定的程度”, 更重要的是,其時與“皇權政體相匹配的帝制社會還處于緩慢形成過程當中。皇權政體的人為架構與帝制社會的自然秩序還需要長時間的相互磨合。凌空高架的皇權體制由于還沒有深深扎根于帝制社會的土壤之中,一有變故就立刻變得岌岌可危。”
換言之,“漢初的‘布衣將相之局’使得漢高祖劉邦此時還僅僅只是‘身’居帝位,享有皇帝之名號,尚未能構筑起皇帝制度原本所內涵的秩序性、權威性、至上性。”
故面對“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的混亂無序,“上患之”。
即是說,雖然同樣是登皇帝位,但基于建國方式的差異,故相較于始皇帝的自信與歡“悅”,劉邦則多了些許惶恐與“患之”,在此境況之下,自然無暇在第一時間深慮太公之名號。
二、仿秦也:“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
歷史的吊詭在于,原本希冀一世二世以至萬世不窮的秦帝國最終卻二世而亡。代秦而興的西漢王朝一方面在社會上掀起“過秦”思潮;另一方面卻又在現實政治中承秦之制,“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
探究其由,就漢初“過秦”而言,一方面,毋庸置疑,“以酷暴為特色的秦朝統治是造成‘過秦’思潮的現實基礎”;
另一方面,誠如韋伯所言,“乃是因為任何權力”“一般都有為自己之正當性辯護的必要”。
就邏輯認知而言,秦政之“過”也就賦予了代秦而起的漢政權以正當性。此外,對代秦而興的西漢王朝而言,出于現實政治求治的需要,亦需要通過揭示秦政之失,以之作為新王朝統治之歷史借鑒。觀“過秦”的主要內容,則著重于批判秦的苛法酷刑、刻薄寡恩,殘民以逞的“專任獄吏”“樂以刑殺為威”,
從而造成民眾生活疾苦,“男子疾耕不足于糧餉,女子紡績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
部編教材全冊要求認識400個生字,會寫200個生字,可以從課文、語文園地以及專門教認字的板塊識字。從識字教材的編排來看,課文不僅有現代兒童文學的活潑,也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厚重,尤其將一些經典古文改編,使課文不失傳統文化的精華,又淺顯易懂,不為難學生。還有,合理安排識字寫字序列,集中識字和分散識字相結合,讓學生能順暢、難易結合地學習識字認字。最重要的是,識字的形式變得更加多彩了,主要新增了字理識字和同類事物舉例識字。
透視“過秦”思潮,可知在時人看來,秦之“過”更多的在于其“政”,而非其“制”。不僅如此,始皇帝所開創的以皇帝制度為核心的皇權政體亦即秦制,還恰是“當時中國最適當的法度”。
一方面,歷經春秋戰國,中國大一統的需要在事實上已經形成;另一方面,秦所開創的大一統中央集權帝國不僅被頌為“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
的偉業,且亦為民眾所期待與認可,“天下之士”“斐然向風”“罔不賓服”。此外,秦制的適宜更體現在秦末楚漢角逐過程中,一定程度可言,劉邦正是憑借“承秦”而戰勝項羽,并最終“立漢”:
劉邦最終卻戰勝了項羽,建立了漢家帝業。導致這一戲劇性結局的原因無疑是多方面的,而劉邦得以“承秦”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所謂“承秦”包括據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等幾個方面。據秦之地,使劉邦由楚將變為秦王,從而控制了關中形勝之地。用秦之人,使原以楚人為主的劉邦集團逐漸變為以秦人為主,使漢成為真正的關中政權。承秦之制,特別是根據秦律制定漢律,是劉邦、蕭何為爭取秦人的支持而在文化上對秦人做出的讓步。這些舉措使漢朝得以繼承秦朝的軍國主義體制,從而真正獲得了當年秦所擁有的優勢。
也就是說,正是因“劉(邦)代表秦帝國的法度規模,項(羽)代表六國的法度規模”,基于秦制在其時的適宜與適當,“當然是最后劉邦成功了”。同時,因著秦制“還是合于時代的要求”,故“非承秦不能立漢”:
項羽稱帝不成,并不意味著楚不能帝。不過要奪取帝業,只有楚的名分還不夠,還必須據有當年秦滅六國的形勢。我們看到,當淵源于楚的漢王劉邦東向與諸侯盟主楚王項羽交鋒之時,他確實是不期而然地居于當年秦始皇滅六國的地位。客觀形勢要求居關中的劉邦之楚消滅居關東的項羽之楚,步秦始皇的后塵,再造帝業。這又出現了反秦而又不得不承秦的問題,出現了以后的漢承秦制,首先而又最根本的是承秦帝制。
即是說,西漢初年雖然有“過秦”之論,但因著秦制在其時的“合于時代”性,故“承秦帝制”也就成為西漢王朝“合于時代”的應然之舉。
《漢書·高帝紀》言:
陳平、王陵、陸賈、酈商、酈食其、夏侯嬰等,皆白徒。樊噲則屠狗者,周勃則織薄曲吹簫給喪事者,灌嬰則販繒者,婁敬則挽車者,一時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將相,前此所未有也。蓋秦、漢間為天地一大變局。
漢初“布衣將相之局”的人員構成特征使其在文化視野上出現一定程度的智障,“三代世侯、世卿之遺法始蕩然凈盡”。
尤其是劉邦本人,“他對于楚國,并無特殊的愛好;對于秦人,也沒有什么深仇巨恨,非報復不可。他不惟不是六國的世族,因而對于過去六國的文化,沒有甚么溫情的留戀;他并且是曾任過秦代吏職的人,對于秦代的制度,反而覺得熟悉和方便。”
即對劉邦而言,相較于久遠而自身又缺乏認知的三代傳統之制,
毋寧更愿意擇取自己所熟悉的秦制。尤其對于秦制所開創的皇權政體的核心——皇帝,“把最尊崇的名號與最高權力結合為一體”,
更成為時人所追逐與覬覦的對象。
此外,對始皇帝而言,追尊其父“太上皇”,亦是藉此凸顯“皇帝”名號,彰顯自身的“創大業,建萬世之功”。
當仆射周青臣進頌“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時,“始皇悅。”
一個“悅”,揭示出始皇帝對于自身功德的認同肯定,以及由此對于擁有“皇帝”名號當仁不讓的自信。
既然身為人子擁有功德兼備的“皇帝”名號,那么作為“皇帝”之父,自然也應享受“最上”“最高”之名號,故唯有冠以社會層次序列中“等而最居上者”的“太上”,方能彰顯其作為皇帝之父的榮耀與尊崇。即是說,始皇帝追尊故父莊襄王為“太上皇”,不僅是使其作為皇帝觀念的一部分,
更多的當是賦予其皇權政體下的一種因子而貴的政治“榮譽稱號”。換言之,始皇帝追尊其父為“太上皇”,也是旨在凸顯身為其子的“皇帝”所創亙古未有之大業,所建萬世之功,足以“昭明宗廟”“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
《史記·高祖本紀》載:
正是基于此,始皇帝雖然自認為開創“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之功,但卻依舊將之歸功于祖先宗廟,“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
故對于祖先,始皇帝表現出相當的禮遇與尊崇。一方面,針對“死而以行為謚”,認為其容易造成“子議父,臣議君,甚無謂”,故“弗取”;
另一方面,不僅追尊莊襄王“太上皇”,且“泰上皇祠廟在縣道者……”,
即在縣、道設有“泰上皇祠廟”。此外,在秦完成大一統的次年(前220),始皇帝第一次出巡,其所選擇的路徑為“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
對此,有學者以為,“秦始皇在統一之后向西北方向的這次出巡,有明顯的追溯秦由西而東遷徙舊跡的意圖”。
這種追溯,一定程度上亦可理解為始皇帝對其先祖奮進之路的追尋、緬懷與認同、彰顯。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后高祖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 。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于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 。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
此外,觀代秦而起的西漢帝國,其打破夏商周三代乃至春秋戰國各諸侯王以及秦帝國由來已久的貴族統治,創建中國歷史上首個“平民王政”,
“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無賴之徒,立功以取將相”,
實乃亙古之未有:
2011年9月23日,早上發生了一起車禍,司機撞人后把車開到一邊停了下來,一會兒,一輛摩托車開過來,當了替罪羊。那天早上,撞人司機給了我5000塊錢。
最后,由于本研究樣本量較小,團體輔導次數和時間較短,成員分享和人際互動不是特別充分.今后研究將進一步擴大樣本量,并在實驗設計上做部分調整,借鑒歐文·亞隆的無結構式團體咨詢模式,嘗試設計成半結構式的團輔形式,留出更多的自由討論時間,促進成員間深入交流,深度覺察自身人際互動模式,從而改善人際關系,增強主觀幸福感,提高團輔干預的外部效度.
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后上朝,太公擁彗,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于是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于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于子,子有天下尊歸于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并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群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 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比較《史記》《漢書》之所載,有同有異。所“同”者,漢高祖尊太公為“太上皇”都是在“家令言”之后;其“異”者在于,《史記》所載彰顯出兩者之間直接的關聯性,而《漢書》于“家令言”后,則不僅多出了劉邦關于“人之至親,莫親于父子”的“人道”之論,更是將自己“提三尺劍”打下的“天下”歸功于“此皆太公之教訓也”,此后方詔封太公“太上皇”,以映證“子有天下尊歸于父”的“人道之極”。《漢書》此番記載,揭示出漢“太上皇”寓含更多深意的政治考量。
形式上,考慮模型M = (W, {~i | i∈G}, V),W為一世界,~i為可及關系,對世界中的主體i∈G,V為賦值。點模型(M,s)包括現實世界s表示事件的狀態為真(可能不知道主體)。這里的可及關系不再是編碼行動,而是信息域:可供選擇的主體可以看作是現實世界。建立在~i上的條件編碼為主體的特殊的觀察力和內省。每一公共知識都是一個等價關系:自返的、對稱的和傳遞的。例如“信息圖”,可用來解釋認知語言。有下面的條件:
考秦、漢兩位“太上皇”,名號雷同,然身份影響卻是迥異。一方面,對秦“太上皇”莊襄王而言,其在位時間雖短,卻是名副其實的秦王,而作為漢之“太上皇”的太公,誠為一介布衣,純屬因子而貴;另一方面,如顧炎武所言,“《秦始皇本紀》:‘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是死而追尊之號,尤周曰‘太王’也。漢則以為生號。”
如此,就使得漢“太上皇”較秦“太上皇”有可能被賦予了更多的內涵與考量。此外,漢之“太上皇”,在名號上誠然為“仿秦也”,然漢高祖劉邦并未如同始皇帝那樣,在登基皇位的同時即為其父太公上尊號。探究其由,當與漢之建國方式、漢帝國之初的政治生態以及劉邦“起細微”的身世背景相關聯。
首先,相較秦“續六世之馀烈”而使得“天下大定”,
建立起亙古未有之帝國,西漢帝國的建立并非如劉邦言說的“父有天下傳歸于子”所得,而是有賴于其“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
考劉邦之為皇帝,亦在于:
(五年)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氾水之陽。
對此,《漢書》記載為:
于是諸侯上疏曰:“先時秦為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儗,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諸侯王皆曰:“大王起于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愿大王以幸天下。”
“太上皇”依附于“皇帝”名號而成,但其一經創設,遂和“皇帝”名號一起,被視為皇權政體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存在。此后,“太上皇”也就作為一種特殊的政治名號與身份,在專制皇權的政治生活中發揮著程度不同的政治效用。此在漢初高祖詔尊太公“太上皇”中即可窺見一斑。
其次,觀漢初朝堂,一方面,作為開國之君的劉邦,乃十足布衣。對其家世,史稱其“父曰太公,母曰劉媼”,
即“是父無名字,母無氏族”,
其家庭之孤微可知。
劉邦以匹夫起事,角逐群雄而驟登皇帝寶座,成為中國歷史上首個匹夫天子。另一方面,其臣亦多出微賤,“自多亡命無賴之徒,立功以取將相”。
統而言之,漢初帝國的匹夫天子、布衣將相之局,一方面前所未有地終結了三代以來的貴族統治,“此尤當時民間心理所未始逆料也”;
另一方面,對于這樣一個“平民王政”而言,其始初對專制皇權政體的認知呈現出明顯的不足與短缺。 史載,“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酈食其獻策“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后世”,如此則六國“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愿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對此,劉邦深以為然,曰“善”。然則,隨后在聽聞張良“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后,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且夫楚唯無強,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的詰問后,其又復罵酈食“豎儒,幾敗而公事”。
對此,有學者指出,“這番戲劇性的過程說明,在一開始,劉邦心里對封邦建國這種政治謀略并無多少主見。”
如此,在其驟登帝位之初,也就遑論藉為太公上尊號而為皇權政體服務的深慮與考量,這在其時而言,多少有些超出了作為布衣天子的劉邦的政治識見。
最后,考夏商周三代乃至春秋戰國各諸侯王以及秦帝國的統治,其合法性的理論模式基本屬于傳統型,即“王權合法主要源于祖宗基業,后世之君‘嗣我祖宗之洪烈’,守成而已”。
即是說,宗廟“血緣”是貴族統治下王權合法性不言自明的論證,“成例相沿”的“繼體之主”更是三代政權被認同的一個重要因素。“自古皆封建諸侯,各君其國,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視為固然”。
然作為西漢第一位皇帝,劉邦以布衣登帝位,既非“成例相沿”,又非“繼體之主”,乃是逐鹿憑“力”而得,這對時人而言,誠為“前此所未有也”,實乃 “蓋天地一大變局”。
相較于始皇帝的 “賴宗廟之靈”,作為漢高祖的劉邦卻是“起微細”。
尤其是觀其父太公,不僅沒有如同秦莊襄王留給秦王嬴政一個統一在即的王國,且“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斗雞蹴踘,以此為歡”。
即是說,作為西漢王朝的開創者,劉邦既缺乏顯赫的家世背景,更沒有祖先榮光可以承繼,純粹以布衣起家,是平民取代貴族成為君主的首例。這就使得西漢政權(亦或劉氏皇權)被屏蔽了由血緣上獲得不言自明依據的通道。
故探究劉邦本心而言,其所認同的天下,當是其提三尺劍馬上奪之,而非賴宗廟神靈。如此,對以“斗雞蹴踘”為歡,常以劉邦不如“仲力”的太公自然更是少卻些許尊崇,“漢以高祖父太上皇執嘉無社稷功,不立廟號,高帝自為高祖。”
明人張燧更言“漢髙祖尊母不尊父”。
要之,一方面,就情感而言,劉邦似乎缺乏始皇帝基于對祖先宗廟的認同而尊封故父“太上皇”的主體能動性;另一方面,就政治認知而論,西漢王朝雖然承襲了秦帝國的皇權政體,但帝國之初,“庶事草創”,基于劉邦的出身與識見,難以主動認識到他和健在的太公之間的“家人父子禮”與皇權政體下皇權主義秩序之間的內在張力。故我們看到,在帝國始初,身為皇帝的劉邦與太公之間所遵循的依舊是基于血緣關系的“家人父子禮”,太公為“父”故受“尊”,而皇帝劉邦因為是人“子”故須“恭”。直至聽聞“家令言”,劉邦方意識到自己與太公既為“父子”又為“君臣”的特殊關系,遂以此為契機,為尚“未有號”的太公上尊號。考慮到高祖的文化素養,要在短時間內為太公上尊號,自然只能是漢承秦制,故有仿秦之“太上皇”,“尊太公曰太上皇”。而所謂的以此為契機,則當視為是劉邦藉此強化皇權政體與皇權主義秩序的過程,即通過詔封太公“太上皇”,一方面凸顯孝道,且通過融孝道于政道,不僅為專制皇權披上一層人倫外衣,更使之為皇權政體的合法性張目;另一方面尤為核心的則是藉此使得劉邦與太公之間由“家人父子”關系向“朝廷君臣”關系轉化,從而使得皇權專制主義秩序在人倫溫情中得以重塑與構筑。
三、“家人父子禮”向“朝廷君臣禮”的轉化
前已述及,相較于始皇帝主動而為的追尊其父“太上皇”,漢“太上皇”卻是肇端于“家令言”。劉邦之所以“善家令言”并加以賞賜,有學者從心理學角度予以分析,認為“這同高祖對叔孫通說的‘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并賜金五百斤是相似的心理”。
即是說,劉邦雖然是匹夫出身,由布衣而為天子,“但并非說當了天子還可代表布衣”。
探究劉邦面對朝堂上“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而“患之”的心理,勞幹先生曾指出,“劉邦也是想當貴族,想為人之貴的”,“不論他原來出身怎樣,到了可以做貴族時,他當然是貴族的意識。”
即對于劉邦而言,為人之“貴”,尤其是皇帝之“貴”自然是其內心所覬覦的。而“貴”的尊享,無疑需要借助諸如“起朝儀”令“無敢歡嘩失禮者”等秩序的構筑來保障。為此,重塑尊君卑臣、皇權至上的社會政治秩序就成為代秦而興的西漢王朝亟待完成的首要任務。家令之言,指出在專制皇權之下,父子關系當服從于君臣關系,即基于血緣的家庭父子之禮應服從以尊君為核心的朝廷君臣之禮,這無疑是對皇權的極大彰顯,對于專制皇權政體的構筑大有裨益,故高祖“善”之。這與始皇帝基于三代王權遺風而禮遇尊崇其父莊襄王為“太上皇”,在出發點上可謂是大相徑庭。
術后疼痛管理是快速康復的核心環節,科室聯合麻醉科組建MDT疼痛小組,制定統一規范的鎮痛措施;護理制定疼痛評估制度,并按照制度及時進行疼痛評估,根據評分結果,醫護患及時進行溝通,并采取規范的階梯式止痛措施;此外,制定早期下床活動量的衡量標準及作業指導書,按照規范指導患者進行活動鍛煉。
換言之,劉邦在聽聞“家令言”后詔尊太公“太上皇”,這種形式上的“孝道”即“治道”很大程度上是為其時“政道”——構筑專制皇權政體服務的。通常而言,一個政權的施政之道源自當政者的統治思想,而當政者大多是在已有的思想資源中擇取能夠與其統治意圖相契合的學說,以其為指導形成施政之道。前已述及,秦二世而亡被認為主要在于其施政的嚴刑寡恩,如此,代之而興的西漢王朝自當以之為戒,采取與之相區隔的施政之道。考秦之政,在于其奉法家學說為圭臬,故對于西漢王朝而言,為彰顯其正當性,必然在形式上舍法家學說而另作它選。在此過程中,根植于三代傳統,以“正名”“禮樂仁義”“孝悌”為核心要旨且長于“守成”的儒學,因其“能對帝國迫切需要的治國方略提供具競爭力的建言”,故為漢初統治者所漸趨認同與接受。
劉邦將原本由自己取得的天下之功歸于其父太公,一定程度上就是希冀借助儒家所主張的人倫孝道,來彌合其因貴族血統譜系的缺失而致其統治合法性在傳統認知上的欠缺。
臨床中早發現、早診斷乳腺癌疾病有助于提升治愈率,降低死亡率。早期乳腺癌疾病目前只是存在25%的發現率,所以,予以早期乳腺癌患者實施有效的超聲檢查不但是判斷重點,也屬于超聲診斷的臨床難點[1]。乳腺癌早期癥狀存在較小病灶,檢查中經常不能觸及到腫塊,存在不典型的病變聲像學特征,臨床漏診率和誤診率都比較高。超聲造影屬于全新且先進的超聲醫學領域技術,雖然在乳腺癌診斷超聲造影表現得到顯著改善,但不能有效研究早期乳腺癌疾病。報道在2016年8月—2018年10月期間收治的60例乳腺癌患者中使用超聲彈性成像檢查、超聲造影檢查的臨床應用價值。
為了彰顯孝道,劉邦不僅因太公所好,建新豐,遷故人充實:
女人死的時候并沒有像其他的死者露出憤怒或是求饒的表情,反而露出了一個無比平靜的微笑,充滿了對生的眷戀和對死亡的坦然。
太上皇時凄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故,答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斗雞蹴踘,以此為歡,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徙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
元代刊刻之《世說新語》,為劉應登刪注、劉辰翁批點的八卷本。其文字多同于董弅刻本但注釋經過劉應登刪削,并補刻劉辰翁的批語,系目前看到的最早的劉辰翁批點本[5](前言,P24)。
太上皇思欲歸豐,高祖乃更筑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徙豐民以充實之。
且在太上皇崩后,更“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
劉邦詔尊太公“太上皇”,在形式上可謂是極盡“孝道”。然則,另一方面,我們卻又看到:
未央宮成,置酒前殿,太上皇輦上坐,帝奉玉卮上壽,曰:“始常以臣不如仲力,今臣功孰與仲多?”太上皇笑,殿上稱萬歲。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
比較上述兩段文字所載,史實所指雖然為一,但其落筆重心卻稍顯不同。一定程度上,《史記》的“太上皇笑”,旨在揭示太公面對已然為皇帝的兒子“清算舊賬”過程中的尷尬,唯以“笑”緩解之;而《漢書》載劉邦與群臣的“大笑為樂”,揭示出在劉邦內心深處所真正認同的還是“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而并非前述詔曰的“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由此也說明了其“子有天下尊歸于父”,故“詔尊太公太上皇”的“孝道”更多是基于政治考量。即進入皇權體制下,尤其是面對西漢王朝“匹夫天子”,作為一個政治體制問題存在的,則是社會上尚遺存的王權時代的“尊尊”“親親”觀念與現實社會中子為人主、父為人臣的皇權制度的沖突:一方面,在皇權體制下,“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故讓身為“天下主”的“人子”對身為“人臣”的“父”依舊躬行“家庭父子禮”,已然不符合現實皇權政治對于專制社會內在的秩序要求;另一方面,“如若為維護皇權體制下的‘天下法’而廢棄對人主之父的尊崇和禮遇,又將使得皇權體制缺失傳統禮制所給予的道義支持”。
為解決這一政治體制問題,“將‘生父’立為‘太上皇’較之秦政(追尊太上皇)就成為一個更為合情合理的必然選擇”。
即是說,西漢劉邦詔封太公“太上皇”承載了較秦之“太上皇”更多的政治考量,同時也是藉此希望對于皇權主義秩序的構建發揮更大的政治效用與政治功能。
劉邦雖基于皇權政體考量而詔尊太公“太上皇”,在形式上和皇帝同享尊榮,然則,太上皇的“不預治國”揭示出兩者間的本質所在。“漢總帝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
即是說,“皇帝”與“太上皇”“有別”之關鍵在于單純的“皇”,是“其差輕者”,“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
這是由專制皇權體制對于專制社會內在的秩序要求所決定的。此外,觀劉邦在朝堂之上對太公發問,進而和群臣“大笑為樂”之行徑,不僅與周禮所主張的“為人子者……不茍笑”
大相徑庭,更揭示出前述劉邦為彰顯孝道而“因太公所好,建新豐,遷故人充實”諸行徑不過是一種基于皇權政體考量的“能養”之孝,“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由此也進一步透視出劉邦詔尊太公“太上皇”,與始皇帝基于“賴祖宗宗廟神靈”追尊其父“太上皇”在情感內涵上的差異。即劉邦在聽聞“家令言”之后,其更多的是將“太上皇”作為皇權體制下一種獨特的政治禮儀符號予以考量,希冀借助此符號彰顯“孝道”“孝治”,讓君道根植于人道,從而為專制皇權披上一層人倫色彩,同時由人道提升君道,助推皇權合理性的建構。“根據一種禮制的規定來給開國皇帝之父一個合法的名位。由此可能使得皇權體制表面上看起來更具有某種人倫情調,也更符合人們的一般心理需要。”
“人之至親,莫親于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于子,子有天下尊貴于父,此人道之極也。”
為了適應國際國內的新形勢,適應消費者需求的變化,中國地板行業必將形成新的格局與發展,地板行業將面臨很大的變化,變局將體現在新渠道變革、新需求變化、新模式沖擊這三個方面,這也是擺在大家面前的三大市場挑戰。
要之,劉邦尊太公“太上皇”,一方面旨在彰顯孝道,擬圖用以孝治國的統治方略,與秦政的嚴刑寡恩相懸隔,由此構筑其統治政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則是藉“太上皇”重塑皇權政體以及皇權主義秩序。“不預治國”,不僅避免了對現實專制皇權的冒犯,規避了“二王之嫌”,更使得“家人父子”向“朝廷君臣”轉換,強化了專制中央集權下皇權的至上性,從而使得“匹夫天子”與父同在的血緣現實同“土無二王”天子獨尊的皇權體制都得以妥善安置,“兼容了皇權政體架構中對禮制和政制的雙向要求,即家法轉換為國法,家族進入國家;孝道融如政道,父權提升為君權”。
綜上所論,我們可以言,始皇帝雖然創設了與皇帝制度、皇權政體相依附的“太上皇”名號,然則,由于其所尊“太上皇”為故父,所以其更多的是彰顯了始皇帝對于三代禮制的一種承襲,以及對于祖宗宗廟和自我功德的認同,其所彰顯的是家人父子禮。西漢初年,劉邦尊太公為“太上皇”,一方面則是旨在解決三代以降的“尊尊”“親親”觀念與現實社會中子為人主、父為人臣的皇權制度的沖突,重塑與皇帝制度相匹配的皇權專制主義秩序;另一方面,則是借助“太上皇”在專制皇權權力結構中的載體作用的充分發揮,將家庭父子的“孝道”轉化為帝國王朝的“治道”,由此不僅構筑起西漢帝國以孝治國的標簽,更彰顯出皇權政體之下專制皇權的唯一性與至上性。這不僅揭示出秦、漢“太上皇”在政治內涵上的差異化,更透視出劉邦“授予”乃父“太上皇”名號時的政治考量,以及借此所特別謀求的一個平衡布局。藉此可知,基于“過秦”基礎上的“漢承秦制”,其對于專制皇權政體的構筑,更具謀略,影響亦更為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