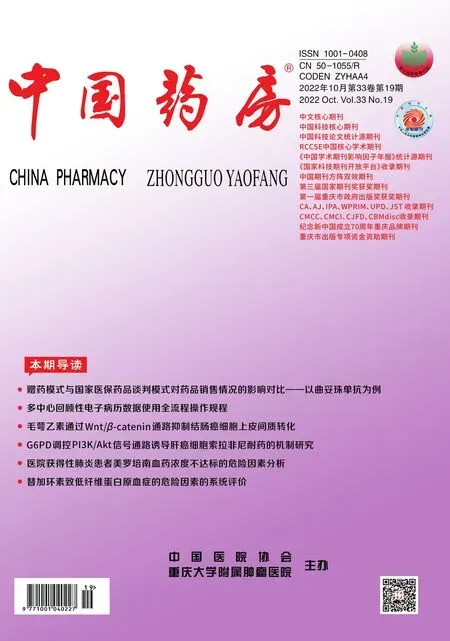手術史對化療所致惡心嘔吐影響的病例對照研究Δ
孫博,張二鋒,陳露,劉勛,李淑芳,馬換青,潘麗麗,劉丹娜,王會品#(.鄭州市第三人民醫院/河南大學腫瘤醫院藥學部,鄭州 450099;.鄭州市第三人民醫院/河南大學腫瘤醫院呼吸腫瘤內科,鄭州 450099;.鄭州市第二人民醫院藥學部,鄭州 450006)
化療所致惡心嘔吐(chemotherapy-induced nausea and vomiting,CINV)是化療過程中常見的不良事件之一,會嚴重影響化療患者的依從性[1],因此準確預測并有針對性地預防CINV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目前已有研究通過構建模型來預測CINV的發生風險[2],而在模型中危險因素的確定至關重要,直接影響預測的準確性。國內外相關指南及研究介紹了一些影響CINV的危險因素,包括性別、止痛藥應用情況、化療惡心嘔吐史等[3―5]。本課題組前期研究顯示,患者的手術史與CINV的發生存在一定的關聯[6],但具體相關性如何仍不清楚。本研究嘗試探討手術史對CINV的影響,以期為臨床提供參考。
1 方法與資料
1.1 研究對象
以某三級腫瘤專科醫院2017-2021年的824例化療患者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為:(1)確診為腫瘤并使用傳統全身性化療藥物的患者;(2)使用帕洛諾司瓊聯合地塞米松預防止吐,具體方案為:靜脈注射帕洛諾司瓊0.25 mg(化療第1天使用1次,多日化療則為每3日使用1次)+靜脈注射或口服地塞米松10 mg(每日1次,化療前0.5~1 h給藥),療程覆蓋化療后48~72 h;(3)CINV發生情況在病歷中有明確記錄。排除標準為:(1)化療與手術間隔時間小于1個月的患者;(2)1個月內接受過放療的患者;(3)病歷資料存在缺失者。
本研究通過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查批準(批件號為2021-04-044-K01);由于在研究中患者是匿名的,因此醫院倫理委員會同意豁免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樣本數量
Logistic回歸要求陽性樣本數量不低于所納入變量的10倍[7―8];大規模人群的觀察性研究要求樣本數量不少于500例[9]。本研究共納入824例樣本,其中陽性(發生CINV)樣本有360例,變量共27項,可見本研究的樣本量可以滿足研究需求。
1.3 研究類型與分組
采用病例對照研究,根據CINV的發生情況分為CINV未發生組和CINV發生組。參考中國臨床腫瘤學會(Chinese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CSCO)《抗腫瘤治療相關惡心嘔吐預防和治療指南2019》(以下簡稱“CSCO指南”),以CINV被完全控制認定為未發生CINV,具體標準為:患者從化療開始至結束后72 h無嘔吐,無需解救性治療,無惡心或伴輕度惡心[3]。以是否有手術史作為暴露因素,手術包括各種外科手術,不包括介入術和穿刺操作。
1.4 資料統計
統計兩組患者的人口學資料(包括性別、年齡、過敏史、飲酒史)、病史材料(包括腫瘤類型、高血壓史、高血脂史、糖尿病史、中樞神經系統病變史、焦慮癥史、既往化療嘔吐史、既往化療史、胃腸道疾病史)、化療前檢查數據[包括體表面積、卡氏功能狀態(Karnofsky,KPS)評分、精神狀況、肝功能、肌酐清除率、電解質水平、白蛋白水平]、化療情況(包括阿片類止痛藥應用情況、化療前預期性惡心嘔吐情況、化療方案致吐等級、單次化療時間、化療方案藥物數量、應用其他影響CINV的藥物情況)等資料共27項。其中,化療藥物主要指傳統的全身性化療藥物,包括烷化劑、抗代謝藥、植物藥和鉑類藥物等。參考CSCO指南,根據致吐風險將化療藥物分為高、中、低-輕微3個等級,其中高風險等級致吐藥物主要包括順鉑、大劑量或聯合蒽環類藥物使用的環磷酰胺、大劑量卡鉑、大劑量阿霉素類、表柔比星等;中風險等級致吐藥物主要包括烷化劑、鉑類藥物(除順鉑和大劑量卡鉑)、阿霉素類(非大劑量)、大劑量白介素、干擾素α等;低-輕微風險等級致吐藥物主要包括紫杉醇、培美曲塞、阿霉素脂質體、口服靶向藥物等。其他影響CINV的藥物參考CSCO指南中影響CINV的伴隨用藥,主要指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等[3]。
另統計患者手術史的相關資料,包括最近一次手術距離化療的時間(以下簡稱“手-化時間”)、手術總次數、是否有腫物切除術史等。
1.5 模型建立與評價
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來估計手術史與CINV發生風險之間的關系,其結果使用比值比(odds ratio,OR)和95%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表示;建立Logistic回歸模型,再逐步納入協變量對模型進行矯正,通過多個模型探討在矯正不同因素的影響后手術史與CINV發生風險之間的關系。所建模型如下:(1)模型1——僅納入手術史,未納入其他任何協變量;(2)模型2——在模型1的基礎上納入患者人口學資料和病史材料;(3)模型3——在模型2的基礎上納入患者化療前檢查數據;(4)模型4——在模型3的基礎上納入化療情況;(5)模型5——僅將模型4中存在統計學意義(P<0.05)的協變量納入,使模型簡化。通過計算各模型的預測概率,繪制受試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ROC)曲線,通過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the curve,AUC)對模型進行評價,當AUC≥0.8時認為模型預測性能良好,模型較為穩健[10]。
1.6 亞組分析
1.6.1 手術史相關因素 以有手術史的患者為研究對象,將手-化時間、手術總次數、是否有腫物切除術史分別納入模型5,用以探索手術史對CINV的影響可能與哪些因素有關,并對有統計學意義(P<0.05)的因素進行進一步探討。
1.6.2 手-化時間對CINV的影響 (1)手-化時間對CINV影響的趨勢:以有手術史的患者為研究對象,以模型5為基礎,對患者手-化時間作不同的分組處理,以探討手-化時間對CINV影響的趨勢。結果以P for trend表示,P for trend<0.05認為趨勢成立。分組1:將手-化時間不作處理直接納入;分組2:將手-化時間分為1年內、1~2年、2年以上3組,每組數值以組間中位值表示;分組3:將手-化時間根據25分位、50分位、75分位分為4組,每組數值以組間中位值表示。(2)不同手-化時間下的CINV發生風險:以全體患者為研究對象,按照“1.6.2(1)”項下“分組2”分組后納入模型5,探討相對于無手術史的患者,有手術史的患者在不同手-化時間下發生CINV的風險。(3)手-化時間與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以全體患者為研究對象,按照“1.6.2(1)”項下“分組2”分組后納入模型5,再分別納入手-化時間與其他各項因素的乘積項[11],用以探討手-化時間與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若該乘積項在模型中有統計學意義(P<0.05),則認為手-化時間與該因素存在交互作用。這里的“其他因素”指模型5中納入的因素,即CINV的獨立危險因素。
1.7 統計學方法
使用Excel 2019軟件統計數據,計量資料符合正態分布者以±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者以M(P25,P75)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秩和檢驗。計數資料以例數或百分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使用SPSS 25.0軟件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納入患者的基本信息
本研究共納入患者824例,其中464例未發生CINV(占56.31%),360例發生了CINV(占43.69%);有手術史的患者為386例,其中190例未發生CINV(占49.22%),196例發生了CINV(占50.78%)。患者基本信息見表1;有手術史患者的相關信息見表2。

表1 患者基本信息

表2 有手術史患者的相關信息
2.2 手術史對CINV發生的影響
表3顯示了未矯正和經多因素矯正后手術史對CINV發生的影響。在未矯正的模型(模型1)中,有手術史的患者CINV的發生風險更高[OR=1.72,95%CI(1.31,2.28),P<0.001]。在矯正了患者人口學資料和病史材料后(模型2),仍存在類似的相關性[OR=1.46,95%CI(1.05,2.04),P=0.026]。進一步矯正化療前檢查數據后(模型3),這種相關性仍未改變[OR=1.46,95%CI(1.04,2.05),P=0.031]。之后加入化療數據進行全因素矯正(模型4,其分析結果見表4),結果仍顯示有手術史的患者有較高的CINV發生風險[OR=1.75,95%CI(1.20,2.55),P=0.004]。最后,將模型4中存在統計學意義(P<0.05)的協變量(包括糖尿病史、既往化療嘔吐史、既往化療史、胃腸道疾病史、電解質水平、阿片類止痛藥應用情況、化療前預期性惡心嘔吐情況、化療方案致吐等級、單次化療時間、應用其他影響CINV的藥物情況)納入,得到簡化后的模型(模型5),發現模型5[OR=1.78,95%CI(1.28,2.48),P=0.001]與模型4的結果相似。

表3 不同模型中手術史對CINV發生的影響

表4 全因素模型(模型4)分析結果
隨著各矯正因素的納入,模型的AUC逐漸增大,其預測性能和穩健性逐漸提高。全因素模型(模型4)的AUC最大,為0.83;簡化后模型(模型5)的AUC為0.81,與全因素模型的AUC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Z=0.77,P=0.443),因此可用簡化后的模型來替代全因素模型。結果見圖1。

圖1 各模型的ROC曲線
2.3 亞組分析結果
2.3.1 手術史相關因素對CINV的影響 對存在手術史的患者進行亞組分析,可發現手-化時間不同,手術史對CINV的影響也會有所變化(詳見“2.3.2”項下),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27)。但無論做過多少次手術,以及無論是否做過腫物切除術,手術史對CINV的影響無變化(P分別為0.866、0.207)。結果見表5。

表5 與手術史相關的因素對CINV的影響
2.3.2 手-化時間對CINV的影響結果 (1)手-化時間對CINV影響的趨勢:將手-化時間直接納入模型(分組1),結果顯示,隨著手-化時間的增加,CINV的發生風險呈下降趨勢(P for trend=0.027);將手-化時間以年份進行分組(分組2),結果顯示,隨著手-化時間的增加,CINV的發生風險呈下降趨勢(P for trend=0.050);將手-化時間以4分位進行分組(分組3),結果顯示,隨著手-化時間的增加,CINV的發生風險呈下降趨勢(P for trend=0.048),詳見表6。(2)不同手-化時間下的CINV發生風險:相對于無手術史的患者,1年以內做過手術的患者有較高的CINV發生風險[OR=2.33,95%CI(1.52,3.59),P<0.001];但當手-化時間超過 1年后,2組間CINV發生情況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7。(3)手-化時間與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結果顯示,手-化時間與其他因素的交互項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明手-化時間與其他因素無交互作用。

表6 手-化時間對CINV影響的趨勢(n=386)

表7 手-化時間對CINV的影響(n=824)
3 討論
本課題組采用病例對照研究,通過Logistic回歸分析矯正潛在的混雜因素,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亞組分析,旨在探討手術史對CINV的影響。結果顯示,有手術史會提高CINV的發生率,這種影響與手-化時間有關,手-化時間越長,手術史對CINV的影響越小,1年內做過手術的患者有較高的CINV發生風險。
本研究盡可能多地收集了患者的相關資料,包括人口學資料、病史材料、化療前檢查數據和化療數據,建立了多個回歸方程模型,用以矯正不同的混雜因素,并檢驗了結果的穩健性;同時,對全因素模型進行了簡化,以方便后續研究。經ROC曲線評價可知,全因素模型和簡化后模型均有較高的預測性能。通過對有手術史的患者進行亞組分析,探討手術史相關因素對CINV的影響,重點探討手-化時間對CINV的影響及其變化趨勢,結果發現,患者無論做過多少次手術,以及無論是否做過腫物切除術,手術史對CINV的影響無變化;CINV發生風險隨手-化時間的延長呈現下降趨勢。
CINV的發生與多種因素密切相關,化療前預期性惡心嘔吐、既往化療嘔吐史、焦慮癥史等均能提高CINV的發生率[12]。Pirri等[13]研究發現,手術會增加化療后出現惡心的風險。本研究結果也顯示,手術史可能是發生CINV的一個危險因素。手術和化療是惡性腫瘤常見的治療手段。有研究證實,術后惡心嘔吐(postoperative nausea and vomiting,PONV)是術后常見的不良反應,全身麻醉手術的PONV發生率為20%~40%[14]。另有研究指出,出現過CINV的患者更易發生PONV[15];而未發生PONV的患者也不易發生CINV[16]。因此,筆者推測,CINV可能與PONV存在某種聯系,這種聯系可能是手術史能增加CINV發生風險的原因。
嘔吐的機制十分復雜,嘔吐中樞通過接收包括胃腸道的迷走神經、大腦皮層、前庭和視覺區域以及化學感受器觸發區的刺激信號來誘發嘔吐[17]。Harrison等[18]研究發現,觀看嘔吐物會使人產生強烈的厭惡感和惡心感,產生低頻心率和胃動過速,并誘發嘔吐。嘔吐的視覺場景會使人情緒劇烈波動,產生厭惡、焦慮等情緒。既往的嘔吐經歷會對大腦皮層和視覺區域產生雙重刺激,這可能是存在既往化療嘔吐史的患者更易發生CINV的原因之一。并且,這種既往的經歷與手-化時間關系密切。本研究結果顯示,手-化時間不同,其對CINV的影響也不同。筆者分析,這是因為隨著時間的流逝,既往經歷帶來的恐懼和焦慮感會逐漸減輕,人的心理和情緒會逐漸恢復。Passik等[19]證明了這一點,其研究顯示隨著時間的推移,患者對化療及CINV的恐懼感逐漸減弱。Molassiotis等[20]研究顯示,心理因素會影響化療前預期性惡心嘔吐的發生,這種影響隨著時間的延長而逐漸減弱。這些研究均說明既往經歷可能會對機體的反應產生影響,但這種影響會隨時間的延長而減弱,這可能是手術史對CINV的影響隨著時間延長而呈下降趨勢的原因。
綜上所述,有手術史的患者發生CINV的風險更高,該風險與手-化時間關系密切并隨時間的延長呈現下降趨勢,1年內做過手術的患者有較高的CINV發生風險。但是,本研究還存在一些不足:(1)由于病歷資料所限,患者手術相關數據無法收集,如手術時的麻醉藥使用情況、PONV情況等,故而無法統計到所有潛在的影響因素;且某些因素(如女性孕吐史、焦慮程度評分等)未被納入,這均可能使結果產生一定的偏倚。(2)研究過程中將一些因素進行分類處理(如化療方案通過藥物致吐風險等級進行分類等),這會損失部分信息,導致一定的偏差。(3)本研究為病例對照研究,是一種回顧性研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得結果還需前瞻性研究予以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