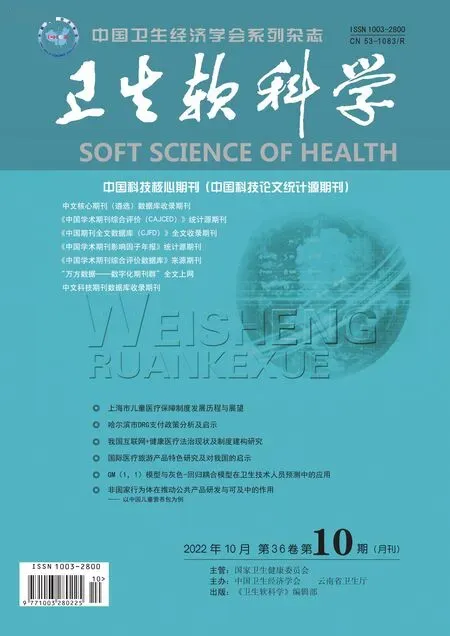我國互聯網+健康醫療法治現狀及制度建構研究
張宏彩
(寧夏社會科學院,寧夏 銀川 750021)
我國推進互聯網+健康醫療發展,是傳統醫療衛生轉型改革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國家大數據戰略、健康中國戰略的重要舉措,是醫療衛生領域發展順應數字智能社會發展趨勢所在。立足我國互聯網+健康醫療發展實際,分析互聯網+健康醫療發展規范化、制度化、法治化發展困境,對我國互聯網+健康醫療穩定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 我國互聯網+健康醫療發展狀況和制度建設
互聯網+健康醫療是伴隨信息技術發展而產生,是在互聯網新場景下醫生與患者、企業與用戶、信息技術與醫療服務等關聯的醫療新生態,其應用發展為傳統醫療衛生改革提供了新路徑,同時,也為人民群眾健康管理提供數字監測預警新機制。互聯網+健康醫療推動醫療數字化服務市場形成同時,也極大便利了廣大人民群眾健康醫療消費。
1.1 用戶數量不斷增長,消費需求趨精細化
當前,我國互聯網+健康醫療消費市場需求已進入快速發展階段。根據2019年2月28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我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8.29億,全年新增網民5653萬,互聯網普及率為59.6%。手機網民規模達8.17億,全年新增手機網民6433萬[1]。至2021年年底,隨著網絡問診、掛號、電商醫藥、人工智能等互聯網+健康醫療業務的不斷拓展,互聯網+健康醫療用戶量持續增加,根據Mob研究院的相關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6月我國在線醫療用戶規模達2.76億人,占網民整體的29.4%[2]。互聯網+健康醫療大眾消費從免費一次性咨詢試探逐漸向付費式問診、健康數據監測、健康保險、醫藥器械網購等全能全鏈條式拓展,互聯網+健康醫療需求時延性和細分領域正在擴大,展示了互聯網+健康醫療用戶消費需求不斷增長,以及群眾對互聯網+健康醫療的認可和依賴度不斷擴大。
1.2 市場規模不斷擴大,競爭加劇
數據顯示,我國2009-2017年移動互聯網醫藥電商市場規模從1億元增長到289億元,在線醫療市場規模從2億元增長到223億元,2017年我國互聯網+健康醫療呈突破式發展,如IBM Watson Health入駐我國,百度發布百度醫療大腦的人工智能問診項目,阿里發布具有臨床診斷檢查和醫師培訓功能的醫療AI“Doctor You”,騰訊發布具有AI醫學影像輔助診斷技術的“騰訊覓影”[3]。隨著更多的新型智能化、網絡化醫療服務產品問世,我國互聯網+健康醫療市場規模逐漸成型。
同時,隨著信息技術不斷更新迭代,互聯網+健康醫療市場競爭加劇。一方面,新興服務項目不斷涌現,例如,互聯網醫院、醫藥電商等相關的智慧健康醫療產業鏈形成,并不斷地在推陳出新,提高服務質效和用戶認可度;另一方面,企業為了客戶源和生存,通過加大投資、投放新產品等措施提高企業市場競爭實力。于是,互聯網+健康醫療頭部企業、大型企業等市場占有率不斷增加,企業規模不斷擴大。為避免市場壟斷和不良市場行為影響廣大人民群眾健康醫療消費,亟待立法予以規范。
1.3 制度化進程加快,法治剛性需求增加
互聯網+健康醫療建設法律體系涵蓋了法律、法規、規章及政策等制度規范體系。目前,我國互聯網+健康醫療法律主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2部基本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疫苗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等關聯性法律;部門規章主要有《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互聯網+健康醫療”發展意見》《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和規范健康醫療大數據應用發展的指導意見》《國家健康醫療大數據標準、安全和服務管理辦法(實行)》《網絡安排審查辦法》等約20余件[4]。此外,也有大量的落實中央和國務院相應法規政策制度地方法規和政策制度文件,如寧夏、貴州、山東等地也就互聯網+健康醫療制定了許多地方法規和政策制度,據統計僅2019年涉及健康、食品藥品、衛生管理、環境保護等“大健康、大衛生”省級地方法規約有213項[5]。這些法律、法規等為我國互聯網+健康醫療法治化提供制度支撐。
從法治實施來源來看,我國互聯網+健康醫療法律比較零散,散見各類法律法規中。除此之外,現階段我國互聯網+健康醫療主要依靠政策性文件、行業標準等來規范其發展。考慮法律的概括性和普遍適用性特征,以及互聯網+健康醫療的特殊性,顯然原有的法律法規不能簡單概況性的適用于當下,需要通過立法修改或制定專門法律予以規范。此外,互聯網+健康醫療發展存在行政強有力監管和技術標準規范特有屬性,需要建立其特有的市場準入、信息安全、醫療安全、數據規范、算法運行等監管機制和行業規范機制,以包容審慎的態度,規范互聯網+健康醫療行為的同時,為互聯網+健康醫療創新發展留有余地。
2 我國互聯網+健康醫療法治化面臨的問題
由于互聯網+健康醫療中網絡空間的虛擬特性和應用場景隨意性,它在突破地域管轄限制的同時,其行業融合和技術拓展不斷擴大和復雜化,不僅給傳統法律規范體系建設帶來挑戰,而且對國家和地方政府市場監管帶來諸多難題,迫切需要通過立法明確互聯網+健康醫療各主體權利(力)義務(職責)邊界。
2.1 服務同質化和優質化競爭法治問題
健康醫療服務本身就存在服務標準化和規范化的同質化現象,互聯網+健康醫療服務同質化問題更為嚴重,國內幾百家企業服務領域、服務內容幾乎相同,非常不利于市場投資和競爭。這與我國互聯網+健康醫療創新保護機制不健全有著極大關系。
此外,健康醫療優質資源聚集城市化和優質服務趨眾化,必然在互聯網+健康醫療沿襲,尤其是隨著“醫共體”“醫聯體”等醫療主體發展規模的不斷擴大,這在一定程度上,不但形成了實體醫院競爭里的擴大,而且也推進了互聯網醫院規模的擴大,增強醫院主體實力的同時,也對那些基層或非公有性醫療主體帶來客戶競爭影響,也即面臨行業競爭存活問題,尤其是一些領頭性互聯網企業和三甲級以上醫院強強聯合,將給基層、個體、專科等小型互聯網企業和醫院帶來市場壟斷競爭局面。這對互聯網醫療資本市場的活躍和醫療行業發展是極為不利的。同時,互聯網醫療行業的激烈競爭,也催生一些不規范診療行為衍生,影響互聯網醫療市場有序發展。
2.2 醫療衛生市場化對行政法治挑戰
我國醫療衛生立法主要是基于行政法規、部門規章,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醫療衛生服務市場,私有化主體不斷增加,致使行政市場準入審批監管和行政行業監督法治作用力受限。尤其在多次“疫苗失效”事件發生后,引起社會對我國醫療衛生立法、執法、司法審視[6]。互聯網+健康醫療的發展再次對我國醫療衛生立法體系完善迫切性提出要求。當下醫藥電商平臺經濟越來越活躍,醫藥互聯網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亟待對國家通過立法對平臺技術、平臺服務等出臺商事立法,以化解行政法規單向制約乏力困境。
此外,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讓全社會認識到公共衛生法治是全社會事件,需要國家和地區構建包括政府、企業、醫療機構、社會組織、個人多元治理共同體,需要通過系統性的法律體系來調整國家政府部門行政行為、醫療主體商業行為、醫療機構和職業人員服務行為,以及公共醫療服務和非公共醫療服務行為和個人健康醫療行為,是兼具行政法和民商法特性的復雜的法律體系。
2.3 互聯網+健康醫療技術性立法規制問題
目前,專門的互聯網+健康醫療國家層面法律制度,主要有3部部門規章,是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制定的《互聯網診療管理辦法(試行)》《互聯網醫院管理辦法(試行)》《遠程醫療服務管理規范(試行)》。這3部規章對互聯網醫院的設立、監管等作出了較為詳細的規定,并對互聯網診療行為中醫師執業資質等審核監管作出規定。但是,這是行政執法層面的法制規范,相較于互聯網+健康醫療涉及到個人醫療海量數據保護、健康醫療數據算法技術運行責任等方面的健康醫療數據立法規范,顯然是空白。
雖然,目前執法和司法層面,我們可以根據《民法典》《刑法》《電子商務法》《網絡安全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公共圖書館法》《國家情報法》《測繪法》等對個人網絡空間數據權益予以保護。但是,醫療實踐中算法等人工智能科技自身缺陷或系統非人力異常問題造成的患者權益侵害問題,是關于生命安全,亦或隱私等倫理規范的事件。在實際操作中,無論是司法法律援引,或執法權法制依據,不是概況適用,而是需要確定的、直接的法律條文來調整。顯然,現行的醫療衛生法律體系是不能完成的,非專門的法律制度只能提供原則性可參考援引依據,不能起到完整的法律規范作用,也可能為科技缺陷提供逃避法律追責的借口。
2.4 互聯網醫療網絡市場秩序法治化問題
目前,互聯網醫療市場主要是社會資本投資成立的平臺運營模式,網絡市場常見競爭手段,就是一些負面或不良信息傳播和攻擊,如“魏則西事件”案例,就是醫療服務網絡宣傳社會效應的直接例證。顯然互聯網醫療網絡市場良性競爭秩序,需要國家立法予以規范。
此外,立法如何保障互聯網+健康醫療服務質量,這不僅是醫療技術發展問題,也是網絡市場規范化發展的問題,同時也涉及到被服務群體(患者)生命健康權益,這是立法需要審慎對待的問題。
2.5 醫療數據流通與保護的立法權衡問題
互聯網+健康醫療服務,是對海量數據的收集、清洗、轉載、儲存、計算等過程,是在不同主體或場域下流動實現的。涉及到用戶個人信息、企業商業信息、服務主體信息諸多信息保護問題,以及后期數據應用中知識產權、患者隱私、倫理責任等內容。此外,互聯網+健康醫療還涉及技術研發創新知識產權保護和信息保護問題。法律既要保護相關數據和信息安全,同時還有確保這些數據和信息能夠有效流動,實現數字紅利。因此,僅僅適用傳統醫療衛生法律法規、倫理規范、以及數據法律法規予以規范和約束,不但不利于互聯網+健康醫療產業創新發展,也不利于互聯網+健康醫療市場穩定,甚至也可能產生國家網絡安全等相關問題。
3 我國互聯網+健康醫療制度建構建議
互聯網+健康醫療的應用,目的在于釋放資源最大效益,實現醫療、技術、數據等資源的共享,套用羅賓·蔡斯對共享經濟的定義[7],在互聯網+健康醫療市場內,構建起“閑置資源+共享平臺+人人參與”的新醫療服務模式,其法治網絡是龐大復雜的。
3.1 認識互聯網+健康醫療立法層級多元性和復雜性
我們必須認清,線上線下結合是未來醫療發展的必然趨勢,它不斷催生新型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出現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法律關系產生。這對現有的法律制度而言,必將加重挑戰,甚至帶來法律秩序的“破窗性”或“創造性破壞”,這必將迎來法律變革,事實上,數字時代的法律變革已然到來[8]。以互聯網+健康醫療中醫療數據管理、數據算法實現、智能醫療行為等為例,它不僅在空間上以虛擬和實體雙層空間交互中產生,而且還存在人機協同不同屬性主體行為融合,這是一個復雜、多元法治空間。這不僅是法律制度體系建設挑戰,也是社會治理的難題。
另外,互聯網+健康醫療立法不僅牽扯到個人生命安全和權益保護、醫療倫理和科技發展、商業合同行為和知識產權等問題,而且關系到政府監管、市場秩序、消費者權益保護等個人的、行業的、國家安全的、社會發展的多層保護機制建設的問題,是公法與私法的法治平衡和社會秩序建設的難題。顯然通過單一的政策等制度文件,無法實現權益保護的法律價值和社會穩定的法治價值。
通過國家和地方立法確立互聯網+健康醫療中多元主體權益,是數字時代法治社會建設的必然趨勢,通過立法不僅要明確政府監管、行業監管、社會監督等多方監督主體責任,還要確立政府、企業、醫院等主體權利(力)義務,更要對醫患用戶主體的權益予以保護,保障各方主體權益得以有效實現的同時,為線上線下健康醫療提供法治支撐。
3.2 明確互聯網+健康醫療立法需要政策制度體系前置
強化互聯網+健康醫療制度體系完善,一方面是國家互聯網+健康醫療法治化探索前期必要過程;另一方面,也是地方推進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和貫徹落實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依據。目前,我國各地互聯網+健康醫療發展水平不一,我國江浙、北上廣等地互聯網+健康醫療業態正走向成熟,西北、東北等地網絡信息技術發展依然相對落后,其互聯網+健康醫療產業規模化、市場化程度相對較低。雖然網絡無邊界,信息技術打破地域邊界,但是經濟落后地區基建項目在人力、資金、設施缺口非常大,亟待政策等制度來吸引發達地區互聯網+健康醫療優質資源帶動發展,實現醫療和信息技術等各類資源有效整合。
此外,互聯網+健康醫療規范化發展,離不開政策等制度規范,離不開行業標準規范,離不開法律強制力保障。互聯網+健康醫療政策制度體系成熟,為法治化奠定制度基礎的同時,也是立法轉化的必要過程。
3.3 明確互聯網+健康醫療技術規范立法的重要性
法律的可預見性,建立起了知識產權法治秩序,推進互聯網+健康醫療的技術創新和發展,其將醫療服務知識價值與計算機技術價值鏈接起來,產生新的醫療信息價值和關系,當然需要建立起相應的法律予以規范保護。放眼全球,不難發現在信息技術應用國際競技場上,那些在法律制度有著重大優勢的國家,其信息技術創新和應用是非常發達的。因此,加緊建立我國互聯網+健康醫療創新應用法律體系建設,不但明確和保護了互聯網+健康醫療各主體價值,而且也能夠有效激勵傳統醫療與互聯網醫療融合深入發展。
加緊我國互聯網+健康醫療創新法治保護體系建設,是深入推進國家科技創新戰略目標有力舉措,同時,也為完善我國科技創新成果知識產權保護法治體系提供有效路徑。我國互聯網+健康醫療、人工智能醫療、5G信息技術應用等已經開始領跑全球,這不僅與我國信息技術開發和平臺建設能力不斷增強有關,也與我國現行法治體系不斷完善有著必然的關系,健全完善的知識產權法律保護體系,不但保護和保障我國信息技術升級發展,而且為我國信息技術走出國門提供制度指引。因此,加強互聯網+健康醫療創新技術知識產權立法,提高國家立法對互聯網醫療創新技術的保護力度,增強我國互聯網醫療國際競爭力。
3.4 互聯網+健康醫療數據安全和流通是立法關鍵
數據聯通是互聯網+健康醫療打破地域限制關鍵,是實現健康醫療數據商業化、市場化的前提,也是健康醫療數據立法的重點。其不僅要確保數據流通和交易,而且還要對賦予數據價值和安全確定法律保護,譬如設立數據采集資格權、數據清洗和處理權等權限,以及數據來源主體的隱私保護權等。
另外,國家立法如何為數據運用提供法律依據,以解決技術、人員、數據在虛擬和實體空間交互行為的合法性問題,是當前互聯網+健康醫療數據流通安全的基礎。在互聯網+健康醫療數據資源市場化過程中,出現數據權益主體多元化、分散化問題,涉及到個人和企業信息安全、知識產權保護、數據合規等法律問題,立法不及時或法制不健全,將產生數據被私有化不能利用起來,或數據壟斷主體泄密等風險。
建立有效的互聯網+健康醫療數據聯通、監管等安全法律體系,不但使數據資源合法應用于醫療研發中,數據本身及流通得到法律權威認可,而且使數據的價值在法律的可控范圍內得到有效發揮。
3.5 構建互聯網+健康醫療市場競爭秩序多元法治框架
結合我國各地互聯網+健康醫療發展實踐,前期互聯網+健康醫療行業發展,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到醫療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經濟社會發展發展相對滯后地區,其醫療行業信息化建設在人力、資金、設施設備等建設存在巨大缺口,政府在引導社會資金投入醫療信息化建設過程中,必然產生信息化基礎較好或發展實力較強的主體。這在法治體系不完善情境下,井噴式融資過熱,將產生多數企業投資流產,亦或基層醫療機構和私人醫療機構無人問津等現象。因此,通過國家和地方發展規劃、政策文件等“軟法”,引導和規范社會資金推進地方互聯網+健康醫療發展。
此外,由于目前我國互聯網+健康醫療服務同質化問題非常嚴重,以及互聯網服務巨頭壟斷問題越來越嚴重,市場主體信息不匹配、不對稱,競爭力強弱懸殊等問題,需要政府為小微服務主體營造發展空間。盡管市場化的目的是實現人民對互聯網+健康醫療的共享共建共治,但必須在法治的空間中,構建起市場主體間良性競爭關系,以避免“大魚吃小魚”和“壟斷霸王條款”不良市場行為和現象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