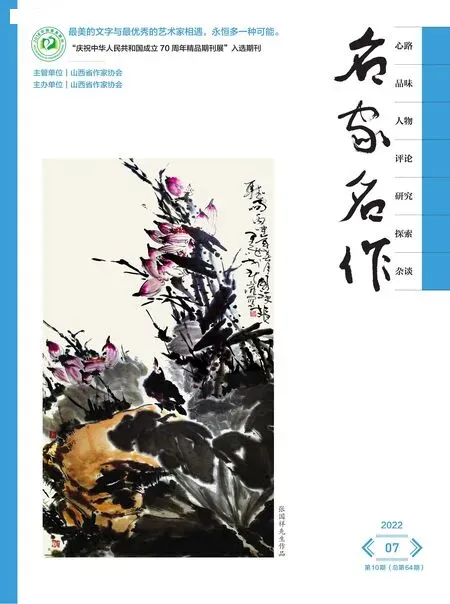論生態(tài)批評(píng)視角下的《屠場(chǎng)》解讀
李 巧 康曉蕓
厄普頓·辛克萊是著名的美國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家,擅長書寫“揭發(fā)黑幕”的小說。他的代表作《屠場(chǎng)》講述了尤吉斯一家移民至芝加哥的悲慘遭遇,書中對(duì)肉類食品加工的描寫推動(dòng)了美國食品衛(wèi)生檢查法的制定,同時(shí)揭示了美國社會(huì)進(jìn)入工業(yè)時(shí)期后嚴(yán)重的生態(tài)危機(jī),具有極高的現(xiàn)實(shí)價(jià)值。隨著人類社會(huì)進(jìn)入工業(yè)化階段,生態(tài)危機(jī)爆發(fā),世界對(duì)生態(tài)給予更加迫切的關(guān)注。由此出現(xiàn)許多反映生態(tài)系統(tǒng)破壞的環(huán)保小說,國內(nèi)外學(xué)者對(duì)此類小說中生態(tài)危機(jī)的揭示,以及其中所蘊(yùn)含的生態(tài)思想做了許多探究,但這些研究比較宏觀,還不夠系統(tǒng)和深入。鑒于此,本文從魯樞元的生態(tài)三分法出發(fā),對(duì)文本進(jìn)行細(xì)讀,探究《屠場(chǎng)》所反映的生態(tài)意識(shí)與生態(tài)思想。
一、生態(tài)批評(píng)的內(nèi)涵
世界進(jìn)入工業(yè)化社會(huì)后,生態(tài)環(huán)境惡化,尤其是1970年末出現(xiàn)了許多環(huán)保小說,越來越多的人對(duì)其進(jìn)行研究,于是逐漸演變成生態(tài)批評(píng)。生態(tài)批評(píng)是對(duì)文學(xué)或者對(duì)生態(tài)危機(jī)的批評(píng),探究人與自然以及文學(xué)的關(guān)系,而后與學(xué)科交叉,繼續(xù)深化。與此同時(shí),世界上對(duì)生態(tài)批評(píng)的研究也隨之而來,歐美西方生態(tài)批評(píng)主要以深層次生態(tài)批評(píng)中的整體主義為核心,而中國本土生態(tài)批評(píng)主要分為中國本土理論構(gòu)建派、歐美生態(tài)批評(píng)理論闡釋派,以及文學(xué)文本理論闡釋派。其中,以中國本土理論構(gòu)建派為代表的魯樞元將生態(tài)批評(píng)與文學(xué)相結(jié)合,形成了文學(xué)生態(tài)學(xué),并且在此基礎(chǔ)上,將文學(xué)生態(tài)學(xué)劃分為以獨(dú)立的自然界為研究對(duì)象的自然生態(tài)學(xué),以人類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為研究對(duì)象的社會(huì)生態(tài)學(xué),以人的內(nèi)在情感生活與精神生活為研究對(duì)象的精神生態(tài)學(xué)。自然生態(tài)、社會(huì)生態(tài)與精神生態(tài)這三個(gè)維度實(shí)際上相互聯(lián)系又相互區(qū)別,三者相互依賴,但是不等同,也不能相互取代。
二、生態(tài)批評(píng)視域下對(duì)《屠場(chǎng)》的生態(tài)解讀
(一)人類中心主義:自然關(guān)系失衡
對(duì)于自然生態(tài),魯樞元有自己的見解,他將獨(dú)立的自然界看作自然生態(tài)研究對(duì)象,而自然界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zhì)環(huán)境,為人類提供了生存空間,同時(shí)也是人類社會(huì)發(fā)展的基礎(chǔ)。但隨著人類工業(yè)社會(huì)的發(fā)展,人類不加節(jié)制地向有限的自然索取,人與自然的矛盾越發(fā)尖銳,導(dǎo)致自然生態(tài)失衡。因此,在小說《屠場(chǎng)》中,自然界中環(huán)境惡化實(shí)際體現(xiàn)了人與自然失衡。在工業(yè)化文明進(jìn)程下,環(huán)境受非自然因素影響而改變,原有的積極自然生態(tài)開始浮現(xiàn)出消極、被動(dòng)的自然景象。主角尤吉斯剛到芝加哥時(shí),人類建立起高大的黑乎乎的建筑物,象征著工業(yè)文明的五六只煙囪,排放的濃霧遮天蔽日,污染著四周環(huán)境,可以看出原有的自然景觀已經(jīng)消失不見,視野中只有人為建造的工業(yè)環(huán)境,人類疏忽了自然環(huán)境保護(hù),一心尋求發(fā)展,天然景觀已經(jīng)被人類磨滅。除了自然環(huán)境破壞,人類社會(huì)生活環(huán)境也極其復(fù)雜。小說中體現(xiàn)的工作環(huán)境污染嚴(yán)重,屠宰場(chǎng)血流成河,肥料廠有害物質(zhì)四溢,罐頭廠醬肉車間肉類腐爛變質(zhì),氣味刺鼻。而這些都是人類無節(jié)制開發(fā)自然而呈現(xiàn)的慘狀,隨著綠色自然圖景消逝,生靈的棲息之地逐漸退去,帶走了綠色的自然生態(tài)氣息,恬靜、安寧的田園式牧歌生活被打破。可以說,人類無盡的物欲破壞的不僅是干凈、清新的自然環(huán)境,還有人類美好、善良、天真的本性。
自然環(huán)境惡化的同時(shí),人類還將動(dòng)物視為滿足物欲的工具,打破動(dòng)物間原有的平衡。小說故事背景為屠場(chǎng),恰好處于動(dòng)物與人類文明的交界處。《屠場(chǎng)》中呈現(xiàn)的大型動(dòng)物屠殺極其殘酷,“一群群的牲畜被趕上一條條大約十五英尺寬的坡道,然后擁向一座座高過畜欄的棧橋。棧橋上畜頭攢動(dòng),川流不息,爭(zhēng)先恐后奔向生命的終點(diǎn)。”很明顯,在人類中心主義下,人類將自己放在高等地位,而將動(dòng)物視為自身的附屬品,可以大肆掠殺作為食物。殊不知,與人類共同生存在自然界的動(dòng)物,他們的生存狀態(tài)實(shí)際上是一面鏡子,映射著人類的行為。并且,動(dòng)物在某種意義上,實(shí)質(zhì)是一種自然之力的象征,人與之處于生物鏈的一環(huán),在生態(tài)系統(tǒng)整體運(yùn)行中,倘若大肆捕殺動(dòng)物滿足人類私欲,人類也會(huì)受到影響,凄慘地走向生命的終點(diǎn),假以時(shí)日,悲慘命運(yùn)的鐘聲也將為人類敲響。
可以說,自然環(huán)境惡化,動(dòng)物倫理觀念這些自然危機(jī)產(chǎn)生來源于人類中心主義。挪威哲學(xué)家阿倫·奈斯最早提出人類中心,它強(qiáng)調(diào)人自身的利益,將自然作為利用的工具,挑起人與自然的對(duì)立。人代表著異化的文明人,自然環(huán)境與社會(huì)環(huán)境則是自然生態(tài)的代表,而機(jī)器則屬于工業(yè)文明的代表。小說中異化的文明人將自己視作萬物的中心,將自然當(dāng)作利用的工具,建立與自然世界相對(duì)的工業(yè)世界,而環(huán)境惡化,生態(tài)破壞則是人類所要付出的代價(jià)。但小說文本中實(shí)際表達(dá)出對(duì)田園牧歌式的自然美景、生機(jī)勃勃的綠意,以及盎然體格“自然人”的贊美。由此襯托出厄普頓·辛克萊內(nèi)心深處盼望原生清新的自然,希望回歸自然的希冀。除此之外,他認(rèn)為動(dòng)物與人之間應(yīng)該是平等的關(guān)系,和睦相處。小說以辛辣的筆觸刻畫了動(dòng)物的悲慘遭遇,凸顯出人類在無盡物欲支配下的丑陋嘴臉,同時(shí)也看出實(shí)質(zhì)上是厄普頓·辛克萊對(duì)動(dòng)物凄慘命運(yùn)的憐憫與同情。總之,反映出厄普頓·辛克萊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反對(duì)人類中心主義,尊重自然,回歸自然,保護(hù)動(dòng)物,與自然和動(dòng)物和諧共處的生態(tài)哲學(xué)思想。
(二)資本主義制度:社會(huì)生態(tài)惡化
除了人類中心主義下的自然生態(tài)失衡,整個(gè)社會(huì)生態(tài)也同樣遭受著嚴(yán)重影響。對(duì)于社會(huì)生態(tài),魯樞元認(rèn)為它主要研究社會(huì)的人與其環(huán)境構(gòu)成的生態(tài)系統(tǒng)。因此,實(shí)際上,在小說中以屠場(chǎng)主為代表的資本主義與以尤吉斯一家為代表的平民共同構(gòu)成了美國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而當(dāng)時(shí)的資本主義制度,尤其是資本主義所有制所引起人與人之間的競(jìng)爭(zhēng)與對(duì)抗、利益爭(zhēng)奪,主要表現(xiàn)在經(jīng)濟(jì)、政治方面引起社會(huì)失衡。
首先,從經(jīng)濟(jì)層面上看,貧富差距是導(dǎo)致社會(huì)失衡問題的重要因素。張守海認(rèn)為貧富懸殊的加劇,將給未來的社會(huì)埋下嚴(yán)重的隱患。小說中處在社會(huì)的上層人士操控著各種資源,剝削著本就貧窮的平民。比如,女工頭因?yàn)閵W娜未給予她金錢賄賂而對(duì)奧娜極度嚴(yán)厲,隨意濫用職權(quán),可以看出作為平民階層的百姓,光維持整個(gè)家庭的基本開銷就已經(jīng)精疲力盡,還需要向上層的人繳納賄賂款。除此之外,伊莎貝塔大娘的孩子沒有得到治療去世,而富人的孩子享有充足的資源治療,這可以看出窮人與富人之間經(jīng)濟(jì)上的差距導(dǎo)致資源分配不均,享受不了同樣的社會(huì)醫(yī)療資源。同樣的疾病,不同的遭遇,由此可見資產(chǎn)階級(jí)實(shí)際上掌握著大量社會(huì)資源,反而繼續(xù)用于榨干“沒有靈魂的軀體”,空殼的平民掙扎于生存底線生存,而極少部分人卻由此不斷滿足自己的物欲需求,造成社會(huì)階層間的巨大差距。私有制所產(chǎn)生的對(duì)抗與矛盾,使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在利益沖突之下,顯示出極度不平等,導(dǎo)致社會(huì)關(guān)系失衡。
其次,從政治層面上看,在《屠場(chǎng)》中,美國進(jìn)入工業(yè)化后,以屠場(chǎng)主為代表的資產(chǎn)階級(jí)與以尤吉斯一家為代表的平民,明顯階級(jí)就不平衡,這種階級(jí)差別是引起人與人、人與社會(huì)間矛盾的重要因素。實(shí)際上,屠場(chǎng)主將平民當(dāng)成壓榨的工具,大機(jī)器生產(chǎn)下不斷提高勞動(dòng)效率,以出賣勞動(dòng)力的平民最基本的物欲得不到保障。在這種情況下,人與人之間關(guān)系逐漸異化,無論是尤吉斯,還是奧娜、瑪麗亞,這些角色隨著情節(jié)推進(jìn),在工業(yè)生活下“他們?cè)骱拮约旱墓ぷ鳌K麄冊(cè)骱薰ゎ^,憎恨老板,憎恨這個(gè)工廠,憎恨這個(gè)地區(qū),甚至憎恨整個(gè)城市,這種憎恨一切的情緒深切而強(qiáng)烈。”他們整個(gè)心境都開始發(fā)生變化。男性成為大機(jī)器下的犧牲品,由此扭曲婚姻關(guān)系,異化的“文明人”尤吉斯反映出資本主義制度下,婚姻狀態(tài)的變化。從移民前對(duì)奧娜溫柔體貼,關(guān)愛有加,到工作后臥病在床,與奧娜之間的關(guān)系逐漸疏遠(yuǎn)。除了男性與女性婚姻關(guān)系的淡漠,城市中人與人之間關(guān)系被機(jī)器擰斷,人成為“腐爛的尸體”。高速運(yùn)轉(zhuǎn)的社會(huì)下,工業(yè)文明對(duì)人的閹割,使他們喪失了生機(jī)活力,在得不到物質(zhì)基本保障的情況下,都漸漸失去表達(dá)愛意與感動(dòng)的交流,而這些都成為人與人之間疏離、人與社會(huì)矛盾加劇的催化劑。
實(shí)質(zhì)上,黑暗社會(huì)下經(jīng)濟(jì)、政治方面的不公,實(shí)際上是資本主義制度所引發(fā)的。小說其實(shí)講述的是人與社會(huì)的失衡,導(dǎo)致人與人的關(guān)系也隨之異化。人類為了謀求利益,加工帶病的肉質(zhì)食品,劣質(zhì)布料、奶粉、藥品等進(jìn)入市場(chǎng)后,整個(gè)市場(chǎng)流動(dòng)著粗制濫造的偽劣商品,就算有金錢也購買不到優(yōu)質(zhì)產(chǎn)品,最終消費(fèi)的還是人類本身。當(dāng)然,小說也從反向警示人與人之間應(yīng)該是平等的,一部分人的發(fā)展不應(yīng)該犧牲另一部分人的權(quán)益,一旦人與人的關(guān)系平衡被打破,最終受到懲罰的還是自身。這體現(xiàn)出厄普頓·辛克萊的生態(tài)整體思想,即人與人之間是互動(dòng)式的,相互依存,共同生活在一個(gè)整體之中,命運(yùn)與共。與此同時(shí),這樣的工業(yè)大背景下,屠場(chǎng)主資產(chǎn)階級(jí)與平民階級(jí)長期兩極分化嚴(yán)重,形成不可逾越的鴻溝,長期以來,平民被殘酷壓榨折磨,人與人的關(guān)系不平衡,甚至逐漸異化,形成封閉惡循環(huán)的畸形社會(huì),而厄普頓·辛克萊向往的是一個(gè)人人平等,政治、經(jīng)濟(jì)和諧、穩(wěn)定發(fā)展的社會(huì),并且他在小說中為社會(huì)危機(jī)的解決提供了社會(huì)危機(jī)的道路,即社會(huì)主義。從中可以看出,厄普頓·辛克萊批判資本主義壓榨,期望建立人人和諧的社會(huì)主義社會(huì)。
(三)工業(yè)機(jī)械文明:精神世界異化
在自然生態(tài)與社會(huì)生態(tài)的異化下,精神生態(tài)也會(huì)受到波動(dòng),這與魯樞元的觀點(diǎn)不謀而合。他認(rèn)為精神生態(tài)探究主體的精神生活以及情感狀態(tài),人的精神與自然、社會(huì)相關(guān)聯(lián)。隨著美國進(jìn)入工業(yè)社會(huì),工業(yè)化、機(jī)械化不斷閹割人的內(nèi)在自然,奪去其生機(jī)活力,因此厄普頓·辛克萊筆下的主角所呈現(xiàn)的自我是“非健康成長”,精神生態(tài)系統(tǒng)也處于“不穩(wěn)定狀態(tài)”。
從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背景來說,美國工業(yè)社會(huì)發(fā)展,諸如信仰缺失、道德淪喪、信任缺失、價(jià)值觀扭曲、精神危機(jī)浮出水面。人們已經(jīng)不信仰教會(huì),諷刺的是,他們甚至把做丑事比作給教會(huì)做工作。這實(shí)際上映射了信仰崩塌,人不再相信宗教所給予的準(zhǔn)則,整個(gè)精神世界處于無主狀態(tài),沒有了精神層面的約束,人性開始不受控制,同時(shí),道德缺失問題接踵而至,小說中,隨著內(nèi)在自然工業(yè)文明的異化,人們?nèi)ゾ瓢珊染茣r(shí),明明只有半桶酒卻收兩桶酒的錢。為了金錢利益,將道德二字拋諸腦后,自我的精神逐漸腐朽,只剩下沒有靈魂的肉體,道德的缺乏,導(dǎo)致人類彼此之間失去寶貴、真誠的信任。小說中尤吉斯一家買房時(shí),對(duì)中介的戒備心理極強(qiáng),透露出嚴(yán)重的信任危機(jī),信任的失去,人類的精神世界充滿猜忌、懷疑,真誠、善良這些人類美好的品質(zhì)也就消失殆盡。實(shí)際上小說中價(jià)值觀的扭曲也成為精神危機(jī)的重要體現(xiàn)。正派的奧娜有著正常的婚姻,卻被價(jià)值觀扭曲的女工頭看不上,可以看出價(jià)值觀已經(jīng)解體,異化的精神狀態(tài)開始顯現(xiàn),這些都揭示著小說中的精神主體處于非正常狀態(tài),精神生態(tài)系統(tǒng)散發(fā)出一種“病態(tài)”的黑暗。
在小說中,工業(yè)機(jī)械文明吞噬著人類的精神世界,是誘發(fā)悲劇的主要原因。精神世界實(shí)質(zhì)是指人的內(nèi)在自然,它包含人的信念與價(jià)值支撐,而工業(yè)化與機(jī)械化如同一個(gè)無良當(dāng)鋪,用極少的錢換取人類極其寶貴的時(shí)間,壓榨、剝削并不斷摧殘著人類的肉體與心靈,并且大工業(yè)機(jī)器的制造越先進(jìn),給予人類的勞動(dòng)報(bào)酬所得越少得可憐,壓榨的勞動(dòng)時(shí)間越長,于是在這樣非人折磨下,人類變得麻木淡漠,失去了自身的活力,如同一具沒有靈魂的空殼游蕩在工業(yè)機(jī)械化的世界里,人的內(nèi)在自然被工業(yè)文明異化。因此,可以捕捉到厄普頓·辛克萊筆下聚焦的人物角色具有病態(tài)性,原本生機(jī)勃勃的自然“人”帶著希冀來到芝加哥,但在工業(yè)機(jī)器的鞭撻下疲于奔命,冰冷的工業(yè)機(jī)器實(shí)質(zhì)割裂了人的自然屬性,讓他們背負(fù)著巨大的生存壓力,生存空間被壓縮。于是在這種黑暗異化社會(huì)中,人的精神世界與精神狀態(tài)都會(huì)出現(xiàn)變化,比如:信任危機(jī)、道德缺失、價(jià)值觀扭曲、金錢至上多種精神狀態(tài),無不說明“文明人”正遭受著嚴(yán)重的心理創(chuàng)傷。由此,《屠場(chǎng)》其實(shí)從側(cè)面反映出厄普頓·辛克萊批判工業(yè)化與機(jī)械化,期望個(gè)人的精神救贖,并建立有利于精神健康、平衡的思維范式。
三、總結(jié)
本文以魯樞元的生態(tài)三分法解讀厄普頓·辛克萊《屠場(chǎng)》中的生態(tài)危機(jī)。小說中,筆者發(fā)現(xiàn)在人類中心主義下,人們將自然視為利己工具,試圖征服自然,導(dǎo)致環(huán)境污染,自然環(huán)境破壞嚴(yán)重,致使自然生態(tài)失衡,除了自然生態(tài)危機(jī),整個(gè)社會(huì)狀態(tài)惡化,人與社會(huì)的矛盾尖銳,并且人與人之間相互疏離,自然與社會(huì)危機(jī)顯現(xiàn),隨之而來的是精神異化、價(jià)值觀扭曲等精神危機(jī)。厄普頓·辛克萊有感于這些生態(tài)危機(jī),因此他反對(duì)人類中心主義,尊重自然,尋求自然回歸。他還指出,資本主義社會(huì)制度導(dǎo)致貧富差距與社會(huì)不公,因此他追求社會(huì)主義,主張構(gòu)建平等、和諧社會(huì)。與此同時(shí),他期望個(gè)人自我救贖,并構(gòu)建精神健康、平衡的思維范式。總之,從生態(tài)視角下解讀《屠場(chǎng)》,為厄普頓·辛克萊生態(tài)思想的解讀提供了新的視角,同時(shí),其生態(tài)哲學(xué)思想也為中國生態(tài)發(fā)展提供了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