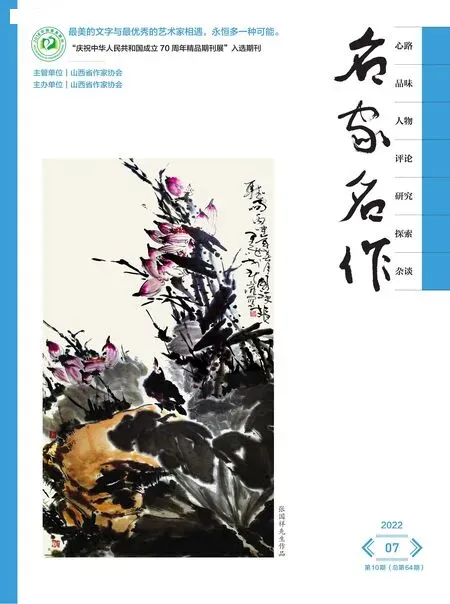新歷史語(yǔ)境下重讀科幻經(jīng)典《弗蘭肯斯坦》的后人文主義之思
石一楠
一、人文主義之 “后”的《弗蘭肯斯坦》
(一)新歷史語(yǔ)境下科幻經(jīng)典逐漸走向現(xiàn)實(shí)
《弗蘭肯斯坦》作為文學(xué)史上里程碑式的科幻經(jīng)典,主要講述了科學(xué)家弗蘭肯斯坦濫用科技手段制造生命最終引火自焚的故事。作者瑪麗·雪萊受到19世紀(jì)工業(yè)革命浪潮和哥特式寫(xiě)作風(fēng)格對(duì)英國(guó)文壇的影響,賦予了這篇小說(shuō)深刻的現(xiàn)實(shí)意義。關(guān)于這篇小說(shuō)的大部分著述,一是集中在科學(xué)與道德相沖突時(shí)的倫理選擇問(wèn)題,二是《弗蘭肯斯坦》中的敘事藝術(shù),三是結(jié)合瑪麗·雪萊自身的女性身份和她母親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特殊影響,從女性批評(píng)角度出發(fā)進(jìn)行分析。而在當(dāng)今的“后理論時(shí)代”,人類進(jìn)入了所謂的“后人類”階段,人類中心的論調(diào)逐漸式微,眾多后人文理論家開(kāi)始批判傳統(tǒng)的人文主義,雖然關(guān)于后人文主義尚未有權(quán)威的定論,但綜合各理論家的共識(shí),將這篇18世紀(jì)的經(jīng)典科幻小說(shuō)放置于后人文主義的全新歷史語(yǔ)境下,可以看出瑪麗·雪萊對(duì)人類社會(huì)科技發(fā)展前景的前瞻性和深遠(yuǎn)意義。雖然局限于時(shí)代的背景和文學(xué)性的想象,但邏輯的自洽和一定的現(xiàn)實(shí)依據(jù)使得作品中的情節(jié)也并不是空穴來(lái)風(fēng)。雖然對(duì)當(dāng)時(shí)的科技發(fā)展而言這種幻想言之過(guò)早,但瑪麗·雪萊“正是在這種人與周圍環(huán)境的雙向互動(dòng)中看到了當(dāng)時(shí)風(fēng)頭正勁的浪漫主義意識(shí)形態(tài)后埋藏的巨大隱患”,而這個(gè)隱患既是以科學(xué)怪物為代表的賽博格和除了人類以外的其他生物,又是后人文主義所關(guān)注的科技發(fā)展與資源濫用對(duì)生態(tài)環(huán)境造成的問(wèn)題。但是關(guān)于科學(xué)怪物與傳統(tǒng)意義上的人之間的倫理沖突,在人工智能和生態(tài)環(huán)境問(wèn)題引發(fā)眾多社會(huì)問(wèn)題的21世紀(jì)不再是杞人憂天的想象,人類不得不重新審視自身的主體性和其他生命的主體性。
(二)對(duì)傳統(tǒng)人文主義的批判
人文主義的傳統(tǒng)對(duì)人類社會(huì)文化的影響滲透在各個(gè)領(lǐng)域,長(zhǎng)久以來(lái)人類認(rèn)為自己對(duì)其他的生命和事物有著至高無(wú)上的統(tǒng)治權(quán)。人文主義定義是“人類的本質(zhì)在于思想和靈魂的理性,是與身體完全分開(kāi)的,因此只要通過(guò)理性的力量是可以改變和提高”。自然科學(xué)的發(fā)展孕育工業(yè)革命與人文主義盛行的背景,讓人們更加篤定人類是萬(wàn)物之首,可以主宰和利用一切自然資源。瑪麗·雪萊筆下的科學(xué)家弗蘭肯斯坦就是18世紀(jì)對(duì)人文主義真理堅(jiān)信不疑的人類的真實(shí)縮影:“開(kāi)始時(shí),我對(duì)到底創(chuàng)造一個(gè)和自己一樣復(fù)雜的生命體還是簡(jiǎn)單的生命體感到困惑,但是最初的成功使我充滿自信:堅(jiān)信自己能創(chuàng)造出和人一樣復(fù)雜、神奇的生命。”可見(jiàn)主人公對(duì)人類智慧潛能的無(wú)條件相信。在塑造弗蘭肯斯坦的人物性格時(shí)是強(qiáng)調(diào)此人物的個(gè)性與價(jià)值的,弗蘭肯斯坦殊不知在否定傳統(tǒng)神的同時(shí),造出了新的更殘酷的神,即人類自己。弗蘭肯斯坦是一個(gè)極度崇拜知識(shí)與解放人性的自由人文主義追求者,強(qiáng)調(diào)人的情感體驗(yàn)和中心地位,即使為了探求知識(shí)也不能違背這個(gè)原則:“一個(gè)完美的人應(yīng)當(dāng)時(shí)刻保持冷靜、平和的頭腦,不應(yīng)讓激情或一時(shí)的欲望打破這種平靜。對(duì)知識(shí)的追求也不例外。”在獲得知識(shí)和濫用科技手段制造生命的事情上,他既服從解放人性、追求自由與快樂(lè)的宗旨,又強(qiáng)調(diào)建立在理性基礎(chǔ)之上的人性,因?yàn)樗某霭l(fā)點(diǎn)最終落腳于“符合人類的思想”,因而區(qū)別于浪漫主義對(duì)縱欲的極致追求。在伊麗莎白寫(xiě)給弗蘭肯斯坦的信中對(duì)給人尊嚴(yán)與幸福的共和制國(guó)家的感激,以及弗蘭肯斯坦對(duì)理想中人類家庭的描述,都屬于這種“符合人類的思想”。而故事并未全盤(pán)肯定這種美好的人文主義典范,而講述的是這種理性的束縛與感性的寬容是如何在企圖獲得兩全其美的人類手中失衡的。怪物感嘆理性與知識(shí)的力量:“知識(shí)是多么不可思議的東西啊!它一旦被你掌握,就像青苔牢牢附著在石頭上一樣。”但是知識(shí)也帶來(lái)弊端:“隨著知識(shí)的增長(zhǎng),我的悲傷也更加深重。”在被出身所定義的人類社會(huì)中,這種痛苦除了死亡沒(méi)有其他辦法可以結(jié)束,暗示傳統(tǒng)的人文主義典范走向窮途,而瑪麗·雪萊作品中體現(xiàn)的批判也是直指?jìng)鹘y(tǒng)人文主義的。
二、后人文主義思想的主要體現(xiàn)
(一)對(duì)人性的探討
正如怪物所控訴的那樣,人類“是由上帝創(chuàng)造的完美的人,快樂(lè)而健康,還受到造物主的特殊關(guān)懷,上帝允許他和比他優(yōu)秀的人談話并學(xué)到知識(shí)”,但同時(shí)也在種種對(duì)待弱勢(shì)群體的態(tài)度中流露出卑鄙低劣的人性來(lái)。弗蘭肯斯坦一面指責(zé)著貪欲對(duì)人性的影響,一面把激情、勤奮、求知欲等一系列傳統(tǒng)人文主義奉為美好的品德不顧后果地傾注在創(chuàng)造的快感之上,在“當(dāng)我發(fā)現(xiàn)自己掌握著如此驚人的權(quán)力,我猶豫了很長(zhǎng)時(shí)間,考慮以何種方式來(lái)使用它”之后動(dòng)用了這種作為人類科學(xué)家的特權(quán)。后人文主義在談?wù)摳脑旎蚧蛘呒藿又w這類仿人或造人手術(shù)的時(shí)候指出,“即使科學(xué)再發(fā)達(dá)也無(wú)法免疫人類對(duì)金錢、野心和聲望的極致追求所造成的傷害”,弗蘭肯斯坦從自身感受出發(fā)創(chuàng)造出的怪物即是欲求掌控他者野心的人性的最極致表達(dá)。
怪物用自身的成長(zhǎng)經(jīng)歷控訴人類獸性與神性分裂之夸張,人類對(duì)非人類生命的迫害之深重。怪物用人性的雙重性來(lái)一步一步解釋自己和弗蘭肯斯坦的矛盾是如何走向極端的,在怪物成長(zhǎng)學(xué)習(xí)的過(guò)程中,他了解到人類社會(huì)的陰暗面:“我知道人類最崇尚的就是高貴、清白的出身和財(cái)富。”而外貌丑陋或者貧窮的人則會(huì)遭到唾棄。在描寫(xiě)怪物接觸人類社會(huì)之初,瑪麗·雪萊對(duì)于人文主義傳統(tǒng)下的社會(huì)等級(jí)現(xiàn)象做了揭露,使小說(shuō)結(jié)局合理化。怪物被制造出來(lái)之前弗蘭肯斯坦懷抱的是掌握制造生命權(quán)力的快感,而到了怪物誕生的那一刻卻又是“令人窒息的恐懼和憎惡”。怪物之于人類的價(jià)值隨人類需求而變,可以隨意篡改,與任何一種殖民不無(wú)差別,所以社會(huì)只肯定傳統(tǒng)的“人”的意義,否定人類以外他者的意義。而后人文主義所批判的正是這種排除異己二分法思維、德里達(dá)所說(shuō)的一切壓迫的源頭或托詞。
(二)人與其他存在之間的去人類中心化的思想
在人類社會(huì)經(jīng)歷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和在科技飛速發(fā)展之后,后人文主義探討的人與機(jī)器之間的關(guān)系也是文學(xué)研究的一個(gè)重要課題。傳統(tǒng)的人文主義價(jià)值觀進(jìn)入困境后,人類的地位會(huì)不會(huì)在生化人或者機(jī)械人的威脅下日漸式微?人造人是否是有生命的?人與其他生物如何實(shí)現(xiàn)和諧共處?這都是人文主義解構(gòu)下新的引人深思的問(wèn)題。后人文主義理論家沃爾夫指明了后人文主義的核心:“人類在宇宙中占據(jù)了一個(gè)新的位置,它已成了一個(gè)居住著我準(zhǔn)備稱之為‘非人類的居民’的場(chǎng)所。”后人文主義一方面認(rèn)為人不再是世界的主宰者,而是與自然界中的其他生命共同享受資源、共同承擔(dān)責(zé)任,另一方面認(rèn)為人類不安于自己所創(chuàng)造的機(jī)器或者恐懼人工智能的大范圍應(yīng)用會(huì)導(dǎo)致就業(yè)停滯、財(cái)富愈加高度集中、貧富差距日漸擴(kuò)大等問(wèn)題。雖然后人文只能作為眾多理論思潮中的一種聲音,但是其思想中人文主義解構(gòu)的特征卻可以在瑪麗·雪萊的作品中窺見(jiàn)一斑。不論是出于恐怖谷效應(yīng),還是受到二分法思想的影響,它仍然是后人文討論的與人共處的群體之一,而怪物所遭受的長(zhǎng)期以來(lái)被人類中心主義賦予了公正性的“人”身攻擊也是后人文主義所否定的。怪物在非自愿的情況下被制造出來(lái),但在沒(méi)有作出任何違反人類社會(huì)道德的行為下被迫邊緣化,在人類中心論的前提下本身沒(méi)有違人權(quán)。科學(xué)怪物的身份在弗蘭肯斯坦看來(lái)不能定義為人,而是歸屬于造物主手下的“物”,將其歸類時(shí)作為異己和威脅來(lái)排斥似乎符合道德層面的正當(dāng)性,弗蘭肯斯坦拒絕承認(rèn)與怪物有任何立場(chǎng)上的相似性,甚至在怪物發(fā)出和解的信號(hào)時(shí),還是無(wú)法逾越等級(jí)的鴻溝。直到它被逼殺死威廉且嫁禍于賈斯汀這一步時(shí)才實(shí)實(shí)在在地危害了自稱為“人”的人類的利益,怪物的暴行就被正當(dāng)?shù)刭N上了“動(dòng)物性”的標(biāo)簽,而維護(hù)人的利益已經(jīng)成了必然。這一套看似完整的邏輯實(shí)際上是建立在深刻的矛盾之上。
怪物在一切程度上無(wú)限地接近于人,具有人類獨(dú)有的最微妙的感情,但自居中心的群體出于自身利益卻并不愿意為邊緣化的群體騰挪生存空間。如果怪物在人類社會(huì)與精神障礙者、基因病患者甚至殘疾人等邊緣人群是相似的存在,那么這些群體是否也會(huì)成為人類中心主義者為排除異己利用到“人類+工具”這一組合中,為更高階層的人類服務(wù)?例如利用這些群體做生化實(shí)驗(yàn)或者成為器官移植的來(lái)源等。后人文主義主張不能忽視一切有生命的東西,因?yàn)榧词苟唐诳磥?lái)是不利人的或無(wú)用的,長(zhǎng)遠(yuǎn)來(lái)看它們也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繁衍的鏈條中的重要一環(huán),是值得人類尊重的。科學(xué)怪人可以看作后人類時(shí)代暗指來(lái)自非中心群體威脅的危險(xiǎn)隱喻。科學(xué)怪物是一個(gè)縮影,對(duì)人類構(gòu)成威脅的不僅是機(jī)器人、生化人或者動(dòng)物,還有人類中心主義所演變出來(lái)的各種中心主義與其他邊緣化群體的矛盾。
(三)人與大自然矛盾之下的去人類中心化的思想
對(duì)于瑪麗·雪萊來(lái)說(shuō),科學(xué)不再是想要迫切了解世界和大自然運(yùn)作規(guī)律的企圖,而成了尋求壓迫正在逃離的女性化大自然的性別暴力的扭曲表達(dá),而后人文主義強(qiáng)調(diào)摒棄這種成見(jiàn),肯定自然環(huán)境對(duì)人類社會(huì)的重要性。以笛卡爾為代表的哲學(xué)家強(qiáng)調(diào)人類不需要依靠神,依靠理性就能獲得真理,加上長(zhǎng)期以來(lái)自由人文主義所營(yíng)造的進(jìn)步神話,人類與大自然的關(guān)系逐漸從敵對(duì)轉(zhuǎn)為征服與奴役,加速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戰(zhàn)爭(zhēng)使人們不禁開(kāi)始反思自由人文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對(duì)生態(tài)環(huán)境和人類自身造成的創(chuàng)傷。生態(tài)文學(xué)研究者克洛伯爾認(rèn)為弗蘭肯斯坦可以看作是20世紀(jì)原子彈或者將來(lái)的基因怪物。在《弗蘭肯斯坦》發(fā)表前,就有人進(jìn)行過(guò)小說(shuō)中主角的類似嘗試,喬瓦尼·阿爾迪尼就在意大利博洛尼亞和倫敦紐蓋特監(jiān)獄的死刑犯身上做過(guò)電擊實(shí)驗(yàn),而最負(fù)盛名的一次是在這部小說(shuō)發(fā)表的前十五年他對(duì)死刑犯喬治·福斯特進(jìn)行的實(shí)驗(yàn),他通過(guò)電擊企圖復(fù)活死者,這可能給瑪麗·雪萊提供了小說(shuō)中人物使用電擊為尸塊注入生命的靈感。二戰(zhàn)中使用“基因改造計(jì)劃”制造基因戰(zhàn)士等濫用科技服務(wù)于戰(zhàn)爭(zhēng)的行為不僅給人類帶來(lái)沉重的代價(jià),還引起后人文主義者對(duì)生態(tài)倫理的思考。弗蘭肯斯坦就是試圖通過(guò)違背自然規(guī)律來(lái)證明人類中心地位的科學(xué)家代表,而事實(shí)證明與大自然對(duì)立以及征服自然的企圖最終將引火燒身。在新的歷史語(yǔ)境下不變的事實(shí)是,這種篡改生命規(guī)律的企圖仍然是對(duì)大自然的不尊重和對(duì)人權(quán)的踐踏。弗蘭肯斯坦的悲劇結(jié)局就是一種警示:人類歷史上經(jīng)歷過(guò)的和正在經(jīng)歷的自然災(zāi)害都是與大自然搞對(duì)立的后果,是來(lái)自大自然的報(bào)復(fù)。《弗蘭肯斯坦》作為科幻小說(shuō),幻想了蔑視自然生態(tài)規(guī)律之后的人類命運(yùn),是一種有教育意義的后人文主義思考。在小說(shuō)中就對(duì)結(jié)局做了消極的暗示:他對(duì)夏季美麗的自然景色毫無(wú)興趣,對(duì)葡萄園的豐收帶來(lái)的物質(zhì)收獲也沒(méi)有需求,這說(shuō)明相比大自然,他更在乎自我實(shí)現(xiàn)的需求,這也是人文主義極致發(fā)展之后整個(gè)人類社會(huì)面臨的問(wèn)題,適度的索取已經(jīng)滿足不了人類的貪欲,而人類開(kāi)始朝著征服自然奮斗。人與自然的疏離已經(jīng)在小說(shuō)中多處得到暗示,人與自然的矛盾升級(jí)到人與人之間關(guān)系的陌生化,在自我實(shí)現(xiàn)需求萌芽后,弗蘭肯斯坦甚至將友情、親情都置之腦后了。這種矛盾陷他于錯(cuò)綜復(fù)雜的網(wǎng)絡(luò)之中,遠(yuǎn)比表面的矛盾深刻得多。
(四)對(duì)賽博格主體性的探討
新的歷史語(yǔ)境下,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發(fā)生了變化,后人文主義談?wù)摰饺祟悓?duì)身體的改造,認(rèn)為靈魂意識(shí)可以脫離肉體而進(jìn)入改造的身體,實(shí)現(xiàn)永生,換言之,就是創(chuàng)造出完全新的軀體來(lái)替代出現(xiàn)問(wèn)題或者衰老的生物學(xué)身體,進(jìn)行意識(shí)的移植而實(shí)現(xiàn)人類的永生。以往笛卡爾將“我思”的主體當(dāng)成“自我”存在的意識(shí)或自明。不應(yīng)當(dāng)是思想的心理現(xiàn)象而已,它是一“思想之物”或稱為“實(shí)體”。既然“我在”是思想的前提,那么怪物的身體也是靈魂的載體。后人文主義對(duì)這種意識(shí)離開(kāi)身體后人的主體性的危機(jī)做了討論,設(shè)想當(dāng)我們的技術(shù)主動(dòng)地、自動(dòng)地使它們自己變得更像人類,就像我們把自己改造得更像機(jī)器的時(shí)候,那么工具和用戶之間的界限就變得非常脆弱,而這樣的科技產(chǎn)物將不再像工具,而像是人的思維器官。在作者所處的年代,即使人們對(duì)科學(xué)飛速發(fā)展持樂(lè)觀心態(tài),但是精神移植和義肢移植對(duì)當(dāng)時(shí)的發(fā)展水平來(lái)說(shuō)仍然是不現(xiàn)實(shí)的。但作者筆下?lián)碛凶灾饕庾R(shí)的人造生命卻是對(duì)人類在新的歷史語(yǔ)境下主體性發(fā)展的預(yù)測(cè)。
后人文主義中的賽博格所強(qiáng)調(diào)的軀體與意識(shí)主體性的關(guān)系可以從《弗蘭肯斯坦》中人物的內(nèi)心獨(dú)白和情節(jié)發(fā)展解讀出來(lái)。在怪物被制造出來(lái)之后的跡象顯示怪物是具有主體意識(shí)和高級(jí)智慧的存在。原著里對(duì)它的稱呼是“being”,而不是中文對(duì)應(yīng)的“怪物”,而怪物是由人的尸體的各個(gè)部分拼湊起來(lái)的,所以這個(gè)存在更大程度上是人性的而非動(dòng)物性的,是具有主體性和自主意識(shí)的。怪物從誕生到思想成熟速度很快,力量也比普通人類更大,更類似于超人類的存在,這也是人們恐懼它的原因之一。是當(dāng)“人”的主體意識(shí)與非人的身份互相矛盾、人與工具的界限逐漸模糊之后,以主體性來(lái)定義的“人”就會(huì)發(fā)生迷失,最終走向毀滅。通常對(duì)人的定義是歷史語(yǔ)境和文化語(yǔ)境下的,也就是被限定在人類軀體內(nèi)擁有有限壽命的活在某個(gè)社區(qū)范圍內(nèi)和歷史時(shí)代的人,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人,是不斷發(fā)展變化的。因?yàn)槭澜绾腿硕继幵诎l(fā)展和變化中,當(dāng)世界變化到新的階段,需要用新的概念表達(dá)新的世界。所以在新的世界即將到來(lái)的時(shí)候,假設(shè)人的主體性意識(shí)與科學(xué)所創(chuàng)造的軀體結(jié)合在某一個(gè)歷史時(shí)期的社會(huì)群體中會(huì)有什么樣的后果?科學(xué)怪物的故事就很有參考性:作為一個(gè)賽博格,缺失了人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建構(gòu),即一個(gè)歷史文化的語(yǔ)境,即使短時(shí)間內(nèi)被補(bǔ)償所缺失的經(jīng)驗(yàn)也是無(wú)法融入人類社會(huì)的。因此缺乏身份認(rèn)同和“人生經(jīng)歷”但擁有主體性的生化人顯然在人文社會(huì)是一個(gè)棘手的存在。
后人文主義對(duì)于賽博格的思考還指向人獨(dú)特的社會(huì)性以及生命的有限性。雖然以科學(xué)怪物為代表的賽博格在人類社會(huì)屬于少數(shù)邊緣化存在,人類也不得不直面來(lái)自賽博格成為未來(lái)人類存在主流形式時(shí)定義、價(jià)值、地位和道德倫理等社會(huì)標(biāo)簽大洗牌的后果。賽博格使人類依賴科學(xué)技術(shù)獲得永生后,原本由人類生命長(zhǎng)短所決定的種種社會(huì)特性在永生中幾乎歸零了。當(dāng)肉體對(duì)人的影響變得不那么重要之后,肉身所攜帶的特質(zhì)對(duì)本性的塑造和影響也因其極高的可替代性而在漫長(zhǎng)的時(shí)間長(zhǎng)河中逐漸消亡,賽博格形式的人類失去了生命有限性對(duì)以往人類產(chǎn)生的種種影響。在科技可以對(duì)抗生老病死的時(shí)候,疾病和容貌等給個(gè)體帶來(lái)的獨(dú)特品質(zhì),例如自卑、認(rèn)同感和優(yōu)越感就不復(fù)存在了。人與人之間原有的倫理關(guān)系就會(huì)發(fā)生巨大的變化,人的主體性不再獨(dú)特,而向一種集體性的方向發(fā)展。
這種設(shè)想仍然是科幻的一種情節(jié),但我們可以看到社會(huì)環(huán)境和肉體塑造個(gè)體獨(dú)特性這一功能。科學(xué)怪物從出生起沒(méi)有任何反社會(huì)傾向,甚至行為符合當(dāng)時(shí)的倫理秩序和道德要求,但就是在肉身的局限下,他的主體性意識(shí)發(fā)生了質(zhì)的變化。怪物的外表是“巨大的身材,丑陋的面孔”。此外,作者還運(yùn)用了很多筆墨來(lái)凸顯怪物外表的丑陋。在被誤解后仍然堅(jiān)持融入人類社會(huì)變成生物學(xué)意義肯定的“人”,都體現(xiàn)怪物有一種對(duì)肉身的不滿。他假設(shè)自己如果擁有一副“正常”的外表,那么他的美德都會(huì)表現(xiàn)出來(lái),說(shuō)明了人類社會(huì)的美德本身也是有前提的,而這個(gè)前提就是肉身所攜帶的人類特質(zhì),從怪物身上我們可以看到肉身對(duì)精神的塑造和對(duì)個(gè)體主體性的影響。這種由生命有限性帶來(lái)的特質(zhì)在新的歷史語(yǔ)境下有可能被技術(shù)所消除,而弗蘭肯斯坦的結(jié)局提醒人們,在后人文主義時(shí)代,威脅不再局限于有限的生命,而面臨著新的困境:無(wú)限的重生帶給人類的沖擊。
三、總結(jié)
不像那些哥特小說(shuō)家,瑪麗·雪萊無(wú)意通過(guò)魔法、迷信,或者幻想來(lái)制造恐懼,而是想表達(dá)來(lái)自現(xiàn)代科學(xué)本身的恐懼。那種實(shí)驗(yàn)已經(jīng)完全失控的“瘋狂科學(xué)家”形象在今天已經(jīng)見(jiàn)怪不怪,但是在瑪麗·雪萊的時(shí)代卻是全新,她走在了時(shí)代的前面。在多年以后今天的歷史語(yǔ)境下,瑪麗·雪萊的這部作品又有了嶄新的后人文主義解讀,對(duì)人與賽博格、人與自然等關(guān)系的和諧發(fā)展有著超前的意義和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