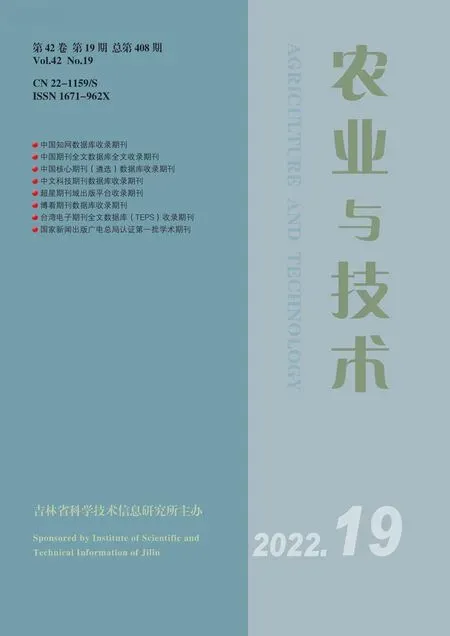基于二調和三調數據的甘肅省生態用地變化分析
蔣晨 徐鳳英 邵寧
(甘肅省基礎地理信息中心,甘肅 蘭州 730000)
引言
生態與人類生產生活息息相關,良好的生態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前提。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生態空間被擠壓的問題日趨嚴重,生態保護已經成為迫在眉睫的任務。生態用地作為一種重要的土地類型,在保障生態系統功能、維護國土生態安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中具有特殊地位[1]。因此,保護生態用地,開展生態用地研究,對于保障生態安全,協調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保護建設的相互關系,具有重要的意義。本文利用甘肅省二調和三調成果中所涉及生態用地數據,對甘肅省生態用地現狀及10a間生態用地的變化情況做了詳細的分析,為后續開展生態用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依據。
1 研究區概況
甘肅省位于我國西北部,地處黃土高原、內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交匯處,地理位置在N32°11′~42°57′,E92°13′~108°46′,國土面積42.58萬km2,東西長1600km有余,地域廣闊,地貌基本覆蓋了山地、高原、平川、河谷、沙漠、戈壁等多種類型。甘肅省地處亞歐大陸中間區段,是古絲綢之路的鎖鑰之地和黃金路段,獨特的區位優勢使甘肅成為西北地區鐵路、公路、航空、水運、管道兼備的綜合性交通運輸樞紐,是西部南來北往、東進西出的交通要沖。
2 數據源
2.1 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2009年二調及2019年三調成果數據。
2.2 生態用地界定
2000年,我國國務院發布《全國生態環境保護綱要》,提到“生態用地”,但沒有做出統一的定義。2001年石元春院士考察寧夏回族自治區時提出“生態用地”一詞,隨后在中國工程院咨詢項目《西北地區水資源配置與生態環境保護》報告中對生態用地概念做了進一步闡述[1]。截至目前,雖然“生態用地”屢次被提及,國內學術界研究者們對“生態用地”的內涵也分別從土地的主體功能[2-4]、土地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5-7]、土地的空間形態[8-10]角度發表了各自的觀點,但國內、國際都未對生態用地的分類有明確、統一的定論。喻峰、李曉波、張麗君對“中國生態用地內涵、分類與時空格局”的研究中,以生態系統服務主體功能為基礎,將生態用地劃分為濕地、森林、草地和其他生態土地4個一級類型、19個二級類型(包括沼澤濕地、湖泊濕地、河流濕地、濱海濕地、人工濕地、落葉林、常綠林、混交林、灌木林、人工生態林、高中低覆蓋度草地、人工生態草地、鹽堿地、沙地、裸巖石礫地、高寒荒漠及苔原、冰川及永久積雪)[11]。王靜對“中國生態用地分類體系及其1996—2012年時空分布”的研究中,將生態用地分為主導功能生態用地和多功能生態用地2部分。主導功能生態用地是指在生態、生產、生活3方面以生態功能為主的生態用地類型,包括灘涂、天然水域、鹽堿地、荒漠、沙漠、冰川及永久積雪、裸地等,以及城市綠地、城市人工水域、防護林等。多功能生態用地是指具有生態、生產、生活多功能的生態用地類型,如耕地、林地等[12]。
本文參照上述作者的觀點,并結合《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工作分類》[13],將三調分類中具有生態服務功能的濕地、耕地、園地、林地、草地、水域(包括河流水面、湖泊水面、水庫水面、坑塘水面和溝渠)、未利用生態用地(包括冰川及永久積雪、沙地、裸地)作為生態用地進行研究。
2.3 數據處理
二調土地分類中無濕地類型,為了保證同口徑分析,本文根據三調分類,將原二調中的內陸灘涂和沼澤地還原為二調濕地來分析。并將三調中的裸土地、裸巖石礫地合并作為裸地與二調裸地進行對比。
3 生態用地現狀
3.1 生態用地結構
三調數據成果顯示,2019年甘肅省生態用地總量占全省土地總面積的96.05%,其中草地所占比重最大,共占生態用地總面積的35.08%,其次為未利用生態用地,占27.71%;林地占19.57%;耕地占12.92%;濕地和園地比重較小,共占3.98%,如圖1所示。

圖1 2019年甘肅省生態用地結構圖
3.2 生態用地空間分布
從生態用地空間分布情況來看,見圖2,甘肅省生態用地的空間差異性明顯。2019年甘肅省生態用地面積超過165萬hm2的縣區主要集中在酒泉市,酒泉市生態用地面積占全省生態用地總面積的40.63%,見圖3,主要原因是酒泉市未利用生態用地和草地面積較大;甘南、張掖、武威、隴南、慶陽5地生態用地面積居中,共占全省生態用地總面積的37.72%;其余市州生態用地面積較少,其中嘉峪關、臨夏州、生態用地面積最少,分別占0.26%、1.58%。總體上看,甘肅省生態用地呈現西高東低、南高北低的特點,人口和經濟聚集地區生態用地空間較為匱乏,河西走廊地區生態空間則相對豐富。

圖2 2019年甘肅省生態用地空間分布圖
3.3 生態用地占比空間分布
從各縣域生態用地面積占本縣區行政區面積的比例情況來看,見圖3,甘肅省生態用地占比小于80%的縣區有5個,主要分布在蘭州市區和臨夏市區;80%~85%的有8個,主要分布在定西東南部、天水西北部;85%~90%的有16個,主要分布在定西、平涼、天水、臨夏州、慶陽等地;90%~95%的有33個,主要分布在蘭州、白銀、慶陽、隴南、平涼、張掖地區;大于95%的有29個,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地區、甘南高原區和隴南地區。總體來看,甘肅省生態用地占比空間分布呈現以隴中地區為中心,向外逐漸增加的特點。

圖3 2019年甘肅省生態用地占轄區比例情況
4 生態用地變化分析
4.1 生態用地結構變化
2009年甘肅省生態用地結構如圖4所示,結合前文2019年的生態用地結構,可以看出,10a間甘肅省生態用地結構變化比較微弱。截至2019年,草地占甘肅省生態用地的比重依然是最大的,但其變化幅度很小,其比重減少了僅0.19%;未利用生態用地相對其他地類來說,變化幅度較大,其比重減少了6.99%;林地變化幅度僅次于未利用生態用地,其比重增加了4.59%;濕地比重增加了2.02%;耕地、園地、水域所占比重變化幅度均較小,其比重分別是減少0.35%、增加0.43%、增加0.10%。

圖4 2009年甘肅省生態用地結構圖
4.2 生態用地面積變化
截至2019年,甘肅省生態用地總面積凈增加14.66萬hm2。各地生態用地面積的變化存在明顯的地域差異,其中面積增加較多的市州依次為張掖、酒泉、隴南、平涼、武威及3個獨立區;面積減少較多的市州依次為慶陽、蘭州、定西、臨夏、天水、甘南、嘉峪關、白銀、金昌,如圖5所示。

圖5 2009—2019年甘肅省及各市(州)生態用地面積變化
從各類生態用地面積變化情況來看,見圖6,10a間,甘肅省生態用地分類中,未利用生態用地變化幅度最大,減少了280.49萬hm2,主要集中在河西的酒泉、武威、金昌等地;其次變化較大的是林地,增加190.17萬hm2,主要集中在酒泉、武威、隴南等地;濕地變化也比較大,增加了82.57萬hm2,主要集中在甘南州、酒泉、張掖等地;耕地減少12.57萬hm2,主要集中在天水和平涼;園地增加17.64萬hm2,主要集中在天水和平涼;草地增加13.27萬hm2,主要集中在酒泉市;水域變化不大,僅增加4.06萬hm2,主要集中在酒泉市。

圖6 2009—2019年甘肅省各市(州)各類生態用地面積變化
4.3 生態用地變化率
從生態用地各地類的變化率看,見圖7、表1,2009—2019年,甘肅省生態用地各項地類的變化率整體呈現正增長,表現突出的依次是甘南州、嘉峪關、獨立區、酒泉、慶陽。甘南州濕地變化率最大,高達4764.05%,草地和未利用生態用地有所減少;嘉峪關林地變化率最大,為1836.38%,草地和濕地變化率也較大,分別為568.27%和475.12%,園地和未利用生態用地有所減少;3個獨立區的濕地面積變化率最大,為1381.71%,居全省第2;酒泉林地和園地變化率較大,分別是416.55%、282.13%,未利用生態用地減少,其變化率為-15.92%;慶陽未利用生態用地變化最大,為575.06%,耕地和草地呈負增長。

圖7 2009—2019年甘肅省生態用地各地類面積變化率
總體來說,甘肅省生態用地中除耕地和未利用地呈現負增長,其他地類均為正增長態勢,主要原因是受近年來城鎮化建設和未利用地開發等因素的影響。

表1 2009—2019年生態用地各地類面積變化率
通過2009—2019年生態用地數據對比計算得出,甘肅省10a間,生態用地面積呈微弱增長態勢,增長幅度為0.36%。從甘肅省縣域生態用地面積變化率的空間分布來看,見圖8,生態用地變化具有明顯的區域特征,臨夏州的臨夏市、蘭州市的城關區、安寧區生態用地變化率小于-4.0%,減少幅度為全省最大;酒泉的玉門、張掖高臺和肅南、隴南中東部、天水北部、平慶東南部生態用地面積變化相對較大,變化率均大于1.0%。

圖8 2009—2019年甘肅省生態用地面積變化率分布
5 結束語
掌握生態用地資源,是加強生態文明建設,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構建社會主義文明的基礎。本文利用2009年二調和2019年三調數據中所涉生態用地數據,對甘肅省生態用地現狀從結構、空間分布及縣域單元生態用地占比空間分布3個方面進行了詳細分析,掌握了甘肅省生態資源分布現狀。并對2期數據從生態用地結構、面積和變化率3個方面進行分析,從而得出甘肅省10a內生態用地的變化情況。總體而言,2009—2019年,甘肅省生態用地面積整體呈現微弱增勢,生態用地地類結構變化也較小,說明甘肅省生態用地10a內持續穩定,且生態逐漸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