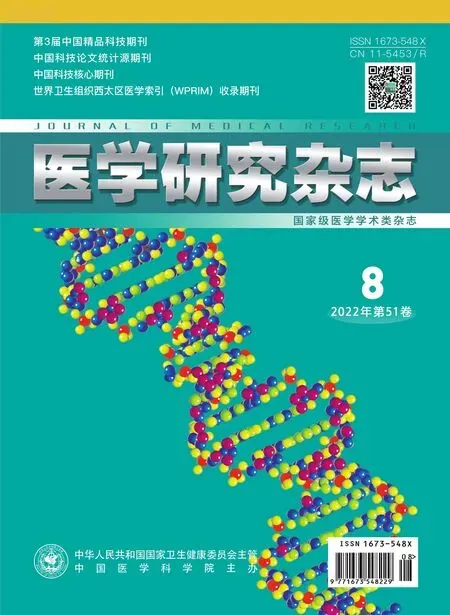結直腸癌微環境的免疫抑制機制及相關治療研究進展
崔婧雯 李袁飛
大量研究表明,結直腸癌的發生、發展強烈依賴于其所處的周圍局部腫瘤微環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而免疫監視及免疫逃逸系統在微環境的形成和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為了逃避免疫系統的殺傷,腫瘤細胞會招募免疫抑制性細胞、分泌免疫抑制性因子、激活有關信號通路等重塑并形成免疫抑制的微環境,來促進自身生長、增殖、侵襲和轉移,并對免疫療法和其他抗腫瘤治療產生耐藥性。另有研究表明,腸道中微生物群落也與一些免疫反應有關,在TME免疫調控中也起著重要作用。因此本文探討了結直腸癌(colorectal cancer,CRC)免疫抑制微環境的各種機制,并總結了目前靶向結直腸癌腫瘤免疫微環境(tumor immune microenvironment,TIME)的治療方法,指出了靶向TIME在結直腸癌治療中的意義、潛力和可行性。
一、免疫抑制性細胞浸潤
在CRC發生、發展過程中,多種免疫抑制性細胞在腫瘤細胞分泌的生長因子、趨化因子、細胞因子的作用下被招募到TME中,主要有腫瘤相關巨噬細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TAM)、骨髓源性抑制細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DSC)、調節性T細胞(T regulatory cells,Treg)、調節性B細胞(B regulatory cells,Breg)等。TAM是CRC中檢測到的最豐富的細胞類型,分為M1型和M2型。M1型(抑癌型)具有促炎特性,通過激活核因子-κB通路在宿主對腫瘤細胞的免疫防御反應中至關重要;而M2型(促癌型)具有抗炎特性,主要分泌白細胞介素(interleukin,IL)-10、轉化生長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TGF)-β等介導輔助性T細胞(T helper cell,Th)2型免疫反應,抑制自然殺傷細胞(natural killer cell,NK細胞)遷移,以及上調轉錄因子叉頭盒蛋白P3(transcription factor forkhead box P3,FOXP3)的表達促進Treg的分化,一般來說TAM更接近于M2型,因此制定策略將M2型逆轉為M1型可以提高抗腫瘤免疫反應能力。MDSC是一類具有異質性的骨髓來源細胞群,在TME中它們成熟受阻,停留在各個分化階段,分為多核MDSC和單核MDSC,后者可以進一步分化為TAM。MDSC抑制T淋巴細胞免疫的機制已經得到了充分的研究。MDSC會下調T淋巴細胞受體αβ鏈的表達、調節T細胞G/G細胞周期、增加Fas配體(Fas ligand,FasL)的表達抑制T淋巴細胞增殖,促進T淋巴細胞凋亡。
Treg是一類維持外周耐受性和限制炎性反應的T淋巴細胞亞群,其特征是高表達CD25(即IL-2受體α鏈)和FOXP3。Treg在大多數癌癥中與腫瘤生長和不良預后相關,但是在CRC中的預后價值一直有爭議。研究發現,在CRC中,Treg根據FOXP3的表達水平可以分為兩種亞群,即FOXP3(hi)抑制型和FOXP3(lo)非抑制型,FOXP3(lo)Treg不具有免疫抑制作用,并分泌炎性細胞因子,與FOXP3(hi)Treg比較,伴大量FOXP3(lo)Treg浸潤的CRC的患者預后更好。研究表明,免疫共刺激分子OX40可以直接抑制FOXP3的表達來直接影響Treg的分化,因此它可能是Treg的一個治療靶點。
腫瘤相關肥大細胞(tumor-associated mast cells,TAMC)是近年來發現在CRC中另一種與不良預后相關的免疫抑制細胞。研究發現,結直腸癌中TAMC和Treg在TME中共定位并且兩者相互作用可以觸發免疫抑制。在人類CRC和小鼠息肉病中TAMC誘導Treg下調IL-10、上調IL-17,來促進自身脫顆粒釋放抗炎性細胞因子抑制T淋巴細胞反應,促進腫瘤進展,因而靶向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也可能有助于控制CRC。與Treg類似,近年來有研究發現,B淋巴細胞也可在微環境中獲得免疫抑制表型,分化為Breg細胞。它可以通過表達程序性死亡蛋白配體-1(programmed death ligand-1,PD-L1),分泌IL-10、IL-35、TGF-β等參與免疫耐受的發展與維持。但是需要更多的研究鑒定其表面特異性標志物以及明確調控它們分化的機制。
二、免疫抑制性信號通路的激活
CRC細胞會發生許多信號通路分子基因突變。與良性腺瘤和正常組織比較,TGF-β在CRC中表達明顯增加,尤其在免疫不活躍的共識分子亞型的間充質型,可以觀察到明顯的TGF-β/Smad信號通路的激活。研究表明,TGF-β/Smad在CRC中可以調節T淋巴細胞、NK細胞、TAM、B淋巴細胞、先天淋巴樣細胞、DC等許多先天性和適應性免疫細胞的功能來幫助腫瘤細胞逃避免疫監視。小鼠模型中,藥理抑制TGF-β信號可以產生比阻斷免疫檢查點更快速而持久的Th1免疫反應,并有效阻斷腫瘤轉移定植。
IL-6/信號轉導和轉錄激活因子(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STAT3)通路是CRC炎癥相關過程的信號通路,其過度活化會下調免疫誘導因子干擾素(interferon,IFN)、IL-12、腫瘤壞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的表達,上調免疫抑制因子IL-6、IL-10、TGF-β、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的表達。Hidemitsu等研究表明,IL-6/STAT3通路也可下調主要組織相容性復合體Ⅱ的表達損傷樹突狀細胞(dendritic cells,DC)的抗原遞呈功能,用IL-6受體抑制劑體外阻斷IL-6可以恢復DC的功能。針對IL-6/STAT3通路的治療目前最有效的是STAT3抑制劑BBI608,其聯合化療的Ⅰb/Ⅱ期的控制率達83%,目前正在進行Ⅲ期(NCT03522649)以及聯合ICI的臨床試驗(NCT03647839)。此外,Wnt/β-連環蛋白(β-catenin)通路和Ras/Raf/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EK)/細胞外調節蛋白激酶(extracellu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ERK)通路的異常激活也與免疫抑制微環境的形成有關,是免疫治療的一大阻礙。
三、免疫抑制性代謝的增強
在TME中為了滿足對營養和能量的要求,CRC在內的大多數癌細胞會經歷代謝重編程,包括有氧糖酵解增加(即Warburg效應)、谷氨酰胺“酵解”、脂質和蛋白質合成增加等。這些代謝改變不僅會剝奪對T淋巴細胞和NK細胞增殖和功能發揮重要作用的營養物質,而且產生的代謝產物也會影響TME中的免疫反應。在體外培養基中,有氧糖酵解產生的細胞外高乳酸會降低細胞內PH誘導NK細胞凋亡,抑制細胞毒性T淋巴細胞增殖并損傷其產生IFN-γ的能力。
一些氨基酸分解代謝水平的增高是TIME的一個標志,微環境中的吲哚胺2,3-雙加氧酶(indole amine 2,3-double oxygenase,IDO)、精氨酸酶會分解大量色氨酸、精氨酸,這些氨基酸的代謝會阻斷CD8T細胞的激活,并誘導CD4T細胞向Treg分化。另外,在CRCTME缺氧、缺血、炎癥條件下,細胞表面酶CD39和CD73活性增高,ATP大量水解,同時腺苷脫氫酶與腺苷激酶活性降低,導致腺苷無法及時分解代謝大量聚集在TME中。一項對人類結腸癌標本的原位微透析分析表明,CRC胞外腺苷濃度比正常組織增加了20倍。高腺苷濃度的長期存在會通過A、A腺苷受體(adenosine receptor,AR)的介導調節T細胞免疫,觸發并維持免疫抑制效應。
研究證明靶向代謝物、酶或者相關轉運受體可以抑制免疫抑制性代謝,如糖酵解抑制劑(1,2-脫氧葡萄糖)、IDO抑制劑(epacadostat)、谷氨酰胺分解抑制劑(CB-839)、CD73拮抗劑(BMS-986179)、AAR拮抗劑(CPI-444)等。CB-839是一種谷氨酰胺酶抑制劑,其與西妥昔單抗在耐藥的CRC細胞模型中顯示有效,說明CRC患者可能受益于這種靶向腫瘤生存所需“燃料”和信號通路的聯合治療。近年來研究發現,免疫檢查點會影響TME中腫瘤細胞與T淋巴細胞之間的代謝競爭,因此ICI聯合代謝抑制劑可能也有協同抗腫瘤效果。
四、新生血管異常
腫瘤血管是腫瘤營養輸送及腫瘤細胞轉移的通道,腫瘤血管密度是影響包括CRC在內的眾多惡性腫瘤臨床預后的重要因素。其中VEGF在調控血管生成中起主要作用,也是主要的免疫抑制因子。臨床前數據表明,靶向VEGF(如貝伐珠單抗)可以減少腫瘤部位的Treg、MDSC,增加效應T細胞(effector T cell,Teff)的浸潤,并同時增加PD-1等免疫檢查點的表達,這為血管生成抑制劑聯合ICI提供了理論基礎。
靶向血管生成素(angiopoietin,Ang)-2是另一種血管抑制策略。Ang-2由內皮細胞產生,作用于酪氨酸激酶受體Tie-2參與血管重構,并促進VEGF的血管生成作用。與VEGF不同,Ang-2/Tie-2對T淋巴細胞沒有直接影響,但它可以刺激TAM M2的極化和分泌IL-10,誘導Treg擴增間接抑制T淋巴細胞。目前Ang-2抑制劑AMG386(Trebananib)已進入臨床試驗。另外腫瘤相關內皮細胞(tumor-associated endothelial cells,TEC)也參與了微環境免疫重塑。此外缺氧會激活缺氧誘導因子-1(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HIF-1),在TGF-β共同存在的情況下,HIF-1可直接與CD4T細胞的FOXP3啟動子區域結合,上調FOXP3的表達,誘導Treg的形成。因此TEC或者HIF-1可能是未來CRC的抗血管治療靶點。
五、免疫抑制性基質
1.腫瘤相關成纖維細胞(tumor-associated fibroblasts,CAF):CAF是CRC間質中數量最豐富的異質性細胞群體。CAF是TGF-β的主要來源,CAF分泌大量的膠原蛋白、牽連蛋白沉積形成瘢痕組織,作為物理屏障阻礙T淋巴細胞、NK細胞浸潤腫瘤。另外CAF可以分泌大量的趨化因子,尤其是基質細胞衍生因子(stromal cell derived factor,SDF)-1,其唯一受體是C-X-C基序趨化因子受體4(C-X-C motif chemokine receptor 4,CXCR4)。在臨床前模型中抑制SDF-1/CXCR4軸可以觀察到腫瘤中大量T淋巴細胞浸潤,逆轉免疫抑制。
2.結直腸癌干細胞(colorectal cancer stem cells,CCSC):CCSC是一群具有自我更新、多能分化和強致癌性的一小群細胞,近年來它被證明擁有強大的免疫調節能力。其可以通過抑制DC和NK細胞的增殖和激活來對抗宿主對轉化腫瘤細胞早期免疫反應,并抑制細胞因子產生之后Teff的活化和增殖。在體外培養基中,用IFN-γ、TNF-β預處理CCSC會使其具有更強的免疫抑制作用,誘導更大腫瘤的形成。針對CCSC的嵌合抗原受體(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CAR)-T淋巴細胞、雙特異性抗體(solitomab)等免疫靶向治療已經被開發出來。另外一些特有的信號通路和表觀遺傳調控因子與CCSC的干性密切相關,它們可能是未來的治療方向。
3.外泌體:外泌體是細胞分泌的直徑為50~150nm的脂質雙分子層囊泡,作為細胞間通訊分子可以調節TME中的免疫反應,其富含多種免疫活性物質,如FasL、PD-L1、IL-10、TGF-β、腫瘤壞死因子相關凋亡誘導配體等。由于外泌體具有低免疫原性和細胞毒性、靶向性強、生物相容性高的特點,作為納米載體有巨大的潛力,可以考慮利用它進行抗腫瘤藥物傳遞。
六、宿主相關因素-腸道微生物
作為人體的“第二基因組”,已有大量研究表明腸道微生物在CRC發生、發展中的作用。近年來研究表明,它們也可作為免疫和代謝調節劑影響機體抗癌免疫反應。具核梭桿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Fn)、產腸毒素型脆弱擬桿菌(Eeterotoxigenic-bacteroides fragilis)和其釋放的細胞死亡毒素、脆弱芽胞桿菌毒素通過激活Toll樣受體和NOD樣受體,增加IL-6、TGF-β的產生,誘導Th17細胞和Treg的產生。并且Fn表面的Fad2蛋白可與NK細胞和T淋巴細胞上的T淋巴細胞免疫球蛋白和ITIM結構域蛋白(T cell immunoreceptor with Ig and ITIM domains,TIGIT)的結合誘導免疫細胞耗竭。而一些保護性的細菌,雙歧桿菌可以下調DC激活T淋巴細胞的閾值,使較少的抗原也能產生T淋巴細胞免疫應答。
海氏腸球菌(Enterococcus hirae)可以增加腫瘤中記憶T細胞的數量。被稱為抗癌界的“明星細菌”——嗜黏蛋白艾克曼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Akk菌),是一種藥物敏感型患者中大量存在的有抗腫瘤效果的有益菌,其可通過腺苷-AAR途徑促進Th1細胞的分化,并且可通過IL-12促進Teff殺傷腫瘤細胞,改善免疫應答反應,增強ICI的療效。Tanoue等在小鼠結直腸癌移植模型中鑒定出11組與PD-1單抗治療效果有關的菌株,并且這些小鼠免疫相關結腸炎的發生率也降低。因此一些腸道微生物群不僅可以促進免疫治療的療效,還可減少免疫不良事件的發生。糞便菌群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的安全性和可行性在既往ICI治療失敗的黑色素瘤的Ⅰ期試驗中得到了初步證實,目前正在驗證是否也可以用于CRC。隨著越來越多的研究揭示了腸道菌群與結直腸癌TIME的關系,它們可以作為抗癌治療的突破口,克服免疫治療耐藥,成為未來抗腫瘤治療的一部分。
七、展 望
本文綜合討論了CRC微環境中幾種主要的免疫抑制調控機制并指出了潛在的治療靶點。由于CRC微環境的復雜性我們對癌細胞免疫逃逸機制的認識仍有限,需要更多的試驗研究和臨床證據。并且在未來可以將多種因素結合起來進行分析,來探索它們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協同的關系。鑒于所有的免疫療法和大多數傳統的抗癌方法都依賴于腫瘤微環境中的免疫反應,靶向CRC的TIME是一種很有前途的治療手段,無論是單獨或聯合其他抗腫瘤治療,都有可能在未來造福結直腸癌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