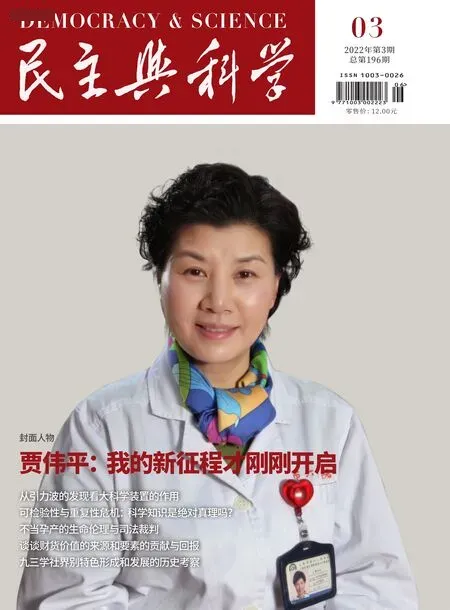從引力波的發現看大科學裝置的作用
谷昭逸 李 俠
一、大科學時代與大科學裝置的興起
“大科學”(Big Science、Mega Science、Large Science)的概念是由美國科學學家普賴斯于1962年率先提出的,在他著名的《小科學、大科學》的演講中,他認為世界自二戰時期起已經進入了大科學時代。在小科學時代,科學家或工程師能憑借個人的財力和興趣投入有限的資源從事科技創新工作,科研活動整體呈現一種分散、個體或小集體的形式特點。與之相對的大科學的具體特點為研究目標宏大、多學科交叉、實驗設備昂貴、投資強度大、科研成果重大、大量人才聚集等。大科學裝置是典型的大科學時代科技發展的產物。
大科學裝置隸屬于重大科技基礎設施一類,但何謂“大科學裝置”尚沒有統一的定義,目前學界通常將“大科學裝置”定義為:需要通過較大規模的投入和工程建設來完成,建成后可以通過長期的穩定運行來持續地為科學技術活動、科學技術前沿突破提供巨大幫助的大型設施。在大科學的時代背景下,從事前沿科學領域研究的門檻越來越高,其中的一個主要障礙就是離不開大科學裝置的協助。
天文學是一門將觀測與理論緊密結合的學科,隨著人類可觀測到的宇宙范圍不斷擴大,科學家們對于天文觀測儀器的精度和準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較于早期基礎的折射望遠鏡和反射望遠鏡,如今的現代大天文望遠鏡通常都具備大鏡面、拼接鏡、主動光學等特點。除了地面上的大型望遠鏡之外,天文大科學裝置還包括觀測衛星、空間望遠鏡等游弋在宇宙中的觀測儀器。天文大科學裝置的使用不僅能產生天文學領域的巨大突破,還能帶動相關科學技術領域的發展。
二、天文大科學裝置的涌現與引力波的發現
基于科學史的梳理可以發現,引力波自1916年提出直至2015年得到證實,對它的研究不間斷地持續了一個世紀,算得上是物理學史中跨度較久、延續時間較長的一個代表性問題。
引力波概念最早由物理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1916年發表的廣義相對論中提出。愛因斯坦認為引力波是指時空彎曲中的漣漪,通過波的形式從輻射源向外傳播,這種波以引力輻射的形式傳輸能量,簡單來說引力波是物質和能量的劇烈運動和變化所產生的一種物質波。
引力波概念一經提出便引起整個科學界的轟動,各國科學家立刻投身于證實引力波存在的工作中。由于引力波的探測屬于物理學與天文學交叉的領域,對其性質的揭示有助于人類對宇宙性質的理解,引力波很快成了國際學術研究的熱點之一。在攻克這個難題的道路上,很多科學家做出了偉大的工作,其中標志性的工作有如下兩項,1993年和2017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也正是授予了推動引力波研究的五位科學家。
美國物理學家拉塞爾·赫爾斯(Russell A·Hulse,1950——)和另一位美國物理學家約瑟夫·泰勒(Joseph H·Taylor,1941——)因發現脈沖雙星PSR1913+16,并通過計算相關數據得出引力波存在的間接證據,憑借該項成果獲得1993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赫爾斯和泰勒利用位于美屬波多黎各島山谷中的阿雷西博射電望遠鏡,對脈沖雙星PSR1913+16進行觀測,發現脈沖雙星的軌道周期在不斷減小,并意識到這兩顆星在越來越緊縮的軌道上越來越快地互相繞著旋轉。雖然這種變化是非常小的,僅為軌道周期每年大約減1秒的百萬分之七十五,普通儀器很難觀測到,但阿雷西博射電望遠鏡因為功能強大便足以觀測出該結果。這種微小的變化可以用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理論很好地解釋,有力證明了脈沖雙星正在以引力波的形式不斷發射能量。于是該觀測結果和結論成為證明引力波真實存在的一個強有力的間接證據。
阿雷西博射電望遠鏡建成于1963年,建成時直徑為305米,后擴建升級為350米,建成時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天文射電望遠鏡。阿雷西博射電望遠鏡配備了一部波長為126厘米,發射功率為百萬瓦的發射機和雙偏振接收機,工作頻率達到了0.05-10 GHZ,出色的收放能力使其滿足了觀測脈沖雙星的硬性指標。赫爾斯和泰勒憑借阿雷西博射電望遠鏡出色的性能,率先觀測到了脈沖雙星的存在,并對脈沖雙星進行了長期的觀測,得到了其20年的軌道周期值,為他們之后的計算工作提供了第一手的數據來源。
脈沖星的輻射一般是很弱的,當時觀測到的最弱的脈沖星其流量密度只有0.1毫央斯基,也就是說在地球每平方米每赫茲只接收到10瓦的功率。因此射電望遠鏡就需要擁有盡量大的天線面積、頻寬足夠寬的接收機才能保證捕捉到如此細微的信號。當時,阿雷西博射電望遠鏡正是具備了上述特點才在天文觀測領域一枝獨秀,使美國科學家在脈沖雙星研究領域遙遙領先于蘇聯和歐洲其他發達國家的科學團隊。1977年,蘇聯在北高加索地區建成直徑為576米的RATAN-600射電望遠鏡,在脈沖雙星觀測的競賽中已經處于后發地位。盡管RATAN-600射電望遠鏡在口徑方面超過了阿雷西博望遠鏡,但其他的硬件配置和科研目標的設定上的落后狀態,使其不能滿足發現并觀測脈沖雙星的條件。
20世紀70年代,除了阿雷西博射電望遠鏡和RATAN-600射電望遠鏡之外,世界上已經建成的條件精良的望遠鏡還包括位于德國埃費爾斯貝格和美國格林班克的兩臺直徑為100米射電望遠鏡。與它們相比,阿雷西博射電望遠鏡從口徑上完勝它們,更不用說阿雷西博射電望遠鏡的靈敏度也遠高于它們。
由此可見,在觀測脈沖雙星的案例中,阿雷西博射電望遠鏡對于赫爾斯和泰勒的科研成果的取得具有基礎性的作用。此后,各國科學界都意識到,在天文觀測領域中,擁有性能出色的大型天文望遠鏡對探索宇宙奧秘的重要性,開始在本國建造精度更高、測量范圍更廣的天文望遠鏡。
隨著科學技術手段的不斷進步,科學家開始意識到,要直接證實引力波的存在,依靠傳統的光學望遠鏡和射電望遠鏡幾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建造激光干涉引力波觀測器(The Laser Interferometer Gravitational-Wave Observatory,簡稱LIGO,國內學界將其翻譯為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臺,筆者認為應該聚焦于儀器,而不是籠統的天文臺)被提上議程。隨著第二代激光干涉引力波觀測器Advanced LIGO的建成,引力波隨即被證實。美國物理學家雷納·韋斯(Rainer Weiss,1932——)、巴里·巴里什(Barry Barish,1936——)和基普·索恩(Kip Thorn,1940——),他們因建造發現引力波的激光干涉引力波探測器(LIGO)而榮獲2017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20世紀末期,發達國家諸如美國、德國、日本和英國都開始建造第一代激光干涉引力波探測器,希望能率先證實引力波的存在。進入21世紀后,美國建成了LIGO;意大利和法國合建了位于比薩附近的室女座引力波探測器(VIRGO);德國和英國聯合建造了位于漢諾威的GEO;日本建造了東京國家天文臺的TAMA300。隨著各國大型激光干涉引力波探測器的建成和投入使用,世界各國進入了新一輪的天文觀測競賽。
激光干涉引力波觀測器的工作原理與1887年的邁克爾遜——莫雷的實驗原理相近,從本質來說是一個精良的邁克爾遜干涉儀。阿爾伯特·邁克爾遜(Alert Michelson)和愛德華·莫雷(Edward Morley)通過著名的判決性實驗測量得到光速在不同慣性系和不同方向上都具有相同的速度,從而否定了以太這種物質的存在。與之相似的是,激光干涉引力波探測器是通過監測等距且互相垂直的兩個方向上干涉條紋的細微變化,若存在細微變化則證明引力波的存在。以位于美國利文斯頓的大型激光干涉引力波探測器LIGO(llo)為例,LIGO(llo)是由兩個直徑超過1米呈“L”型放置的空心圓柱體組成,在兩臂交會處,從光源發出的激光束被一分為二,分別進入互相垂直并保持超真空狀態的兩空心圓柱體內,激光束在空心圓柱體內會運行4千米,再被終端的用導線懸掛的帶有鏡面的重物反射回原出發點,并在那里相互干涉。這時若有引力波通過,便會引起時空變形,即一臂的長度會略微變長而另一臂的長度則略微縮短,于是干涉條紋發生變化。因此只要探測到這種變化存在,便可證實引力波的確切存在。
由于引力波的振幅極小,因此在與物質相互作用時所能引起的尺度變化是極小的,這種細微的變化甚至連第一代靈敏度為10的激光干涉引力波探測器也無法捕捉到。為了能成功探測到引力波的存在,各國科學家在第一代激光干涉引力波探測器的基礎上,將它們升級改造為第二代激光干涉引力波探測器。
在2015年9月14日,美國的第二代激光干涉引力探測器即高級激光干涉引力波探測器(Advanced LIGO)成功觀測到了兩個黑洞合并產生的引力波事件(GW150914),由此證實引力波的確存在。
Advanced LIGO是以LIGO為基礎升級而來的,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精度最高的引力波觀測器。Advanced LIGO是由加州理工學院和麻省理工學院共同負責運行,它由兩個干涉儀組成,其中一個干涉儀LIGO(llo)位于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利文斯頓,另一個干涉儀LIGO(lho)位于美國華盛頓州漢福德。其中位于漢福德的觀測器雙臂長度分別為4千米和2千米,在利文斯頓的觀測器雙臂長度為4千米,兩地相距3002千米。與第一代LIGO相比,升級后的Advanced LIGO激光功率從原來的10瓦特提高至了200瓦特,探測頻道下限從40Hz延伸到了10Hz,并將觀測器的靈敏度提高至10——10這一量級。在當時,Advanced LIGO相較于法國的VIGRO、德國的GEO和日本的TAMA300,無論是在探測精度、干涉儀雙臂長度以及探測頻率都優于它們,這使得美國在引力波觀測領域遙遙領先。也正是因為這次的全面升級,Advanced LIGO的探測范圍和探測能力得到極大提升,為美國科學家優先證實引力波的存在提供了堅實的科研儀器保障。
在證實引力波存在的百年征途上,阿雷西博射電望遠鏡和Advanced LIGO都證明了天文大科學裝置在探索宇宙未知現象中的重要地位,美國也正是因為擁有了當時無出其右的大科學裝置才能夠拔得頭籌,最終獲得發現的優先權,進一步強化了在科學界的話語權和科技霸主的地位。
三、天文大科學裝置的價值和作用
通過上述對引力波的提出到最終證實的發展歷程的考察,可以看出天文大科學裝置在科學發展中具有如下顯著作用和價值:
1.天文大科學裝置對天文科學前沿領域突破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隨著人類能觀測到的宇宙范圍在不斷擴大,原有的技術和觀測裝置已經滿足不了天文學快速發展的客觀需求。縱觀近年來在諾貝爾物理學獎項上有所斬獲的天文學家,他們的成功大都離不開天文大科學裝置的幫助。例如,2020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了德國天體物理學家賴因哈德·根澤爾(Reinhard Genzel,1952——)和美國天文學家安德里亞·格茲(Andrea Ghez,1965——),他們通過使用夏威夷凱克(Keck)望遠鏡和智利的甚大望遠鏡VLT(Very Large Telescope)對銀河系中心恒星進行運動學測量,并憑測量結果從動力學角度準確發現了超大質量的致密天體從而獲獎。此外,2019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了瑞士物理學家米歇爾·馬約爾(Michel Mayor,1942——)和瑞士天文學家奎洛茲(Didier Queloz,1966——),他們因發現繞著類太陽恒星飛馬座51運轉的系外行星飛馬座51b而獲獎。他們在觀測系外行星飛馬座51b時采用了徑向速度法的方式,并通過普羅旺斯天文臺的埃洛迪射譜儀發現了這顆行星,這一發現也被利克天文臺的哈密爾頓譜射儀的觀測數據所佐證。在飛馬座51b被發現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對于系外行星的觀測一直不太順利;但隨著高分辨率光譜學和更加精準的攝譜儀的出現,才使探測由可能轉變為了現實。值得一提的是,自馬約爾和奎洛茲開啟了系外行星探測的序幕后,該領域逐漸成了行星科學和系外行星探測中的熱門方向。在系外行星的探測工作中,根據掩星法原理設計的開普勒空間望遠鏡做出了極大貢獻,截至2019年底,共有4130顆系外行星被確認,其中利用掩星法發現了2962顆,占總數的71.72%;其中開普勒空間望遠鏡發現了2734顆系外行星,占總發現數的66.20%,占用掩星法發現數的92.30%。除了大型天文望遠鏡對宇宙探索做出的杰出貢獻外,在某些特定領域探測衛星也功不可沒。早在1989年,美國宇航局(NASA)發射了一顆專門探測宇宙微波背景輻射(cosmic microwave background,簡稱CMB)的觀測衛星,即宇宙背景探測者衛星(COBE),在當時以極為完美的精度驗證了CMB的黑體分布律以及背景溫度,并首次觀測到了均勻溫度背景下的溫度漲落,而這一漲落后來進一步被美國宇航局的威爾金森微波各向異性探測器(WMAP)和歐洲空間局的普朗克衛星驗證。COBE衛星的發射標志著所謂的“精確宇宙學”的來臨,也使得COBE衛星項目的兩位首席科學家約翰·馬瑟(John Mather,1946——)和喬治·斯穆特(George Smoot,1945——)被授予了2006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由此看來,當下對于宇宙中未知領域的探索,將會越來越依靠這些先進的大科學裝置,缺少這些裝置的國家甚至可能被永遠排除在科學的前沿之外。
2.大科學裝置是科學家獲得優先權的強大幫手
就在Advanced LIGO探測到了引力波后,法國的VIGRO就以Advanced LIGO為參照對象,采取了相應的設備升級,并在2016年與美國的兩臺Advanced LIGO合作,一起證明了在距離地球18億光年外的恒星質量黑洞合并產生的引力波信號。VIRGO對于引力波的探測,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證了在大科學時代一旦有了前車之鑒,“依葫蘆畫瓢”是件相對容易的事情。當代科研的難點通常在于如何取得原創性的科研成果。
科學社會學家默頓曾指出:科學界的多重發現是科學活動中的一種常態,即遠在不同國家的科學家們會在近乎相同的時間段內提出同一種理論或發明。長期以來,科學發明或發現的優先權之爭是科學界最為持久的競爭,因為它是每個科學家獲得科學共同體承認的基礎,一旦擁有優先權,科學家就能獲得比后來者更高的收益。因此,在存在多重發現的背景下,智力水平相近的科學家沿著幾乎相同的研究路徑與方法,此時實驗儀器的精度如何將會直接關系到誰能率先爭奪到發現的優先權。從引力波的案例就可以看出,阿雷西博望遠鏡和Advanced LIGO的出色性能為美國科學家在優先權的爭奪中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此外,加拿大天文學家布魯斯·坎貝爾(Bruce Campbell)早在1988年就預言過系外行星的存在,但由于當時觀測技術水平有限,觀測數據質量不佳,坎貝爾本人和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對觀測結果有所保留。盡管2002年,麥克唐納天文臺憑借最新的觀測數據證實了坎貝爾的發現,他也得到天文學界的承認,但卻錯過了成為首位發現系外行星的科學家的機會,也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
3.天文大科學裝置也是國家綜合國力的體現
天文大科學裝置往往建設周期長,耗資十分巨大,需要政府通過公共財政投入予以支持。早在1990年哈勃空間望遠鏡發射時,發射成本已經高達12億美元,算上運行以來的所有維修費用,目前哈勃空間望遠鏡總共花費了近100億美元;發現引力波的LIGO天文臺造價為20億美元;最近美國航空航天局、歐洲航天局和加拿大航天局聯合研發的詹姆斯·韋伯望遠鏡(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簡稱JWST)也已發射升空,據學者估計其成本高達100億美元。以我國為例,貴州建成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射電望遠鏡天眼(FAST),該大科學工程的建造耗時8年,投資超12億人民幣。因此,耗資巨大的大科學裝置建設不是科學界內部可以獨立完成的事情,而是需要國家力量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說,通過觀察一個國家擁有的大科學裝置數量以及對于建造大科學裝置的意愿,可以反映出該國對基礎科研設施和前沿科學探索的重視程度和投入力度,這也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一個外在表征。
四、我國天文大科學裝置的現狀及問題
1.我國天文大科學裝置總量偏少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力穩步提升,國家針對科技領域尤其是基礎研究方面的投入不斷增多,比重也在逐年加大。總體而言,目前我國大科學裝置建造工作已經平穩渡過萌芽期和成長期,與發達國家間的差距正在不斷縮小。雖然在大科學儀器數量上已慢慢向發達國家靠攏,但在天文大科學裝置數量方面依舊偏少,我國目前僅擁有郭守敬望遠鏡(LAMOST)、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FAST)、新疆太陽磁場望遠鏡等少數幾臺天文大科學裝置。
2.大科學裝置研發過程效率低下
目前,我國大科學裝置的研發通常采用“牽頭人+合作單位”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下,牽頭人與合作單位的負責人是處于一種平級關系,并非隸屬關系,由于雙方存在利益訴求的差異,經常出現合而不作的現象。相較于常規的科學裝置的開發,大科學裝置的研發往往會聚集行業內的頂尖學者,各個合作單位一般是由院士或是長江學者帶頭,這樣頂級的人員配置,會帶來研發過程中牽頭人的話語權不夠,共識難以達成、扯皮敷衍盛行,使得研發效率大打折扣。最后在驗收環節,面對行業內的頂尖專家,驗收評審人往往會出于一些人情方面考慮而非科學的評估而放水,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驗收評價的客觀性,從而導致某些大科學裝置建造成為爛尾項目,即便一些裝置勉強投入使用,其實際效果也不明確。
3.天文領域重大科研成果產出較少
大科學裝置的建造都是具有明確的科研目標和國家使命的,主要目的就是為原始創新和原始探索提供全新的素材與載體,并最終將其轉化為科研成果。盡管我國科學家也依托FAST射電望遠鏡、LAMOST望遠鏡等天文大科學裝置在、等學術頂刊上發表許多研究成果并獲得多項專利,但在獲取頂尖科學成就的天平上卻依舊寥有所獲。在評價科研成果的含金量時,最重要的一個指標就是看是否獲得了該領域中最高級別的獎項,具體在天文領域中,最負盛名的獎項有邵逸夫天文學獎、格魯伯宇宙學獎和諾貝爾物理學獎。目前,我國雖然在天文領域已經產出了一定數量的科研成果,但在我國天文科學家群體中,并沒有出現邵逸夫天文學獎得主或格魯伯宇宙學獎得主,也沒有出現過在天文學領域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科學家。這表明,在天文大科學裝置與研究領域,我國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不小差距,正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五、結語與余論
通過對天文大科學裝置在引力波發現中作用的分析,可以明確得出兩個結論,首先,未來的許多科學前沿工作一刻也離不開大科學裝置的協同,科技前沿競爭日益演變為科技綜合實力的比拼。在這份科技綜合實力的清單里包括三大要素:人才、制度(經費支持)與設備,與科技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大科學裝置方面存在明顯的短板,亟須改善。其次,我國在大科學裝置建設的模式選擇中存在明顯的低效甚至無效的安排模式。這種低效模式主要體現在“牽頭人+合作單位”的建設模式,尤其是那些建設周期長、投資大的大科學裝置項目,僅憑牽頭人的組織協調能力根本無法保證完成項目任務。我們不妨看看科技部的重大儀器專項的實施過程,以2017的重大儀器專項為例,當年計劃支持50個研究方向,經費投入7億元,建設理念是:儀器原理驗證——關鍵技術研發(軟硬件)——系統集成——應用示范——產業化的國家科學儀器開發鏈條,實現產學研用的融合。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我們不知道本著這套理念運行的儀器專項到底有多少合格的儀器被制造出來了?基于這個現實,筆者認為,對于那些超級大科學裝置必須由國家牽頭,解決管理中組織協調能力不足的困境,而且,這也是我國比較習慣的舉國體制的具體運用。對于那些特殊的、中型的科學裝置建設,必須采用新的管理模式,否則無法避免停留在講故事階段的現實,畢竟科學裝置的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它要求每個環節都要盡量達到最優,然后才有可能使整個系統最優,而這些并非一蹴而就。
大科學裝置的建設會帶動相關產業與技術的發展,一旦能夠有序運轉起來,其溢出效應和輻射效應也是非常廣泛的,并能產生巨大的經濟與社會效益,如2020年全球醫療器械公司100強名單中排名第一的美敦力年銷售額達到289億美元,最后一名的銷售額也達到了1.5億美元,遺憾的是百強公司中沒有一家中國公司。由是觀之,中國的大科學裝置與儀器建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1] 沈律:《小科學,大科學,超大科學——對科技發展三大模式及其增長規律的比較分析》,《中國科技論壇》,2021年第6期,第149-160頁。
[2] 李建明 曾華鋒:《“大科學工程”的語義結構分析》,《科學學研究》,2011年第11期,第1607-1612頁。
[3、14] 西桂權 付宏 劉光宇:《中國大科學裝置發展現狀及國外經驗借鑒》,科技導報,2020年第11期,第6-15頁。
[4] 引力波參考資料引力波(物理概念)_百度百科。(baidu.com)
[5] 厲光烈 李龍:《諾貝爾物理學獎百年回顧》,《現代物理知識》,2001年第5期,第3-8頁。
[6] 吳鑫基 溫學詩:《摘取桂冠之旅:射電脈沖雙星的發現》,《科學》,1998年第3期,第46-50頁。
[7] 邵立晶:《引力波視角下的世界圖景》,《科學通報》,2020年第35期,第4013-4017頁。
[8] 邁克爾遜-莫雷實驗_百度百科。(baidu.com)
[9] 張妙靜 厲光烈:《諾貝爾物理學獎百年回顧(續)》現代物理知識,2021年第1期,第24-40頁。
[10] 黃宇傲天 張軒中:《介紹201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相關的引力波的知識》,《大學物理》,2018年第1期,第68-70+80頁。
[11] 馬波:《太陽系外行星的探測——201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成果簡析》,《科技導報》,2019年第24期,第30-35頁。
[12] 鄢盛豐 蔡一夫:《宇宙環境新認知——有關2019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理解》,《科學通報》,2019年第36期,第3793-3797頁。
[13] R.K.默頓著:《科學社會學》(下),魯旭東林聚任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490-495頁。
[15] 李俠 繆秋民 呂慧云:《重大科研儀器研發的現狀與困境》,《創新》,2018年第1期,第61-7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