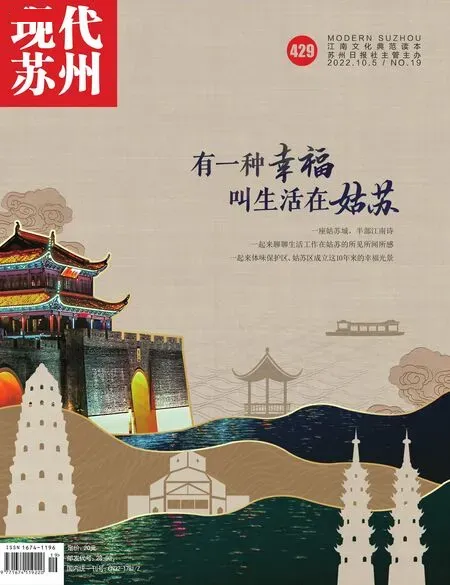錦衣織造話“蘇羅”
文 徐凰
在中國絲織品中,“綾、羅、綢、緞”是四大代表名品。其中“羅”的透氣性好,穿著涼爽,親膚性極佳,垂感流暢,成衣美觀。但“羅”的紡織難度大、成本高,其技術在晚清逐漸失傳,只有極少數地方還保有“羅”的紡織技術。
“吃穿住行”老百姓把穿排在第二位,“衣食住行”老百姓把“衣”放在了第一位。這樣的排序很有意思,日子不好過的時候,吃飽肚皮、活命當然最為重要,然后再考慮活著的起碼尊嚴“穿”,這里的“穿”達到的目標似乎只有兩個,第一個目標遮蓋必要的部位,第二個目標寒冬之季要能保暖;等到日子好過了,“吃”就退居其次,遮蓋的尊嚴發展為文明、文化,“衣”的功能就要夏日涼快,春秋透氣,冬天要保暖,除此之外,“衣”還要能表現人的身份、地位、心情等。
這時候,人們對織造就會提出較高的要求。
小眾的“羅”以漸進的方式進入大眾的生活,順應了這種較高的要求。身穿最接近肌膚特征、會呼吸的羅衣,身心愉悅,可能是人與自然最為合度的表現。
我對羅的認識是很無知的。小學讀“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老師沒告訴我,羅綺是一種有文彩的絲織品。我曾經接受的教育是穿這樣衣服的人都是“紈绔”,不是好人。我還知道“羅紈”的本義既指精細美麗的絲織品,比喻義還有“用盡心思,巧取搜括”的意味。這說明了,羅的織造花時花力。時間成本、智力成本、物質成本太高,消耗底層人的心血太多。這樣的衣服披在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群居終日言不及義的人身上,當然是極大的浪費。

我對羅的認知是從蘇羅開始的。關于蘇羅,從各種媒體上了解的第一個人物是朱立群先生,知道他47年一直都撲在花羅的織造工藝上。引起我高度關注的是朱先生在羅織物復制上的獨特造詣。2014年朱立群受邀對江西南昌靖王夫人吳氏墓出土的壓金云霞翟紋霞帔面料進行復制。這件霞帔,經專家認定,是迄今為止經密度最高的“八經循環四經鏈式絞羅”,工藝繁復,技藝高超。
我好奇地查閱了江西南昌靖王夫人吳氏的壓金云霞翟紋霞帔的形制,其色彩、文飾著實驚人:
“吳氏墓出土霞帔正面刺繡云霞翟紋,紋飾以系帶為中心分為前后兩段,前段各繡翟鳥4只,后段各繡翟鳥3只。翟為長尾雉屬的各種禽鳥的統稱,又有幼鳳一說。霞帔之上的翟鳥紋長17厘米,寬9厘米,冠小,喙短,喙下無墜,直尾無鳳鏡,做展翅飛翔之態。翟鳥四周繡如意朵云流霞紋,云朵散點狀布局,流霞環繞其中。翟鳥頭身及云紋使用絨絲線,先以平繡做地,繡出紋飾主體,后用單根圓金線釘縫,以勾勒紋飾輪廓及細節;流霞紋使用圓金線,2根一組盤繞釘縫;翟鳥紋尾部每5至6根圓金線為一組緊密釘縫成一根直尾,8根直尾長短有序,布局講究。兩條帔帶上的翟鳥紋飾做對稱狀布局,上身披掛后均為正身橫向對飛的視覺效果。
要復制這樣的色織羅料,難度很高很高,得找到獨具慧眼的天人。
是什么機緣讓中國社會科學院紡織考古研究所找到了朱立群呢?
師從服飾研究大師沈從文的王亞蓉是紡織考古專家、中國織繡領域研究第一人。她一直高度關注蘇州“中國絲綢檔案館”的建設。2014年,王亞蓉專程到蘇州,就絲綢的保護和修復工作進行專題講座,并且赴木瀆參觀了朱立群于1995年創辦的蘇州錦達絲綢有限公司,她驚奇地發現公司居然還存有幾十臺傳統的老織機,織的是小眾的已經式微的羅。朱立群、李笑蘇夫婦織羅的情懷和技藝打動了王亞蓉,她就此找到了那件壓金云霞翟紋霞帔的復制者。吳氏之霞帔由癡迷吳羅的人修復,也許是冥冥中的注定。

其實從明清以后,羅的織造工藝已經接近失傳。“八經循環四經鏈式絞羅”要復制,必須打開一個人的“天眼”。復制者一要有長期的織羅實踐;二要有豐富的想象能力;三要在不斷試錯比照過程中逼近原作,逼近宮廷織造的技藝,這必須得有精益求精的勇氣和膽略。朱立群、李笑蘇夫婦,幾次在北京查看實物,細察四經絞羅的精微之處,研究400多年前的羅織結構,他們用三年時間不斷對原料調整,多次去北京與專家溝通,與原樣比照,最后終于復原了“壓金云霞翟紋霞帔”制作工藝,并將這種失傳的織羅技法總結歸納,樹立了中國羅織技藝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王亞蓉曾這樣說過:“攻克花羅各種制造工藝是紡織界的歌德巴赫猜想一樣的難題。” 朱立群當之無愧成為蘇州吳羅織造的非遺傳承人。
蘇州市錦達絲綢有限公司總經理李笑蘇跟我說,“羅有神話般的結構”。她的話讓我覺得,織羅本身就是在創造神話,作為一個門外漢,在我而言,織羅就是在閱讀神話。查閱相關資料獲知,嬌貴的蘇羅要經過三十多道復雜的工序,以蠶線為原料,采用地經、絞經和緯經相互扭絞、交織的方法,在織物上形成分布均勻的絞孔,從而呈現若隱若現的花紋。
作為一個門外漢,因為對蘇羅的好奇,我一直想,朱立群和李笑蘇這對夫婦藏著怎樣的織造基因。
1976年至今,朱立群與羅打了47年交道,中途經歷絲織廠改制下崗,面臨失業的彷徨。1995年朱立群、李笑蘇夫婦在木瀆鎮這一文化氤氳之地創立蘇州市錦達絲綢有限公司他們守著幾十臺織機,守的也是祖宗的舊業。但他們意識到這份舊業,藏著文化的擔當。
一直關注“朱伯伯的蘇羅”這一抖音,朱伯伯作為一個織羅人,又是一個網絡達人,身著羅衣,有著文化人的儒雅。今年暑假隨教育系統、僑聯赴木瀆參觀蘇州市錦達絲綢有限公司,見其人,風神綽姿,盡顯儒雅。給我一個直覺,他做蘇羅這一非遺項目,很快樂。
前幾天通過微信聯系李笑蘇,談起蘇羅,我能感覺到她的自在和快樂。她跟我說起羅,就如談起自己的孩子。她說,羅的色彩最具中國文化的審美特征。因為羅的織造不同于其他織物,地經、絞經和緯經相互扭絞,在織物上形成分布均勻的絞孔,它也有太湖石瘦、漏、透的審美特征,在視覺上形成了虛虛實實的色彩。軟煙羅的銀紅色是天上霞光映射下來的顏色,松綠色是深邃雅致的松樹樹葉的顏色,秋香色帶著秋天的香氣,天青色是雨過天青下雨后天空的顏色。
夫唱婦隨,他們夫婦倆真是找到了職業和事業的黃金分割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笑蘇說,他們的兒媳放棄了在上海做公務員,正在跟王亞蓉讀博士。
一個家庭都癡迷于羅的世界,真可謂,鉆進了天羅地網。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有女同行,顏如舜英。”朱立群、李笑蘇夫婦,在古老的《詩經》里尋找靈感,是他們讓《詩經》里走出的木槿花開在蘇羅的面料上。他們織就的絲羅“木槿繁花”面料疏密有致、柔軟輕透,在“2015中國四季絲綢面料大賽”中,評委們一致認為這是演繹“窈窕淑女著羅裙”的最好面料,獲得了大賽唯一的金獎。
錦衣織造話蘇羅,今天蘇州市錦達絲綢有限公司已經有了“蘇州紗羅技藝館”,蘇羅作為古老的織造文化被記錄下來。在技藝館里,我們能看到古老的羅藏著舊學的功力,式微的技藝,因織羅人的癡愛在盛世綻放。

衣冠有等、貴賤有別的時代一去不回,蘇羅隨著時代的發展,完全可以走進普通家庭,我們每個人都可以進行“私人定制”,穿出中國范來。
向朱立群、李笑蘇為代表的癡迷蘇羅織造的人致敬,他們把論文寫在蘇羅上,用絲綢詮釋蘇州文化,用蘇羅演繹中國精神。他們,用經線和緯線編織著新時代的絲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