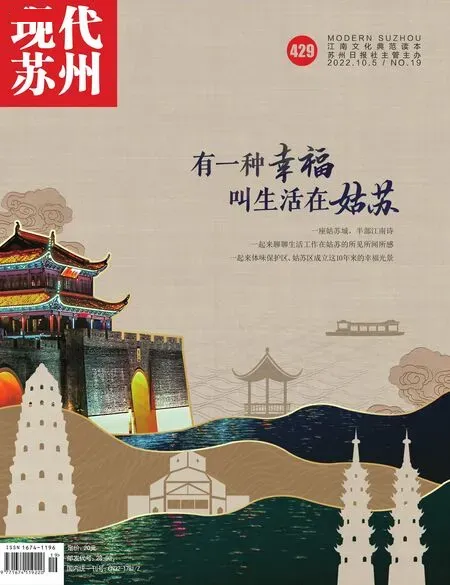殷銘:為姑蘇古城的歷史傳續一棒
記者 丁云
殷銘,蘇州名城保護集團古城投資建設有限公司總經理,江蘇省勞動模范。自2011年蘇州啟動古建老宅保護修繕工程以來,他參與修繕了蘇州古城內10多處古建老宅。每一處修繕,背后的故事都曲折而不可復制;每一處修繕,又讓這些古老建筑延年益壽、永世傳承。仿佛是一段歷史的交接與延續,前人在這些古建筑中留下訊息與痕跡,而殷銘與他的團隊在修繕時找到、解碼,然后又將今天的密語訊息留給后來人。

尤先甲故居的清理現場,殷銘指著一座清代乾隆時期的磚雕門樓,講述其歷史文化價值
搶救性保護,讓古建遺產延年益壽
蘇州古城古建遺產面廣量大,它們中的大部分歷史一般都在百年至二百余年間,年久失修,亟待搶救性保護。一處古建老宅的保護修繕,好比做復雜的大手術,是一項系統化的工作,涉及7個專業、10多項傳統工藝。步驟并非一定按照遞進式,有時同步或者穿插進行:最先是立項研究,隨后歷史文化的再挖掘與居民搬遷同步進行。居民搬完,項目公司委托有資質的單位現場勘測,一些古建要做考古斷代,研究形制,出設計方案。之后進入報批流程,涉及文物、規劃、住建、環保等多部門,整個流程走完要1年時間。
拿到規劃、施工許可證后,通過招投標選出隊伍進場施工,小一點的宅子估計得大半年,大部分上體量的宅子要1年左右的時間才能修復完。“比如像木門窗的制作,還是傳統的榫卯工藝,現場參與修復的工匠就是傳統的老手藝人,他們是這項工作的重要力量。”殷銘說。
根據10來年的實踐總結,不把搬遷時間計入,一處古建老宅從開始勘測到最后完整修復,要1.5年至2年時間。而實際過程中問題叢生,瓦落下來清理墻體、檢查構建時才能發現更真實的情況,壞多少補多少,“關鍵是搶救性修復是手藝活,花的都是慢功夫,效率快不起來。”殷銘介紹,作為2011年蘇州市首批啟動修繕的12個古建老宅試點之一,清代探花潘祖蔭的故居以三路五進的完整格局、融合南北風格為一體、建造技藝精湛細膩而著稱,先后用時10年、分5期分批實施才得以完整修繕。項目成為近10年間蘇州完整保護修復的規模最大的一座古建筑。完整的修繕和活態化的保護,能夠確保這些古建遺產可以健康地永續傳承。“一個14.2平方公里的古城里,到處是古樹、古井、古橋、古建、古街……其中很多世界文化遺產的歷史年限都在六七百年以上,這就是蘇州的驕傲。”

今天,活態化保護古建遺產成為普遍共識。修繕的目標之一就是古為今用,功能多樣,進一步發揮出它們應有的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在潘祖蔭故居基礎上活化利用的花間堂探花府,既是酒店,可住宿用餐,同時附帶主題書店,兼帶舉辦會議、文化交流的功能,成為蘇州古建筑保護利用的典型樣板。潘世恩是乾隆時期的狀元,歷事4朝,為官40余年,位極人臣,是蘇州狀元的頂尖代表。其鈕家巷故居經完整修復后,其中一路辟為蘇州狀元博物館,展示和承載著蘇州作為狀元之鄉的強大文化IP屬性。“外地很多團隊及游客慕名到訪蘇州必到蘇州狀元博物館,實地體驗和感受蘇州崇文重教之風和悠久的狀元文化傳統。”殷銘挺自豪,成功的博物館功能設置無論對于蘇州文化或者故居深厚的歷史都做了極好的外化詮釋。
蹚出一種古建修繕的蘇州模式
2011年底,蘇州市啟動古建老宅保護修繕工程,涉及古城內多處宅院。剛剛成立的市屬國企蘇州文化旅游發展集團有限公司(2022年06月后成立蘇州名城保護集團有限公司)組建專門團隊,負責具體實施。作為專業技術人才,殷銘應聘至文旅集團古城公司,從一開始就參與了這項漫長而偉大的工作。
然而10年前,這項工作從起步就肩負沉重的任務和巨大的壓力。因為歷史原因,古建老宅的土地權屬、房屋性質、管理關系錯綜復雜,種種機制和政策壁壘都是障礙。“我們得去解決老百姓的居住問題,得去保護修繕老宅,還要考慮日后的活態化利用。”怎么搬、怎么保、怎么修、怎么用是四道難題。
“從本質上說,古城保護、城市更新就是城市治理。”殷銘說。老宅很不適宜老百姓再居住,條件非常差,長此以往又對古建的損壞不斷累積。他們最近著手修繕的第二批古建老宅尤先甲故居有約280年歷史,長期的使用和管理不當,已令該處古建到了需搶救性大修的地步。古城保護問題因而成為了全社會的系統性問題:文化遺產要加強保護;老百姓的生活條件需要改善;承擔項目的企業投入巨額搬遷、修繕成本,必須顧及回報。此外,還有修得好不好、修得對不對的爭議,“搬、保、修、用”等系列問題,要走通、走順,不容易。

古建老宅修繕多了,殷銘和團隊能漸漸摸著、感應到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與血脈
殷銘說,做對的事和把事做對是兩個邏輯,在古建老宅的修繕問題上,他們一直堅持做正確的事。潘世恩宅、潘祖蔭宅、宣州會館、過云樓等項目,當年就是整個工程系統化全盤考慮,考慮修,更考慮用,因為“修繕時采用的技術、報批的流程都影響著后期使用。”
項目需經歷多部門審批,手續一個不落,最長流程經歷10余個部門60多個審批環節,以保證三權——地權、房權、管理權歸集到一個主體,后期方能順利地辦理消防手續,辦理特種行業許可證,辦理衛生防疫手續……為活化利用提供合法成品,真正實現建筑遺產的盡其用、善其用。
這是 出來的一條路,“我們認為這是一種蘇州模式,但前提基礎還是市委、市政府對蘇州古城保護工作的高度重視,敢于拓新。”2012年頒布的《蘇州市古建老宅保護修繕工程實施意見》為開路解放了思想,繼而也在全國產生了示范效應。
解碼城市的文化基因與精神品格
幾乎每一處古建,在修復時都能發現前人留下的痕跡。“發現時,我最開心、最激動。”殷銘說,像是親手揭開被塵封的歷史。
潘世恩故居修繕前,住戶留到最后不走,殷銘照其指點,爬到頂上找到了清代道光皇帝為賀潘世恩80歲大壽御筆的盤龍鑲金“福”字匾。進場拆除搭建時,又有住戶指著一個被白瓷磚包裹的洗衣臺說是琴磚,將信將疑、小心翼翼地清理,果然。德鄰堂吳宅的住戶們全部搬空后,已故古建筑專家陳從周先生書中記錄的明代遺構終于全部露出了真容:須彌座磚雕、很粗的柱子,木質柱礎,而非石礎,“蘇州大部分古建筑的柱礎是石頭的。”殷銘解釋,從遺產保護的斷代來講,木質的年代比石質的要早,“也證明宅子的規格、檔次比較高。”
每一處古建老宅都藏著類似的“密碼”,讓殷銘更加堅信自己工作的價值與意義:這么破的房子為什么要保護?因為每一處都負載著大量歷史文化信息,隱含著當時的社會狀況和個體生活等價值,累積著地方、城市千百年來的文化積淀。
古建老宅修繕多了,殷銘他們能漸漸摸著、感應到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與血脈是鮮活的,一直在流淌和傳承。
去年,殷銘帶領團隊完成修復著名古籍版本學家顧廷龍的故居,其子,2020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獎者顧誦芬院士小時候正是在這所院子里長大,顧氏祖祖輩輩注重詩書禮儀。“你能真切感受到,‘崇文重教’在這里真不是空談,讀書人以耕讀為本,不以財富傳家。”除去大量國保、省保、市保,古城內的大街小巷轉角就是名人故居,有很多還是歷史上有一定影響的人物。這200多處宅子,沉淀了數百個家族的歷史和文化,每一個家族綿延數百年,深刻影響著蘇州的城市品格與風尚。
在蘇州的文化屬性里,就不太追求物質的張揚和顯露,內秀文雅。這些古建老宅,從門庭外圍看,完全就是普通老百姓的房子,看不出顯赫。“像潘祖蔭宅里的木雕,還是比較精細,比較高檔次的,但也跟北方華麗的雕刻不在一個頻道,分屬不同的文化風范。”潘祖蔭23歲探花及第,官至工部尚書,通經史,精楷法,金石、藏書都甚是豐富,這樣的文人雅士們愿意在深宅大院里自得其樂,而基本上每個家族都會編詩集文集。姓氏不同,背景不同,卻殊途同歸,追求文化精神的回歸。
殷銘說,顧廷龍故居磚雕門樓鐫刻著狀元潘世恩題寫的匾額;尤先甲故居內有乾隆時期著名書法家題寫的門樓字牌……“久而久之我們在古建老宅里有體會,每一處的設置都不是隨便設的,所有的表達都有說法,是留給后世的無價之寶。”這是誕生了吳門畫派、吳門醫派的城市文化底子,千百年來又養成了性情溫和、注重文化的生活習慣。
快馬加鞭,古城公司目前正推進多個項目的保護和修復,未來兩三年里,會有更多有標志性的名人故居、古建老宅完成修繕后,相繼向外界展示。“自與西方開啟交流時起,蘇州就被西方人稱作東方威尼斯,并且一直以這種優雅的面貌展現在世人眼中。古城代表著蘇州在世界的一種影響力,魅力獨特,價值深遠。”殷銘已在蘇州待了20年,這里已然成為他的第二故鄉——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他負責的古建老宅一座座修復完畢,再現了它們應有的神韻和恢復建筑該有的功能,這座古城在他心中早已生根,再也離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