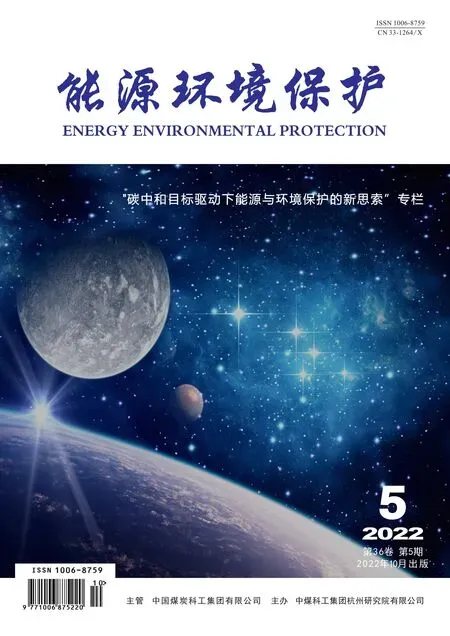基于SBM模型的區域碳排放效率評估研究
郭 茹,田博文,呂 爽
(1.同濟大學 環境與科學工程學院,上海 200092;2.同濟大學 碳中和研究院,上海 200092)
0 研究背景
氣候變化是當今全球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推進低碳發展是我國實現2030年碳達峰和2060年碳中和目標的關鍵。當前我國已經進入了經濟發展新階段,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不斷優化升級經濟結構,是實現低碳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中國幅員遼闊,區域差異大,因此低碳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需要兼顧國家整體戰略需求和地區稟賦特色。“十四五”期間是我國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美麗中國的重要時期,也是落實國家自主貢獻目標的關鍵時期。為實現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必須科學測度不同區域的碳排放效率,推動區域之間協同實現雙碳目標。
已有研究中,對碳排放效率的評價往往僅考慮能源消耗因素或經濟因素,效率測算的科學性仍有待改進和完善。雖然國內外已有學者采用數據包絡分析法(Data evelopment analysis,DEA)從全要素視角對碳效率評價進行了改進,但選擇不同的效率測算模型,往往導致了不同的研究結論,尚未形成統一的共識。本研究對區域碳排放效率全要素測算模型進行了改進,選擇考慮非期望產出和松弛變量的Slacks-based measure(SBM)模型,構建了區域碳排放效率評估方法,并應用于我國省域層面的碳排放效率分析。基于前述分析結果,結合當前我國不同區域碳排放現狀和碳排放效率的差異性,提出了相關政策建議。
1 研究方法
1.1 數據包絡分析法
數據包絡分析法(Data evelopment analysis,DEA)是一種利用線性規劃方法,用于評價多投入、多產出系統中決策單元(Decision making units,DMU)相對效率,已被廣泛用于健康[1]、航空[2]、銀行[3-4]、交通[5-6]、能源[7]、教育[8]、環境[9-10]等領域。相較于參數法,DEA不需要假定具體的函數形式,可以用來測算包含“多投入、多產出”DMU的相對效率。常見的DEA模型可以分為徑向和非徑向模型,CCR、BBC模型是典型的徑向DEA模型,而基于松弛變量的SBM模型是典型的非徑向模型[11]。采用徑向模型進行效率測算時,無效的DMU通過同比例的改變投入或者產出指標到達前沿面的距離,實現DMU有效。對于非徑向DEA模型,DMU的投入或者產出指標則不需要同比例的增加或者減少。
1.2 單要素和全要素碳排放效率評估
本研究分別從單要素指標和全要素指標兩個視角對中國的碳排放效率進行評估。其中,碳排放強度是常用的單要素評價指標,定義為一個地區單位GDP的碳排放量,可以較好地反映CO2排放總量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碳排放強度作為反映區域能源利用效率的指標,較低的碳排放強度值表示較高的區域能源利用效率和較高的碳排放效率。
在單要素評估基礎上,進一步從全要素視角對地區間的碳排放效率進行分析,提出改進的區域碳排放效率全要素測度模型。根據已有DEA評估方法的比較分析,選取非期望產出的SBM模型對我國30個省級行政區域的碳排放效率進行測算。以勞動力、資本存量、能源消耗量作為投入指標,以GDP作為產出指標,CO2排放量作為非期望產出指標,將中國30個省級行政區作為DMU,構建了碳排放效率評估方法。具體方法如下:
(1)

2 結 果
2.1 單要素碳排放效率特征
研究計算了2000~2017年中國各省級行政區的CO2排放強度。其中,中國各省級行政區碳排放數據來自CEADs官網的公開數據,GDP數據來自2001~2018年《中國統計年鑒》中的地區生產總值(折算為2000年不變價)。結果表明,就單要素碳排放效率而言,區域碳排放強度呈現“北高南低”“西多東少”的特征。
具體來說,2000~2017年間,除了山西省、海南省和寧夏回族自治區外,其他省級行政區的碳排放強度都在下降。山西省、內蒙古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這4個省級行政區的碳排放強度始終處于高位。這些中西部地區化石燃料豐富,對重工業依賴程度高,能源生產和轉化產業是當地經濟的支撐產業,例如內蒙古自治區煤礦資源的開采、煉焦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油田的加工,存在產業結構不平衡、制造業過剩、能源利用效率較低、技術落后的現象,經濟增長導致了高強度的能源消耗,導致碳排放強度居于高位。
相較之下,東部地區排放強度較低,2017年北京的碳排放強度為0.25 t/萬元、上海為0.52 t/萬元、廣東為0.59 t/萬元,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94 t/萬元,這些地區生產工藝和技術水平先進,碳排放強度的下降主要源于第二產業比重的不斷下降,經濟發展主要來自于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對能源的依賴較小。隨著經濟的發展,部分省級行政區在這期間的碳排放強度變化巨大,例如遼寧省、吉林省和黑龍江東北三省的碳排放強度從2000年的6.22 t/萬元、5.27 t/萬元和5.29 t/萬元下降到2017年的2.20 t/萬元、1.42 t/萬元和2.23 t/萬元;河北省的碳排放強度也由5.07 t/萬元下降到1.59 t/萬元;貴州省的碳排放強度也由5.07 t/萬元下降到1.59 t/萬元。江蘇省、廣東省的碳排放量雖然位于全國前列,但排放強度卻很低。
2.2 全要素碳排放效率特征
基于構建的SBM模型對我國30個省級行政區的全要素碳排放效率值進行測算時,由于寧夏回族自治區缺乏2000~2002年能耗數據、海南省缺乏2002年能耗數據,考慮到數據的一致性,研究時間尺度調整為2003~2017年。2003~2017年我國30個地區的碳排放效率測算結果見表1。從時間變化來看,相較2003年,2017年只有北京市、湖北省、重慶市、四川省和貴州省5個地區的效率上升,占比16.67%。從各省級行政區效率測算結果來看,2003~2017年各省級行政區碳排放效率值高于整體平均值的地區有13個,其中只有上海市的效率平均值始終為1;效率值低于整體平均值的地區有17個,其中,效率值低于0.3的地區有4個,分別是山西省(0.29)、貴州省(0.25)、青海省(0.25)、寧夏回族自治區(0.18)。

表1 2003~2017年我國30個省級行政區的碳排放效率Table 1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ies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7
2003~2017年區域全要素碳排放效率平均值結果見圖1。分析發現,從效率平均值來看,省域間的碳排放效率差距明顯,只有上海市在2003~2017年間達到了碳排放有效。在研究期間,碳排放效率最高的地區是上海市、福建省、廣東省、北京市、江蘇省、天津市等東部地區。上海市、江蘇省、北京市、廣東省和天津市作為我國最發達的地區,以通信和信息設備制造業為代表的高科技產業可以實現較高的經濟產出,因此碳排放效率處于高水平。福建省的CO2排放效率高主要歸因于工業化比例低以及現代服務業主導的產業結構。在研究期間,CO2排放效率最低的地區是寧夏回族自治區、青海省、貴州省、山西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甘肅省。就排放效率最低的地區而言,這些省級行政區大多數位于中國的西部欠發達地區,人口密度低、人才稀缺且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總的來看,超過一半的省級行政區的碳排放效率值低于中國平均值,多數區域還存在很大的效率提升空間和減排潛力。

圖1 2003~2017年區域全要素碳排放效率平均值Fig.1 Average value of regional total factor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from 2003 to 2017
3 政策建議
根據前述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區域碳排放效率改進建議:
(1)在科學測算和綜合統籌的基礎上,通過逐步建立統一碳市場推動區域碳排放協同治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體作用,碳排放效率較高的地區適當增加獲得更多碳排放配額的機會,通過地區間協同推進雙碳目標的落地,實現整體碳效率的提升。
(2)東部地區經濟發達、人才集中,擁有技術創新的良好基礎,應以產業結構更新和資源配置優化為重點,持續進行產業結構轉型,大力推動現代服務業的優質高效發展;在提高碳排放效率方面發揮帶頭示范作用。例如,充分發揮長三角地區對周邊地區碳排放效率的正向輻射作用。
(3)中部地區應借助其“聯通東西”的區位優勢,加強與東部地區的合作交流,積極推動先進產業替代落后產能,打好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轉型的組合拳;合理引導和配置中部地區制造業資本投資,鼓勵外資企業對高科技產業及節能環保產業進行投資,并努力將中部地區的中心城市建立成新的碳排放效率正向輻射地區,帶動西部地區的發展。
(4)東北部地區作為老工業基地,應通過繼續貫徹落實國家“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政策,完善過剩產業的退出機制,依規有序淘汰落后產能;提高核心技術研發、制造、系統集成和產業化能力,提升東北地區的低碳競爭力。
(5)西部地區應嚴格限制污染密集型企業發展,逐步淘汰落后產業,促進產業合理化發展,大力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積極吸引先進技術從沿海地區向西部地區轉移,提升西部地區的綠色低碳科技水平;同時加大對外資企業投資方向的審查和把控,與外資企業展開高質量、綠色深入的合作。
4 結 論
準確地測算中國不同區域的碳排放效率,是推動雙碳目標導向下區域協同治理的基礎。研究構建了基于SBM的全要素碳排放效率測算模型,以資本存量、勞動力和能源消耗量為投入指標,以地區生產總值為期望產出,以CO2碳排放量為非期望產出,建立了區域碳排放效率評估方法,并分析了我國30個省級行政區域的碳排放效率特征。結果表明,我國多數省級行政區的碳排放效率值低于國家平均值,各個區域總體上還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間和減排潛力。未來應針對不同區域的資源稟賦和低碳發展優勢,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體作用,通過地區間協同推進雙碳目標的落地,實現整體碳效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