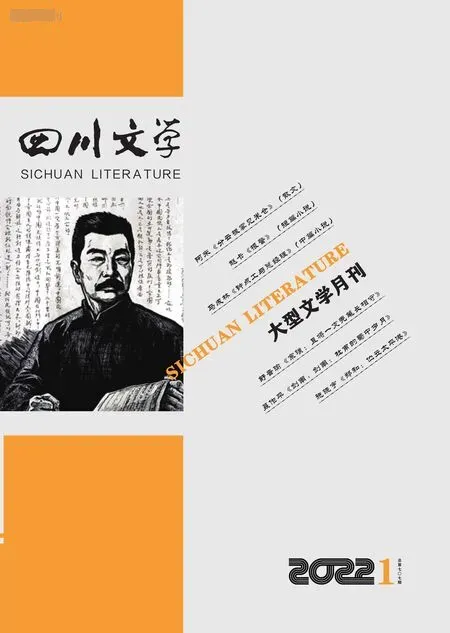宗璞:且將一支禿筆長相守
□文/舒晉瑜
“我最想做的事情是周游世界。可是如今我只能臥游!”88歲的宗璞說話間朗聲大笑,看不出絲毫倦意。她想到唐河父親的紀念館去看看。2011年就建造的馮友蘭紀念館,參觀的人很多,可她一直沒有去過;世界上許多地方她都想去,桂林、希臘……她笑著說,自己只能夢游世界。
實際上,她因去年夏天的時候有過一次中風,今年春天也因病剛剛出院不久。為了防止身體再出問題,中風恢復些時,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未竟的小說結尾寫好。
近年來,她的各種作品集源源不斷,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她的《風廬散記》,海豚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童話。她在《關于琴譜的懸賞》《尋月記》《花的話》《總鰭魚的故事》等作品中,細膩生動地為讀者展現了孩子純潔天真的內心世界。她說,自己很喜歡寫童話,寫的時候覺得自由,不為現實生活拘泥,全憑想象。
“我這一生,一個求真,一個求美。我一直在想,在民國時候常常提的真善美,現在好像不大提了。”宗璞說。她希望歷史能夠真實,不要瞎編亂造;希望藝術創作能夠真的像個藝術品,不是很粗糙的一堆。
曾經有人問她,為什么寫小說?她說,不寫對不起在身邊凝固的歷史。為什么寫散文?不寫對不起胸中的感受。為什么要寫童話?不寫對不起腦子里的夢。為什么要寫詩?不寫對不起耳邊歌唱的音符。
現在聊可告慰的是,她寫了自己想要寫的長篇小說。“看我和它誰先到終點吧。生命剩下得已經不多了。”語氣既風趣灑脫,又有些許悲涼。
少年時,宗璞讀到東坡一首《行香子》,最后一句是“幾時歸去,做個閑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席云”,她覺得這正是自己理想的生活。可是現實生活的紛擾,讓她永遠也過不上那樣的日子。現在的宗璞,自評為“一只螞蟻”,認為她的寫作像螞蟻在爬,寫一天病兩天。可是如果不寫完很不甘心。于是每天臥床之余,她仍會堅持一個小時坐在電腦前,繼續寫作。
能談談童年閱讀對您的影響嗎?
我小時候的閱讀分成三個部分,一是背詩詞。我5歲開始上小學,父親會給我選一些詩,每天早晨背上書包在母親床前背了再去上學;那會兒背白居易的詩多一些,像《長恨歌》《百煉鏡》都背過,因為白居易的詩容易上口。父親對我有要求,規定每天背多少,但是容易完成,我也很有興趣,一點兒都不吃力。父親從來不講,他主張書讀千遍,其義自見。
二是兒童讀物。那時候讀了《格林童話》《愛麗斯漫游仙境》,還有一套少年兒童讀物的文庫,其中改寫的《西游記》非常好讀。從前我看的《西游記》很煩瑣,一上來就是“有詩為證”。
三是成人讀物。那個時候看書也是囫圇吞棗,但是我在八九歲時讀《紅樓夢》,讀了很感動,看到林黛玉死的那章,哭得不得了。還有一些別的書,在小孩子中很流行,比如清代俞曲園改編的《七俠五義》,再就是《隋唐》《小五義》,也讀《水滸》《蕩寇志》。
這些詩詞對您有怎樣的影響?
大致說起來,詩詞對我來說非常重要,詩詞是我的好朋友,是我的終身伴侶。我父親晚年時也常背杜甫的詩,現在我也常讀。現在很多學校倡導小孩子背詩詞,應該鼓勵,中國是詩的國家,詩詞是中華民族的瑰寶。
您如何評價父親?
他是自由主義的教育家,幾十年如一日,始終在北大、清華、聯大維護和貫徹那些教育理念:學術至上、為學術而學術、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他認為大學要培養的是“人”而不是“器”。器是供人使用的,知識和技能都可以供人使用,技術學校就能做到。大學則是培養完整靈魂的人,有清楚的腦子和熱烈的心,有自己辨別事物的能力,承擔對社會的責任,對以往及現在所有有價值的東西都可以欣賞。
《馮友蘭論教育》(人民出版社)引起很大反響,您如何看待父親的教育思想?
我想可以概括成三點:一是教育出什么樣的人,應該是合格的人,而不是器,是有獨立頭腦、通曉古今中外事情、能自己做出判斷的人,而不是供人使用的工具;第二點是大學的職能,我父親非常善于把復雜的事情用簡單的話說出來,他用四個字概括大學的職能,這四個字是“繼往開來”,就是說,大學的職能不僅是傳授已有的知識,還要創造新知識,我覺得清華的傳統,就是富有創造性,清華校箴“人文日新”,就有“開來”的意思;第三點,怎樣辦大學呢?大學不是教育部的一個司,大學是自行繼續的專家集團,就是自己管理自己,懂得這個事情的人有權發言,一般的人不要發言。
馮友蘭先生晚年曾打算寫一本《余生札記》,把哲學之外的各樣趣味雜感寫進去,但是這本書最終沒有寫成。
我猜想這本書里會有“論文學”“論詩詞”“論音樂”等等,大概還會有一篇講《紅樓夢》的文字,父親曾高度贊揚《紅樓夢》的語言,便是三等仆婦的話也都很有節奏,耐人尋味,而且符合講話人的身份。一次在飯桌上,父親邊吃飯邊談論《兒女英雄傳》,說這本書思想不行,但描寫有特點,他講到十三妹的出場,和以往舊小說的出場完全不同,有現代西方小說的手法,不是先自報家門,而是在描寫中逐漸交代人物;講到鄧九公洗胡子,認為寫得很細,很傳神。那時我太沒有先見之明,應當記下來。父親對詩、對詞曲、對音樂,都有很好的意見,父親曾說,如果一個人對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都懂,他會喜歡中國哲學;如果一個人對中國古典音樂和西方古典音樂都懂,他會喜歡西方古典音樂。
1948年您在《大公報》發表處女作《A.K.C.》。您是怎么走上文學創作道路的?
我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其實是一篇寫滇池月光的散文,十五歲寫的,現在找不到,就把十九歲發表的短篇《A.K.C.》算第一次發表作品。之前十七歲還寫過一篇小說。
1957年《紅豆》發表在《人民文學》,引起很大震動。您當時的文學創作,起點很高,也比較順利吧?
當時我所在的《文藝報》在五樓,《人民文學》在四樓。有一天我拿著稿子去找涂光群,不久就發表了。后來《紅豆》被打上“毒草”標簽,無奈擱筆,這一擱就是14年。“文革”結束后才陸續寫了《弦上的夢》《三生石》《我是誰?》……在中國寫小說不容易。20世紀50年代我下放回來后寫了篇小文章《第七瓶開水》,下筆寫了第一句話:天下的母親都愛自己的兒子。后來一想,不行,這不是人性論嗎,要批判的,趕緊改掉了。但這句話我卻永遠記住了。后來我發明了“心硬化”這個詞,就是說在革命中,人人要硬下心腸來說假話。但不管怎么說,我還是要堅持,把我的小說寫完。父親寫完了他的《新編》,我也能寫完我的東西。
在童話中,您的很多作品如《關于琴譜的懸賞》《尋月記》《花的話》《總鰭魚的故事》等,細膩生動地為讀者展現了孩子純潔天真的內心世界。您的童話內涵很豐富,也很深刻,不僅是給孩子看的。在童話的寫作過程中,您是怎樣的心態?
我很喜歡寫童話,他們給我出了專集,寫的時候覺得自由,不為現實生活拘泥,全憑想象。
您的作品一向追求“誠”和“雅”的品質。
“誠乃詩之本,雅為詩之品”是金代詩人元好問的詩句,后來郭紹虞先生將之總結為“誠”和“雅”,沒有真性情,就寫不出好文章。但要做到“誠”,就要能夠正視生活的很多問題。“雅”便是文章的藝術性,這只能靠改,不厭其煩地改。
寫作《野葫蘆引》的起因是什么?為什么會從“文革”的敘述轉向抗戰題材?
20世紀50年代的時候,我就想寫一部反映中國讀書人在抗日戰爭時期生活的長篇小說。《紅豆》被打上“毒草”的標簽,此后十多年我一直沒動筆。直到“文革”結束后才開始寫作。抗戰這段歷史對我童年和少年時代的影響太深了。另外我想寫父兄輩的歷史。在《宗璞文集》前頭我寫了幾句話,我說,“寫小說,不然對不起沸騰過隨即凝聚在身邊的歷史。”
《野葫蘆引》是在寫作之初就擬定四卷嗎?這四卷的創作過程中,經歷了什么?
從寫《東藏記》開始,我視網膜脫落,頭暈頻頻發作,半邊身子麻痹,在助手的幫助下口述成文,7年才寫完。
《南渡記》寫完,我父親去世了。《東藏記》寫完,我先生去世了。對人生,我覺得自己好像懂得越來越多了。一個小說寫這么長時間,我覺得對小說是一件好事,因為作者經歷的更多了。在最初兩年寫的時候,情調是較明朗的。后來經歷越來越多,對人生的態度也有一些變化。現在我設計的《北歸記》結尾,和我最初想的略有不同,不過總的來說,基本設計改動不大。在經歷了“文革”以后,對世界的總的看法已經定了。不過,經歷了更多死別,又經歷了一些大事件,對人生的看法更沉重了一些,對小說結局的設計也更現實,更富于悲劇色彩。
這么多年過去,小說的人物也都有了變化。回顧這些作品的創作,您是一種什么樣的心情?
我寫得很苦,實在很不瀟灑。但即使寫得淚流滿面,內心總有一種創造的快樂。小說里的人物都慢慢長大,孟靈己出場的時候10歲,回去的時候19歲了,而且經歷了西征的戰爭、李家大女兒的死、凌雪妍的死,尤其是瑋瑋的死,這都影響她成長的過程。有人說我每本書要死一個人,我想生活就是這樣,一面向前走一面就要消失,舊的消失然后又有新的。
王蒙曾經說,《野葫蘆引》“噴發著一種英武,一種凜然正氣,一種與病弱之軀成為對比的強大與開闊”。
“野葫蘆”是一段源自真實生活的動人故事,是小說,也是歷史。“七七事變”后,一大批教授、學者在戰火硝煙中跋山涉水,把西南邊陲造就成保存中華民族文化命脈的“圣地”,在物質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他們精神富有,理想不滅。
這四卷作品的寫作,歷經這么多年,如何保持其文脈的連續性?
我記性好。寫完了不能從頭再整理一遍,要聽人念,很費時間,都是片段的。算一算三十幾年了。寫寫停停,實際寫作的時間沒那么長,我做得太慢了。
編輯楊柳對我的幫助很大,需要什么材料都幫助去找。還有一個以前的老同學段承鵬,是我西南聯大附中的同學,也幫我看這稿子。
第二卷《東藏記》獲得第六屆茅盾文學獎。您還記得當時的情況吧?您對自己的作品是否能獲獎抱有期待嗎?
我對茅獎也沒有期待,好像不大知道,也沒有過問。
獲獎當然是讓人高興的事,但那是對過去工作的一種評價,也是一種鼓勵。過去的已經過去了,前面還有許多沒有做的事,那才是更重要的。《南渡記》于1988年出版以后,《東藏記》1995年在《收獲》發表第一、二章,2001年出版全書。有人告訴我,在網上看到一個小小的討論,說他們等得太久了。這樣的遲延使我不安,簡直對不起那一段歷史,也對不起讀者。我一再鼓勵自己要堅持寫下去,但總是覺得好像說大話,因為不知道還能寫多久。
您如何看待茅盾文學獎?
獲得茅獎是一種鼓勵,但是也不一定就比不獲獎的作家寫得好。沒獲獎的作品中也有好的。因為身體不好,我沒去參加頒獎典禮。
《野葫蘆引》中,知識分子在面對抗戰與投身抗戰的過程中,在羈絆中成長、在實踐中不斷地摸索前,最終完成了自身的蛻變。《野葫蘆引》中出現了幾代知識分子也各有不同。您愿意怎么評價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和影響?
我寫《南渡記》《東藏記》,還是把知識分子看作中華民族的脊梁,必須有這樣的知識分子,這個民族才有希望。那些讀書人不可能都是骨子里很不好的人,不然怎么來支撐和創造這個民族的文化!
我一直在琢磨“清高”和“自私”的問題,這兩者的界限怎么劃分?比如莊子,看上去莊子好像很怎么,好像是無情的,可是他其實是最有情、最真情的。比如說魯迅,諷刺、揭露、罵人很厲害,可是這些底下是一種真情。如果寫東西到了完全無情的地步了,那就是“刻薄”。
您的作品中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品格(自強不息、剛毅進取的人生觀;強烈社會使命感的價值觀;“發乎情,止乎禮”的道德觀;“修身以立道”的修養觀;恬淡灑脫的個性等等)在今天,仍然是我們知識分子精神建構中可以汲取的精神資源寶庫。您如何看待今天的知識分子?
有評論者認為我書中的知識分子形象,體現了“漂泊與堅守”,很多知識分子的人生似乎都與這個主題相關吧。那時人的精神境界和現在距離很大,以致有人認為我寫的人不夠真實。他們很難想象,會有人像書中人物那樣,毀家紓難,先公后私。其實,對于那一代人的品格,我寫得還不夠。我寫這部書,是要尋找一種擔當的精神,任何事情要有人做,要有人擔當,也就是責任感。在擔當起責任的時候,是不能只考慮個人得失的,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您的作品在抗戰題材的作品中,有何獨特之處?
《西征記》寫的人物不只是學生、軍人,還寫到了普通民眾。我要表現的是我們整個民族同仇敵愾的那種精神。除了主要人物以外,我穿插了一些小故事,如本和阿露,兩個年輕生命互相愛慕是很美的,苦留和青環之間那似乎沒有感情的感情我也很喜歡。小說是虛的,但它從現實中來,如果不從生活中來,它就是無根之木,很快便會枯萎,可能根本就長不起來。小說又不是現實生活,這是老生常談了。因為小說是作者自己的藝術世界,作者不會滿足于照搬現實,必須攪碎了重來,對號入座是無意義的。考據可能很有趣味,是研究小說的一種方法。但讀小說要讀小說本身,若是照著考據學去讀小說,就沒有小說了。不過我對適當的考據還是有興趣的。
《西征記》直接描寫了抗日正面戰場的悲壯,格局很大,人物眾多。女作家寫戰爭題材似乎不能算是有優勢。您以為呢?為什么要寫戰爭題材?
我是必須要寫,不得不寫。因為第一,西南聯大先后畢業學生共2000多人,從軍者800余人,當時別的大學如重慶中央大學,從軍的也很多,從軍抗日是他們的愛國行動,如果不寫上這一筆,就是不完整的。
第二,滇西戰役是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一次重要戰役,十分輝煌,長時間被埋沒、被歪曲。抗日老兵被審查,流離失所,翻譯官被懷疑是特務,他們徽章上的號碼被說成是特務編號。把這段歷史從塵封中磨洗出來,是我的責任。
第三,從全書人物的發展看,走上戰場,也是必然的。瑋瑋在北平淪陷后,就憋足了勁要去打日本。第四,我的哥哥馮鐘遼于1943年志愿參加中國遠征軍,任翻譯官,那年他19歲。隨著戰事的推移,他用雙腳從保山走到畹町,這段歷史對我有一種親切感。現在用各種方式寫這段歷史的人已經很多了,但《西征記》是獨特的,我是盡心而已。我看見一篇評論說,這樣一部作品,沒有出現在充滿豪氣的男兒筆下,倒是宗璞寫出來了,令人驚嘆。我很感動,還要繼續努力。
的確,您的小說一般都充滿詩意,但是《西征記》中寫到了遠征軍、美軍飛行員、游擊隊、老百姓、土司,國民黨軍中的腐敗等,有一股俠氣,不像出自女作家之手。
我現在是老弱病殘都占全了,可若是只看書,我相信你想不到是我這樣一個老人寫的。我為此自豪。也有讀者告訴我,《西征記》有一種俠氣。我十分同意這個看法。
寫這卷書,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最大的困難是寫戰爭。我經歷過戰爭的災難,但沒有親身打過仗。憑借材料,不會寫成報道嗎?
困惑之余,澹臺瑋、孟靈己年輕的身影給了我啟發。材料是死的,而人是活的。用人物統領材料,將材料化解,再摶再煉再調和,就會產生新東西。掌握煉丹真火的是人物,而不是事件。書中人物的喜怒哀樂燭照全書,一切就會活起來了。我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只有誠心誠意地拜托書中人物。他們已伴我三十余年,是老朋友了。
我驚訝地發現,這些老朋友很奇怪,隨著書的發展,他們越來越獨立,長成的模樣有些竟不是我原來設計的。可以說是我的筆隨著人物而走,而不是人物隨著我的筆走。當然,并不是所有的人物都這樣,也只在一定程度內。最初寫《南渡記》時,我為人物寫小傳。后來因自己不能寫字,只在心中默記。人物似乎膽大起來,照他們自己的意思行事。他們總是越長越好,不容易學壞。想想很有趣。
您說過,“我一貫認為,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應帶有中國個性”,怎么理解中國個性?您的翻譯以及對外國文學作品的理解秉持怎樣的原則?
我不記得當時是怎么想的了,我現在頭腦退化了,照我現在的想法,研究外國文學要時時關心中國文學,尤其是現在的創作。和馮至先生在一起談過,馮至先生也是這樣認為的。我們的外國文學研究所是注意到這一點的,這是一個自然事實,就是當時外文所的老一輩先生們,許多位都是曾經從事創作的。馮至先生自己在新詩方面和小說創作方面都很成功,他的小說《伍子胥》是有探索性的。馮先生對中國古典文學也很有研究。卞之琳先生本身就是詩人,《十年詩草》篇幅不多,卻能流傳。楊絳先生的小說和戲劇也有一定的影響,我記得有一個劇本《弄真成假》,臺上有一只貓,坐在一堆書上,有人把它一提就放在椅子上,我和我的弟弟都喜歡這個場面。我說我們的外國文學研究,應該帶有中國特色,不是應該有,應該是自然就有。并不是說研究外國文學的人必須也要創作,只是說要關心中國文學。
關于翻譯,一般說要做到信、達、雅,當然,那也不是容易做到的。至于文學翻譯,那就應該是一種再創造,而且最好是適合原作風格的再創造。讀者從翻譯中要感受到原作的全部是不可能的。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讀者不能看到原作語言的美。要靠翻譯的文字來代替,可以感受到與原作相等的各方面價值。如《魯拜集》是波斯詩人奧瑪·海亞姆所作,是愛德華·菲茨吉拉德翻譯的,而成為不朽的英詩,這是再創造。
我在五六十年代,曾將《霍桑》的一篇童話譯成中文,故事說的是:一個國王愛金子,魔法師使他能夠把任何碰到的東西都變成金子,他得到很多金子,但是災難來了,因為他碰到的東西都變成了金子,食物到嘴里也變成了金子。他親愛的小女兒,向他撲過來,一下子也變成了金子。這篇作品我很喜歡,但譯成后不知放到哪里去了。在20世紀70年代,有一段時間,大家已經上班,可是沒事做。當時的領導安排我和另外兩位同志翻譯韓素音作的《毛澤東傳》,我們完成了。大概是世界文學復刊以后,我翻譯了霍桑的小說《拉帕奇尼的女兒》,很得好評。后來,有人向馮至先生建議,讓我翻譯美國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作品,我沒有做到。后來,只翻譯英國女作家曼斯菲爾德和波溫的一些短篇作品。
我曾想,一個人有三個頭,一個搞創作,一個搞研究,一個搞翻譯。但是,我只有一個頭。我現在聊可告慰的就是我寫了我要寫的長篇小說,看我和它誰先到終點吧。而生命剩下的已經不多了。和前輩們談到幾個頭的問題,馮至先生說:不只一個人想同時進行創作和研究,都覺得是不可能的,只能是有所側重。因為,一個是形象思維多,一個是邏輯思維多。
您理想的生活狀態是什么?
我少年時,讀到東坡一首《行香子》,最后一句是“幾時歸去,做個閑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席云”,這是我理想的生活。可是現實生活的紛擾,讓我永遠也過不上那樣的日子。
您現在的狀態如何?
我就是一只螞蟻,像螞蟻在爬。寫一天病兩天。如果不寫完很不甘心。2015年5月中風后,很怕自己再發生意外,就把小說后面該怎么結局寫好了。現在每天臥床,有一個鐘頭坐在電腦前,繼續寫幾句。
是什么動力在支撐您寫下去?
曾經有記者問我,為什么寫小說?不寫對不起在身邊凝固的歷史。為什么寫散文?不寫對不起胸中的感受。為什么要寫童話?不寫對不起腦子里的夢。為什么要寫詩?不寫對不起耳邊歌唱的音符。前三個都有所得,詩是毫無進展。
您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為了真善美。
我這一生,一個求真一個求美。我一直在想,在民國時候常常提的真善美,現在好像不大提了。我希望歷史能夠真實,不要瞎編亂造;希望藝術創作能夠真的像個藝術品,不是很粗糙的一堆。大家應該研究研究,尤其是年輕人可以談一談。
我想表達我這個時代。尋求美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我父親在他的一生里,遭受過很多不公正,人們對他不夠認識,我也做了一些事情,常常在說話。我是在求真。求歷史得到它本來的面目。
您自己曾戲稱是“四余”居士?
在運動之余、工作之余、家務之余、和病痛作斗爭之余寫了些作品,也實在是很努力了。我已進入耄耋之年,成為真正的老年人。這一階段可以說是人生的“余”了。我現在應該稱為“五余”居士了。余的力量不多,總還有一點吧。我收到的讀者來信不多,有兩個年輕人的信給我印象很深。他們說等市面上看《西征記》《北歸記》,等得不耐煩了,他們要我加油,后面打了三個驚嘆號。老實說,這油也剩得不多,不過我會努力寫,以稍減慚愧之情。創作的道路很長,攀登不易,人生的路卻常嫌其短,很容易便到了野百合花的盡頭。我只能“托破缽隨緣走”。我的破缽常常是滿滿的,裝的是大家的關心和愛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