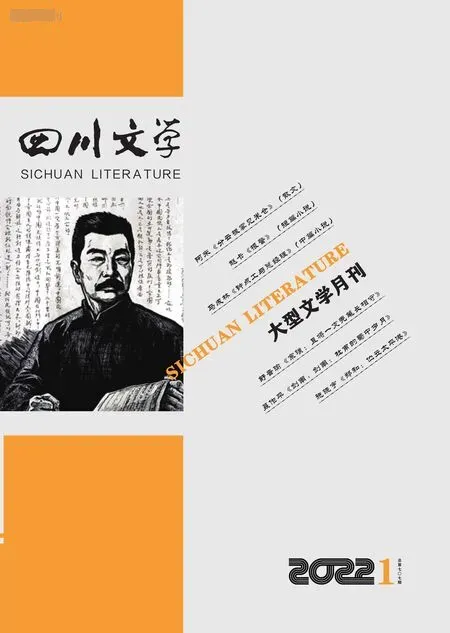隔壁有人
□文/宋曉杰
一
直到現在,我也沒見過那個人,但他卻時刻影響著我的生活。
有時候,我覺得他并不存在;有時候,又覺得他不存在才怪呢,難道是我有病?
二
我家所在的小區,是我們這兒比較牛的小區。雖然比不上最高檔的樓盤,但綠化好、衛生好,物業費單價才一塊二。“樓道里的樓梯扶手、樓外的不銹鋼垃圾箱,有專人天天擦,哪個小區能做到?”
小區正好處于兩個重點高中之間。小城就這兩個重點高中。挨著學校的學區房鬧鬧嚷嚷,一放學,滿街孩子,家成學生宿舍了,孩子們腦子換不過來擋,不好。這兒呢,路不遠,孩子們過條馬路,放開大長腿十分鐘八分鐘就到了。關鍵是能吃上自家的熱乎飯,還能瞇個囫圇覺,保證下午上課精力充沛。
更主要的,我還沒說呢——清靜!樓與樓之間有百十米距離,中間有楓樹、楊樹、柳樹、草坡隔著。還有從南方移植過來的大樹,我不認識,樹干上掛著藥袋子,輸著營養液,長途跋涉它們肯定累壞了。不過,它們很快恢復過來,一撒歡兒,就躥到三四十米高了。小區成了市里的標桿,小區大門兩側并排掛了一溜金色鐵皮的匾,刺眼睛。來參觀的人隔三岔五就一幫一伙的,我們都習慣了。
我搬到這兒,是閨女上大學后。沒辦法,我總比別人慢半拍。知子莫如母。我不到兩歲,我媽就開始叫我“二老慢”。原因很簡單,幼兒園小朋友吃飯快吃完了,我才把一碗飯捅個坑兒。人家玩“老鷹捉小雞”跑老遠了,我肯定是剩在最后被捉住的呆雞。我媽說,她得跟我操一輩子心。
這不,剛搬來時,我媽說裝修千萬不要花太多錢,把大票“呱嘰呱嘰”貼墻上、“吧嗒吧嗒”踩腳底下,你不心疼?!那可是熬心血熬出來的。
我媽說得沒錯。我是化工廠工人,三班倒。套用一句時髦話:沒倒過班的人,不足以語人生。我雖然技校畢業,但啃過幾本書,不明白硬啃,結果啃得半生不熟的,像吃了七八分熟的牛排,怎么說營養也能吸收點兒。
我家離工廠有半小時車程。白班還好,像個人兒似的,神經和思維都能在“正點”上。四點班也說得過去。下午四點接班,夜里十二點下班,跟打個游戲、看個夜場電影沒啥區別。最難受的是零點班。從零點接班,到第二天早上八點下班。為什么難受?前半宿相當糾結。睡吧,睡不爽,不舒服;睡爽了,起不來。不睡吧,后半夜熬不動。
同班的鋼子說:“笨!就算打個通宵唄。多大事兒,至于憋屈成禿瓢兒嗎?”
要是前幾年——不用多,五年前,我準跟他急。現在他說得沒錯,我是笨,快五十了,整天迷迷瞪瞪的,腦袋基本可以當燈泡了。我跟鋼子說,你去撩妹兒吧,我給你當正經燈泡,半費,算是還你當“更夫”的人情。
上零點班時,鋼子從來不睡覺,或者說,他坐在控制室里就能睡著。“你豬啊!精神點兒,聽到動靜趕緊起來不就行了。”鋼子有這能力,一邊嘴里嚼著飯,一邊就睡著了。可你跟他說話,他還能答上來。服不?年輕啊!我可不行。
更衣室在控制室對面,我得把自己反鎖在更衣室里,幾把椅子排在一起當床。鋼子給我打更。可是,我最怕鋼子沒輕沒重地突然跑過來敲門,大喊:“快出來!隔壁有人!”
三
隔壁,是指合成車間。集團的人巡檢、查崗基本按這個順序。鋼子敲門時,說明查崗的人已經到那兒了,或者,正勻速朝我們控制室走來。我總是在這個節骨眼兒被生生地從夢中喊醒。
我驚恐地卷起軍大衣,往更衣柜里胡亂地塞,像把情人硬塞進大衣柜。媽的!我的心突突跳,血往上涌,像被抓了現行。
說真的,讓巡檢抓到可不是鬧著玩兒的,檢討、扣分、罰錢,說不好就直接開了。現在哪缺人吶,人都沒虱子稀罕。
年輕時,游戲剛時興,我動不動就玩通宵,第二天該吃吃該喝喝,啥也不耽誤。現在可好,上個零點班,臉鐵青,像他媽殺豬的,不得不白天補覺。
可是,補覺卻成了難題。
第一次知道那個人的存在,是在一個下午。或者也可以說,從那個下午開始,我開始了與他曠日持久的糾葛。
那天,我正在玩游戲,聽到隔壁傳來一陣怪異的笑聲。怎么說呢,那怪異沒法形容,聲音響亮、豪放,沒遮沒擋的,像馬松開四蹄在草原上瘋跑那樣。也可能喝高了、喝爽了,反正聲音挺浪。
我仔細聽,他不會是年輕人,起碼得四十多歲。但聲音的爆發力強,肺活量大,常常是沒有任何前因后果,笑聲破空而來,絕塵而去。像控制不好的按鈕,說笑就笑,說停就停,音量根本沒有過渡。
那天,聽到他的笑,我想應該是家里來客人了吧,而且,是很久沒見面的朋友,不然聲音里的熱烈程度不至于那樣。起碼,也得有三四個人同時在。因為不只是笑,他還大聲說話。可是,即使我把耳朵貼到墻上,也聽不清他具體說了什么。
當時我正萎靡著,就關了電腦,歪著身子倒在床上睡著了。
再次醒來,是被那個聲音“震”醒的。起初,我感覺睡得很沉,像掉進沼澤池里,怎么也掙脫不出來。我還看到沼澤池的邊沿兒上有鋼管的扶手,像游泳池那種,豎的兩根鋼管之間還橫著鋼板做踏板,順著踏板可以爬上岸。我心里什么都明白,可怎么也抬不動手腳,像被什么釘著。
我瞇著眼睛。窗外的光線太強了,看墻上西斜的程度,應該三點左右。摸過手機瞄一眼,嗯,不錯。我繼續躺著沒動,讓自己慢慢還陽。
這時,那個聲音更響亮了。像什么?嗯,像吃不上飯的人撿了狗頭金,馬上就要笑斷氣兒了那種,弄得我后背涼颼颼的。可能人家得了大筆遺產,成人之美嘛。讓他一次笑個夠吧。
可是,我太幼稚!從那天起,我的厄運便開始了。
四
幾天后,第二次笑聲再次響起。那天下白班,我跟朋友約好,晚上十點,一起打《英雄聯盟》。待家人都睡了再玩兒,不能干擾別人。我們激戰正酣呢,隔壁的笑聲又響了起來。
什么墻啊這是,太薄了!我第一次對小區的口碑開始懷疑。轉念一想,還好。虧得提醒,不然晚上和老婆睡覺,正忘我“大戰”,隔墻有耳,有人聽聲兒啊。
五六十萬,鬧玩兒呢?!傾囊而出買的房子,還能怎么辦。
管他呢!沒那么矯情。他笑他的,我玩兒我的。各不相擾,不就得了。
可是,我把事情想簡單了。
不知道是笑聲原來就在,我沒留心;還是他們是才搬過來的新住戶,人家本來就有那癖好。反正,接下來的日子,隔壁的笑聲已經成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了。
我開始嚴重失眠,黑眼圈不說,掉頭發。正說著話呢,竟忘了想說啥,動不動就走神兒。鋼子逗我:“縱欲過度吧,人都塌了。這把年紀,老弟勸你一句……”
還沒等鋼子說完,班長也來逗趣。“是不是化驗室的婚前女友又來勾搭你了,咱可得保持晚節啊!”班長平時不太愛開玩笑,忽然冒出幾句,只能說明我的黑眼圈兒已經發展到大熊貓級別了。我翻翻眼睛,不知道怎么回他。
趁送飯盒的工夫,我向更衣室的鏡子里掃了一眼,再左左右右扭扭腮幫子,看看自己的臉。天!的確,臉色黑不黑、紅不紅的,豬肝啊,還不如本來就黑好看呢。眼睛像紅眼耗子。媽的!怎么搞的。
實在扛不住了,得想個辦法。
有一天,我撥通了物業的電話。“麻煩你們給他打個電話吧,不是不讓人家玩兒,那是人家自己的家。可是,我也有權利在自己家里睡個好覺呀。能不能讓他小點聲兒,別那么興奮,我都要精神崩潰了。”
接線生應該是個小姑娘,聽聲音,年紀應該跟我閨女差不多。除了應有的職業禮貌,聲音里明顯透著膽怯。我知道我給她出了道有點兒難的題,總比問她什么時候繳物業費、什么時候供暖難些。
又過了幾天,情況依舊。我不得不再次撥打物業電話。
應該還是上次接線的那個孩子,因為是她搶了我的話。她說:“真是對不起!我們打過電話了,他家沒人,估計是上班了。不過,晚上我們也打過了,他家里也沒人。”
我覺得她沒誠意。打幾遍我不管,但事情沒解決是真的。“是不是他們家電話壞了呀?”我明顯不滿意了。
小姑娘見我仍然不依不饒,像咬牙擰著硬餅子,只好懂事兒地說:“您別急,我馬上再打。如果還沒人接電話,我就去他家敲門。”有了這句話,我心里落底兒了。
誰知,半夜,笑聲又響起來了。
大半夜的,物業有沒有人值班我不知道,但這么點個事兒,騷擾人家也不好,有點兒小題大做了。
好吧!再忍一下。
我給自己倒了杯熱水,披了睡衣在客廳里遛,像什么大人物似的憂國憂民。估計我們集團老總都沒我這么操心。最起碼,人家現在摟著媳婦兒睡覺呢,不像我有床不能上,明燈大燭遛狗一樣遛自己。
也不知遛了多長時間,驚動了媳婦兒。她開了房門,見我閉著眼睛逛來逛去,很好奇。“你夢游啊?”
還是媳婦兒心疼我,讓我到她的“閨房”去睡。
自從生了閨女,媳婦兒就和閨女睡在一起了,還給她們的臥室取名“閨房”。門框上,貼著閨女二年級時用毛筆寫的這兩個字。搬家過來時,閨女稚嫩的字沒跟過來,可“閨房”卻成事實。
這可苦了我嘍。我有什么要求得事先提申請、打報告。人家給面子,打開“閨房”,我才能“吃”一頓,解解饞。不然,也不好意思去打擾。這會兒女兒上大學了,但“閨房”的“傳統”卻一直保留下來。媳婦兒說,這樣可以保持婚姻的新鮮度。女人啊,多大歲數都覺得自己十八。沒治了!有時,結束“戰斗”,我就偷偷地溜回我的“男生宿舍”(當然,后來媳婦兒也叫她的屋“女生宿舍”),要不睡不踏實。媳婦兒也習慣了這樣分屋睡,睡在一起反而不習慣了。
這不!看我可憐見的,媳婦兒收留了我。還是親媳婦兒親啊。
可是,在一個床上睡覺,我又睡不著了。她也翻來覆去烙餅。不是這個屋子也能聽見笑聲,是兩個人各自待習慣了。她嫌我打呼嚕。我嫌她磨牙。也沒有第三者裁決,這官司打得真沒名兒。第二天早晨,上班臨出門時,媳婦兒一邊沖我翻白眼兒,一邊把門摔得山響。
你生氣?我還氣呢!
好吧!睡沙發。沒什么難題解決不了。沙發挺大,把靠墊拿下來,相當于單人床大小。不錯。
在沙發上,我還真睡了幾個好覺。可以不必天天洗腳,呼嚕可以全頻道隨便打。好像還做過兩回美夢,男男女女的,甜甜蜜蜜的,像詩,甜嘴巴舌的。場景并不確切,但美好的感覺一直在腦子里轉悠。有時,半夜爬起來玩手機,看鋼子轉來的黃段子、抖音啥的,媳婦兒也不會發現。撿了大便宜。挺美!
可是,沙發住了大半個月,我忽然心理不平衡了。
憑什么呀?幾十萬買的房子,還得睡沙發?我又不是來的客,更不是保姆。
一想到這兒,我的氣又來了,操起電話給物業,吼道:“我要投訴!再不解決,我就起訴小區!”
那姑娘都要哭了。“打電話沒人接啊,我天天打,敲門也沒人開。業主登記本上留的那個手機,是空號。他家也沒留工作單位。誰知道他家咋回事兒呀!”
“我自己解決!我就不信了!”我狠狠地掛了電話,頭有點兒暈。好像我的聲音太大了,把自己都震暈了。
五
那天,半夜里下起了小雨,我越想越氣。還得找,不能忍!
我做了兩手準備。先找了碳素筆、A4紙,寫了張字條:“鄰里以不驚擾他人為基本的禮貌。請您打游戲時放低音量!謝謝合作!!隔壁鄰居”
這是留個后手。在此之前,我準備先敲門。
做好了這些準備,我信心滿滿、牛氣沖天地下了樓。下樓時,沖著門,我還像出征前的將軍那樣,揮了揮右拳,大喊一聲,為自己提振士氣。
因為心里想著事兒,順手我就把房門帶上了,門舌頭輕輕一扣,我心一涼。完了!忘了帶鑰匙。單元門的鑰匙也在鑰匙串上。不過,比起高昂的士氣,這個小插曲,根本不是事兒。
推開單元門,我站住了。雨還不小。
怎么跟個娘們兒似的,一胯子遠,三步兩步就到了嘛。我罵自己一句。
那張肩負歷史使命的A4紙,被我頂在腦袋上。我縮著肩,沖進雨夜。
我住在二單元,我要去的一單元的鐵門同樣也緊關著。沒事兒把單元門關上,小區要求這樣,目的是防止送外賣的、送快遞的直接入戶,不安全。
我算計著我隔壁的房間號碼,按了門鈴。按了八九遍,也沒人接聽。
在雨夜中,鈴聲兀自響起,小夜風再一吹,我不禁打了個寒戰。現在,我太怕聲音了。
但是,別忘了,我不僅叫“二老慢”,還叫“二老狠”。小時候,我敢打比我大好幾歲的男孩。我的強項是蔫下手,村頭小潑皮欺負我,我拿我爸的小矬刀當彈子,用彈弓射得他嗷嗷叫。好漢不提當年勇,誰知,越長大越窩囊。
我越想越氣,對著單元門猛踹一腳。鐵門沒咋樣,卻把我右腳的“小老五”挫疼了。我是趿拉著拖鞋出來的。
我又按了兩下門鈴,還是沒反應!我只好悻悻地回家。
雨忽然大了起來。從一單元跑到二單元的工夫,我就淋了個半透。我氣急敗壞地把那張紙撕碎,丟在雨夜中。
六
媳婦兒睡眼迷離,半天,才起來解鎖。聽到單元門“咔噠”一聲,我的心里一下子亮堂了。
家門媳婦兒替我留著。我進屋時,媳婦兒不僅在“女生宿舍”門口留下一個松松垮垮的背影,還留下一句“神經病”!
我勃然大怒,“你直接叫我‘精神病’好了!全世界都有病!”
媳婦兒迅疾地轉回身。她轉身的速度太快了,嚇了我一跳。不過,她的聲調卻是故意壓低的:“大半夜的,我不想跟你吵架,讓鄰居笑話。一個大老爺們兒,天天神神道道的,矯情!”說完,這次是真的進了“女生宿舍”。
雖然我是個大老粗工人,但從結婚那天起,我還真沒跟媳婦兒粗門大嗓吵過。人家出生在教師世家,乖乖女。想當初,沖破家庭阻力嫁給咱,入洞房時咱可答應過人家,不許欺負人。還說自己有“兩怕”:一怕(媳婦兒)不幸福,二怕(媳婦兒)哭。
我沖進洗手間,看到鏡子里的自己哭笑不得。身上的背心、運動短褲被雨水淋過,濕乎乎地貼在身上——這次我看清了——真他媽性感,肋骨都看得清清楚楚。難怪鋼子說,這條兒!你可以當健身“達人”了,上選秀節目。我還不承認呢。現在看來,瘦得離魚刺不遠了。
我惡狠狠地把背心、短褲扒掉,丟進洗衣機。把冷水開到最大,報復似的沖著胳膊、腿、頭。
跟被雨淋相比,笑聲真不算啥。還因為這點兒破事兒,搞得媳婦兒跟我別別扭扭,太不值了。難道,是我錯了?
“你睡你的唄。現在的住宅哪個不是空心磚砌的墻?不然開發商怎么掙錢?怎么蓋得那么快?墻壁都是空心磚立著碼的,又快又省錢,還省面積。別人能睡,你為啥不能?就你硌楞!”
看來數學老師沒白當,道理講得頭頭是道。
我忽然覺得自己很無聊。是啊,不就是笑嗎,又不是哭。
不過,我心里還是別扭。我知道媳婦兒連珠炮兒似的說這么多,還有重要的話被她省下了,言外之意我懂。“你一個臭工人,難道還是豌豆公主不成?事兒爹一枚!”每次我倆之間的戰爭,都是由此做導火索。這一套,像她編排好的教案。
今天,這一章她還沒講到底,可能是看我淋得太慘,留了情面。唉!我搖搖頭,想讓自己清醒點兒,把事兒再捋一捋。
為了更好地解決問題,趁著早上人們里出外進的工夫,我又拿了張A4紙,重新寫上要說的。意思沒變,但語氣更嚴肅了,還加了好幾個感嘆號。兜里揣上透明膠帶。
貼紙條之前,我還是照例敲了敲那家的房門。沒人。
可能我敲門的聲音太大了、太急促了,倒是把對面屋的人敲了出來。
“他們家沒人!敲什么敲!”門開了,一個女人和狗的卷卷頭發一起卡在門縫里。聽語氣,她壓著火兒呢。
“怎么可能?我聽見他家天天晚上有人笑。”我也有點兒不高興了。
沒見到天天晚上笑的人,那個女人倒是真的笑了,輕蔑地笑。
“你這人有意思啊。我是這個小區的第一批住戶,一直住這兒,快十年了。低頭不見抬頭見的,我家鄰居有沒有人,你比我清楚?!”
不管三七二十一,在那個女人歪著嘴角兒的冷言冷語中,我把我的憤怒貼在了那家門上。貼好了,我還不放心,又用透明膠帶沿著紙的四邊“哧啦哧啦”橫豎粘了好幾遍膠條。
出了單元門,我聽到鐵舌頭清脆地落在鎖槽里,心里一陣輕松,腳步也輕快許多。
七
接下來的幾天,似乎沒有動靜了。可能紙條起了作用。這么文明的小區,文明人還是多啊。誰玩游戲不是玩兒到嗨呢,表達興奮也是可以理解的嘛。我忽然對自己的思想轉變表示滿意。因為我也是文明人。
可是,隔了幾天,我剛躺下,還沒把氣喘勻,笑聲又響了起來。我第一反應就是:對門那個女人是那家伙的同謀!
只要我在家,天天晚上,我像蝙蝠一樣,豎著耳朵靜聽隔壁的動靜,我已經成為習慣。不然,反而像丟了什么。
有一天,我繼續當“蝙蝠”,竟然有了重大發現。
隔壁的家里很吵,但不是來客人很多那種吵,七嘴八舌的,高高低低的,而是他一個人的聲音!仔細聽,一聲高、一聲低。不過,確實是他一個人的聲音。
我嚇得汗毛都豎起來了……他,他,他是不是人類呀?不會是外星人吧。大仙兒?
我鉆出被窩,在屋子里巡視半天,發現窗簾后面有一個棍子,是當初裝修時干活剩下的。
我開始用棍子敲暖氣管子。試試探探地敲。先小聲,后大聲;先慢,后快。直到相信我的信息他能聽見并聽懂了,為止。
果然!隔壁的笑聲和說話聲,小了下來。曾經有一段時間,還相當安靜,什么聲音都沒有了。
八
我斗智斗勇,終于睡了一個好覺。
第二天,鋼子發現了我的變化,眼睛在我臉上掃來掃去,猜我昨晚“濤聲依舊”了。
我打了鋼子一拳,但心里也是美的,覺得平時不愛看的設備、儀器,在太陽的照耀下那么美,充滿硬漢的光輝。
既沒跟媳婦兒吵架,也沒對前女友相思成災,只是因為睡不好覺。一高興,我跟鋼子說了實話。
“哎呀!我以為多大個屁事兒呢!不就是笑嗎,他做愛我都不怕,他還能24小時不間斷?滿格電呀?跟你說件事兒,我們家樓下的老太太死了,四五個兒子,老太太活著時沒一個孝順的,死了卻來整事兒。請了和尚超度不說,還請了哭喪的,那叫一個死去活來!我聽得都直掉眼淚。我說,親哥!你想想,整整三天啊,因為老太太是零點剛過沒的,也就過十分鐘八分鐘吧,是大三天,我勒個卻!我記得我小時候一聽哀樂就吃不下飯,現在可好,連誦經帶哭喪,你用腳趾頭想想……”
鋼子悠著臉,兩只眉眼明顯不在一條線上,看樣子真要哭了。
“實在不行,你換個房,租個也行,再不就度個假,說不定回來就啥事兒沒了。干受這氣,多不值呀!
“對了!我大舅哥有個平房,離咱廠不太遠,就是冬天沒供暖,得自己燒土暖氣。再不,我跟他說說,你搬過去住幾個月?”
算了!不用!
鋼子這么一說,我倒也覺得是自己太事兒了。跟媳婦兒——不!是媳婦兒跟我慪氣慪幾天了,想想還是自己這兒出了問題。大丈夫要能屈能伸。
那天是白班。晚上下了班,我特意到大潤發超市,買了媳婦兒愛吃的雪魚。回到家,七七八八地做了紅紅綠綠好幾個菜,還開了一瓶雪花純生。
媳婦兒一進屋,愣了一下,“你中彩票了?”
“沒沒沒!”我結結巴巴的,順手提過酒瓶子,給媳婦兒滿上一杯。
九
可是,我高興得太早了。好日子過了幾天,笑聲又起,我又犯病了。
我在想,可能,是不是他在跟別人打游戲,跟群里的同伴說話呢。有可能,那伙計戴著耳機。怎么忘了,我也有打游戲戴耳機的習慣,不受外界干擾。起初,是因為媳婦兒天天晚上追磨磨嘰嘰的韓劇,連哭帶號的,我注意力不能集中。后來,我覺得戴上耳機好啊,完全可以沉在自己的世界里,海洋是真海洋,宇宙是真宇宙。老過癮了!
對呀,我為什么不能戴耳機睡覺呢?
后來,我就這么干了。
還別說,這是個好主意。
戴上耳機,什么聲音都屏蔽了。我都能聽到自己心跳的聲音了。
還有,我還學會了根據那個人的時間表走。隱身人不說不笑,我就趕緊睡。隱身人開始發聲,我就起來玩游戲。我甚至想過,哪一天,我們一起聯手打一場游戲,說不定,我們還能配合得挺好呢。
十
說實話,在心里,我與他已經和好了。甚至,隱隱地還有了幾分期待。
他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呢?糙老爺們兒吧,肯定是!別看我叫“二老慢”,但在心里,我還是喜歡干脆利索的爺們兒。連大蔥大蒜都不吃,忸忸怩怩,拿五作六,動不動就捏著鼻子、關半個嗓子說話的主兒,我可不喜歡。但是,他在哪兒呢?
有一天,我從單元門出來,見一個男人在我前面十幾步遠,大大哧哧地晃來晃去,手里提著一瓶白酒、一袋溝幫子燒雞和綠葉菜。這時,迎面過來他的一個熟人跟他打招呼,他有禮貌地回著哈哈。我的心“咯噔”一下——戀愛時,我也沒記得有過心“動”的感覺呀——那聲音!對!那聲音跟晚上我聽到的太像了。
我快走幾步,想看一下他到底長什么模樣。如果可能,跟他搭個話兒,確認一下。放心!我早就不生他的氣了。
那個人“吱吱”兩聲按了車的遙控器。停在路牙子下邊的一輛“泥猴”車車門被他拉開。放好酒和菜,跟車有仇似的,他一腳把油門踩到底,“泥猴”忽地一聲竄出去,冒著黑煙,跑遠了。
從搖下的車窗,我看到了他模糊的側臉。三百度近視眼啊,我只能看清到這種程度了。不過,我覺得那個人歲數有點兒大。跟誰比呢?我認識“他”嗎?我知道他有多大?笑話!我都有點兒搞不懂自己了。
我愣愣地站在原地,像物業工人正在扒的半死不活的那根木樁子。
十一
后來,我根本沒想到,我的境界已經上升到更高的層次了:沒有他的笑聲,我睡不著了。換句話說:只有聽到那瘆人的笑聲,我才能像嬰兒在搖籃中一樣,甜甜地睡熟。
媳婦兒看我一忽好一忽壞。一直想帶我去看醫生。她說,你別總神叨叨的,就是神經衰弱,倒班倒的。不如讓醫生給你開個證明,你趁機辦個病退得了。
我媽更離譜,讓我去看心理醫生。我和媳婦兒結婚這么多年,她們倆在這件事兒上第一次達成共識,總是背著我嘰嘰咕咕泡電話。咋知道?我一進屋,媳婦兒就趕緊提高嗓門兒,收了電話。“媽,沒事兒了。天熱,注意血壓。白天你就別出屋了,晚上去廣場跳跳舞就行了。”我就當沒聽明白、沒看懂。
“病退?有個班上,好歹我還能月月有那么多工資呢,還有年節的福利。再說,退了我干啥?我能干啥?”
我對自己認識得很清楚。老死不如賴活著,雞肋也是肉。我可不退。
一想到退休,我就更珍惜每個上班的日子,連零點班也珍惜得不行不行的。有時,下了夜班,即使睡不著覺,我眼睛也像燈兒似的,歡喜著。有時,每晚睡覺前,還會把臉貼在墻上,好像與隔壁那個隱形人打招呼,“你好!兄弟!”然后,睡不睡覺也沒那么重要了,天下要做的重要事兒多著呢。
可是,一連好幾天,隔壁的聲音卻忽然沒有了。
搬家了?旅游去了?還是進了精神病院?或者……出了什么意外,死了?
“阿彌陀佛!”我怎么可以這么想。罪過。罪過。
十二
我又恢復了從前的狀態,整夜失眠。但與從前不同的是,這次是因為聽不到隱身人的聲音,睡不著。
那天,在樓下,見一樓的女人在給菜地澆水,我指了指隔壁二樓的窗子問她,聽沒聽過有人在夜里笑。
那女人說:“是呀,是有人笑。”很確定的回答。可是,不到兩秒鐘,她又含混著說:“好像有吧,我也不確定……我睡覺可死了,別人把我抬走都不一定能醒。”說完,還神秘地嘿嘿干笑了幾聲。
她指了指那扇窗子。“你是說那間吧?”窗子黑漆漆的。雖然是白天,但有一層米色也許淺咖啡色薄紗窗簾,拉得嚴嚴實實。
我倆一起抬頭,向那扇窗子望去。
二樓陽臺的曬衣繩上,搖著幾件黑不黑、灰不灰的衣服。那是什么年紀的人應該穿的衣服呢?不能確定。
我開始播放隱身人的笑聲入睡。晚飯可以不吃,像催眠曲一樣,每晚最需要的就是它了。
常聽說,老年人在床上睡不著,躺在沙發上、開著電視就能睡著。是不是同一個道理?我老了嗎,難道?
什么時候用手機錄了隱身人的笑聲,我竟忘了。
有一次,在班上,我本意是想從手機里翻找一張照片,不知怎么竟翻出了那段音頻。我嚇了一身冷汗。鋼子連忙螞蟥見血似的湊過來,“什么聲音,你做愛的嗎?我聽聽!”
我白了鋼子一眼,趕緊收了音頻。
這回可好了。放上那段音頻,我就能睡得著。不放,就睡不著。真他娘的邪門兒了。
十三
很久沒有隱身人的聲音了,我倒擔心起來。
這時間越長,我越覺得從前的生活是虛幻的。這個人真的不存在?
我開始把這段日子往回推,回到自己最初搬來小區的時候,確切地說,回到第一次聽到隔壁笑聲的時候。
我仔細分辨著、猜想著,聲音有可能傳來的方向。我開始懷疑——也許笑聲不是來自墻壁那邊,而是我家樓上?樓下?對面?對面隔著走廊和電梯,首先肯定不是。
我又敲了樓上。三口之家。男人說話的聲音比娘兒還小。家里有一個三四歲的小女孩。小女孩在屋子里跑來跑去,我還能聽到男人的勸說:不要跑了!樓下叔叔阿姨會生氣的。
樓下呢,是一家五口,老兩口、小兩口加一個男孩。那三個男人的聲音都不是我夜里聽到的聲音,不是。
關于這些,我是知道的。但是,為了說服自己,我都一一去確認、去排除。
我要絕望了。起初也絕望,一度,是因為恐懼,因為那笑聲讓我想起《簡·愛》中的女瘋子。后來,是因為無法擺脫。現在,我覺得是失去了一個伙伴。“說不定,他也在找我呢。”我這么想。
不行!我要找到他!一定!即使他是外星人。
一個雨夜,我大笑著沖出了家門。
媳婦兒聽到了關門聲,衣冠不整地從陽臺上探出半個身子,朝我的背影大喊大叫,“你瘋了嗎,快回來!”
可是,那聲音離我太遠了,隔著幾里地,好像,中間還隔著大霧。
我頭也沒回,笑得更響了。
雨,越下越大。
再回頭時,我看見媳婦兒站在雨幕中,大張著嘴,卻一點兒聲音也沒有,像電影中的慢鏡頭。
我的笑聲那么響。越來越響,越來越響。擴散出去,又被什么彈回來,在我的身前身后環繞。我幾乎被自己的笑聲迷住了。
可是,笑著笑著,我一下子就停住了,像觸了電——我的笑聲,多么熟悉啊!怎么,與那個隱形人的笑聲,竟然毫無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