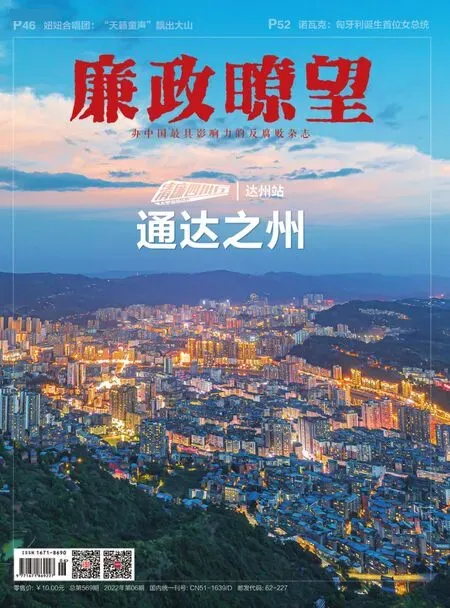蘇軾一生為何只給這五個(gè)人寫墓志銘?
│文 曾勛
古人講究“蓋棺定論”,除了留下事跡、作品和口碑,最直接的形式莫過(guò)于用墓志銘記錄墓主人的生世、品德和功績(jī)等等。
對(duì)士人來(lái)說(shuō),墓志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而,找誰(shuí)寫,怎么寫,大有講究。有點(diǎn)身份地位的人離世后,其后人必定會(huì)找與逝者關(guān)系親近、級(jí)別相當(dāng)或者著名的賢良為其寫墓志銘。自然,受邀寫墓志銘的人為誰(shuí)寫,不為誰(shuí)寫,更有講究。
所以,墓志銘不僅表征逝者生前的道德、財(cái)富、人脈、地位,其象征意義,還遠(yuǎn)遠(yuǎn)超出石刻悼文內(nèi)容本身。它承載著古人的性情喜好、人情世故,亦可從中窺見(jiàn)當(dāng)時(shí)的政治脈絡(luò)。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 年),距離蜀州青城農(nóng)民王小波、李順作亂已經(jīng)過(guò)去了60年,當(dāng)時(shí)有謠言說(shuō)六十年一甲子暴亂又會(huì)卷土重來(lái),部分造反分子在暗中摩拳擦掌。宋仁宗命禮部侍郎張方平入蜀安撫人心。張方平進(jìn)入四川后,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措施安撫民眾,迅速穩(wěn)定了局面。
蜀中經(jīng)過(guò)幾十年的休養(yǎng)生息,文教昌盛,人才輩出。這次入蜀,張方平還肩負(fù)朝廷安排的另一個(gè)重要的任務(wù)——為朝廷物色人才。他聽(tīng)聞眉山三蘇父子文冠蜀中,便去拜訪,后來(lái)又把三蘇父子引薦給歐陽(yáng)修,成就了“一門父子三詞客,千古文章八大家”的佳話。元祐六年(1091年),85歲的張方平逝世,謚號(hào)“文定”。蘇軾聽(tīng)聞噩耗,對(duì)恩師的離去悲痛萬(wàn)分,為其撰寫了墓志銘,并服孝三月。
后來(lái),蘇軾在《祭張文定公文》中傲嬌地表示,我從來(lái)就不愿為人撰寫墓志銘,我一生只為五人寫過(guò)墓志銘,這是因?yàn)樗麄兇_實(shí)有大功大德。實(shí)際上,蘇軾一生為七個(gè)人寫過(guò)墓志銘,分別是富弼、司馬光、趙抃、范鎮(zhèn)、張方平,另外兩人趙庸敬、滕元發(fā)的墓志銘,是他幫張方平代寫的。
富弼、司馬光自不必說(shuō),他們都是當(dāng)時(shí)的名相。嘉祐年間,蘇軾作為職場(chǎng)菜鳥(niǎo)在京城當(dāng)“京漂”時(shí),就寫過(guò)自薦信給宰相富弼,夸贊富弼“勇冠于天下,而仁及于百世”。這里面肯定有拍馬屁的成分,不過(guò),蘇軾的政治主張與富弼大體一致。
后來(lái)王安石主張變法得勢(shì),蘇軾站在司馬光一邊反對(duì)變法。直到宋哲宗上位后,王安石被罷相,司馬光拜相,因反對(duì)新法而被貶的蘇軾、蘇轍、劉摯、范純?nèi)实热嘶氐街醒氡晃灾厝巍K^“志同道合方為謀”,蘇軾為富弼、司馬光寫墓志銘,不光體現(xiàn)了他們政治理想的一致,也能看出蘇軾對(duì)知遇之恩的報(bào)答。
蘇軾為有“鐵面御史”之稱的趙抃作墓志銘,除了感恩,恐怕還有欽佩。趙抃跟蘇洵同輩,嘉祐四年(1059年),52歲的趙抃調(diào)任成都府路轉(zhuǎn)運(yùn)使,當(dāng)時(shí)眉州屬成都府路。之前兩年,蘇軾、蘇轍同科進(jìn)士及第,名震蜀中,京師的賢良均有所耳聞。
趙抃約見(jiàn)三蘇父子之后,推薦蘇洵為試校書(shū)郎。蘇軾兄弟對(duì)趙抃推薦父親的舉動(dòng)心存感激,后來(lái)在書(shū)信詩(shī)文中多有提及。趙抃退休回家,琴鶴相伴,過(guò)上了清苦閑適的生活。蘇軾寫詩(shī)說(shuō),“清獻(xiàn)先生無(wú)一錢,故應(yīng)琴鶴是家傳”,贊揚(yáng)趙氏治事清廉。趙家和蘇家經(jīng)常詩(shī)文唱和,相互扶持,實(shí)則為君子之交的典范。
而選拔蘇軾兩兄弟的主考老師之一,就是四川華陽(yáng)人范鎮(zhèn)。范鎮(zhèn)作為蜀中學(xué)者的代表,在翰林院曾多次負(fù)責(zé)貢舉考試。嘉祐二年(1057年),范鎮(zhèn)與歐陽(yáng)修、梅堯臣為知貢舉,選拔出了蘇軾、蘇轍、曾鞏等一大批有識(shí)之士。范鎮(zhèn)支持司馬光反對(duì)新法,與王安石不合,他指責(zé)王安石主張的青苗法為“殘民之術(shù)”。
在北宋涇渭分明的政治結(jié)構(gòu)中,蘇軾毫無(wú)疑問(wèn)是另類的存在。他不贊同王安石的所有新法,但在私下,他們?nèi)栽诮鹆旰染瞥停貌豢鞓?lè)。即便王安石知道這名后生與自己的政治理想相悖,仍舊在“烏臺(tái)詩(shī)案”過(guò)后,勸誡皇上“豈有圣世而殺才士乎”,力保蘇軾。他們都以身示范,澆筑了士人寬厚仁義的可貴品格。
蘇軾選擇性地為敬重的師友做墓志銘,縱有政治站位和感情親疏的考量,但正如他所言,這些人無(wú)一不是敢作敢當(dāng)?shù)墓⒔橹俊N娜讼缃穑鲋簞t直抒胸臆,文思如泉涌,這也算一種境界和情懷吧。
到后來(lái),蘇軾反對(duì)司馬光將新法盡除的極端做法,結(jié)果搞得兩頭碰壁,此后大半輩子不是打鋪蓋卷走人就是在被貶的路上。不過(guò),也正是蘇軾的“傲嬌”,成就了他的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