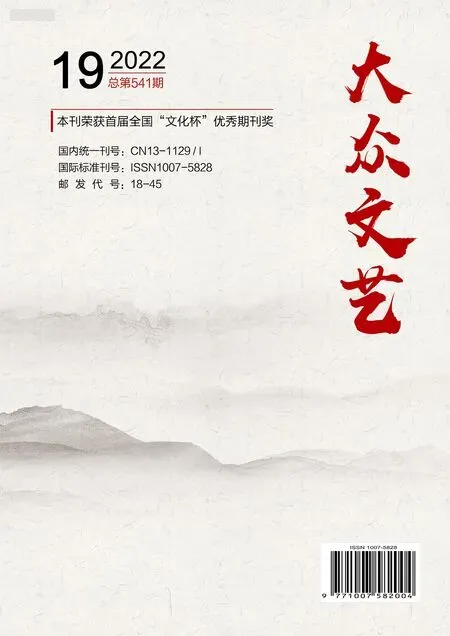延異視角下視覺隱喻在視覺傳達設計中的應用
方遠
(中國美術學院,浙江杭州 310024)
視覺傳達設計是一門運用視覺符號傳達信息的學科。在當下的數字信息時代,圖像借助數字技術大量替代文字成為主要的傳播媒介,語言作為文化符號的主導地位呈現出讓位于圖像的趨勢。然而在文字文本被邊緣化的同時,文字的文學性并沒有消亡,而是通過敘事、描述、虛構、隱喻等文學模式滲透到現代社會的各個領域,“在人文學術和人文社會科學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學性的”。在傳播領域,文學性滲透到圖像媒介中,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視覺語言與視覺文化,原本與語言文學相關的修辭學研究也開始“轉向研究多維性、動態性和復雜性為特征的新的修辭領域”。其中,視覺符號傳播這一新興領域受到越來越多研究者的重視,使得視覺修辭這一圍繞語言、圖像以及音像綜合媒介的修辭行為研究方向得到快速發展。
視覺隱喻作為視覺修辭的一種手法,在視覺傳達設計中被廣泛應用,具有顯著的文學性價值,其含義與美感的生成遵循西方后結構主義理論中“延異”的路徑。本文通過探討“視覺隱喻”與“延異”的共通之處,旨在追溯視覺修辭中的文學性在當代視覺傳達設計中的沿用與體現,拆解當下視覺文化的構建方式,為視覺傳達設計學科的科學系統發展提供新的理論依據。
一、視覺傳達設計中的文學性
“文學性”是當今人文科學研究領域的研究熱點之一。20世紀初,俄國形式主義學者雅各布森在《最近的俄國詩歌》中提出“文學性”是“文學科學的對象”,即“使一部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特性”,指的是在文學作品普遍存在的構造原則和表現手段,一種存在于文學語言中的藝術形式,也是文學的趣味之所在。在當下的數字圖像時代,影像媒介的興起伴隨著傳統印刷媒介的衰落,承載在屏幕上的數字影像正大量替代印刷產品中的文本,發揮著作為一種“視覺語言”的信息傳遞與交流的作用。在此環境下,文學在藝術中的主導地位逐漸被影像取代,文學似乎被迫面臨一種“邊緣化”的窘境。
然而,文學中的敘事、描述、想象、虛構與修辭早已滲透在廣大的非文學文本中,其中包括哲學、法律、歷史、人類學、傳播學、精神分析等領域,成為潛在的支配性成分。解構主義學者大衛·辛普森與喬納森·卡勒最早對文學滲透、轉移的現況進行了闡釋,國內學者余虹將其總結為狹義的文學“終結”的同時,廣義的“文學性”正在其他領域與媒介中“蔓延”,其中也包括以圖像信息為傳播主體的視覺傳達設計。
視覺傳達設計作為一門通過二度空間的可視藝術形式將特定信息傳達給受眾的學科,營造視覺美感的同時強調信息高效傳達的功能性。視覺傳達設計的“文學性”體現在視覺符號表達中大量與文學表現手法具有共性的技法與結構,例如修辭、敘事、象征等。因此可以推論,在傳播領域,數字時代下的視覺表達在占據原本屬于文本的傳播份額的同時,文學的特性仍被繼承在圖形與影像之中。合理運用“文學性”手段能夠拓寬視覺傳達設計的創作路徑,豐富讀者對視覺文本的體驗,其本身也具有藝術內涵。
二、延異理論視野下視覺傳達中的視覺隱喻
隱喻,作為一個將所指應用于不按字面適用的能指的概念,既是一種修飾話語的修辭現象,也是存在于人類思維中的認知現象。隱喻廣泛地存在于人類的文化藝術活動中,包括廣告、傳媒等基于視覺表達的領域。視覺修辭的意義依賴于圖像元素與元素之間形式上存在的類似于“修辭格”的關系,而隱喻作為一種修辭格是將某類事物看作另一類事物,是一種目標意義(本體)與某種具體已知的代表物(喻體)之間產生的互動與對話。
視覺隱喻在視覺傳達設計中的是一種構建視覺要素的方法:“是視覺形象的一個子集——構成符號的各個要素通過知覺被認識。”隱喻手法通過關聯具有相似性的“喻體”與“本體”,是兩個不同的語義場的語義映射,利用“喻體”幫助人們產生對“本體”的理解。在視覺傳達設計中,視覺隱喻的應用能通過這種意義的映射吸引觀眾的注意力,增強設計趣味性與信息說服力。
延異(differance)是由法國解構主義哲學家雅克·德里達創立的術語,包含延宕化(temporalization)和間距化(spacing)兩層含義。其中延宕化指的是時間上的推遲、延緩,而間距化則意指空間上的非同一、差異或分裂。在索緒爾所提出的符號學理論中,構成符號的能指與所指是由“系統內關系項之間的否定性差異” 決定的,例如“花”的能指與所指是由其不等同于“草”“土壤”“空氣”等其他符號狀態的差異性所決定的。德里達在這種否定性差異的基礎上,指出單一符號的釋義需要借助更多其他符號,由此推延形成不斷交織的符號鏈,在這個過程中構成了符號之間空間性的間隔和時間性的延伸,符號活動因而可以被總結為“由一個能指鏈滑向另一個能指鏈的延異運動”。
上文所討論的隱喻的定義中,“本體”和“喻體”具有相似性與非同一性,兩者之間通過隱喻“由此及彼”,發生了轉換運動。在設計過程中,創作理念的闡釋物通過視覺隱喻發生了轉移,從而造成了意義實現的推延,這種轉移與區分正是延異的精髓所在。因此可以推論,視覺修辭手法中的“視覺隱喻”與“延異”具有原理上的共性。
1.傳達環節中的隱喻
設計師Storm Thorgerson領銜的工作室與插畫家George Hardie合作為英國迷幻搖滾樂隊Pink Floyd設計了彩虹棱鏡的專輯封面。該專輯《Dark side of the moon》描繪了一代人面對現實產生的彷徨與焦慮情緒,通過超現實的歌詞表述和迷幻的聲音效果呈現出前衛的幻想空間。該唱片發布后一炮走紅,成為樂隊成名之作,而棱鏡折射彩虹光芒的視覺形象也成了專輯封面設計中的經典。對于創作團隊設計概念與靈感的記載主要有兩個來源:根據阿歇特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Comfortably Numb: The Inside Story of Pink Floyd》記載,創作靈感并非與歌曲相關,甚至并未考慮到深刻含義。樂隊成員Richard RickWright曾向以攝影與超現實視覺手法為長的設計團隊提出盡量“簡單”的建議。而設計師Powell偶然間看到物理教科書上光線透過窗戶形成彩虹效果的圖形,確定將其作為封面的主要元素。Storm Thorgerson在2011年接受音樂雜志滾石記者采訪時也否認了棱鏡與歌詞內容的關系,表示“我認為三角形是思想和野心的象征”,棱鏡作為包含三角形的載體因而能代表Pink Floyd樂隊。
從Thorgerson的解釋來看,棱鏡與Pink floyd樂隊的精神通過三角形的結構具有了一定的隱喻關系,與歌詞并不構成具體關聯。然而大眾則自專輯發行之日起對棱鏡符號的內涵進行了廣泛討論,大部分猜測依然圍繞與音樂主題相關的含義,例如新聞社交站點reddit上的評論中較為公認的說法是白色光束代表生命的開始,彩虹光束代表人一生中走過的諸多路徑和它們為人類帶來的影響。
可見,這些觀點基于一種主觀的隱喻假設,與創作者的意愿并不相關,而與歌詞內容、視覺符號蘊含在歷史文化中的隱喻意義具有關聯性。在西方古典時期,光線在基督教語境中具有和神同樣神圣、超然的神秘性質,而上帝賦予人類生命,由此光線被寄予了生命的隱喻意義,一如歌詞“And all you touch and all you see,is all your life will ever be”所討論生命議題。同樣的,彩虹在西方宗教語境中是上帝與人類立約“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滅絕”的記號,代表了憐憫與希望,似乎與歌詞中訴說平凡人生時的悲憫色彩共通。因此可以說,在視覺傳達的傳達環節,畫面中的符號受到受眾的主觀能動性調配產生了視覺隱喻:視覺符號與創作行為相關的事物、社會文化背景共同關聯,成了某一新釋義的喻體,該新釋義與原創作思想具有沿襲、轉變的關系,從而構成了信息傳達和釋義上的延異。
2.視覺設計環節中的隱喻
2013年,為慶祝《Dark side of the moon》40 周年紀念日,Storm Studios設計了原封面的不同變體,使原本極簡的畫面變異為不同的視覺風格。變體設計沿用了原本的三角棱鏡元素,并加入不同的視覺符號,例如金字塔、黑人的臉、女性的脊背、拿著匕首的人和低頭的人的剪影、眼球、花朵等等。這些新的視覺符號鏈接向新的文化語境(例如金字塔通常關聯著神秘未知與生命的永恒、女性與黑人關聯著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因此也與歌詞中的和平反戰思想、神秘的孤獨感與對生命的反思構成隱喻關系。
新的變體與原設計形成互文,原符號棱鏡的含義借由新加入的諸多視覺符號也有了新的解釋空間,這個過程是對視覺符號“意義解釋”的時間上的推遲與結果上(空間上)的差異。因此,新設計作為對于原設計的延展、闡釋和變體,是延異產生在視覺隱喻的應用中的體現。
而今天,大眾仍能在各大社交網站看到由粉絲的自由再創作構成的Pinkfloyd藝術專欄,作品不乏極具視覺張力的平面設計作品,例如ninthtaboo于2010年發表的《goodbye blue sky》中,作者運用黑色的不規則圖形與棱鏡標志構成的環狀旋渦煙隱喻戰爭中的天空,是其針對歌詞“Did you see the frightened ones? Did you hear the falling bombs”的視覺化表達,形成了對原專輯及封面釋義的延宕化和視覺呈現的間距化,同樣是延異理論的體現。
在希臘設計師Dimitris Arvanitis的2004年創作的海報作品《人權》中,畫面由上方細繩吊起的石頭和下方白凈直立的雞蛋構成。單獨的雞蛋或石頭似乎都與人類以及人類權利的議題相去甚遠,但通過題目“人權”的文本意義的介入,兩者之間通過畫面所形成的關系構成了對于主題的隱喻:粗糙的細繩相比起石塊的體量顯得強度堪憂,下方的雞蛋似乎岌岌可危,卻仍以一種非現實的方式直立著,與石頭形成對抗拉鋸的關系,似乎一如人類捍衛人權時,即便面臨巨大的阻礙和困難仍然頑強對抗的毅力。人權作為一個抽象、復雜的主題,通過視覺隱喻的手法被巧妙地轉化為了人們所熟知的客觀事物——雞蛋與巨石之間的關系,這種轉化是設計中延異的過程。閱讀者借由對“雞蛋”“石頭”所具備的物理性質、文化意涵的聯想,產生對于創作者立場的理解,也構成了上文討論的傳達接納層面的延異。在延異中,尖銳的社會議題借由視覺隱喻具有的模糊性得到了溫和的闡釋,關于主題的反思也在延異中得到了傳遞。
總結而言,在視覺傳達所包含的視覺設計與信息傳達的兩階段過程中,視覺設計通過視覺符號構建起完整的視覺敘事。這些視覺符號本身是創作者對于傳達概念主動營造的視覺隱喻,同時符號自身包含著各種各樣的“非原創性書寫”——正如羅蘭巴特在《作者之死》中提到的,“文本仿若一張寫滿引語的綿紙,從不計其數的文化中心汲取著成分”,視覺符號亦是如此,是對于社會文化歷史語境中的無數“上下文”的隱喻。因此,符號其中符號與傳達意圖之間、符號與符號之間通過視覺隱喻構成了意義的無限延異。
而在傳達的過程中,受眾的解讀將視覺符號主觀地假設為與主題事物相關的視覺隱喻,產生的理解極有可能與專輯設計時最初的構想具有差異。這種差異與信息從設計到接納(產生新釋義)中時間上的推延個和結果上的變化也是延異的體現。
結語
在數字圖像時代,圖像作為主要的傳播媒介,改變了信息傳播乃至人們生活生存的方式,展開了新的文化語境。視覺傳達設計通過視覺符號傳達信息,是對于視覺美感 與 “文學性”意義的整合。通過視覺隱喻,創作者初始的設計意圖在轉換為視覺符號并被受眾理解的過程中實現了延異,一如自然生命在遺傳、變異和進化中實現的延續。以作為喻體的視覺對象為中介,作品的意義在圖像符號的本意與隱喻意義之間滑動,引導受眾深入思考與探索,設計作品的美感和意義也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升華,其藝術生命也在延異中得到了永恒的延續。
視覺隱喻作為一種視覺設計構建的方法和策略,是視覺文化中西方思想的載體與表現形態之一。站在延異的理論視野下分析視覺隱喻這一重要的藝術手法,可以探索西方思想在當代視覺文化中的體現,同時也有助于藝術創作者從中反觀當下視覺文化,探究其組成和構建方式,并從對于創作原理的探究出發,拓寬視覺傳達設計的創作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