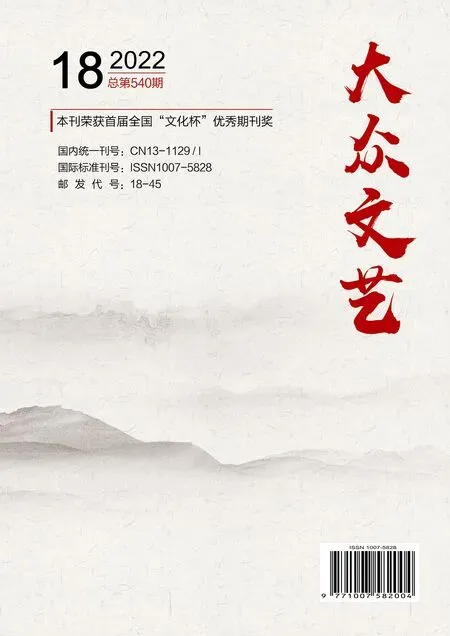靜止的困境:探析《電車狂》中的人物與主題書寫
楊一欣
(北京電影學院,北京 100091)
一、英雄與英雄的補集
《電車狂》作為黑澤明創作生涯中第一部彩色電影,似乎從某種角度看來,又是黑澤明最為灰暗的影片之一。追溯黑澤明的創作生涯,不難發現在他的作品中,始終存有的是一種對英雄人物,抑或是武士道精神的奇特情結——《七武士》是對英雄化身的認可與褒揚,而《亂》卻是對武士這一傳統英雄形象分裂異化的設問,甚至到《生之欲》或是晚年最后一部作品《裊裊夕陽情》,黑澤明雖然善于書寫悲劇性的英雄史詩,但他仍舊期望在尋常個體身上,找到對英雄形象的此心相似的注解。
在羅伯特·麥基的故事理論中,經典故事中的人物往往屬于“英雄”一類,而此類角色在整個故事中都要與一個來自外界的沖突做對抗,并在一個封閉時間與空間內不斷地追求自己的欲求。但善讀好萊塢典籍,并對好萊塢創作者影響頗深的黑澤明一反他對經典理論的熟稔,在《電車狂》這部影片中,他并沒有刻畫一個傳統的英雄人物形象,而是讓從未踏上“英雄之旅”的銀幕群像,共同成為一部完整電影長片的集體主人公。
在黑澤明的鏡頭中,小人物可能會有迷惘和軟肋,但黑澤明仍舊相信個體的力量可以改變和造就群體的福澤,即便英雄可能孑然一身,但他孤獨,卻決不會孤單。甚至如同《裊裊夕陽情》中,始終對人生問題追問“得未”“未得”的內田教授,也有一幫無比忠心愛戴的學生來為他做出熱切的回答。換言之,黑澤明始終相信的,是一個人或許可以感召另外的人,一個追尋目標的個體可以喚起另一股集體的決心。就像《生之欲》的結尾葬禮上,渡邊勘治的同事仍會表現自己的悔悟,以此反證黑澤明自己對“道不孤”的信心。
但《電車狂》不僅脫離了對單一主角的描摹,成了對在宛若垃圾場的鄉村生活群像的刻畫,而且事實上觀眾不難發現,《電車狂》中的每一個家庭,似乎并不交集它們的關系,互通它們的悲歡:從一開始的“電車白癡”小六,再到打散工的增田河口夫婦,以及患有痙攣和短腿的島悠吉、被姨夫性侵泄欲的勝子……《電車狂》在長達近兩個半小時的時長中,毫不疲倦地描畫了數對各不相同卻又各有“病癥”的家庭。與其說這是向心的敘事策略,倒不如說這更像借某一個共同的地點,將各具不同的家庭苦難史分別敘述而出。百年前托爾斯泰曾提筆感喟說:幸福的家庭總是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這點上,同樣具有人文氣質和人道主義精神的創作者黑澤明,秉持了同托爾斯泰一樣的想法。
如果說,以往的黑澤明是經典式的,莎翁式的,那么此次的銀幕刻畫,則不再讓他一貫具有史詩氣質的角色,走上那條慣常通往悲劇又帶有樂觀情結的英雄之旅。在羅伯特·麥基看來,故事中的人物總要以行動追尋自己的欲求,而在《電車狂》中,幾乎所有的人物都像是中國畫作散點透視中的一角,他們各自為營,也不期望并無法期望自己能夠踏上一條預設終點的旅途。
窮街陋巷,三教九流,比鄰而居……這些煙火味十足的底層群眾,在黑澤明的幕布中,不僅替代了那些舞刀弄劍的武士貴族,并且獨守自己的陋室一角,共同組成了一首有關底層家庭的詠嘆調。換言之,在這出兩個多小時時長的電影中,觀眾很難判斷誰才是真正的主角,從這個角度來說,黑澤明的呈現重心,已經從單一的英雄人物,轉移到了日本底層民眾——這些傳統英雄人物的補集之上。
二、現實困境的符號意指
在克里斯蒂安·麥茨看來:“電影的特性,并不在于它可能再現想象界,而是在于,它從一開始就是想象界,把它作為一個能指來構成的想象界”,從某個角度來說,電影的本質敘事,就是依靠符號的構建來展示作者的表達。但頗為微妙的是,黑澤明不僅在《電車狂》中設計了許多特別的符號,并且在此基礎上,他更依靠人物群像來構成了一個特殊的符號,從而完成對主題的指涉。
《電車狂》的開頭展示的是一個長相頗為古怪的男孩小六——他剃著近乎青皮的平頭,穿著一身服務員式的舊西裝,整個腦袋也大得出奇。而他的母親正近乎瘋狂地朝神龕大聲祈禱,在觀眾看來,似乎在這個家庭中,“有問題”的人是他的母親。但實際上,這是黑澤明在敘事上做的一個小技巧:緊接著小六不僅安慰母親,并稱自己“再不走就來不及上班了”。于是觀眾看著他戴上臟兮兮的手套,系好自己的皮帶,在好似虛幻又仿佛真實的電車聲中,拿起那些實際上并不存在的工具,開始他對想象中“電車”的駕駛。直到此時,墻上貼滿的蠟筆畫才以近景顯出它的內容:上面全都是對電車近乎瘋狂般的涂抹描繪。
以小六這對“電車”的癲狂患者作為開頭,事實上頗具意味:從符號角度來說,電車不僅是現代化的象征,也是日本“勞碌”大眾的符號意指。其“dodesukaden”的聲響,不僅是小六古怪的呢喃,也是這一工具宣告發動的聲響;而讓正處青少年的小六作為這一“電車狂”的具體對象,也使得這種窮苦不幸有了更為深刻悲哀的底色。當小六穿戴整齊,走到屋外用規規矩矩的動作完成他以為的電車運行操作(如打開車門,擦拭車窗,嘀咕保養人員不賣力),然后駕駛著并不存在的電車,橫沖直撞地“行駛”在垃圾堆似的鄉村中時,他不僅具有遭受遺棄,承受貧苦的不幸少年的縮影,而且更具備“電車”這一他想到癡狂的對象所散發的涵指意味。在對小六的刻畫中,黑澤明的鏡頭不僅鐘于停留,剪輯不多,而且在給予其全景從下搖上的客觀鏡頭后,黑澤明對應地給了一個小六視點的搖晃主觀鏡頭。可以說,黑澤明并不帶有消費的心態,而更近于以一種體恤的方式,去直面這種不幸的荒誕性。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用小六作為《電車狂》這些不幸縮影的提領開頭,在本質上具有一種更為純粹的意蘊:他對電車的想象駕駛,實際上成了一種特殊的儀式——對現代工具的渴望和追求,卻成為如同癲狂的病癥,而這些不幸的結果,最終投射在下一代即青年兒童身上。
另外一處頗值一提的,是接在小六出場后患有面部痙攣和短腿的島悠吉。他穿戴齊整,衣著考究,正頗為禮貌地沖聚在一塊兒洗衣的婦女們打招呼,結果過不多時便突然面部痙攣起來。洗衣服的婦女們在本片中極為巧妙地充當了許多“旁觀者”的角色:在一方面,她們起到了介紹的作用,譬如看似在談論有關如島悠吉、增田河口夫婦等人的具體信息,實際上在為觀眾介紹人物;另一方面,她們也通過各具性格的對話,坦陳出這些女性對某一個家庭的議論,而她們的態度就顯露于這些七嘴八舌的議論之中。頗為有趣的是,這些洗衣服的婦女們所聚集的地方,正是這堆破舊屋子前空地的中心處,她們圍繞所接水的源頭,也恰好形成了一個向心的中心點,而她們聚集的談論,事實上也成為四散輻射的輿論,成了電影借她們之口所塑造的“旁觀者見”。
這些形態各異的人物角色,或訴說或展現著自己的故事,而他們的生存狀態,以及自身的生活困境,共同構成了《電車狂》的言說本身。甚至,為了讓他們在鏡頭前呈現得更為自然,黑澤明放棄一貫的精密排練,而選擇更多地讓演員在開拍時即興表演。而正是這種與黑澤明以往動態風格不太一致的“靜態”呈現,使那形態各異但又各有苦衷的人物生活,成了整部電影最重要的影像能指。
實際上,黑澤明一直是一個慣用電影符號來敘事的大師。譬如在他的早期作品《野良犬》中,他讓一個年輕的警察在一個熱天午后,不小心丟失了隨身的手槍,而全片幾乎就是在講述一個急躁的青年警察尋找配槍的故事。從符號的文本去分析,尋槍不僅是尋找一個丟失的物件,同樣也是以象形的相似性去指代一個男性的尊嚴,并用文化意涵,去用丟槍來指代日本戰后政府對威權與社會公信力的遺失。而在《電車狂》中,黑澤明自然對這種創作的手法舉重若輕,但他更刪繁就簡,令一個角色為另一個角色鋪墊,并用這些角色所組成的組群,共同去構建出了一幅有關日本當代底層社會的畫卷。
那一扇扇時時緊閉又不知何時開啟的家門,那一張張不知從何而來也不知所往的麻木面孔,組成了一個既指代日本,也指代全人類的符號——黑澤明用它來反詰世界,并同所有偉大的文藝作品一樣,去對遭逢苦難的人類,投去關切的目光。從這點來說,《電車狂》不僅由一個個符號構成,它自身或許也成了某個深刻的符號。
三、悲劇中人物的自洽
善于描繪悲劇的黑澤明,無論是在《亂》還是在《七武士》中,都喜好將愛恨情仇講述得跌宕和深邃,而他也善于將有價值之物高高捧起,再毫不留情地打得稀碎。但在《電車狂》中,黑澤明似乎對悲劇自身的否定之否定,悲劇必備的調和統一,也不再抱有熱情——他將鏡頭對準窮街陋巷的每一處,而這些角落的角落,不僅不具有生機上揚的可能,連消亡和犧牲都是默不作聲的。
從另外一個頗具悲哀底色的人物——被姨父性侵的勝子身上,我們似乎更進一步,能看到黑澤明對“悲劇”演繹的反思:
在影片大致第20分鐘處,我們看到黑澤明給了勝子的家庭一個固定的長鏡頭:勝子坐在畫面前景的右下角,一聲不吭地干著女紅方面的活兒,而她的姨父坐在畫面后景的右上角,背對著觀眾,正一邊大口喝著酒一邊大肆談論著不著邊際的話。從他的話中,觀眾可以了解到,勝子不僅寄人籬下,而且親生的阿姨住院了,現在需要干大量的活計來補貼家用。緊接著是送酒人來了,觀眾很快發現,送酒的男青年同勝子之間似乎有曖昧的情愫。但即使送酒青年憂心地說“你又瘦了”,勝子仍舊是一幅迷離無力的神情,而這種神情一直貫穿著影片中勝子出場的每一個鏡頭。這也暗示著勝子早已被勞力的工作、不幸的家庭關系壓抑得幾近麻木。甚至換言之,這一個家庭的主角自然是勝子,而她所展現的一個特殊主題,或許便是這種異化家庭關系中的“麻木”狀態——面對生活的難題,只能逆來順受,用沉默捱下所有的苦難。于是,在影片的后半段,姨父真的如禽獸一般侵犯了勝子,后者對此也幾乎不做任何神色上的改寫,而對于送酒青年的關切,她也顯得無動于衷。
對于《電車狂》的相應困境,黑澤明并沒有像以往他對“英雄”或是“解救者”的特殊情結一樣,設計一個救人于苦海的角色,甚至就連遭遇困境的角色自己,陷于矛盾中也便溺于矛盾的僵局中,他們對生活并沒有什么具體的盼愿,也對自救提不起興趣,而所謂的希望和生機,對他們而言也是一個從未想到的東西。或者,在某一個方面來說,此時作為導演的黑澤明考察的并不是宏觀的“史詩命題”,而是聚于微觀的“家庭議題”,而對于后者,他顯然并不抱有那種洋溢于《生之欲》或《裊裊夕陽情》中“道不孤”的信心和希望。如果說《電車狂》中如勝子這樣的人生,從一開始就是一潭死水的話,那么這些人物及其故事的各自終點,似乎也只是如水消失在水中。
對于這一點,在《電車狂》中對島悠吉的描繪頗可佐證:在影片后半段,幾個同事一起來到島悠吉的家中,但島悠吉的妻子卻頗不耐煩,將面前的幾人視為空氣,不做招待便自顧自地出門洗澡。同事們看不下去,在島悠吉面前直接吐出了對其妻子的不滿,并一邊為島悠吉說話,一邊為其感到不值。沒想到,島悠吉大為光火,直接摁倒了同事,稱對方并不懂妻子在從前如何和他一起忍耐貧窮,一邊為他付出一邊為他犧牲。從這個頗為微妙的段落看來,黑澤明設置這些并不太多“糾纏”的家庭苦難,事實上或許也已經展現了他的態度——就如同上文提道的托爾斯泰的那句話:“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而這些不幸事實上是由不同的家庭條件,生活環境,個體情感交織而成,而這種不幸也是被當事人消化和自洽的。或許,在黑澤明看來,在具體的家庭困境中,旁人很難去充當一個粗泛的解救者,而也很難真正介入到另一個個體具體而微的生活之中。而這些從未踏上過英雄之旅,也不曾有過具體欲求與終點的故事人物,會如同現實中的每一個底層居民一樣,不僅同上路追尋無緣,而是漸漸在生活中溺水消失,并始終與故事宏觀敘事中的一波三折,三幕推演沒有任何的關聯。
也就如在影片之中作為穿插段落,也意在表現黑澤明自身態度的段落戲里,始終有一個陪著小乞丐侃侃而談日本建筑的老乞丐。他們兩人雖然總在夢中建造屬于他們的精舍,但實際上卻只能臥睡在廢棄的汽車之中。老乞丐對于“理想房子”的向往,也同《電車狂》中無處不在的破舊、荒蕪、廢棄和失落成為反差極強的對比。而到了結尾,當小乞丐中毒近死,老乞丐悲哀到近乎瘋狂,卻始終無法時,我們才發現精神的“富裕”,事實上仍舊解決不了現實的悲哀。或許,在這一點上,才是有關“悲哀”最為悲哀的答案。
黑澤明對此最消沉的態度或許頗能展現于老乞丐的境遇上:旁人很難介入你的生活,他最多陪你一起挖墳。但事實上,每一個人自己的墳墓,早就被自己挖好了。
結語
作為黑澤明晚年無論在票房與口碑上,都不算太成功的作品,《電車狂》實際上帶有黑澤明自身的反思和感喟。無論是從傳統的人物構建方面,還是從符號呈現,及主題表達上來說,《電車狂》都算是黑澤明對悲劇故事的某種頗為悲觀的自反。
作為一個偉大的導演,黑澤明似乎頗為敏銳地察覺到:悲劇并非一定在英雄人物身上上演,它也出沒在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但面對悲劇,真正現實的做法或許只能是讓個體去消化和自洽。從某種意義來說,這也對現當代導演與劇作創作跳脫傳統模式,更緊貼現實基底,在人物塑造與主題呈現上,提供了他自己獨特的方法論。
①劉迎新,曲涌旭.日本民族性對日本電影的影響[J].文藝爭鳴,2020.(02):190-193.
②[法]克里斯蒂安·麥茨《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與電影》,王志敏譯,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頁.
③唐納德·里奇[M].黑澤明的電影:海南出版社,2010:259-273.
④吳文忠,凃力.淺談黑格爾的悲劇理論[J].人民論壇,2011.02.001:218-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