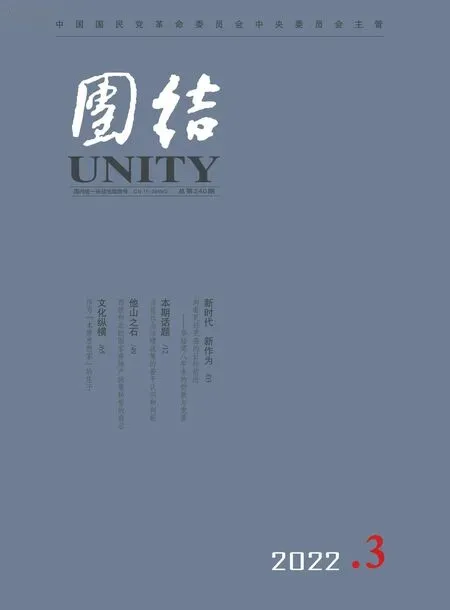互聯網時代群眾工作機制的效能提升
◎余 茜
在現代化過程中, 政治取向發生了“從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轉變”。 隨著生活政治的到來, 解放政治的問題重要性沒有削弱, 但信息化引起的整個社會結構、 生活結構發生的 “解傳統化” 變化的 “新條件”, 已改變了解決問題的標準, 對社會問題的考察和解決應遵循生活本身的價值, 以“生活決定的政治” 作為解決問題的標準。 “國計民生, 罔存念慮”, 做 “人的工作” 在互聯網時代愈發凸顯了其獨特價值和意義。 眾所周知, 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就是緊密圍繞著“人” 的群眾工作, 將“一切為了群眾, 一切依靠群眾, 從群眾中來, 到群眾中去” 的群眾路線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根本生命線。互聯網時代, 如何既傳承群眾路線的精神內核, 又能主動適應互聯網時代的政治生態特征, 創造性轉化群眾路線、 高效做好群眾工作? 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具有深刻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本研究擬從機制建設的角度探討怎樣創新黨的群眾工作。
一、 互聯網時代群眾工作機制面臨的挑戰
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第49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 顯示,截至2021 年12 月, 我國網民規模達10.32 億, 互聯網普及率達73.0%。 且現有行政村已全面實現“村村通寬帶”, 貧困地區通信難等問題得到歷史性解決。互聯網等信息技術為新時代群眾工作機制的完善提供了良好契機和條件, 但互聯網信息技術觸發的政治、 經濟和社會生態的復雜性、 多變性和風險疊加性等, 也為高效能做好群眾工作帶來了一定的挑戰。 挑戰既包括 “技術利維坦”降臨, 技術反噬引發 “人的政治” 頹敗產生的新問題, 也包括從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轉變過程中, 新老問題交織疊加帶來的沖擊和挑戰。 概括而言, 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 群眾工作的“代表性難題”。 一是群眾意見的代表性。 盡管互聯網等信息技術有助于民意的表達與擴散, 但眾說紛紜、 眾聲喧嘩之后仍有一系列的問題: 如多元、 分化的意見如何集中? 乃至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識? 在輿論場中, 競爭性的共識能否受到政策制定者的關注? 傾聽之后是否會有所回應? 即便有意見層面的回饋, 后續是否會采取針對性的行動舉措? 行動是否有效以及效果的持續性等等問題。 “數字鴻溝” “數字離散” 等現象恰恰揭示了, 信息技術的運用并未盡如人意地解決民意的代表性問題。 不少實證研究表明: 互聯網信息技術對一些社會群體進行了賦權, 而對另一些社會群體則沒有。 仍有部分的群眾意見被邊緣化或被淹沒, 也無法用他們自己的語言來發出他們的關切和需求。 輿論場中“沉默的螺旋” 并未因技術的進步而停止轉動, 甚至因為算法推薦對“去中心化” 傳播模式的打破, 通過影響信息呈現、 搜索排序、 信息熱度和傳播效果等, 讓信息傳播再次服務于少部分的精英人士, 普通公眾在自覺不自覺間將自己置于被動接收端, 逐漸放棄表達權。 而且, 普通公眾也會將自身桎梏于“信息繭房” 中, 拒絕與其他群體進行對話協商和理性溝通, 用戶的個人偏好和社群的同質信息, 往往會加劇社會群體的撕裂, 阻礙了理性公共輿論的形成, 就更談不上將共識上升為政策議題了。 二是群眾利益的代表性。 “人人有需求, 各個有要求”, 技術應用的場景化與普及化讓社會價值觀多元化、 利益訴求顯性化和碎片化的趨勢更加明顯。 在此種情況下, 在做群眾工作時, 如何識別并代表群眾的合法利益, 兼顧具體利益, 就成為十分重要的問題。 尤其是在新經濟領域, 面對平臺經濟的擴張, 面對被“困在系統里、 綁在算法上、 捆在抽成里、 游離在社保外” 的普通群眾, 又該如何去維護其權益?
第二, 群眾工作的“有效參與難題”。 互聯網時代的公眾政治參與盡管在渠道上有所擴充, 但在參與的深度和有效性方面仍面臨新的阻礙。 一方面, 公眾進入一個數字化公共領域的門檻很高, 如有效參與公共討論和辯論所需的溝通技能和批判性思維。 然而, 信息的娛樂化和商業化導致公共領域很難建構, 甚至淪為海市蜃樓般的幻影, 公眾也會在“廣場式狂歡” 的娛樂體驗中放棄對于價值理性的思考和公共事件的參與。 另一方面, 擁有社會資本是公眾政治參與的重要基礎, 而數字化生存帶來了民眾社會資本的流失。 社會資本產生了參與式平等, 而密集地使用信息技術可能會減少這種社會資本, 從而使信息技術的使用抵消了在參與式平等中獲得的任何東西。 “信息技術似乎在破壞傳統的、面對面的人類互動”, 數字化的人類互動幾乎無法引發民主商談。 既源于“情感傳播” 消解了輿論的公共理性, 也與互聯網時代“群以類聚” 的景觀所引發的“網絡巴爾干化” 問題有關。 有研究指出,互聯網將網民轉化成了能夠被情感傳播所動員、 聯系或分化的“情感公眾”, 他們雖然更關注公共事件, 但也極易受到情緒的傳染, 讓公共輿論變得非理性化、 割裂化。
第三, 群眾工作的 “高效落地難題”。 技術治理帶來了新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 與傳統官僚主義一樣, 電子化的官僚主義其本質仍然是脫離實際、 脫離群眾、 高高在上的工作方式和行事作風。 盡管在 “加強信息化管理” 的潮流趨勢下, 通過電子政務、 網上辦理等能更便捷、 高效率地做好群眾工作, 顯得 “名正言順、 義正言辭”。 但處處依賴技術加持、 規章條約設定, 而缺乏面對面解釋、 溝通的工作方式, 也容易滋生“電子衙門” 的弊端。 形式眾多的電子官僚主義,催生了花樣繁多的電子形式主義。 盡管工作中處處要設立 “臺賬”, 運用信息技術等進行 “痕跡管理”, 但 “工作留痕” 卻未必能在群眾內心“留情”, 未必能收獲群眾的高滿意度。 “好的政治沒有捷徑”, 互聯網時代群眾對于黨和政府的信任已經超越簡單的意識形態而變得更加理性、務實, 對于黨和政府信任的判斷也不僅僅依據“是否在做正確的事”, 而更為關注 “是否正確地做事” “事情是否做到位” “工作是否落實落地” 等效果、 效益、 效能層面的問題。
二、 高效能群眾工作機制的創新路徑
無論是線下密切聯系群眾, 還是走網絡群眾路線, 都只是一個工作方式問題, 最根本的,是要高效地解決群眾面臨的 “急難愁盼” 問題。為此, 原則層面一是要把握好互聯網信息技術及時性、 交互性的核心技術特征和作為權力資源的政治特征; 二是要把握 “政治信任” 作為黨政部門與群眾互動關系建構的本質。 在交互建構的過程中, 以更加復合、 開放、 動態的視角探索群眾工作機制的多維度創新, 具體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第一, 民意吸納與整合機制。 在很大程度上, 治理就是一個信息問題。 信息是治理的關鍵所在, 是開展群眾工作的前提和基礎。 無論是小數據、 大數據, 終歸是要掌握信息、 探索群眾工作信息流轉規律。 為此, 要繼續推進社情民意大數據平臺的建設, 建構民意吸納和整合機制, 通過對社情民意信息的及時把握, 從多元領域、 立體層面動態、 精準地了解群眾需求的細微變化。如有追蹤調研發現: 在脫貧攻堅完成后, 貧困群體的需求也開始逐步升級和轉移, 由滿足當下基本生活轉向對未來持續穩定收入來源的需求; 由農村蓋房轉向城市買房的需求; 由小病保護轉向大病保障的需求; 由獲得教育機會到對于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 由物質獲取轉向心理和精神層面支持的需求等。
第二, 基于群眾類型化區分的協同機制和多元互動溝通機制。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 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 當前中國的情境中, 群眾工作的主體還是黨政部門, 主要依靠“黨領導、 政府主導” 的群眾工作格局, 在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下, 僅僅依靠既有的黨政力量是不夠的, 要協同多方力量, 才能更好地完善基于群眾類型化區分的多元互動溝通機制。 如工青婦等群團組織, 作為黨聯系各社會群體的橋梁和紐帶,其政治性和群眾性決定了其組織的“軟權力特征”,這樣就能克服行政理性的弊端, 將行政理性同群眾路線結合起來, 在做“人的工作” 時, 更好地實現情感治理、 柔性治理, 有助于在技術治理盛行的趨勢下, 實現“人的政治” 的回歸。
第三, 協商參與機制和“規范—利益” 博弈均衡機制。 從之前的共建共享, 到共建共治共享, 對共治的強調, 突出了一個“參與權” 的問題。 實踐證明, 互聯網時代, 隨著信息獲取成本的降低、 群眾素質的提高, 不同領域群眾對協商共治、 參與共決的需求都在逐步提升。 研究表明: 參與的過程本身也能創造幸福感、 增進政治溝通和對黨和政府的認同感、 信任感。 因而, 高效能群眾工作的實現,要更多地從“為群眾” 轉向“依靠群眾”。 也就是說, 群眾不僅僅是治理的對象, 群眾工作也不僅僅是靜止的點, 更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要讓群眾更多地參與國家和社會治理的全過程, 通過民智匯聚機制來充分激活社會活力, 以完善群眾的協商參與來促進“規范—利益” 雙重博弈均衡機制的建立, 始終站在公開公平公正的立場實現群眾矛盾沖突的調解和群眾合法權益的維護。
第四, 全過程的精細化服務機制。 要促進與群眾相關的法規、 政策文件真正發揮預期效應, 就必須克服一些理念“懸浮” 難落地、 工作機制“低效能運轉” 的瓶頸。 當前不少地方黨政部門群眾工作的創新, 都涉及到優化群眾辦事流程, 做實、 做細服務工作的探索。 如浙江省的 “最多跑一次” 改革, 將與群眾密切相關的政務服務“最后一公里”給打通了, 做到了辦實事、 高效便捷為群眾服務;“無證明城市” 的探索, 確實體現了精準地解決群眾“急難愁盼” 問題; 又如北京市的“接訴即辦”改革, 實現了對民意訴求從“傾聽回應” 到“反饋行動” 的延伸。 這些從辦事全流程、 服務全過程的角度來“捋順、 優化、 細化” 的精準化服務創新,有助于將群眾路線的制度優勢, 持續不斷轉化為高效能的群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