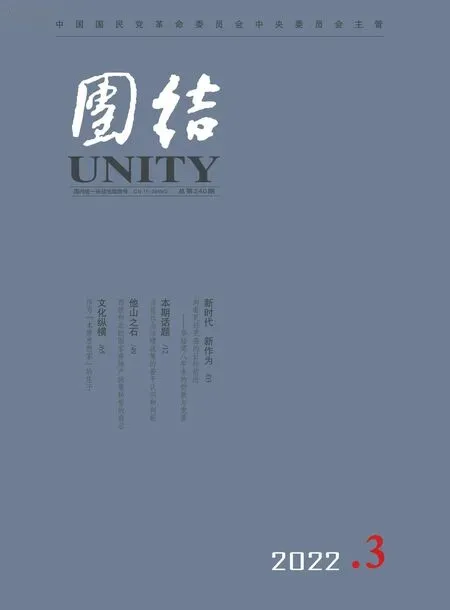修改《企業破產法》,賦予檢察機關破產程序申請權
◎湯維建
破產是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重要機制保障, 破產機制的功效發揮取決于破產程序啟動機制的順暢。 全國法院在2019 年共審結了破產案件的數量為4626 件, 2020 年該數量增至10132 件。 2021 年該數量又上升至1.3 萬件。 盡管數量逐年增長, 但與每年數以千萬件計的民商事案件相比仍極其微小, 與我國經濟規模和市場化程度也并不匹配。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國破產立法在破產程序的啟動機制上實行絕對的當事人申請主義, 脫離了現實情況, 忽視了“破產難” 的困境, 忽略了破產程序啟動機制上的國家公權力的存在和作用空間。 為克服此一弊端, 我國有必要修改 《企業破產法》, 在繼續堅持當事人申請主義的基本原則的同時, 加入國家公權力啟動元素, 賦予檢察機關以啟動破產程序的申請權。
一、 賦予檢察機關破產程序申請權的理論根據
1.市場出清理論。 市場出清 (Market clearing) 是指商品價格具有充分的靈活性 (flexible), 能使需求和供給迅速達到均衡的市場。 在出清的市場上,沒有定量配給、 資源閑置, 也沒有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 但我國目前仍存在大量應當出清的 “僵尸企業” 躺平在市場主體的目錄簿上, 未能及時排解,造成擠占市場資源、 損害營商環境的不良后果。 造成此一狀況的原因之一就是優勝劣汰的破產法機制未能有效建立起來。 賦予檢察機關以破產程序的申請權有助于通過破產程序及時有效地清理 “僵尸企業”, 促使市場經濟的新舊動能轉換, 助推國家對經濟發展的宏觀調控, 減少乃至避免交易陷阱侵害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保障市場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僅如此, 通過破產程序的強制性啟動, 也有助于對 “病患企業” 進行分類甄別、 精準救治、及時清理, 梳理出盤錯結節的社會資源, 盡快釋放經濟活力, 使破產制度的價值功能得到最充分、 最有效的發揮。
2.破產申請責任理論。 賦予債務人以破產申請權是破產法發展史上的一大進步, 標志著破產保護本位開始由債權人絕對本位主義向兼顧債務人利益本位的方向轉變和傾斜。 然而與此同時也產生了一個問題, 就是最了解債務狀態和財產狀況的債務人對其所陷入的債務清償危機隱而不發, 繼續在市場上與他人交易并持續消耗其財產, 其結果在客觀上便是降低了債權人的清償比例, 損害了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為避免此一弊端的發生, 有的國家規定了破產預警制度, 在債務人陷入債務危機受到破產預警時, 它便具有了申請破產的法律責任和義務,否則該債務人就會被認為是不誠信的, 將承擔相應的法律制裁后果。 例如, 根據德國法的規定, 如果企業的經理或其他責任人沒有履行及時破產申請義務的, 且新債權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與企業達成了交易, 那么債權人依據 《德國民法典》 第823 條第2 款以及 《有限責任公司法》 第64 條第1 款之規定, 可以向負有破產申請義務的責任人主張賠償損失。
我國 《企業破產法》 第7 條規定: “債務人有本法第二條規定的情形,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 和解或者破產清算申請。 債務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 債權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對債務人進行重整或者破產清算的申請。 企業法人已解散但未清算或者未清算完畢, 資產不足以清償債務的, 依法負有清算責任的人應當向人民法院申請破產清算。” 據此規定, 對企業法人負有清算責任的人具有向法院申請破產的法律責任, 也間接地規定了債務人在一定情形下的破產申請責任制度。 《公司法》 第188 條第1 款做出了類似的規定: “清算組在清理公司財產、 編制資產負債表和財產清單后, 發現公司財產不足清償債務的, 應當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破產。” 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司法文件進一步明確和發揮了破產申請責任制度。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 《關于審理公司強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 第32 條規定: “公司強制清算中, 清算組在清理公司財產、 編制資產負債表和財產清單時, 發現公司財產不足清償債務的,除依據公司法司法解釋二第十七條的規定, 通過與債權人協商制作有關債務清償方案并清償債務的外, 應依據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八條和企業破產法第七條第3 款的規定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破產。” 再如, 《公司法司法解釋 (二)》第18 條規定: “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 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東未在法定期限內成立清算組開始清算, 導致公司財產貶值、 流失、毀損或者滅失, 債權人主張其在造成損失范圍內對公司債務承擔賠償責任的, 人民法院應依法予以支持。 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 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東因怠于履行義務, 導致公司主要財產、 賬冊、 重要文件等滅失, 無法進行清算, 債權人主張其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的, 人民法院應依法予以支持。 上述情形系實際控制人原因造成, 債權人主張實際控制人對公司債務承擔相應民事責任的, 人民法院應依法予以支持。”
不僅如此, 我國有的地方性破產法規中也有破產申請責任制度的某種探索。 例如, 2021年11 月, 上海市人大常委會通過了 《上海市浦東新區完善市場化法治化企業破產制度若干規定》 第4 條規定: “企業董事、 高級管理人員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本企業出現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 第二條情形的, 應當及時采取啟動重組、 向債權人披露經營信息、 提請企業申請預重整或者破產重整、 和解、 清算等合理措施, 避免企業狀況繼續惡化和財產減損。 企業董事、 高級管理人員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違反前款規定造成企業財產損失, 管理人或者債權人主張其在造成損失范圍內向企業承擔賠償責任的, 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
然而, 我國破產法并沒有直接規定債務人的破產申請責任制度, 司法實踐中對清算責任人的破產申請責任制度的落實也基本上形同虛設, 這樣就導致了普遍出現的 “破產申請難” 的制度困境, 大量的事實上的破產案件無法進入破產程序的司法門檻。 為破除此一困境, 破產立法應當導入破產程序啟動的公權力因素, 賦予檢察機關以破產申請權就是彌補我國破產申請責任制度不足的一個理想選擇。
3.國家干預理論。 破產法教科書告訴我們,破產程序的啟動自古及今始終并存著兩大原則:一是當事人自治原則, 另一是官治主義原則。 官治主義原則還包括法院主動依職權啟動破產程序的立法例, 但此后鑒于司法程序 “控審分離” 的要求, 法院便從破產程序的啟動者行列退了出去, 而將官治主義的破產啟動權讓位給了其他國家主體。 從比較法視野看, 國家機構啟動破產程序的立法例主要有兩種: 一是專門設置官方申請人制度。 官方申請人是行政機關, 由行政機關申請啟動破產程序。 英國便規定: 如果破產案件中涉及破產犯罪, 則官方申請人有權提起破產申請。 另一是將破產申請的國家職權賦予給檢察機關行使, 如荷蘭法律規定檢察機關可以對與公共利益有關的破產案件提出破產申請。 意大利《1942 年破產法》 第6 條規定檢察官有權申請債務人破產。 法國也有公訴機關可以提起破產申請的規定。
筆者認為, 鑒于破產案件的公益性較強、 社會影響力較大、 往往關系到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政策性因素、 同時與社會穩定與和諧發展之大局密切關聯, 國家干預主義在破產程序中應有一定的適用空間。 《民法典》 確立的法律規則中透露出一個鮮明的立場: 當國家必須出場的時候, 國家不能缺位。 因此, 基于國家干預理論, 從法律上賦予檢察機關提起破產申請的權利是解決破產程序啟動難的重要途徑。
4.法律監督理論。 我國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權乃由 《憲法》 這一根本大法所授予, 《憲法》第134 條規定: “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 第136 條規定: “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 不受行政機關、 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2012 年修訂通過的 《民事訴訟法》 的將檢察機關對民事訴訟的法律監督權擴展到了包括破產程序在內的全部領域。《民事訴訟法》 新增第242 條規定: “人民檢察院有權對民事執行活動實行法律監督”, 作為概括執行的破產程序自然也處在該條款的規范輻射范圍之內。 《民事訴訟法》 第15 條規定:“機關、 社會團體、 企業事業單位對損害國家、集體或者個人民事權益的行為, 可以支持受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 同法第58條第3 款規定: “前款規定的機關或者組織提起訴訟的, 人民檢察院可以支持起訴。” 就立法規定而言, 檢察機關對破產程序適用全面監督原則, 包括事前監督、 事中監督和事后監督。目前從法律的明確依據來看, 檢察機關對破產程序實施事前監督僅限定于支持當事人提出破產申請, 還不包括直接提出破產申請的權力。這是從解釋論角度得出的結論。
然而, 從立法論上說, 檢察機關是否應當享有向法院提出破產申請的權力呢? 答案應當是肯定的。 因為, 從檢察監督的制度體系而言,如果缺乏檢察機關對破產程序的事前監督, 則檢察機關對破產程序的事中監督以及事后監督有時會被司法實踐所架空, 破產程序既然無法啟動, 則所謂事中監督和事后監督便無從說起。凡是涉及到國家利益、 社會公共利益民事活動,檢察官參與其中就可以充分發揮維護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作用。 因此, 為了使檢察機關對破產程序的事中監督和事后監督富有實效真正落地, 立法上賦予檢察機關提出破產申請的權力顯有必要。
二、 檢察機關啟動破產程序的具體規則構想
1.啟動監督模式。 檢察機關對破產程序實施法律監督可以劃分為啟動監督模式、 法定監督模式、 職權監督模式、 申請監督模式以及邀請監督模式等五種形式。 啟動監督模式是指檢察機關對破產程序的法律監督是通過向法院提出破產申請從而啟動破產程序的方式來進行所形成的監督模式, 其具有自始性、 全程性、 完整性、內在性的特征。 在啟動監督模式中, 檢察機關從破產程序的一開始就予以介入, 破產程序的啟動也是取決于檢察機關的破產申請, 在破產程序的全過程中, 檢察機關對破產程序實行全方位、 不間斷、 連續性的法律監督。 由于檢察機關在啟動監督模式中的全程參與性, 同時又由于破產程序的啟動本身也是源于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所致, 因而檢察機關在破產程序中具有破產程序主體和破產程序監督者雙重身份。檢察機關在對破產程序行使法律監督權的同時,也需要對破產程序中應當由申請人負擔的推進程序發展的事項承擔法律上的責任, 如要提供證據證明債務人達到了破產界限、 具備了破產原因等。
2.檢察機關提出破產申請的前置程序。 前述已經論證了立法授予檢察機關提出破產申請權力之必要性及正當性。 但立法上授權檢察機關破產申請提起權并不意味著檢察機關行使該項權力就可以不受限制而任意行使。 檢察機關提起破產申請應當在兩個方面受到限制: 一是從前置程序上看, 檢察機關只有在破產當事人以及諸如清算組之類的適格當事人不提起破產申請之時方能夠作為最終保障力量行使破產申請權。 也即, 檢察機關提起破產申請要遵守“破產申請受阻” 原則, 只有在破產申請人缺位的情況下才能由檢察機關行使公權力啟動破產程序。 這不僅是尊重破產程序私權自治原則的需要, 也是檢察監督謙抑性原則的具體表征之一。 因此, 檢察機關提出破產申請應當仿照檢察公益訴訟制度的模式, 設立一個前置程序,由檢察機關發出公告或通知, 催促相關利害關系人或相關組織、 機構提出破產申請。 經過前置程序, 如果沒有其他適格程序主體提出破產申請, 則檢察機關即可提出破產申請; 反之,檢察機關則不宜提出破產申請, 但如果檢察機關認為確有必要, 也可以加入破產申請, 成為破產申請的支持者和破產程序的協助者。
3.檢察機關提出破產申請的案件范圍。 從案件范圍上看, 檢察機關提起破產申請應當符合一定條件, 恪守有限性原則。 檢察機關之所以被賦予提出破產申請權, 其目的不在于取代破產當事人啟動破產程序, 而在于維護破產案件所涉及的國家利益和社會公益。 誠然, 凡破產案件, 通常會涉及或多或少的公益性因素,但即便如此, 檢察機關對所面對的破產案件也要進行篩選和甄別, 不得來者不拒、 不附條件地提出破產申請, 否則即有損及私權自治性、濫用檢察監督權之虞。
筆者認為, 檢察機關對以下類型的破產案件, 在無人提出破產申請的前提下, 可以依職權向法院提出申請從而啟動破產程序: 其一,混雜刑事犯罪的破產案件。 如涉嫌構成破產詐欺罪、 虛假訴訟罪等, 檢察機關可以提出破產申請。 因為此類破產犯罪的案件通常涉及刑民交叉復合司法程序的運用, 檢察機關依職權提出破產申請有助于將相關聯的法律案件進行合并處理, 從而消弭司法沖突以及程序緊張, 最終達到以 “刑” 促 “破”、 以 “破” 補 “刑” 的效果。 其二, 因人數眾多、 涉及面廣等原因容易導致群體性事件的破產案件。 例如上市公司破產案件即屬此類范疇。 其三, 有關國計民生、關乎社會和諧穩定的重大破產案件。 如國企破產、 金融機構破產等案件即可劃為此一范圍。 其四, 政策性破產案件。 政策性破產案件是基于國家經濟政策調整等方面的原因所導致的破產, 對該類破產案件的處置往往涉及較強的政策問題,由檢察機關出面提出破產申請也是理之所歸。其五, 涉及職工安置難、 企業辦社會的功能疏解難等因素的破產案件。 此類破產案件通常涉及需要政府協助解決的問題較多, 檢察機關提起破產申請有利于破產善后問題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