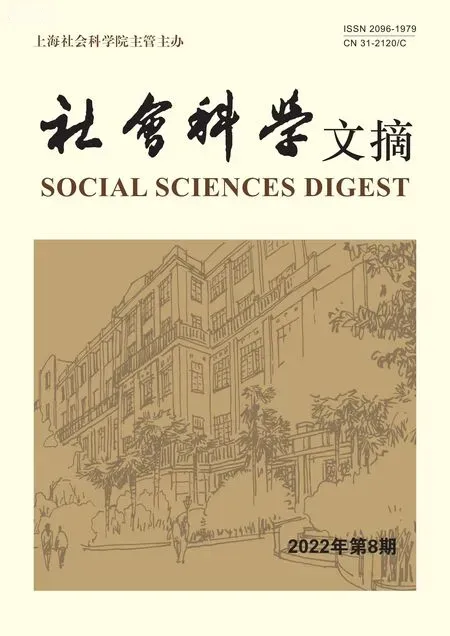重識歷史政治學的比較方法與因果邏輯
文/釋啟鵬
歷史政治學為宏觀歷史想象力的復興提供了有力支撐,并在短短數年的時間里形成了可觀的學術影響。但立足當下學術生態,從經濟學蔓延到政治學的“因果推論革命”極有可能窄化人們對“科學”“因果”等核心范疇的理解,進而將以反事實邏輯為核心的實驗法視作實現科學因果推論的唯一途徑。為此筆者深感當代政治學研究方法在“豐裕的貧困”中展現出的“自我狹隘化”傾向,許多有意義的議題會因不符合“科學規范”而遭致拋棄。為避免歷史政治學甫一問世便陷入盲目的科學主義崇拜,本文意圖通過討論具體研究方法的“上游知識”,為這一新興流派提供更為堅實的方法論基礎。
歷史分析中的科學主義偏執
歷史學與社會科學對話的一大障礙就是,人們根深蒂固地認為自然科學模式是社會生活研究的康莊大道。由于對“科學”的片面理解,當代主流社會科學依舊將尋求能夠媲美自然科學的分析模式視作其最終歸宿。在本體層面,他們堅持牛頓世界觀,認為世界是客觀且遵循著某種特定規律運行;在認識論層面,他們將“科學”視作探索客觀規律。以此哲學基礎形成的實證主義主張因果解釋是將社會生活的一般規律與特定案例相結合的邏輯結果,研究者可以在社會世界中尋找出像自然世界那般存在的普遍規律進而實現對結果的預測。類似地,對確定性的追尋也貫穿了從蘇格拉底到黑格爾以來的西方哲學發展。
這種科學觀所形成的因果觀將實驗法視作實現因果推論的最佳選擇,該方法可以通過人為操縱和干預關鍵性解釋變量來確立因果關系并排除虛假關系。在宏觀政治社會分析中,“控制性比較”通過對那些非解釋性因素進行控制以接近“準實驗”的狀態。尤其是近些年興起的“歷史的自然實驗”更是為歷史政治學提供了有益借鑒,研究者對具有共同點和不同點的歷史事件、現象和結果進行控制性比較,以尋求特定因素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同時也將歷史事件的長期沖擊納入因果框架。
控制性比較為歷史政治學中的比較研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操作工具,研究者得以通過相似案例中的關鍵差異識別因果機制。盡管如此,“遺漏原因”和“測量誤差”依舊困擾著從事歷史分析的研究們。愈加主流的觀點認為,“除非放棄小樣本比較的方法轉而擁抱大樣本統計或定性比較分析,案例研究意圖通過比較方法以實現因果推論所遇到的種種難題便永遠無法得到克服”。這是因為,控制性比較將自己建立在了一個自身永遠處于弱勢地位的認知模式之中。一旦采納通過“控制”以實現“因果”的認識論路徑,那么小樣本比較本身將永遠處于弱勢境遇。在宏觀政治社會分析中,控制性比較所謂的“控制”遠未達到實驗法的標準。
與此同時,過度依賴于“控制”的小樣本研究還可能存在方法論至上主義風險。當“可比性”成為第一準則,那么許多有意義的問題便無從開展。例如新冠疫情暴發之后,探索中美兩國在抗疫問題上展現出的巨大差異無疑是一個既有學術意義又有現實關懷的問題。然而對于科學原教旨主義者而言,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巨大差別導致對二者的任何比較都無法得出確信的因果結論。因此,控制性比較所賴以存在的社會科學哲學基礎無法恰當地安放歷史政治學的宏偉抱負。超越實證主義與狹隘科學觀所帶來的偏見與桎梏,是重塑歷史政治學方法論基礎的應有之義。
社會世界的建構性與作為話語策略的比較分析
“科學主義”所帶來的“豐裕中的貧困”歸根到底在于那些“上游知識”。對于“科學觀”而言,相對論和量子力學所引發的科學革命已經使人們對“科學”的理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同于牛頓世界觀強調世界的確定性、客觀性與規律性,量子理論認為世界是由一系列不連續的、分立的、獨立的事件構成,不確定性才是世界的本質特征。這對社會科學的啟發在于,社會世界同樣具有不確定性,對政治社會現象的“介入”即具體研究工作的開展會使“不確定”變得“確定”:當尚未被視作分析對象時,社會事件或歷史進程雖然真實發生,但它們宛若處于黑暗之中的多棱體一樣不為人所知;一旦被選為分析對象,研究者通過理論之光照耀經驗材料,多棱體的某個側面得到呈現,同時另一些側面依舊處于黑暗之中。面對同樣的研究對象,不同的理論和方法會展現出完全不同的圖景,但它們無一例外是研究者“建構”的過程。
社會世界的建構性具有本體意義,它意味著社會科學研究的諸“范疇”并不是真實世界的簡單映像。例如,將幾千年前的雅典和如今的美國都稱為“民主政體”,其依據并不是這兩類政體高度一致,而是因為研究者“認為”它們是“民主的”。也就是說,社會世界諸要件被納入特定范疇的依據源于人們主觀的共享觀念。社會世界的建構性打斷了實證主義傳統對確定性的追求,因為即便是同一個概念,其背后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意涵。對于社會科學研究者而言,在這些被建構的概念之間尋找穩定的因果關系是徒勞的。
當充分認識到社會科學“由心驅動”這一事實,我們便可以放下對控制性比較的執念。它意味著“社會世界根本不是作為某種同質的對象而給定的,而是通過某種由各種視角組成的復雜系統而給定的”。對于歷史政治學而言,比較研究與其說是一種研究方法,不如說是一種話語策略,比較研究是否可行,取決于研究者的研究問題與理論框架。從這種意義上來看,所謂“可比性”問題很大程度上源于本質主義的立場,即研究對象之間是否存在可供比較的“本質”。但社會世界的建構性打破了這種本質主義想象,它意味著是否可比全然取決于人們的觀念。例如我們無法籠統地回答中國和新加坡是否可以進行比較:倘若討論國家治理問題,國土面積、人口數量等方面的巨大差異使得兩國很難具備可比性,反而中國與印度、墨西哥等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國家更具國家治理層面的比較意義;但如果討論執政黨建設與現代化道路,長期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與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又賦予了兩國可比性。將“比較”作為一種話語策略,可以有效地釋放因果推論對比較方法的束縛。
這樣一來,比較研究最為關鍵的并非研究技藝上的“可比性”,而是研究者在構建“可比性”過程中所秉持的理論視角或史觀。歷史政治學不單要“找回歷史”,更重要的是塑造一種“新史觀”。世界政治史的推進正體現出了這方面的努力,它力圖超越政治思想史、國際關系史以及全球史等既有歷史敘述模式,探究政治思潮誘發的國內制度變遷以及在此基礎上塑造的國際關系和世界秩序。世界政治史在歷史本體論的意義上找回全球參與主體的國家性,剖析世界政治體系形成以來的帝國主義性質及其帶來的“反向運動”,由此更好地理解中國崛起之于世界政治的文明價值。
那么,倘若不是為了因果分析,我們如何權衡比較研究在歷史政治學中的意義呢?馬克思曾說過:“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把這些演變中的每一個都分別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們加以比較,我們就會很容易地找到理解這種現象的鑰匙。”筆者認為,“理解”而非“解釋”才是比較研究的核心使命。通過比較,研究者可以觀察抽象的概念與理論在經驗世界中是如何穿行的,可以提出和驗證一些理論與概念,可以對復雜的政治社會現象進行概念總結與類型學建構。“比較”豐富了研究者對于復雜政治社會現象的認知,在相似性與差異性中更好地理解世界,從而避免僅立足一時一地便得出偏隘的結論。
在歷史敘述中實現因果推論
如果說歷史政治學中的“比較”只是為了“理解”這個世界的話,那么因果推論則應在“歷史”本身中尋找答案。不同于反事實傳統強調通過“控制”以最大程度地逼近實驗,筆者認為,歷史敘述本身就可以實現因果推論。然而,當代主流觀點認為,歷史敘述充斥著雜亂無章的文字、任意隨性觀察糾纏不清的邏輯,從而使得其自身很難稱得上是“科學”研究方法。
個中緣由,歸根結底在于研究者忽視了因果觀的多樣性。當下流行的“因果推論革命”將“因果”狹隘地理解為反事實邏輯,對研究者而言,似乎只有該傳統才是社會科學中實現有效因果推理的唯一方法。然而一旦我們接受了社會世界的建構性,那么所有被人類賦予其意涵的存在都應該具有多重理解——對“因果”的理解也不例外。有一種歷史悠久的因果觀恰契合了以歷史敘述為基礎的宏觀政治社會分析,即休謨開啟的“因果的規則性理論”或曰“律則論”的因果觀。該傳統認為,“因果”包含三個要素:時序優先、時空連貫以及恒常聯系。
“時序優先”與“時空連貫”展現出休謨傳統對時間與空間的敏銳,這是實驗法與定量分析所欠缺的。律則論的因果觀強調原因需發生在結果之前,進而能夠賦予歷史敘述以清晰的時間坐標。在宏觀社會分析中,“時空連貫”往往體現為“間接連貫”,它意味著原因X是經由一系列事件與結果Y相連接的。探究原因與結果之間的復雜因果鏈條,恰是歷史敘述的使命與優勢所在。與此同時,只有律則論的因果觀才將連接原因與結果之間的“機制”視作因果關系本身的一部分,并將“機制”定義為相互聯系的事件。以實在論尤其是批判實在論為哲學基礎的“因果力”學派將“機制”視作真實存在的推導動力或深層結構,但鑒于社會世界的建構性,我們無法在兩個建構性范疇之間發掘似自然世界中那樣的作為實體的機制。
律則論的第三個特征是“恒常聯系”,它在休謨看來更重要且更具決定性,因為這一特征有效地區分了兩個事件之間的關系是因果性的抑或純粹是偶然性的。但也正是這一特征使律則論飽受批評。人們認為它過于強調因果分析中的預測功能,并忽視了因果機制與因素組合的作用。但筆者認為,這些批評與其說是針對經典的律則論因果觀,毋寧說是休謨傳統在20世紀的一個發展分支。即“覆蓋率模型”或亨普爾所謂的“演繹-規律模型”,該傳統認為因果關系意味著原因X后面總是伴隨著結果Y,因果關系就像自然科學中的定律那樣恒常不變。然而經典的律則論傳統并不認同這一觀點,在休謨看來,原因與結果之間的“規律”只有在“相似的情況下”才可能出現。
基于新“科學觀”和“因果觀”,人們得以重新認識歷史敘述在宏觀政治社會分析中的地位。本文將這種基于建構主義和因果的規則性理論的分析技藝稱為“歷史性因果敘述”:它是“敘述”的,因此需要回答復雜世界中“是什么”的問題;它也是“因果”的,故而致力于追問造成變化或生成特定結果的緣由。筆者認為,歷史性因果敘述足以為歷史政治學提供更為堅實的方法論基礎。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歷史政治學以一種歷史本體論的關懷區別于其他以“歷史”為名的社會科學,它致力于研究過去與現在的直接關聯性并從中提出解釋性概念或理論。雖然鮮有明確提及,但筆者依舊認為目前有關歷史政治學的諸多論述已然暗示了該傳統所秉持的某些哲學立場。基于“使方法論與本體論一致”的原則,歷史政治學的分析技藝需要契合自身所主張的哲學立場。一方面,本體論層面的歷史政治學關注“知識主體性”問題,強調所有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概念是地方性知識的產物,不同文明實踐塑造了學者們的認知模型從而形成了不同的理論形態,這顯然是一種建構論的立場。另一方面,歷史政治學將歷史視作一種本體性“存在”,學者們應該在研究這個“存在”以及過去與現在的直接關聯性中提出概念或理論。很顯然,“過去與現在的直接關聯性”必然需要契合“時空連貫”的原則,而理論的生成無疑需要提煉那些具有“恒常聯系”的政治社會現象。這樣一來,歷史性因果敘述因其獨特的科學觀和因果觀巧妙地契合了歷史政治學的本體主張。
歷史政治學的另一核心特征體現為“以史為鑒”,即“求善治”的功能屬性。中國長久以來的政治史傳統形成了獨特的“史觀”,即政治方針、政治見解多從對歷史的分析中得出,政治觀點與歷史知識互動與循環。“以史為鑒”的關鍵在于對歷史規律的總結,而這正是關注“恒常聯系”的歷史性因果敘述所具備的。“以史為鑒”其實也是一個“理解”的過程,《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提到了十條歷史經驗,我們很難說這些歷史經驗的得出是依據怎樣的“科學”研究方法,相反,這些經驗是基于對歷史的“理解”而形成的。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強調,“理解”才是歷史研究的指路明燈。在特定理論視角和研究目的的雕琢下,歷史性因果敘述在“講故事”的過程中為讀者呈現出了歷史經驗與教訓,敘述本身賦予結論以可信性。中國共產黨的三個歷史決議都將很大的篇幅放在了黨史敘述上,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歷史敘述可以實現因果推論并達到“以史為鑒”的目的。“以史為鑒”是目的導向的,而非學究式的刨根問底。因此,連接溝通原因與結果之間的橋梁,甚至可能只是一些“隱秘聯系”。歷史政治學的功能屬性意味著研究者無需進一步探索“隱秘聯系”背后的奧秘,他們更加關注的是在“以史為鑒”中提供治國理政的智識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