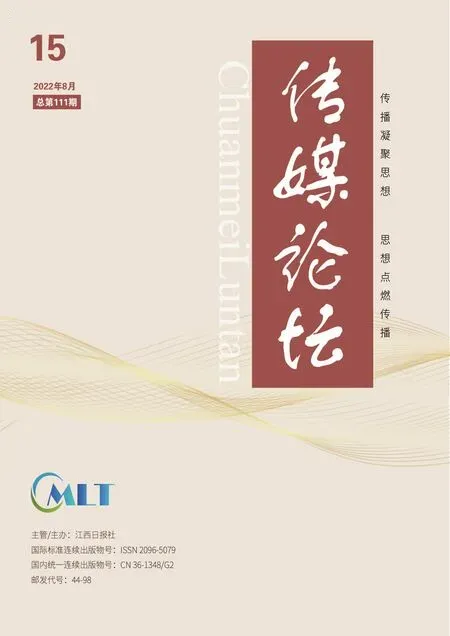基于CNKI數據庫的萬瑪才旦電影研究熱點及前沿探析
程婭娟
萬瑪才旦執導藏族題材電影,主要電影作品《靜靜的嘛呢石》(2005)、《尋找智美更登》(2009)、《老狗》(2011)、《塔洛》(2015)、《撞死了一只羊》(2019)、《氣球》(2020)。他在近兩年的創作中不斷嘗試先鋒性和探索性,堅持在影片靈感與創作、詮釋與解讀層面下功夫,嘗試探尋諸如《撞死了一只羊》中的藏地現代化主題,與非藏族地區受眾對話,因此對萬瑪才旦的研究也在近些年來層出不窮。
通過探賾與萬瑪才旦電影研究焦點相關的波折變化和新興趨勢,打通在內視角、外視角兼顧創作下的藏族題材電影中,藏民族文化與現代主流文化關系的橋梁、中介,方能進一步轉向對現代藏族文化主體本身的關注。
一、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與處理
對萬瑪才旦的研究呈現開放式狀態,以2022年3月前知網期刊數據庫收錄的445篇與萬瑪才旦相關文獻為分析樣本,包括涵蓋的93篇來自核心期刊的篇目,文獻研究整體水平較高,將近四分之一的權威學術期刊證明了萬瑪才旦在電影創作、影視傳播、文化塑造等方面贏取了話題度。與此相悖,萬瑪才旦影視研究的跨學科分類發展不均衡,以戲劇電影與電視藝術學科領域居多,高達38.03%,少有涉及信息科技、文化經濟等門類,對其影視方面的研究尚未得到多個學科的關注。
(二)基于跨學科理論的文獻計量研究方法
本文將跨學科的計量方式融入電影批評領域,擇取文獻計量與數據可視化分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應用中國知網系統信息可視化分析功能,對萬瑪才旦電影研究的主題、發文期刊、來源類別、發文量、核心作者、高頻關鍵詞共詞等進行計量,厘清其研究趨勢及發展前沿。
二、萬瑪才旦電影研究熱點與知識發現
本文構建了題為“萬瑪才旦”相關研究的分布圖、共現圖、演進圖。基于中國知網庫,洞察其導演電影研究的“文獻焦點的生長點”“研究創新點”以及形成特征。
(一)學術關注度
將檢索出的文獻按照在時間維度分布上的年度發文數量,得出發文量的分布圖(如圖1)。國內對萬瑪才旦電影研究始于2000年,發文量僅一篇,且為評析他的小說創作。2013年后的發文量猛速上漲。同時,在2019年、2020年的兩年中達到發文數量持平。2021年,中國知網可視化分析曾預測萬瑪才旦導演電影研究的發文量值高達59篇,實則發出42篇;2022年,系統再次預測值達到45篇,發文境況呈微增長趨勢。文獻數量的變化從側面反映出萬瑪才旦的研究熱度與上映作品話題度息息相關,真正走進學界市場范圍的是電影文本范例。真正意義上最早的國內電影學術評論文章是2013年來自上海戲劇學院的蘆辰芳碩士論文《靜靜的唐卡——萬瑪才旦電影作品研究》[2]等。基于可視化中呈現的電影《靜靜的嘛呢石》《尋找智美更登》,萬瑪才旦早期將現實主義精神建構于西藏人民真實生活之上,后使得電影《塔洛》描繪出藏族人民在現代化轉型時宣泄身份迷失的痛苦,電影不再是單純借藏族景觀發力,這徹底轟動了藏語、藏人、藏地三位一體的“藏地電影新浪潮”,藏族題材電影未來的研究發文量趨勢有望勇創新高。

圖1 在時間維度上的“萬瑪才旦”相關研究發文量的分布圖
(二)研究核心作者及機構分析
2021年6月止,萬瑪才旦電影研究的發文量前五的作者:胡譜忠5篇(首都師范大學)、袁智忠2篇(西南大學)、杜慶春2篇(北京電影學院)、鞏杰2篇(西北大學),國外作者研究發文量盡達30余篇。顯然萬瑪才旦影視與作者之間的合作強度稍顯不夠,這是本土新銳導演起步時間較晚帶來的結果之一,也是學界領域對傳播藏文化廣度的效果展現。
基于進一步對萬瑪才旦電影研究熱點在國內電影學有關機構的引文數據探索,首當其沖的是北京電影學院14篇,對比以往的數據結果,其機構是在2022年之際反超原本首位的河南大學,河南大學發文12篇;后是青海民族大學發文量并列為12篇;排列第四的是中國傳媒大學9篇,再是西藏民族大學和西北民族大學,發文數量接近。這些機構均以我國北方地區高校為主,具有一定的學科專業性和民族地域表征,但研究文獻始終被囿于該民族電影作品的生產進度,滯后的電影生產速度不得不使萬瑪才旦電影研究的熱度步入良性的發展軌道,這對大部分電影導演和電影產業來說都是一項巨大的考驗與沖擊。
(三)關鍵詞共現知識圖譜分析

圖2 國內“萬瑪才旦”研究的重要機構分布
中國知網庫中出現頻次最高的主題關鍵詞是萬瑪才旦(總次數:88),其余高頻關鍵詞還有塔洛(總次數:34)、撞死了一只羊(總次數:27)、氣球(總次數:19)、少數的藏語電影及現代性、長鏡頭、作者電影為次要的文獻主題,關于萬瑪才旦的研究關鍵詞主要通過一種單向度的視角,從電影作品的研究層面去審視藏族地區的文化,再進一步探討其與現代文化的關系。
再諸如上述關鍵詞涵蓋的影像書寫、電影敘事研究、空間敘事研究、作者電影美學研究,在中國知網庫的碩士、博士學位論文中的應用率形態豐富多元,研究方向多維立體,研究熱詞中以萬瑪才旦電影本體化、電影美學特征為主,少量內容開始觸及少數民族電影中的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建構研究。這種荒誕性和魔幻現實主義的寓言式故事的研究價值,正體現了萬瑪才旦電影中對藏群人民在現代社會中前進與發展時所創造出雙重身份的過程,背后更是蘊含著對藏族傳統文化與現代主流文化呼應與融解的思索,也為推進影視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開辟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局面。
三、研究熱點及前沿探析
萬瑪才旦影視研究相關的主要、次要主題均包括民族題材電影、視聽語言、身份認同等議題,焦點主題演變發生質的遞進飛躍。
(一)導演論——藏族電影創制力量的培育與發展
以“萬瑪才旦”為第一關鍵詞的主要主題篇目共88篇,占總主題的27.24%;次要主題篇目共148篇,占總主題的42.05%。萬瑪才旦可以稱為中國居于首位在國際、國內備受關注的藏族題材電影導演。以“萬瑪才旦”為次要主題研究之多是在于“作家導演”電影下涵蓋的新維度:民族電影+文化身份書寫,他在作品中力圖實現藏族文化身份的建構,為其電影注入了源頭活水。除此之外,藏族導演團隊的創制已具有清晰的譜系化表征,出自本土的導演對影像中的故事會抒發明顯的遼闊感,他們為非藏族人民提供了透視藏區的文化視野,在這點上,親身的本土化培育路徑將進一步帶動人們與藏族電影文化的交流。在尊重民族文化的前提要求下,非藏族地區的創作人員開始有意走進該民族影視環境,建立起某種“去身份化”的觀察策略,為當代影壇激活新興力量。
(二)電影文本論——影像符號與主體信仰的解碼
中國知網中數據分析得出《塔洛》(發文量34篇,占10.53%)、《撞死了一只羊》(發文量27篇,占8.36%)、《氣球》(發文量19篇,占5.88%)、《靜靜的嘛呢石》(發文量6篇,占1.86%)。位居前列的具體電影作品與文化傳播之間聯系緊密,研究從電影文本出發,這表明學術界對電影作品水準和電影藝術性都給予了相當程度的關注。尤其在鄉愁敘事文本與現實主義的層面上,鄉愁的書寫實際上是西藏民族的多重焦慮,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鄉土文學或者藏語電影愛好者所處時代里的信仰指數。這種信仰不再是狹義的宗教文化,而是從敘述民族主體表達到共述母體普世的價值觀念,它觸碰到了當前的中國社會的信仰癥結。
(三)藏文化——去宏大化敘事下文化意指的回歸
文獻研究中的主要主題并非藏文化本身,而是附載于其中的主要主題。萬瑪才旦既關注民俗風情本身,又放眼于藏文化的廣泛傳播。如果說導演在電影文本中所有關于藏民族符號的表達,包括喇嘛、靈塔等,旨在建構藏族圖景和藏族形象,那么在藏文化影響下群體與個體的人類現實生存境況,更是引發民族思考的終極命題。基于此,民族符號的呈現都寄托在民族文化表述中,是在轉向對藏族文化主體本身的關注和撫慰,對民族主體情感的維系和感悟。
四、討論:“發展意識”與實踐導向
關于現代文明的發展,不僅通過意象和指涉的符碼不斷影響著西藏人民認識理解宗教傳統文化的過程,而且改變著西藏的世俗生活和精神境界[3]。萬瑪才旦曾自詡電影有反叛的意味,暗示本民族將對某些傳統有一個終結,這流溢著未來更廣的藏語電影中不斷尋找純粹、活力的民族生命力的激情。而進一步追蹤萬瑪才旦電影的研究趨勢的變化,揭示萬瑪才旦電影研究的廣泛關注大致分為三層導向:第一層是最早研究風情民俗的寫意式電影作品;第二層是呼應文學創作,考究創作出發點,延續了學界對其作品改編的電影背后的藏文化關懷;第三層是探索先鋒影像,關注族群現代性,即轉向對現代藏族文化主體本身的關注和撫慰,使得民族電影文化表征日趨顯現,維系群體身份歸屬感。
從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傳播的對象、觀念、渠道等來看,作為民族文化品牌符號的電影應當響應國家電影的方針政策、文本故事與藏族風情的藝術結合、擴大多元化形式的媒介傳播手段。學術界對藏族甚至其他少數民族電影傳播的學術研究主要集中在電影作品、電影敘事轉型和國家作為文化傳播載體的象征意義上,對民族影視創作者的關注相對較低。例如藏族,目前僅有松太加、張揚數個名導,他們的創作團隊需要培養更多本土影視人才,學術研究可以挖掘更多藏地文藝作品,含蓄地表達了外視角導演下的民族認同和文化地位,為西藏電影的身份表達和藝術生存提供了新的道路。
當前,藏族乃至其他少數民族領域的影視作品尚未成為主流,市場收獲未呈現良好趨勢。在媒介助長的少數民族地區影視行業的網絡化、數字化會逐漸延伸,如何更好地適應媒體時代?筆者認為應該大力發揮媒介的優勢,拓寬影片良性營銷市場。并且在今后的學術研究中,多立足于考察藏族及其他少數民族電影如何對民族團結和國家認同進行多維度地傳播,凸顯少數民族電影參與國家主流文化建設的重要性,開拓其發展的政治與文化空間,進而適應全球文化的融合。
五、結語
可以預知,在數字人文交匯的創新引擎下,藏族題材電影乃至我國少數民族電影領域的研究成果會不斷摸索、不斷更新。目前,中國知網數據庫中小成本藏族題材電影研究熱衷于顯露當前藏區面臨的身份焦慮與現代意識,完成其轉向對現代藏族文化主體本身的關注和撫慰,民族電影文化表征日趨顯現,重在維系群體身份歸屬感。日后,對藏族乃至其他少數民族電影領域的研究主題、研究內容、研究熱點,將會隨著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進一步構建,逐步尋找到打通民族文化與現代主流文化關系的橋梁,而不斷變化多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