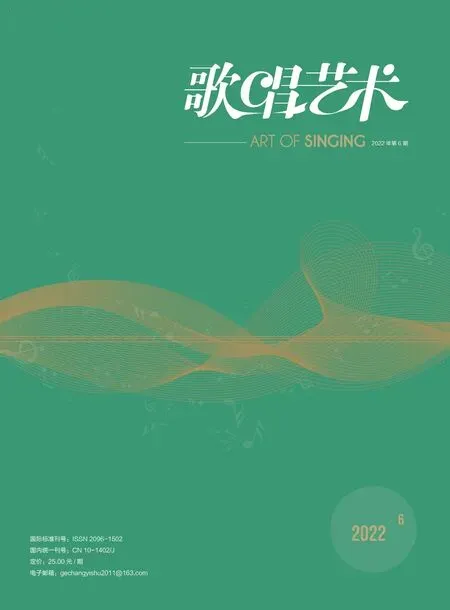一家人不說兩家話
—— 訪人民音樂出版社李航
俞子正
訪談?wù)撸河嶙诱懈咭舾璩遥淌冢陡璩囆g(shù)》常務(wù)副主編)
嘉賓:李航(人民音樂出版社期刊中心主任,編審,《鋼琴藝術(shù)》常務(wù)副主編)
(下文中,俞子正教授簡稱“俞”,李航編審簡稱“航”。)
李航好!居然采訪《鋼琴藝術(shù)》的您,實在是有點意思,您作為兼管《歌唱藝術(shù)》雜志的期刊中心主任,應該是最了解這本雜志的,知道它的前世今生、它的現(xiàn)狀,以及出版社對它的期望。
非常感謝俞老師!您的“午后會客廳”做得非常好,能夠到您的會客廳是我的榮幸。我作為一名雜志辦刊人已經(jīng)二十五年了,應該說走過了《鋼琴藝術(shù)》和《歌唱藝術(shù)》兩本雜志的最初階段。《歌唱藝術(shù)》創(chuàng)辦的起因,源于《鋼琴藝術(shù)》,鋼琴和聲樂可謂是姊妹藝術(shù),所以初衷也是希望可以做成“姊妹刊”。
雖然去年開始接手《歌唱藝術(shù)》的常務(wù)副主編工作,但實際上我對這本雜志的歷史完全不清楚,只是想把它盡可能做得好一點。您能先介紹一下《歌唱藝術(shù)》的創(chuàng)辦過程嗎?
《歌唱藝術(shù)》的創(chuàng)辦過程可能還真是我最清楚。在我印象里這本雜志之前應該是在2005年左右有過一次醞釀,也是籌備了一年時間,但是無疾而終。或許是因為一直有這樣一粒種子,所以在土壤、空氣都適合的環(huán)境下終會長成。2011年1月,在出版社的全力支持,以及雜志創(chuàng)刊時各位同人的共同努力下,《歌唱藝術(shù)》雜志正式出刊了。經(jīng)過了三年的合作辦刊,我們終于申請到正式刊號,2014年《歌唱藝術(shù)》改刊名為《歌唱世界》,2016年改回《歌唱藝術(shù)》,真正和《鋼琴藝術(shù)》成為“姊妹刊”。
是的,當年我看到《歌唱世界》這個雜志名字,感覺特別業(yè)余,有點像“XX大世界”之類的,后來改回《歌唱藝術(shù)》了,感覺就舒暢一些。您覺得這本雜志的文章質(zhì)量如何?請誠實地評價。

這個問題太尖銳(哈哈)!客觀地說,每一本雜志每一期內(nèi)容每一篇文章的質(zhì)量參差不齊,這也是很正常的,不可能篇篇文章都是“鮑魚魚翅”,會很難消化的。目前來說,雜志有質(zhì)量的文章越來越多了,就像前兩期訪談鄧垚老師和張美林老師的文章,非常有意思,很生動,對讀者很有啟發(fā)。所以,當時文章在雜志微信公眾號推送后,第二天閱讀量就接近五萬!但是,普遍來講,聲樂方面能寫的、寫得好的人太少,所以有關(guān)聲樂方面的好文章產(chǎn)出量也就相對少。
我注意到《歌唱藝術(shù)》的發(fā)行量很小,影響力不大,您覺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應該說是方方面面的原因都有吧。首先,我想談?wù)勅?nèi)現(xiàn)象。我自己也是音樂學院“泡”出來的,接觸過很多聲樂系、歌劇系的同學,現(xiàn)在也都是歌唱家了。聲樂這個專業(yè)太有自己的個性,太因人而異,并且天賦在這個專業(yè)中占據(jù)絕對重要的位置。沒有天賦,沒有天生的好嗓子,一切都是零;但是有了天賦,這個長在身體里樂器還隨時會有各種潛在的、突變的可能性。從根兒上講,大家從來都是認為唱得好是老天爺給的、天生的;理論也好,教學也罷,沒有多大意思,也說不清楚。從唱到說,再到文字,何其難!如何能用文字把種種現(xiàn)象寫出來?太難了!寫得不生動,沒人看;寫得大膽的,稍有偏差,招人議論;剩下寫得好的,就少之又少了。所以,雜志在內(nèi)容方面很受局限。
其次,我也想說一下整個的大環(huán)境。現(xiàn)在是一個網(wǎng)絡(luò)時代,是大家刷“抖音”、上“小紅書”看視頻的時代,書刊、報紙,對很多人來講,已經(jīng)不重要了,除非迫不得已。太多的想知道的,動動手指,打開“百度”看兩眼,也就都有了。不追求精益求精,只需大概了解。可能我說得有一些過分,但做雜志二十多年,我說的一定是最誠實的。這個社會太浮躁,很少有人還會靜下心來閱讀。不夸張地說,閱讀這個習慣正在慢慢消失。
是的,人們似乎滿足于碎片式的資料,什么“抖音”啦、“百度”啦,都懶得動腦子思考。讀書沒有了書,人也就沒有了書卷氣。譬如,一套線裝的《史記》改成電子版在平板電腦上看,感覺好像是另外一本書,讀書的方式不同了,感覺也會隨之改變。看屏幕讀書似乎是進步了,但只是閱讀工具上的便捷,是不是進步還很難說。我覺得閱讀工具的差異對人的知識攝入量是有影響的。我也偶爾在屏幕上讀書,但總覺得和書本不一樣,好像讀書本時都能記住,看屏幕會看了就忘。而且,沉不下來,不像讀書本那樣安心,可能是我的陋習吧。那么,我們?nèi)绾尾拍芴岣唠s志的質(zhì)量,包括文章的質(zhì)量、被引率等,讓更多的人讀這本雜志,在業(yè)內(nèi)產(chǎn)生更大的影響?這是一個工程,一個很大的工程。提高雜志的質(zhì)量還是要靠各方的共同努力。從編輯者、辦刊人——因為每一本雜志都會真實反映出辦刊人的思想——到每一位與歌唱相關(guān)的人士,只有大家都關(guān)心中國的歌唱事業(yè),這本雜志的質(zhì)量才會越來越高,才會越來越有意義。至于被引率和業(yè)界的影響力,一方面,確實需要一個過程,道路還很漫長,仍需不懈努力;另一方面,辦刊還是需要有互動性,只有更多的走出去,才能讓更多的人了解你、認識你,直至喜歡你、愛上你,希望以后雜志可以開展更多的全國性活動。例如,《鋼琴藝術(shù)》雜志每年都會舉辦活動,全國的教師需要一個這樣的平臺交流互動,了解彼此,共同成長。
一般來說,表演藝術(shù)類的文章相對比較難寫,很多是感性的,大部分教師憑教學經(jīng)驗在傳授歌唱技術(shù),很少有人認真地研究音樂史、聲樂史,以及其他與歌唱相關(guān)的學科,如人體的結(jié)構(gòu)、共鳴的原理、歌唱動力等。因為大家覺得沒有必要,憑經(jīng)驗把聲音搞對、各顯神通就可以了。寫文章時,由于每個人不同的感性體驗和經(jīng)驗差異,常常寫得云里霧里、不知所云。我看過很多聲樂方面的論文,大部分缺少科學分析和理論依據(jù),有點像個人體驗的經(jīng)驗匯總。有些話甚至看不懂,譬如“吸著唱”“聲音從后腦勺出來”“氣息吸到小腹”等,你說誰能夠吸著氣唱歌?太神奇了!可是這種現(xiàn)象已經(jīng)存在很久、很普遍了,似乎也很難改變,您覺得我們該怎么辦呢?
是的,確實存在這種現(xiàn)象,鋼琴學科也同樣存在,我想還是需要引導。作為雜志,尤其是學界的一本專業(yè)刊物,還是應該肩負這樣的歷史使命的,它一定要有自己的聲音、有自己的方向。
您剛剛講到音樂史、聲樂史,以及邊緣學科,我認為是很重要的,還有相關(guān)領(lǐng)域、交叉學科,文化的、歷史的,等等。我想作為一位歌者、表演藝術(shù)家,或者是聲樂教師,只有實踐和理論相結(jié)合,才可能在藝術(shù)的道路上走得更遠、更長久。有天賦,唱得好,這是最初階段。想要登高,需要有文化的積淀才能踏實。想要唱得好,保護好自己的嗓音,更需要了解人體結(jié)構(gòu)、發(fā)聲原理等,才能避免出現(xiàn)問題。至于很多所謂的“道理”“說法”,還是需要有人站出來厘清的。當然,這種“站出來”需要勇氣,更需要有理論知識和實踐的結(jié)合與積淀。
我一直認為,在我們目前的藝術(shù)評論界、理論界需要有更好的風氣和氛圍,鼓勵有學術(shù)見解的不同發(fā)聲,但是現(xiàn)在的“空氣”還有待培養(yǎng)。大家是共同探討,而不是聽不得不同的聲音,不要互相攻擊和謾罵。藝術(shù)本身就是一個可以有千萬種表達形式的東西,沒有絕對的對與錯,但是要有道理。可以允許試錯,只有在試錯過程中才能得到答案,但是要學會在錯綜復雜中厘清是非對錯。
還有一個現(xiàn)象,我說了可能會得罪同行。我觀察很久了,每個學校都有圖書館,學院還有資料室,每年學校花了很多錢買各種書籍、音像資料,訂各種雜志、期刊。但是,事實上很少有聲樂教師去讀書看雜志,圖書館幾乎就沒有表演藝術(shù)方向老師的蹤影。我查了近兩年我們學校圖書館的記錄,沒有聲樂教師去過圖書館,這也可能跟前面說到的閱讀工具發(fā)生了變化有關(guān)系,您覺得這會是什么后果呢?
是的,我曾經(jīng)也有過這樣的思考,這到底會導致怎樣的結(jié)果?歌唱家、鋼琴家,都屬于“表演藝術(shù)家”范疇,但如果只是單純的能唱能彈,只能成為這個范疇內(nèi)最低層次的匠人,這樣一代傳一代,會有“青出于藍”嗎?
我們倒回頭再說表演藝術(shù)家,“表演”二字,有很多含義——表現(xiàn)、演繹。演繹的依據(jù)是什么?如何演繹才更加準確?在準確演繹的基礎(chǔ)上如何做到優(yōu)秀?如何突破固有的傳統(tǒng)而做到有個性標簽的演繹?……沒有這些思考,又如何能擺脫匠人的思維模式,上升到“大家”“藝術(shù)家”?如何能有“代代相傳勝于藍”?
我想,還是要有一些方法和手段激勵、鼓勵大家多讀書、多思考,不是能彈會唱就滿足了。從領(lǐng)導到藝術(shù)家,再到教師、學生,或許都需要重視。
藝術(shù)家們都認為自己的專業(yè)成就和學術(shù)都體現(xiàn)在歌唱上、舞臺上和比賽中,能夠培養(yǎng)出優(yōu)秀的歌唱家才是自己的主要工作,我以前也是這樣認為的。但是,現(xiàn)在看來,還是需要在理論上好好做功課的。否則,我們說的那些教學術(shù)語猶如天方夜譚。有一次,我和幾位聲樂愛好者海闊天空聊唱歌,有個朋友談及“聲音從后腦勺出來”后,其中有一位醫(yī)生直接嘲笑我們居然如此無知。
當然,藝術(shù)家、歌唱家的成就首先體現(xiàn)在表演,體現(xiàn)在自身的能力和功底,舞臺表演實踐一定是第一位的。但是,作為音樂學院和綜合性大學的教授、教師,如何把這些實踐的經(jīng)驗轉(zhuǎn)化成理論,轉(zhuǎn)化為讓更多人能夠借鑒學習的知識和學問,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們不僅僅是歌唱家、鋼琴家,還是教授、教師;他們的能力不僅體現(xiàn)在舞臺上,更重要的是講臺,是教室。我們面對的或許有很多是未來的教師,教師對于學生潛移默化的影響是非常強大的。
那么,從您的經(jīng)驗來分析,您覺得哪一類的文章比較受歡迎?
聲樂方面,我是“門外漢”,但是從《鋼琴藝術(shù)》雜志的內(nèi)容來看,相對于音樂史論的文章,演奏、教學類的文章會比較受歡迎,大的方向講就是可以讀之受益,又可以運用于實踐。我想,聲樂方面的文章也大概如此吧。
《歌唱藝術(shù)》不僅是面向?qū)I(yè)人士,也應該吸引一部分業(yè)余讀者。對于業(yè)余歌唱愛好者來說,他們是不是也可以參與這本雜志?那樣會不會降低雜志的質(zhì)量?
有些業(yè)余的歌唱愛好者在他們自己的學術(shù)領(lǐng)域里是很優(yōu)秀的人才,他們看問題、研究問題的角度和方法甚至比我們專業(yè)的更客觀、更全面,多一種視角看待問題只會打開我們的眼界和思想。業(yè)余和專業(yè)只是行當不同、職業(yè)不同,并不代表業(yè)余愛好者的水平就是業(yè)余的。我認識很多音樂發(fā)燒友,他們對于音樂的認知比我們音樂學院的人更加全面,他們會把音樂和歷史、文學、哲學等其他學科,以及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相結(jié)合,從他們身上我學到很多。您和美林老師的書法都是業(yè)余的,我看比大多數(shù)專業(yè)書法家寫得好!
嘿嘿,那倒真是的!我注意到您也擔任《鋼琴藝術(shù)》雜志的常務(wù)副主編多年,但是似乎它們的文章質(zhì)量和影響力要比《歌唱藝術(shù)》大一些,是不是您更多關(guān)心的是《鋼琴藝術(shù)》?一家人不說兩家話,其實,這兩本雜志都是您負責的,手心手背都是肉,您不能“厚彼薄此”,是吧。您希望《歌唱藝術(shù)》如何改進?
《鋼琴藝術(shù)》雜志創(chuàng)刊的時間比較長,所以她積累的資源相對就會更豐富。在辦刊的過程中,我們積累了很多優(yōu)秀的作者,也有很多忠實善良的讀者。而且,近幾年,我們通過辦活動也在社會上不斷擴大影響力,增加讀者的黏合度。我想雖然刊物不同,但是辦刊也可以有異曲同工之處吧。作為《歌唱藝術(shù)》雜志,首先要找準定位,堅持不動搖,根據(jù)定位找準方向、確定內(nèi)容,用好的內(nèi)容和文章吸引讀者。同時,我想也要做辦刊之外的很多事情,如何運用好新的技術(shù)手段、運用新媒體,如何辦好社會活動,等等。一本好的雜志要觀照傳統(tǒng),反映當下,引領(lǐng)風向。
還有一個問題,以前我們和“珠江鋼琴廠”一起辦過多次全國性聲樂比賽,后來改成了展演,也不發(fā)等級獎項,而學校教師的職稱晉升和業(yè)績考核都與比賽獎項息息相關(guān),人民音樂出版社今后會不會再搞比賽,給教師們提供一個藝術(shù)展示平臺呢?據(jù)我所知,“珠江鋼琴廠”還是很留戀以前的那個比賽,教師們也都很懷念那個比賽。如果能把比賽和《歌唱藝術(shù)》雜志的發(fā)展結(jié)合在一起,或許是個好的主意。
是的,我們以前成功舉辦過多屆比賽,在全國的影響力還是很大的,因為這是一個專門為在校教師和學生舉辦的比賽(活動),這個性質(zhì)的比賽(活動)目前為止在國內(nèi)好像還是唯一的。我們還是非常想把比賽(活動)繼續(xù)下去,其實只要我們把心態(tài)放好,積極地看待這個問題,以后一定會有更多的機會。無論是比賽還是活動,這就是一個大家在學術(shù)上交流互動的平臺,是一種成果的展示,對我們的教學也是一種檢驗和推動。
我今天提的問題有點為難您,您不要見怪。因為我們必須找到《歌唱藝術(shù)》的問題所在,尋求改變,解決問題,讓這個全國聲樂教師、學生和愛好者的園地好起來、豐富起來,成為一本高質(zhì)量的雜志,成為大家喜愛的雜志。謝謝航主任!請相信《歌唱藝術(shù)》會很快發(fā)生變化的。
感謝俞老師的采訪,讓我們一起努力建設(shè)、耕耘自己的精神家園,并且熱愛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