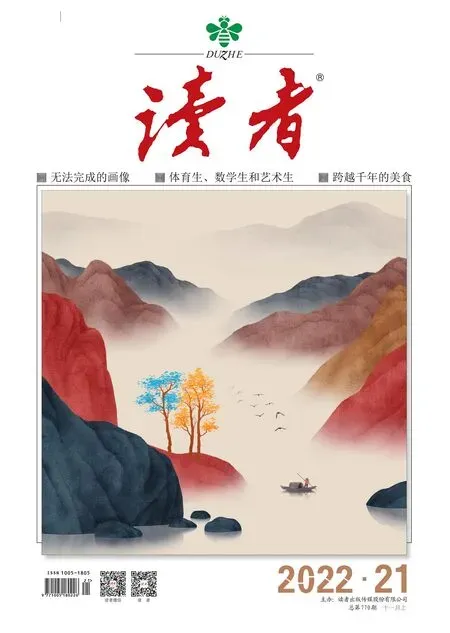聊贈(zèng)一枝春
☉黎 戈

古人循農(nóng)時(shí)而播種,依天時(shí)來(lái)收割,靠植物獲取節(jié)序感。對(duì)詩(shī)人、畫(huà)家來(lái)說(shuō),植物也是寓興抒情的意象源泉。植物與生活密切相關(guān),血脈相連——我們生來(lái)與天地草木親近。
讀東坡尺牘,最?lèi)?ài)的,就是他話家常的那些。有封信,是關(guān)于種樹(shù)的,他在信中寫(xiě)道:“白鶴峰新居成,當(dāng)從天侔(人名)求數(shù)色果木,太大則難活,太小則老人不能待,當(dāng)酌中者。又須土砧稍大不傷根者為佳……”人生如寄,風(fēng)波不止,貶謫無(wú)奈,空談抱負(fù),徒增傷感,還好有植物可以相親相慰,當(dāng)作友人傳輸關(guān)懷的載體,拉起一張日常生活的網(wǎng),打撈被虛無(wú)感籠罩的失根之人。
細(xì)想起來(lái),熱愛(ài)園藝的作家相當(dāng)多。說(shuō)到底,寫(xiě)字也是“筆耕”,和種植有異曲同工之妙:長(zhǎng)時(shí)間的資料準(zhǔn)備,類(lèi)似于好的農(nóng)夫會(huì)用大量的時(shí)間備好營(yíng)養(yǎng)土,土層豐厚,靈感的幼苗才能生長(zhǎng)好,加之日夜不輟、辛勤的耕耘,尊重植物生長(zhǎng)的節(jié)奏——作家也得低頭傾聽(tīng)內(nèi)心的波濤,待它起時(shí)才能落筆,而一篇滿意的成稿帶來(lái)的滿足感,正像看到一株親手植下的花開(kāi)放。
比如簡(jiǎn)·奧斯汀,她一向是自己動(dòng)手釀蜂蜜酒,飼養(yǎng)火雞,種植豌豆、土豆、葡萄、草莓、美洲石竹和藍(lán)色耬斗菜。我想,她筆下的很多調(diào)味品和蔬菜應(yīng)該是她自己栽種的。那個(gè)時(shí)代很流行“廚房花園”,很多鄉(xiāng)下莊園都附有大塊菜地,以便為自家提供蔬食。奧斯汀的媽媽就是一個(gè)種菜高手,在鄰居間率先種了土豆和番茄。每次看她筆下的人物吃卷心菜濃湯和炸土豆時(shí),我都會(huì)想到她們的菜園。
還有畫(huà)彼得兔的波特小姐。波特小姐雖是中產(chǎn)階級(jí)家庭出身,但一直聲稱自己有一顆“農(nóng)婦的心”。她從小就非常喜歡鄉(xiāng)間生活,喜歡在奶奶的鄉(xiāng)下莊園、爸爸的湖區(qū)度假別墅里度過(guò)美好的時(shí)光。她潛心畫(huà)畫(huà),用畫(huà)筆記錄了蘇格蘭無(wú)垠的牧場(chǎng)、落在地面的黎巴嫩雪松枝、瘋長(zhǎng)的野香芹、攀爬在農(nóng)場(chǎng)煙囪上的野薔薇和笑臉一般的三色堇。她一路積累,最后將這些東西變成彼得兔故事中優(yōu)美如詩(shī)的背景及細(xì)節(jié)。在彼得兔被園丁追殺的場(chǎng)景里,我認(rèn)出了那倒地的花盆里散落的三色堇花瓣;在彼得兔年鑒里,我認(rèn)出了波特小姐冬日里的最?lèi)?ài)——雪花蓮;在啪嗒鴨蹣跚走過(guò)的林間小徑上,我又認(rèn)出了波特小姐最?lèi)?ài)的粉色指頂花。晚年時(shí),她買(mǎi)下農(nóng)場(chǎng),專心蒔花弄草,她在屋墻上,鋪了粗布以便于這些花攀爬。她和鄰居、好友,常常以花為禮,彼此交換,這既是一種園藝的分享和溝通,又是默默的情感交流。
還有美國(guó)女詩(shī)人狄金森,到了晚年,她從喧囂的交際中隱退,只與家人和植物為伴,幾乎是隱居狀態(tài)。幼年時(shí)代的她,就是一個(gè)喜歡孤獨(dú)地徜徉在野花叢中的小女孩。“當(dāng)我還是個(gè)小女孩時(shí),我常跑入樹(shù)林中,他們說(shuō)蛇會(huì)咬我,說(shuō)我可能會(huì)摘到有毒的花朵或被哥布林綁架,但我依舊獨(dú)自外出。”這個(gè)與草木相伴的習(xí)性貫穿她的一生。
她稱春日為“洪水”,“草坪上滿是南風(fēng),氣味互相糾纏。今天是我第一次聽(tīng)見(jiàn)樹(shù)中的溪水聲”。春日如此宏大,“如此明亮、如此湛藍(lán)、如此艷紅又如此潔白”,櫻桃的花光,藍(lán)天白云,春日的光影之中,狄金森取出裝在紙袋里的花種,小心地培植在溫床和腐殖土中,“我種下我的——盛典的五月”。傍晚在花園散步的時(shí)候,她會(huì)去扶正金銀花的藤。當(dāng)雨天無(wú)法從事園藝,她寂寞于無(wú)鳥(niǎo)的安靜,慨嘆“那些小詩(shī)人(鳥(niǎo))都沒(méi)有傘”。
雨停后,她出門(mén)采摘芳?xì)馑囊绲霓ь?lèi)植物,夾在書(shū)信里寄給朋友。她常常采下新鮮的玫瑰花、藍(lán)鈴花甚至一枝貓柳,寄給友人,詼諧地打趣道:“這(貓柳)是大自然的銀黃色信件,它把信留給你。它沒(méi)有時(shí)間拜訪。”這不就是中國(guó)古人說(shuō)的“春消息,夜來(lái)陡覺(jué),紅梅數(shù)枝爭(zhēng)發(fā)”嗎?而狄金森干脆把這個(gè)消息寄出去了。寫(xiě)詩(shī)的時(shí)候,如果暫且沒(méi)有靈感,她會(huì)拿玫瑰花做“抵押”,夾在信紙空白處,先算作將來(lái)的詩(shī)句,到時(shí)候再兌換成文字……一個(gè)靈俏生動(dòng)的狄金森,就這么在花葉的邊角處、字里行間,探出頭,向我吐吐小舌頭。透過(guò)這些細(xì)微的舉動(dòng),我依稀看到了她年輕時(shí)如雀鳥(niǎo)般俏皮的身影。
以花相贈(zèng),作為日常表情,似乎是文人常用的抒發(fā)路徑。寫(xiě)《塞耳彭自然史》的吉爾伯特·懷特,他是一位沉溺于內(nèi)心世界、與天地親近之人,與一位叫馬香的朋友長(zhǎng)期通信,兩個(gè)人都是自然愛(ài)好者,通信的內(nèi)容不外乎是家燕歸窩了,村口的一棵老樹(shù)被砍了,貓頭鷹的對(duì)唱是A調(diào)還是D調(diào)。在遙遠(yuǎn)的18世紀(jì),兩個(gè)樹(shù)友、鳥(niǎo)友,就這么飛鴻往來(lái),在庸常的生活之外,共同翱翔在一片無(wú)垠的精神天空之中。
他們談得最多的,還是樹(shù)。懷特用大量的筆墨深情地描繪他見(jiàn)過(guò)的大山毛櫸:“龐大臃腫的山毛櫸、中空的山毛櫸、修過(guò)枝的山毛櫸……所有陌生人都愛(ài)這些樹(shù)。”他們都很愛(ài)這種樹(shù),在信件中交換了各自的大量觀測(cè)數(shù)據(jù)。為了酬謝懷特的情誼,有一次,馬香還把自己修剪的一株小山毛櫸寄給了他:“我希望其垂下的樹(shù)枝,能碰到從樹(shù)下騎馬而過(guò)的人,從遠(yuǎn)處看,這種樹(shù)就像綠色的山丘一樣美。”他們心意相通,正如地下根系相連的樹(shù)。
中國(guó)古代也有很多這樣的“素心人”。陸凱與范曄為友,在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zhǎng)安與曄:“江南無(wú)所有,聊贈(zèng)一枝春。”《子夜四時(shí)歌·春歌》里更有:“蘭葉始滿地,梅花已落枝。持此可憐意,摘以寄心知。”遙想古時(shí),交通不便,舟車(chē)遙遙,那一株小小的花枝,就是烽火中抵萬(wàn)金的書(shū)簡(jiǎn),知己傳達(dá)心意的便箋,愛(ài)人輾轉(zhuǎn)不寐的相思淚,攥在手心的體溫。那些出沒(méi)在詩(shī)詞駢賦中的芳菲,蘊(yùn)藏著何其豐富和充沛的情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