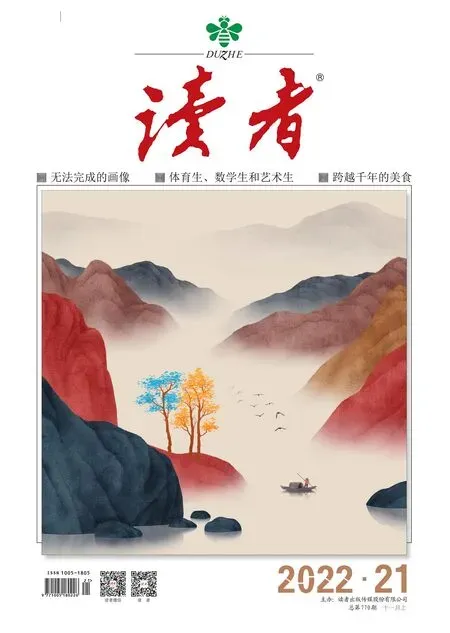媽媽抱一下,我就會骨折
☉張志軍口述
◎陳拙整理

我患有成骨不全癥,從小就被稱為“瓷娃娃”,我的骨頭比普通人的脆很多,受到任何輕微的磕碰就會骨折。我必須安安分分地活著。因為我的病,爸媽習慣了把我當“皇帝”供著。我很想做點兒什么,但看著爸媽擔心的眼神,又覺得我少動或者不動,就是幫他們最大的忙了。
我可以去客廳吃飯,但不能喝涼水,因為那會刺激脾胃,促使我打嗝——我的身體受不了這樣輕微的震動。去衛生間洗澡,爸爸將我放在一張小凳子上,拿起淋浴器,緩慢地揉搓我的身體。就連我上廁所也得大人看著,因為骨骼發育不全,體形過于瘦小,我坐在馬桶上隨時可能掉進去。
這些就是我從小被要求做到的“正常”。
我8歲前從沒進過自家的廚房。每次被爸媽抱到飯桌前,我只需要張開嘴,就能填飽肚子。
直到我看了一部叫《查理和巧克力工廠》的電影。電影里的小男孩住在全世界最大的巧克力工廠旁邊,那里有嘩啦啦的“巧克力瀑布”,“瀑布”下是茂密的“口香糖草地”,一切都像被施了魔法。我忍不住想,平日里我吃的這些飯菜是怎么來的?幾步之外的那扇門后,也有魔法嗎?
一次趁爸媽不在家,我決定偷偷去廚房看看。當時我還沒有輪椅,父母去上班時會把我放在一張小凳子上。那天,凳子變成我的腿,我雙手抓住凳子邊緣,腳尖輕輕蹭地,嘗試讓身體小幅度前后扭動。原地打轉了一會兒,凳腳開始在地板上摩擦,發出第一聲尖銳的“刺啦——”。
我卻覺得悅耳。這是我第一次靠自己的力量向前“走”。這幾步路走得很艱難,我很快沒勁了,但渾身虛脫的感覺像在說:我活了這么多年,為的就是這一刻。
推開廚房門的瞬間,眼前的場景和電影里、夢里的完全不一樣。我的父母不是魔術師,廚房里也沒有魔法,所有東西都不是憑空出現的,它們真實存在著。
幾次意外骨折后,爸爸覺得我坐在凳子上也很危險,只能平躺,把彎曲的小腿放在枕頭上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受傷。
我連唯一的小板凳也保不住了。這回我沒有妥協,長久以來積壓在心底的煩悶一下子涌上來,人生第一次,我對爸爸發火。8年了,我沒有一天用這兩條腿走過路,甚至連站都沒站過,坐著時,至少我能感受到它們是存在的;而躺在那兒,我只能不斷地被提醒:你的腿已經廢了。
一番激烈爭吵過后,爸爸最終同意我坐凳子,但得等他下班到家后才可以。
我能活動的范圍本就不大,被限制使用板凳后,一天有近12個小時我只能躺在沙發上,對著天花板。我的世界就和我看到的一樣,一片空白。
“這個孩子活不過13歲。”給我看病的老教授說。13歲是人體二次發育的關鍵節點,骨骼會迎來新一輪生長,但對于成骨不全癥患者來說,那可能就是生命的終點。
我的身體每骨折一次,爸媽就越相信老教授的判斷。所以爸媽曾經對我最大的期望僅是:安分地活到13歲。
距離13歲還剩3個月時,我為自己寫了一封遺書。
白紙上,一行字寫得像螞蟻在爬,我怎么也寫不下去了。回想這12年多,我疼過、害怕過、憤怒過,但停下筆的那一刻,我被極深的無奈與不甘包裹了。沒有比“等死”更壞的結果了,我在心里告訴自己:為什么不再爭取一下?
我決定邁出第一步——找一家醫院,給我的腿做手術。如果能站起來,我靠自己就可以去很多地方。
在網上搜索了上百條相關信息后,我發現,天津有一家可以治療成骨不全癥的醫院。
說服爸媽帶我去治療是最艱難的一步,讓他們拋掉十幾年的恐懼和成見并不簡單。他們見多了這種醫院的小廣告,第一反應就是我在找事、瞎折騰。
然而我沒有放棄,白天大人不在家,我就挪著凳子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反復練習。幾天下來,我已經能很熟練地用凳子“走路”了。第四天晚上,我終于搶在爸媽要進臥室前,用凳子在門口把他們“攔”了下來。
地板被凳子蹭得“嘎吱”響,像在代替我發出抗議,我昂著頭與他們對峙:“不管那家醫院是真是假,咱們都應該去了解一下,如果真的治不了,那我就認了。”最終,爸媽同意了我的請求。
坐在醫院配備的輪椅上,爸爸推著我。醫生看了我雙腿的X光片,建議我做一個髓內釘固定手術,先把骨頭在彎折處截斷,再在骨腔內植入一根金屬物,串聯起兩截骨頭。
此時,距離我滿13歲只剩兩個月,骨骼很快將進入新一輪生長期,時間耽擱越久,骨質越差,手術風險就越大。
“確定要做嗎?”醫生又問。
我重重地點了點頭,就算會死我也要做。
那成為改變我一生的決定。
50天后,2厘米厚的石膏從我腿上被剝下來。爸爸拿來助行器,我扶著它,嘗試第一次站起來。
我握著助行器的手開始蓄力,試圖先讓屁股從椅子上抬起來。我像一把彎弓,身體的重量順著手臂往下傳——突然,膝蓋發出一絲很輕的“咯吱”聲。
我被嚇了一跳,立馬停下。頻繁的骨折讓我對身體發出的聲音很敏感。等了幾秒,我才敢讓雙腳完全踏在地面上,又用了點兒力踩穩。直到腳掌發熱,變得酸麻,好像有一股電流穿過腿間,我才覺得自己的雙腿13年來第一次被“激活”。
我咧開嘴,笑容從眼角溢出。從此,我徹底從那個幾十平方米的小屋子里走了出來。
我沒有死在我的13歲。
我想把自己的經歷講出來,好讓下一個病友不至于死在他的13歲。
我從老家來到北京,加入了國內最大的“瓷娃娃”公益組織,負責醫療救助項目,卻沒想到“垮”在了第一步。一次培訓時,我半夜不小心從床上摔下來,造成左大腿90°錯位骨折。
但噩夢是從救護車把我送到醫院開始的。我忍著疼痛陳述病情、進行拍片檢查,一個小時后,醫生卻告訴我:“我們不能為你做手術。”
同事幾乎幫我咨詢了北京各大排得上號的醫院,每一家的態度都是拒絕。
當晚,我又被救護車送回住的地方。
爸媽從老家趕來,把我帶去專治成骨不全癥的醫院,耽擱了好幾天我才做了手術。
在那幾天漫長的等待里,我被巨大的無助感包圍。這是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識到罕見病患者都面臨著什么。但遇到這種困境,恰恰是因為我們身上的病罕見:人數少、需求少,呼救也很難被聽見。
該怎么做才能讓我們被看到、被聽到呢?
我回想起自己在等待手術期間,曾在醫院做過的一件“瘋狂的小事”。
當時,我和3個同齡病友住在一間病房。我發現,自己是唯一一個之前沒用過輪椅的,直到來醫院后才用上。原因是我的父母覺得坐輪椅就代表“殘疾”,所以他們替我選擇了小板凳。
看著同齡的病友坐在輪椅上可以原地拐彎,可以翹起輪子過減速帶,行動很靈活,我在心里暗暗地想,輪椅只是工具,只要你想,它也可以是一輛酷炫的跑車。
于是我和病友組建了一支“輪椅車隊”,在醫院狹窄的走廊上,駕駛4輛輪椅“巡游”了3天。
第一天,不少人來圍觀,有人直接上來問我們,是不是走丟了。這一次,我大方地亮出身份。
第二天,好多人已經知道我們是一群成骨不全癥患者,紛紛向我們投來同情的目光。我們沒停下,繼續駕駛著輪椅“巡游”。人群中有人豎起大拇指。
第三天,一些陪護的家屬開始主動為我們讓出一條路,像在為我們加油。那是我從沒見過的景象,我能感覺到大家在和我們互動,給我們鼓勵,做我們的支撐。
我想起我在書里看到的一句話:“當你下定決心去完成一件事時,整個世界都會幫助你。”
組建“車隊”的經歷給了我啟發,我有了答案,得先讓病友們過上“正常”的生活,盡量降低疾病帶來的影響,我們才有可能向外界爭取更多,譬如醫療救助。
那就從解決最基本的穿衣需求開始。
我仔細觀察過,身高1.2米左右的病友,穿童裝也不完全適合,他們長期坐輪椅,手臂被過度使用,要比一般人的粗;雙腿則相反,因為幾乎不用,發育不良,細得像竹竿。這就需要上下身搭配不同尺碼的服裝。
在仔細瀏覽了300多家網店后,我選出了40家品質不錯、尺碼選擇較多的店,還標記好了每家店的衣服風格,整理成文檔。
一個病友先開口:“夏天出門,身上容易長痱子,衣服穿一會兒就濕了。”
“我每次打開衣柜都不知道穿什么,只會買白T恤和牛仔褲,不敢嘗試其他款式,怎么辦?”另一個病友問。
新的提問不斷涌來,這是第一次,我和病友們聚在一起交流穿衣問題。
在改變病友生活的過程中,我13歲之前的很多遺憾也在一點點得到彌補。
我的第一個救助對象是一個小女孩,她才3歲,骨折已經超過30次。
經過多次手術,女孩在6歲那年已經可以獨立行走,很快就要到入學年齡,女孩的媽媽卻猶豫了:孩子到了新環境會不會出意外?身邊的同學、老師會怎么看她?他們會不會直接拒絕一個四肢隨時可能骨折的“異類”?
我愣了愣,第一次不知道該怎么回答。
我沒有上過一天學。從7歲起,家里那個面積20平方米的客廳就是我的學校,爸媽分別做我的語文、數學老師。
看著這對母女,我總覺得幫助她們,也是讓自己重新活一次。我在網上搜來《殘疾人教育條例》,整理成文檔,用不同顏色重點標注了第二章“義務教育”的內容,讓女孩的媽媽打印出來,帶著這沓文件去跟校長溝通。
為了幫助小姑娘適應新環境,我還安排了物理治療師遠程給她做康復訓練,盡可能降低活動風險。
在教育局的協調下,小姑娘成功走進校園。在那兒,她將看見不一樣的世界,我很確定。
借著這些救助活動,我和病友得到了一些關注,人生中第一次有了上臺演出的機會。直到很久以后,我仍會想起那個發著光的畫面——舞臺上,輪椅、拐杖甚至身體,都是我們的樂器。我們用力拍打、敲擊著一切能代替我們發聲的東西。
最后,我們要邀請陌生人一起跳一支舞。我緩緩滑動輪椅,停在一個女孩的面前,伸出手,向她發出邀請。
女孩很靦腆,笑著擺了擺手:“我不會跳舞。”
“沒事。”我也笑了,“可以跟著音樂節奏來。”
女孩想了想,把手交給我,我們一起登上舞臺。